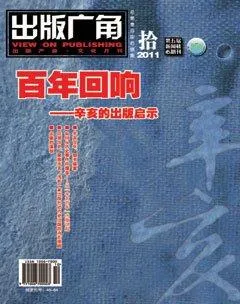必要的溫故
2011-12-29 00:00:00半夏
出版廣角 2011年10期

半夏
專欄與書評寫作人。在《南方周末》《經(jīng)濟觀察報》《南方都市報》《文匯讀書周報》《中華讀書報》《新京報》《法制晚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今晚報》《晶報》和《書屋》《散文》《文史知識》《隨筆》《南方人物周刊》《美文》《博覽群書》《看世界》等報刊及《讀庫》發(fā)表作品。作品入選各種年度散文選集。著有《西皮二黃》(北岳文藝出版社)、《蟲兒們》(中國工人出版社)、《城市感官》(海峽文藝出版社)、《中藥鋪子》(南方日報出版社、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果子市》(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半夏讀〈史記〉》(花城出版社)、《神仙一把抓》(花城出版社)、《我的花鳥蟲魚》(花城出版社)等散文隨筆集。(215095star@sohu.com)
有朋友曾經(jīng)問,如果可能,會選擇生活在哪個年代。這種類似好萊塢式穿越的提問,當(dāng)然具有鮮明的游戲色彩,但也絕非僅僅游戲那般簡單。
辛亥革命已經(jīng)百年。正如美國人說的,每一場革命都令人驚奇。不論從哪個角度說,1911年的那場革命,都無疑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大事件。從歷史角度而言,這個大事件最重大的意義,便是結(jié)束了盤桓中國兩千年的帝制,皇帝被真正拉下了馬,建立了共和。
而自辛亥肇始的民國,作為一個年代,即便將所謂政治揮之而去,留給后人的,實在也是一個世象紛繁,人物輩出的時代,且不談大勛章把來當(dāng)扇墜兒的章瘋子太炎先生,以及一口純正洋文足以駁倒洋教授腦后卻拖著一條小辮子的辜鴻銘,或者懷揣十塊鷹洋從巴格達來到上海撈生活居然在靜安寺東建起了奢靡的愛儷園的猶太巨富哈同,單就底層草根普羅大眾最為津津樂道的才子佳人橋段而言,也不乏蔡鍔與小鳳仙,梅蘭芳與孟小冬,徐志摩與林徽因,胡蘭成與張愛玲,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傳奇。
百年在歷史的流逝中,也許正如文藝描述的那樣,只是短暫的一瞬,但歷史老人的一眨眼,并不影響它成為中國人心中一個不可以忽略的年代。誠然,在當(dāng)下大眾的記憶之中,它似乎的確已經(jīng)多有淡出。連那個時代百姓感觸最深的革命之外觀變化——剪辮和放足,作為今天的后人,印象也多有含混。我們當(dāng)然可以抱怨追趕前途的奔跑中,連路邊的風(fēng)景都無暇顧及,更何況存在于歷史講述中的舊時代。然而我們無疑也應(yīng)該檢討,將路邊風(fēng)景以及其他的什么都一概棄置的奔跑,意義究竟何在。歷史,除了大眾耳熟能詳?shù)膼蹏髁x教育,也還有其他的深長意義,或者說,歷史之于后人,之于今天,乃至之于奔跑,都具有令后人之所以成為后人,今天之所以成為今天,奔跑之所以成為奔跑的特殊意義。
所以,很有必要借助這個走到一百的紀念,對辛亥,對民國,做一個溫故,像張鳴老師說的那樣,“能想起點什么,想出點什么”(《辛亥:搖晃的中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年1月,17頁),不要辜負這一個百年,這實在比哈雷彗星和地球的交集,更其具有生活的實在意義。
當(dāng)然,這個溫故,鑒于新近出版物資料上的豐富和內(nèi)容上的可讀性升級,在閱讀和了解的享受系數(shù)方面,提供了相對舒展的平臺。于是,這個溫故,不僅可以令人體味由君主專制的權(quán)威統(tǒng)治走向民主共和的諸多細節(jié),更可以領(lǐng)略各類人物各色事件的別樣景致,起碼可以讓這個搭車百年的歷史常識的“惡補”乃至掃盲,在過程上饒有興味。
譬如,作為這次革命的領(lǐng)導(dǎo)和發(fā)起者,歷史教科書上寫明,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lǐng)袖孫中山。這在政治判斷上無疑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具體到辛亥,乃至之前的一系列武裝起義,就不僅僅是作出判斷那樣的簡單。
由于革命黨人并沒有自己的軍事武裝,所以,這一系列的起義,其實只能利用甲午戰(zhàn)爭之后各地不斷興起或恢復(fù)的秘密結(jié)社也即會黨,還有就是清政府在1895年之后建立的新軍。在利用會黨等民間力量時,革命黨能夠做的,其實就是利用在海外通過華僑華人募集來的錢購買武器彈藥,然后將這些交給那些民間力量,同時也要給他們一些錢作為補償或軍餉,這是同盟會成立后組織的重大武裝起義使用最多的一種手段。
正如馬勇先生在《1911年中國大革命》(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5月)中寫到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lǐng)袖與會黨的合作,其實很像后來的“代理人戰(zhàn)爭”,即同盟會負責(zé)籌措資金,提供武器裝備,提供軍事顧問方面的支援,而會黨提供基本的人力,于是這些在名義上由同盟會、革命黨發(fā)動的武裝起義就這樣發(fā)生了。由此,起義的結(jié)果在起義籌備時期就大體注定。革命黨是要制造影響,會黨是為了金錢,為了維持它那規(guī)模龐大且日趨龐大的眾弟兄最起碼的物質(zhì)生活。至于革命黨方面也當(dāng)然很清楚,能夠籌到多少錢,就能夠做到多少事,起義的結(jié)果,一般來說,革命黨領(lǐng)袖特別是孫中山心中都有數(shù)。這些革命領(lǐng)袖之所以能夠在每次起義失敗后順利逃脫,其實是他們早都有了失敗的預(yù)案。(136頁)
當(dāng)然,作為同盟會一個組成部分的光復(fù)會,做派略有不同,“光復(fù)會策動的武裝起義雖然也是從聯(lián)絡(luò)會黨,利用會黨的力量入手,但光復(fù)會所組織的起義,一般說來總有光復(fù)會的領(lǐng)袖沖在前頭,充當(dāng)中堅或先鋒,所以要說震撼力的話,光復(fù)會的幾次暴動,其影響似乎要遠大于孫中山、黃興等人組織的起義”(同上)。這就無怪乎,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后被剖腹剜心的徐錫麟,暴露后不肯走掉就義于紹興軒亭口的鑒湖女俠秋瑾,給人更其剛烈豪氣,更其英氣逼人的感覺——這段鄉(xiāng)賢的壯烈故事,被魯迅寫進《吶喊》中的《藥》,并成為后來義務(wù)教育課本中的篇目,只是不知如今是否由于“時過境遷”的緣故,已經(jīng)或者準備剔除了。
毋庸置疑,發(fā)生于辛亥年的廣州起義中,率領(lǐng)敢死隊員猛攻總督府,與水師提督親兵大隊激戰(zhàn)時斷掉一根指頭,最后只身改裝逃至香港的黃興,一樣留給人深刻印象。而英勇不屈,屢敗屢戰(zhàn),一次又一次地在兩廣發(fā)動武裝起義,直至將“一個人的革命”演化成全民族的覺醒,孫中山的膽氣和信念,亦無人能及。
具體到辛亥的武昌首義,盡管是湖北革命黨原本有計劃的武裝暴動,其中也有孫武、居正這樣的領(lǐng)導(dǎo)人預(yù)謀,甚至確定了行動成功后軍務(wù)部、參謀部、內(nèi)務(wù)部、外交部、理財部、調(diào)查部、交通部等各部部長副部長的大致人選,但討論到新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卻是沒有誰覺得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來領(lǐng)導(dǎo)大家完成這次行動。于是只好派人前往上海邀請黃興以及宋教仁、譚人鳳來武昌主持。實際上,直到起義發(fā)生后的第四天10月14日,同盟會領(lǐng)導(dǎo)人譚人鳳和居正才從上海抵達武昌,而作為革命黨人中最懂軍事的領(lǐng)導(dǎo)人黃興,其時則遠在香港,直到10月28日,他方才攜太太以及宋教仁、陳果夫等抵達武昌。而在起義之前,上海方面一直沒有消息,而計劃卻發(fā)生了變化。參謀長孫武等人在俄租界起義總指揮機關(guān)配置炸彈,一個進來圍觀的老弟,手里拿的紙煙掉出了火星,落入裝滿炸藥配料的面盤,登時引發(fā)大火,驚動了租界巡捕,搜走革命黨人的旗幟、印信、文件,還守株待兔地抓捕了一些前來辦事的革命黨人。
計劃敗露,被抓捕的革命黨人和查抄到的文件移交官府,革命黨人只有及早起事,但軍事總指揮下達的炮聲為號,由于命令沒有及時送達南湖炮隊而并未響起,而那位引發(fā)大火的小老弟熬不住嚴刑拷打,供出了起義計劃,官府派出的軍警趕到起義指揮所,總指揮蔣翊武機敏逃脫,但潛伏在新軍各標營中的革命黨人,卻沒有了既定領(lǐng)袖。工程營一個排長的驚問,引發(fā)了他和士兵的搏斗,槍聲響起,革命士兵與前來彈壓的管帶發(fā)生正面沖突,起義在無法估計的形態(tài)中爆發(fā),革命黨人正目班長熊秉坤集合隊伍,打響了首義第一槍,其他各部中的革命黨人迅即響應(yīng),各路義軍在楚望臺軍械庫建立大本營,推舉的臨時總指揮吳兆麟,軍階不過是個隊官,也就是連長。
這些下層的軍官和士兵,雖然可以率兵攻下武昌,卻無法撐起起義之后的政治臺面,而必須推舉一個具有全國威望和影響的人物出面主持。于是,大家公舉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統(tǒng)領(lǐng)也即旅長黎元洪為湖北軍政府都督,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為湖北民政總長。盡管“逼請”而來的黎都督,一開初只是個泥菩薩一般不肯開口的黎菩薩,但這個軍政府的影響是披靡的,其他各省,群起相應(yīng),原咨議局議長譚延闿于長沙,新軍標統(tǒng)閻錫山于太原,新軍協(xié)統(tǒng)蔡鍔于昆明,同盟會員陳其美于上海,同盟會員胡漢民在廣州,紛紛就任都督,如你所知,這些人后來大多成為影響民國乃至中國的著名人物。
從上述細節(jié)不難看出,武昌的首義,帶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其間固然有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lǐng)袖積年的堅持和流血犧牲,但立憲黨人關(guān)鍵時刻的反水,也是辛亥革命終于成為全國性質(zhì)大革命的助推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北革命黨人當(dāng)初謀劃起義時就已經(jīng)屬意黎元洪,是有一定政治遠見的。而立憲黨人之所以會挺身參與辛亥的革命,自然與清政府的立憲程序密切相關(guān)。譬如,就在辛亥年5月宣布的第一屆內(nèi)閣中,13人里皇族竟然占了7人,漢族出身的只有4人,因此被稱為皇族內(nèi)閣。如此缺乏誠意的“十三太保”名單,坐實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多年的指責(zé),證明滿洲貴族統(tǒng)治集團果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權(quán)力,絕不會讓漢族人掌握政府的主導(dǎo),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于是,原本處于賽跑狀態(tài)的立憲和革命,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正陷入困境的革命,頓時傾斜了天平,立判高下。立憲黨人原本通過立憲分享權(quán)力的意愿遭到粉碎,徹底失望的他們就勢選擇另外的方式嘗試權(quán)力的分享就成為一個不壞的路徑。歷史的偶然,其實都是一系列因素促成的,蝴蝶的效應(yīng)堆積到一定的臨界,就會凝聚成必然。
至于說到革命黨的領(lǐng)袖孫中山,武昌首義乃至各省紛紛響應(yīng)時,正在美國,得知消息后即刻爭取歐美各國支持革命,切斷清政府的外援,在美英法等國進行外交活動,但并未取得預(yù)期的成果。直到辛亥年12月的下旬,他方才回國,隨即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并于次年的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一個月后的2月12日,宣統(tǒng)帝溥儀宣布退位,君主專制制度結(jié)束,共和成為國家的制度。
上述故實的縷述,對于以往教科書上判斷性的陳述,當(dāng)然是有血有肉的解讀,而作為革命的領(lǐng)導(dǎo)者,孫中山之于武昌的革命,其實與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發(fā)動的起義,譬如南昌起義和秋收暴動,革命領(lǐng)袖周恩來毛澤東均親臨現(xiàn)場坐鎮(zhèn)指揮,并非相同的概念。
實際上,中山先生作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意義自然不能僅僅從武昌首義的是否現(xiàn)場來理解。其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上建立的功勛,是不可磨滅的;其在政治上為后繼者留下的遺產(chǎn),也是彌足珍貴的。
不過,這樣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今天的人對他的了解,或許真的只是教科書上留下的一個簡單判斷,而于具體,則未必了了。譬如,孫中山這個名字的究竟。
發(fā)生于武昌首義整整15年前的1896年10月11日的“Kidnapped in London”,字面意思該叫做倫敦蒙難或曰倫敦綁架事件后,作為當(dāng)事人的孫中山,在自己開列的生平里,姓氏則是“仆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因此,“孫文”或者“孫逸仙”,才是他那時更多被提到的稱謂。這也是中山先生的英文名字寫作Sun Yat Sen的緣故——這當(dāng)然是威妥瑪式“孫逸仙”的拼法——“逸仙”則是孫氏的老師區(qū)鳳墀所起。孫氏在蒙難獲釋兩個月后所撰寫的作為文本的“Kidnapped in London”,署名即為Sun Yat Sen,盡管嚴格地說,那該是他和乃師康德黎的合著。這是孫氏最早的一本英文著作,出版后,迅即轟動歐美政界,引發(fā)西方諸列強對中國社會變革的路徑關(guān)注,孫逸仙的海外聲名也由此奠定。需要格外指出的是,此書的中文譯本,雖然在英文原著問世15年之后,也即辛亥革命勝利后的民國元年1912年出版,但上海商務(wù)以及民智書局、三民書局的譯本,盡管至今流行了百年,卻是文言意譯的刪節(jié)本,并且其中多有與英文原著頗有出入的“誤讀”。令人欣慰的是,完備意義上的白話譯本,已于2011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給了百年之后的讀書人一個從容展讀的全豹。這算是不算題外的題外話。
至于“中山”的稱謂,則來自其于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的化名中山樵。中山自然是日本姓,明治天皇的生母便叫做中山慶子。按照日本的習(xí)慣,他當(dāng)然會被稱為中山先生。其后再將他的孫姓加在前面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而“孫中山”本人,當(dāng)然不會用“孫中山”這個名字的。這就不難理解,那位武昌首義前造炸彈的孫武,要將自家的名字由孫葆仁改為孫武,取法便是要和“孫文”對稱,否則怎好拉大旗說是乃弟呢。
說到炸彈,卻是那時革命黨最常用并且的確令清廷和清軍聞風(fēng)喪膽的利器,廣州起義時敢死隊員邊沖邊扔的是炸彈,銀錠橋邊汪精衛(wèi)們刺殺攝政王埋下的同樣是炸彈。當(dāng)然,那時的汪兆銘,是抱定和攝政王同歸于盡的革命黨,獄中寫的供詞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所做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還流出監(jiān)獄,被人一時傳頌。而居然沒有被判死刑的他,出獄時據(jù)說路人爭睹風(fēng)采,道路為之阻塞,頗似今天偶像出街的場面。
于中山先生名諱之外,類似的簡單“了解”,大約還有他經(jīng)常被提到的總理稱謂。今天人對這個稱謂的內(nèi)涵定位,大約只限于國家首腦。其實,孫先生果然不止一次擔(dān)任過總理,但卻只是同盟會和國民黨的總理。當(dāng)然,你可以說那個“總理”內(nèi)中隱含著對未來政府的構(gòu)想,譬如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初,就接受孫中山的建議,創(chuàng)設(shè)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這無疑顯示同盟會的革命目標,就是推翻清政府,奪取政權(quán),創(chuàng)建新的國家。
需要說明的是,那時的“總理”一詞,并非僅僅具有政府首腦的意義。譬如引發(fā)保路運動的川漢鐵路公司就設(shè)有總理,而大清國在設(shè)置內(nèi)閣總理大臣也即首相之前,也有一個總理衙門,但那卻是辦理洋務(wù)和外交事務(wù)的機構(gòu),全稱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wù)衙門,又稱總署、譯署,40年后改為外務(wù)部。不過,從后人的角度看,那時的清廷,國家政治中大約最要緊的,就是外交事務(wù)了。就此似乎也可以略顯吊詭地勾勒出彼總理與此總理之間的某種關(guān)聯(lián)。
誠然,關(guān)于孫先生的稱謂,還有基本不為大眾簡單“了解”的,譬如所謂“四大寇”。這卻不是《水滸》里面被宋官家當(dāng)作心頭禍患寫在屏風(fēng)上的四股賊寇,甚至不是老佛爺們對革命黨的蔑稱,而是革命友人當(dāng)年對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的戲稱。
不用說,除了孫中山,余下幾人,并不被當(dāng)下大眾所知道,甚至聲名顯赫如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吳佩孚,等等,更多的僅僅是作為符號意義的負面形象,留在大眾的印象中。這當(dāng)然是一種失之幼稚的歷史觀,歷史從來不是紙片一樣單薄的集成,不過也的確需要用心才可能讀懂。也許有人會質(zhì)問為何要讀懂并且還是用心去讀懂歷史,對此,真的是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