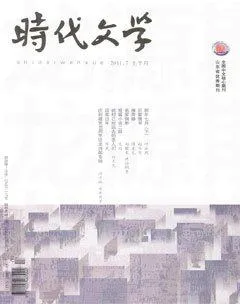進得此門的人有福了
多年之前,我還在念中學,有一天,在學校的圖書館里讀到了一部小說,因為圖書館的藏書實在不多,這本書已經(jīng)被翻閱得殘破不堪,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它的作者姓甚名誰,但是,一經(jīng)讀過,從此記得——書里寫的,是一起尋常的鄉(xiāng)村案件,但卻毫無疑問地包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經(jīng)由這起案件,人心的軟弱與貪婪、一個蒼老的家園在面對不斷更新的世界時手足無措的惶恐,還有強大的外部世界施加給村野鄉(xiāng)民的那些令人難堪的沉默。它們,都被作者清晰而果決地傳達了出來,更重要的是,它們并未被刻意篡改,我們依然能清晰地看見質樸的炊煙和河流,聽見嬰兒的哭泣和隱藏在田野深處的一聲號啕。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這部小說是中國最好的鄉(xiāng)村小說。
還要等上一些年,等我上了大學,這才知道,我當年看過的那本書,叫做《威風凜凜》,他的作者,名叫劉醒龍。人世自有機緣,機緣自會流轉,誰能想到,有一天,我又會和這個叫劉醒龍的人成為同事和相隔不遠的鄰居呢?經(jīng)歷了十年的寫作,我已經(jīng)習慣于將世上的作家分為兩種:一種人依靠揭示和發(fā)現(xiàn);一種人依靠于傾訴和追憶。在回答一些人的提問時,我曾廣為散播我的如此之念,好吧,我還是承認了吧,這仍然和這個叫劉醒龍的人有關,仍然和那本《威風凜凜》有關,假如我沒記錯,在那本書的封面勒口上,他曾寫過這樣的話:“我認為,世界上的作家有兩種:一種是用思想和智慧,一種是用靈魂和血肉,我希望成為后者。”
倏忽之間,我和他成為同事已經(jīng)六個年頭,這大好的六年,卻恰恰是他因為寫作《圣天門口》而深居簡出的六年,我偶爾能在樓下的餐館和散步的路上遇見他,也就多少見證了他六年里的悲欣交集。在許多時候,寫作是一件殘酷的事情,孤立無援,惟有一己之力,《圣天門口》行將完成之時,他有好幾次對我說起自己的大腦供血不足,有許多次,坐在電腦面前,竟然忘記了自己是誰,自己又在干什么,他感到悲傷,但是,幾乎是下意識地,他覺得自己正在擁有巨大的幸福。毫無疑問,我能夠理解他,當一個人將熱愛視為自己的命運,他往往會變得無所畏懼,就如陳獨秀所說:“什么是革命?所謂革命,就是閉上眼睛往火坑里縱身一躍。”
“進得此門的人有福了”——無論是寫作還是生活,這樣的人也理應獲得歡樂和奇跡。這個叫劉醒龍的人,他身上一直有我所羨慕的充沛的底氣,無論是身體里的信念,還是夢境里的土圩與田野,都是他可以依靠的東西,他是少數(shù)有信念有依靠的人,而對于更多的作家來說,他們的信念和依靠又在哪里呢?毫無疑問,寫作賜予他安寧和淡泊,但是同樣會帶給他緊張和對峙,這種對峙既發(fā)生在他與寫作之間,也發(fā)生在他與身外世界之間,這沒有辦法,既然將這些不安寧視為一場生涯的前提,那么,它們就會和那個叫做信念的東西一起作用于寫作,并且來指導自己的生活,上天造化,心性鑄成,他唯有順從它們的旨意。
因此,我可以負責地下一個論斷,他并不是一個我們見慣了的聰明人,從很多地方說來,他仍然是一個正在不斷生長的人,那些熱情與執(zhí)拗、感動與慷慨,都還鮮明地停留在他身上。有一回,我們在餐館里吃飯,為了一個字的正確讀音爭論起來,飯吃完之后,我才剛剛到家,他的電話就來了,原來,他是手拿字典,要和我繼續(xù)討論這個字,必須承認,一想到他的認真樣子,我當時的確是有些忍俊不禁了。而另外一些時候,我也數(shù)次見識過他的慷慨之氣,譬如在一個不少要人參加的會議上,他突然殺出,要求給新近調來的同事林白分房子,語聲激昂,許多人都痛心地看到,他將會議主題越帶越遠,最后的結果,是真的有人答應要給林白分房子了。
六年里,劉醒龍沒有變成那種“我就是唯一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他也從來就不是,稍加留心就可以注意到:從他的《大別山之謎》系列開始,再經(jīng)過聞名遐邇的《鳳凰琴》、《痛失》等等,直至今日的《圣天門口》,那么多的欣樂與痛失,他根本不愿意匆忙給它們定下一個判斷,甚至不熱衷于給它們定下一個標準,如果它們是寫作的血肉,他其實是把自己當作了血肉中的一塊,跟隨他們一起輾轉浮沉,長歌當哭,大樹還小,他惟有繼續(xù)這危險與無望之旅,才有獲救的可能。為什么說這是一趟危險與無望之旅?因為他總是在發(fā)現(xiàn)而且展示這些樸素但是致命的問題:知青是否只代表著過去歲月的美好情懷,如果是,它難道不可疑嗎;即使在天門口一隅,革命與仇殺、愛情與茍且,等等等等,究竟哪一時刻里的哪一樁事情,才是真正作為最真實的人性而存在于世?很不幸,他還是探究者,就像他是發(fā)明了武器的人,卻還要作為武器的一種被投擲于戰(zhàn)場,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是許多優(yōu)秀作家共同的宿命而甘愿的悲劇,我們知道托爾斯泰死于對“幸與不幸”的追問之中,我們也知道凡高在陽光與向日葵所迸發(fā)的金色之光中瀕于瘋狂,但是對不起,我們愛莫能助,對于這個名叫劉醒龍的人身懷之悲痛與呼告,我們同樣愛莫能助,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清楚:悲痛的人有福了,這幾乎是一個真正作家的美德與福分。
這么多年,在一些人的筆下,劉醒龍及其作品,一時被認定于此,一時又被認定于彼,其實,大多數(shù)人未能說清楚的一個話題是:和那些效顰者不一樣,劉醒龍不是一個機械地熱衷于充當時代書記員的人,那些在眼前、甚至在當代產生的道理,他并不喜歡用來關照他要描述的現(xiàn)實,是啊,與其說他描述現(xiàn)實,莫如說他是要描述暗藏在現(xiàn)實之下的幽秘而銳利的神經(jīng)。從根本上說,支撐他的寫作的,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藝術氣質和現(xiàn)代性,正是在如此質地之上,城市也好,鄉(xiāng)村也罷,他認真地諦聽過眾生的內心,成為了少數(shù)真正明白在新的時代中國人的內心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的作家之一,才產生了劉醒龍式的簡樸道德和沉郁情懷。
詩人沃爾科特有云:“不要問你的寫作抵達了哪里,而要問你的生活抵達了哪里。”對于劉醒龍來說,他的生活和寫作恰巧平行,“進得此門的人有福了”——他行走在接送可愛的女兒上課下課的路上,與此同時,他也行走在自己的傷口與夢想之上,已經(jīng)開始,必將持續(xù),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我不再費心追問自己的出處和來歷,像他一樣對自己的依靠知根知底,那么,我也是有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