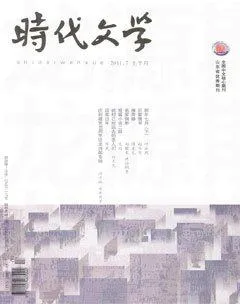劉醒龍印象
湖北作家劉醒龍似乎無論春夏秋冬一直留著短短的小平頭,給人一種精明能干的印象,初次見面是上海文學召開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研討會上。那時他的小說《分享艱難》幾乎成了整個研討會的關鍵詞。在一起吃飯聊天的時候,盡管他也坦言“分享艱難”不是他的原小說名字,而是周介人給他改的,功勞還是應該記在周介人身上。但是劉醒龍這個作家就此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之列。一位前國家領導人曾多次要求各級干部都要看根據(jù)劉醒龍的小說《鳳凰琴》改編的電影《鳳凰琴》,并要求一定要解決好鄉(xiāng)村民辦教師問題。后來上海電影制片廠也的確請他來寫過主旋律劇本,然而似乎又沒有搞成,不知怎么回事?那幾年,他一下子完成了四五個長篇小說,其中上海文藝出版社還給他的《彌天》召開了研討會。因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多了,當然談話的內(nèi)容主要還是小說創(chuàng)作,從他的話語里偶然會流露出自己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上有所顧忌。他似乎更愿意人家說他是個現(xiàn)實主義作家。
在我的眼中醒龍是個很有個性但又不是那種過分張揚的人,有一個小細節(jié)特別能看出他的為人處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壇時興現(xiàn)代派小說,他在早期執(zhí)著書寫的一組系列小說,原本自己命題為“大別山之迷”,寫得也頗有現(xiàn)代派風格,然而,幾乎所有發(fā)表這些小說的雜志編輯,都以為是劉醒龍的筆誤,問也不問就將題目改成了“大別山之謎”,于是此“謎”決非那“迷”,少了現(xiàn)代派的許多意味,雜志出來之后劉醒龍傻了,但畢竟木已成舟,劉醒龍只能默認而已。以至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劉醒龍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步實際上和現(xiàn)代派文學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
劉醒龍的小說不僅在國內(nèi)有影響,在海外也很有影響,美國的一位女作家翻譯了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說集,把他看作是當代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代表作家,前幾年還特意來中國,并到劉醒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過的湖北英山,實地考察大別山一帶的風土人情。為此醒龍還特意邀請了我一起參加,見到了劉醒龍的父母及家人。可能是因為劉醒龍的父親也是縣里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他家的小院挺漂亮。種著的石榴樹高高地懸掛著果實,還有伺弄得十分整齊的花草。醒龍在老家當過工人。英年早逝的作家姜天民在縣文化館工作時,是他的兄長和朋友。姜天民因小說獲全國獎而被調(diào)走后,醒龍就被調(diào)到文化館搞創(chuàng)作,就連所住的宿舍,也是姜天民先前住過的。以后,他也被上調(diào)到了黃岡和武漢。大別山一帶的風土人情在我看來到也沒有多少人杰地靈的環(huán)境,相反和其它山區(qū)一樣,憑借那樣的人文氣息,劉醒龍的平步青云顯然要有著超常的毅力和信心。劉醒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任何事,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也包括打撲克,打麻將,總有那么一股不服氣和不服輸?shù)膭蓬^,甚至是不求輸贏,只要一時的酣暢。
他新出的長篇小說《圣天門口》一百萬字,囊括了當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歷史文化的厚度和復雜人性的深度,前后花費了六年時間。在我看來其動力也是出于那么一股不服氣和不服輸?shù)膭蓬^,因為當時在《彌天》的研討會上,有評論家發(fā)言認為,當代中國鄉(xiāng)土文學到《白鹿原》已是不可超越的,誰再寫也沒有太大意義。所以我想劉醒龍的那口氣一直憋著,直到《圣天門口》寫完才放松了。
凡見過劉醒龍“風華正茂”的模樣,很難料到劉醒龍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尤其是他講話的語速快捷有力更顯得精神抖擻。惟獨他的語速放得舒緩甜美之時,那一定是在和家里的小女兒說話。我曾經(jīng)建議他再寫就寫一本專門給女兒讀的書,不要像《圣天門口》那么長,那么厚重。醒龍后來還真的這樣寫了,這本關于寫給天下所有做女兒的人看的書正在定稿,很快就要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