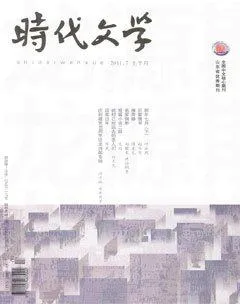現實關懷與歷史敘事
我們注意到,在與周新民的談話中,劉醒龍曾經把自己的小說創作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早期階段的作品,比如《黑蝴蝶,黑蝴蝶……》、《大別山之謎》,是盡情揮灑想象力的時期,完全靠想象力支撐著”;“第二個階段以《威風凜凜》為代表,直到后來的《大樹還小》,這一時期,現實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也給現實主義的寫作增添了新的魅力”;“第三個階段是從《致雪弗萊》開始的,到現在的《圣天門口》。這個階段很奇怪,它糅合了我在第一、第二個時期寫作的長處而摒棄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⑴在我看來,劉醒龍此處所謂“糅合”,其實明顯意味著作家一種思考與寫作能力的增長——即從僅止于對于現實表象層面的描摹與表現到具備某種能夠穿透現實的卓越思想能力的蛻變。正如我在以前的一篇關于劉醒龍的文章中所作出的論斷:“對任一優秀的作家而言,僅有對現實世界充分的關注與表現是遠遠不夠的,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于作家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關注并進入現實世界的。無數的文學事實證明,舉凡一個優秀的作家,在其觀照表現現實世界的過程中,其實都是擁有一種相對成熟成形的或可稱之為世界觀的精神哲學的。此處所謂精神哲學并非某種哲學理念,當然也并不是在要求作家應該成為哲學家,而是強調作家某種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具備。”⑵從劉醒龍的寫作歷程來看,這種思想藝術蛻變的發生是理所當然的,可以說是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寫作實踐過程中所逐漸完成的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變化。按照不同的時段區分來理解分析劉醒龍的全部小說創作,固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思維方式,從作品的取材方向來進行切割,那么,自然也就不難發現,實際上,劉醒龍迄今為止的所有創作,都或是對于現實生活困境的關注,或是對于某種歷史情景的探究。換言之,所謂劉醒龍的現實關懷與歷史敘事,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作是對于劉醒龍全部小說創作的一種整體把握。本文之主旨,就是要從現實關懷與歷史敘事兩個層面切入,嘗試著對于劉醒龍的小說創作有所發現。當然,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雖然在其相對漫長的寫作過程中,關注的對象或有變化,但一個有趣的現象卻是,劉醒龍的思想盡管一次次地抵達讓人驚訝的高度,但其創作思想的基本坐標卻自始至終沒有改變過。那就是,從創作之初一直到長篇巨制《圣天門口》在新世紀的問世,劉醒龍一直清醒而堅定地遵循著自己一種不迎合、不媚俗的寫作理念,保持著自己對更為闊大的現實與歷史世界的關注與表現。
一、“沒有浮華、虛偽和欺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西方文藝思想的強勢進入與各種文學樣式興盛,促使許多作家的文學觀念發生著重大的轉變,文壇遂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景。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卻是,在文學多元化的同時,曾經作為主流存在的現實主義卻日漸式微。我們的文學似乎確實在逐步地疏離于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之外,日漸遠離了人民大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方方、池莉、劉恒、劉震云等一批所謂“新寫實”作家的出現,終于讓文壇“舒了一口氣”。這批現實主義作家,開始把他們的關注視野轉換到了平庸的世俗生活之上,特別注重“小人物”的日常瑣碎生活,努力還原生活,以充分展示這些普通人的生存狀況。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市場經濟的發展,促使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日益趨向于“邊緣化”。這樣的一種現實處境,迫使他們開始對自身的價值觀和文學觀產生了最初的懷疑。創作主體心態的這種變化,便使得這個時代的現實主義作品呈現出了與八十年代頗為不同的思想藝術內涵。洪子誠認為:“在90年代文化意識和文學內容中,80年代那種進化論式的樂觀情緒受到很大的削弱,而猶豫困惑、批判和反省、頹廢等基調分別得到凸現。”⑶實際的情形也的確如此,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使舊的格局被打破,九十年代新的格局正在努力地被重新構建。各個階層的人們,在參與的過程中逐漸走向了成熟,主體參與的意識和使命感愈來愈強烈。而且,“中國十多年的漸進式改革的實效已經大大緩解了中國知識分子因文化滯差而產生的焦慮感和亢奮心理。這使人們能更冷靜和理性地認識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和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性。”⑷一批作家敏感地察覺到了現實生活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以一種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其中。這批作家把創作轉向更加豐富而復雜的現實人生,傾力關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況,給文壇帶來了新的氣象。批評家張新穎,把這種文學現象稱之為“現實主義沖擊波”。而劉醒龍,則很顯然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給我們呈現出了社會轉型期間的艱難世事和尖銳矛盾。《鳳凰琴》中的民辦教師們,在一個被繁華所遺忘的角落里艱難地生存著,《路上有雪》中夾在矛盾中心的村支書被逼無奈只能選擇集體大逃亡,《分享艱難》中為了河西鎮的發展、為了顧全大局一次又一次放棄道德準則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孔太平……就這樣,劉醒龍用他的筆搖醒我們沉睡的思想,直面殘酷真實的社會現實。這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一種現實主義回歸,而是站在傳統現實主義的基礎上以新的、更高的起點對新時代的冷靜審視。在我們充分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一種轉型過程的艱難。在傳統的價值觀念已被瓦解,但新的體制和價值觀卻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就必須承受這種動蕩帶給他們的沉重的精神負擔。
對當下社會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劉醒龍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有意識地選擇的一個創作方向。雖然說現實主義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寫現實題材,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現實主義品格,關鍵要看作品中的人文內涵和批判精神,要看它是否抓住了實存世界中根本的精神沖突和價值追求,是否能夠表達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精神發展的軌跡和形態,但反過來說,能夠以短兵相接的方式直面復雜的現實生活,也的確應該被看作是對于現實主義精神的一種充分體現。從劉醒龍發表于九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如《鳳凰琴》、《分享艱難》、《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威風凜凜》、《痛失》、《彌天》中,都不難感覺到它們有著一個顯著的共同特點,即正面描繪回應中國社會轉型期間一些無法回避的重大時代命題。作家在勾勒社會利益格局下不同生命的真正形態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一種深沉的思索和憂慮。導致這一點的關鍵原因在于,他總是能夠在市場經濟浪潮中,敏感地感受現實世界的巨變給生命帶來的痛楚。因此,對于那些在繁華的時代表象下艱難生存著的人們的諦視與表現,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了劉醒龍小說所表現的重心所在。諸如《秋風醉了》、《清流醉了》、《菩提醉了》、《去老地方》、《分享艱難》、《路上有雪》、《痛失》、《村支書》、《挑擔茶葉上北京》等作品所集中描寫表現的,就是一大批中國基層官員在面對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種種問題時的各種情態。其中,《村支書》中所塑造的方支書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方支書可以說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官,劉醒龍對這一人物的刻畫塑造,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處在國家、社會和個人重重矛盾中的中國基層官員的形象。為了得到五千元的修水閘資金,方支書騎著自行車前后來來回回地跑了十八趟,但卻依然沒有拿到手。待到最后大壩遇險時,方支書只好自己抱著棉被跳下去堵住了裂縫。而《分享艱難》所描繪的,卻是一個與方支書截然不同的另類官員形象。鄉鎮干部孔太平總是面臨著種種艱難的選擇,當洪塔山被告嫖妓,孔太平不僅沒有對其嚴懲,反而花錢找關系將檢舉材料銷毀;洪塔山強奸了他心愛的表妹,但他卻向派出所所長求情放出了洪塔山。從這些自覺“保護”其實劣跡斑斑的洪塔山的行為來看,孔太平實在并不能被歸入“好官”的行列之中,但是他的種種行為的出發點,卻是為了保全河西鎮的利益。除此之外,《寂寞唱歌》、《生命是勞動與仁慈》等一類型的作品,所展示的也都是身處在國家、社會和個人重重矛盾之中的中國基層官員的生存境況。通過他們的種種掙扎與無奈,劉醒龍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總是被遮蔽著的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可以說,劉醒龍總是這樣,總是以一種直面的姿態來揭示轉型期中國社會獨特而復雜的狀況,把人性最真實的一面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讓諸如孔太平此類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強力侵占我們早已被溫情式的閱讀所培養出的日漸疲軟的精神世界。
李揚曾經指出,以劉醒龍等人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強烈關注當下,把目光和筆觸直接切入“大中型企業”與“基層農村”兩大陣地,某種意義上填補了文壇的空白或斷層,但這種填補僅限于“主旋律下的現實”,他們所宣揚的良知是“有限度的良知”。在我看來,這種說法未免有失偏頗,在劉醒龍的作品中,我們并沒有看到來自作者主觀意愿的妥協,而他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恰恰是隱藏在殘酷逼仄的現實空間中,我們不能單單從一個頗具復雜性的人物——孔太平的形象上就斷定其“‘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雙重缺失。文學并不只是呈現美與善,也會呈現丑與惡,殊途同歸,但它的藝術旨歸卻終歸是善。從劉醒龍在九十年代寫作的中篇小說《鳳凰琴》,以及在新世紀重寫的長篇小說《天行者》這兩部作品中,我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作者在敏銳關注現實的同時,心中滿懷著的是愛與善。
發表于1990年代初期《鳳凰琴》是一部中篇小說,描寫了一群山區的民辦教師。張英才高中畢業當年差三分未能考上大學,于是就又補習了一年,沒想到補習一年的結果居然是不進反退,離分數線又多差了一分,變成了四分,這樣當然就更沒指望上大學了。沒指望上大學,張英才只好在舅舅萬站長的幫助下,來到全鄉最貧窮的界嶺小學,當了一名民辦教師。然而,界嶺這樣一個只有三個,不,準確地說應該是四個民辦教師,因為除了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之外,還有同樣身為民辦教師但卻早已癱瘓在床的余校長的妻子明愛芬,只有二、三十個學生,辦學條件極其惡劣的小學,卻只能讓心高氣盛的張英才感到萬分失落。然而,隨著對余校長等人的慢慢了解,張英才逐漸改變最初的看法。他把自己來到界嶺小學之后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篇名為《大山·小學·國旗》的文章,并把文章投寄給了省報,結果不僅文章見報,而且上級部門還格外開恩,專門給了界嶺小學一個民辦教師轉正的指標。那么,這唯一的指標應該屬于誰呢?余校長他們這幾位民辦教師的高尚人格,在這樣的試金石面前,也就自然是熠熠生輝了。先是張英才主動讓出了這個指標,然后,又是大家一致同意把指標留給早已對轉正望眼欲穿的明愛芬。多年的愿望終于滿足,癱瘓多年的明愛芬溘然長逝,這唯一的指標最后還是落到了年輕的張英才身上。小說借助于張英才的獨特視角,通過轉正指標事件,將余校長他們這些民辦教師發展教育事業的自我犧牲精神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恐怕才是劉醒龍多年前創作中篇小說《鳳凰琴》真正的意圖所在。“只要生活有一份寄托于充實,生活之外的任何‘指標’都不再那么誘人和重要了。”這一曲“鳳凰琴”曾感動過無數人。
到了2009年,劉醒龍在《鳳凰琴》的基礎之上,推出了同樣是以民辦教師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說《天行者》。文本還是緊緊圍繞“轉正”的問題,但張英才這個角色的離開使得小說的敘事重心從《雪笛》開始轉向了對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這幾位民辦教師人生歷程更為充分的藝術展示。它充分展示了那些民辦教師苦難的命運遭際、堅韌的生存姿態、崇高的精神境界。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明愛芬等這樣一些幾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偏僻貧瘠的界嶺小學的民辦教師們,雖然生存條件十分艱難,雖然只有極其微薄的工資收入,但為了能夠讓這些身處窮鄉僻壤的孩子們能夠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卻硬是以自己十分單薄的身架,承擔起了教育孩子健康成長的重大使命。雖然這些民辦教師并沒有什么豪言壯語,雖然他們之間也還是避免不了會發生一些蠅營狗茍你蹬我踹的矛盾沖突,但是,在以一種兢兢業業的姿態對待神圣的教育事業這一點上,他們卻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余校長說:“當民辦教師的,什么本錢都沒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這么多孩子,不讀書怎么行呢?拖個十年八載,未必經濟情況還不會好起來嗎?到那時候再享福吧!”在一個消費主義觀念早就占據了上風的市場經濟時代,劉醒龍的作品依然能夠感動許多人,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學的、甚至是精神上的奇跡了。《天行者》的封底介紹道:“中國農村的民辦教師,一度有四百萬人之多。他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里,擔負著為義務教育階段的一億幾千萬農村中小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將現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不可否認,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真正承擔“傳道授業解惑”職責,真正把現代文明傳播到窮鄉僻壤的廣大農村世界的,正是如同余校長這樣普通的民辦教師。六七十年代的讀者可能還都擁有這樣的記憶。在某種意義上,“不缺良心和感情”正是支撐著這類小說的堅韌脊梁,或者說,是作者所期望的能夠讓整個時代發展的精神支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又何嘗不是作家的“良知與責任”?
縱觀劉醒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品,無論是思想精神內涵,還是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都呈現著某種日益上升的趨勢。我們發現,雖然他所涉及的題材都扎根于現實主義,但是,他思想的縱深卻在逐漸增強——對時代命題的深刻思考,對深沉而勃發的生命力的執著表現。一句話,劉醒龍用他的小說拷問著時代,希望能夠喚醒社會的良知,尋找到對癥的良藥,從而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在《鳳凰琴》和《天行者》中,劉醒龍雖然一直在圍繞民辦教師“轉正”的問題大做文章,但兩部小說卻又有著明顯的不同。《鳳凰琴》只寫了一次轉正事件,這次轉正事件的描寫擁有著十足的正劇意味,而且,這種描寫很顯然是為了凸顯余校長他們的崇高精神服務的。但到了長篇小說《天行者》中,卻先后出現過三次關于轉正事件的敘述。這三次對轉正的描寫疊加在一起,與《鳳凰琴》中一次描寫的意味絕不相同。如果說,“鳳凰琴”中第一次關于張英才轉正的描寫,還具有著崇高的正劇意味,那么,到了“雪笛”中關于藍飛轉正的描寫,就已經帶有了明顯的鬧劇意味,而到了“天行者”中關于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他們最后的轉正描寫,所表現出的干脆就是帶有突出荒誕色彩的悲劇意味了。這種突出的悲劇意味,就表現在余校長他們總是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樣地期盼著能夠有一個轉正的機會,然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這種轉正的機會終于降臨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卻居然由于自身的貧窮而轉不起正了。多少年來一直孜孜以求地謀取著轉正的機會,希望能夠通過轉正的方式改變自己貧窮的生存方式。然而,令余校長他們根本無法預料的一點卻是,等到轉正機會來臨的時候,同時來臨的居然是要求民辦教師們必須首先繳納一萬元左右的所謂工齡購買費。如果不能夠按時交納這一筆對民辦教師來說特別昂貴的費用,那么,所謂的轉正自然也就成了幻滅的肥皂泡。轉正本身,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貧窮狀態。但要想轉正的前提,卻又必須繳納自己根本拿不出來的昂貴費用。這樣的一種描寫,讀起來頗有一些“第22條軍規”的意味。余校長他們這樣充滿悖反意味的人生遭際,只能被看作是徹頭徹尾的一出人生悲劇。這樣看來,雖然同樣是余校長、鄧有米、孫四海幾位在《鳳凰琴》中出現過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卻已經是一種曲折深沉的命運感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從這兩部小說的對比中可以體會到劉醒龍對世事的思考愈發深入,他所呈現的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強烈的悲憫情懷,還有一種對社會、體制等批判的鋒芒噴薄而出。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的是,文學的表現形式并不只一種,對“90年代末出現的以‘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出現作為中國文學的世紀結局是悲劇性”的這樣的定論恐怕還是有待斟酌的。⑸
雷達在《思潮與問題:20世紀末小說觀察》 中談到當代文壇的鄉土小說創作時說道:“……當代鄉土小說,在人們習焉不察的遲鈍中,在某種沉落的氛圍中,正在艱難地向深處探索。它在藝術視角、任務類型、切入矛盾的深度和揭示時代性精神困惑的程度上,呈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由靜態的觀照、揭示轉向自傲動態中的剖析、挖掘;城鄉二元視角的自覺運用;拋開正負的兩極化偏執,更客觀地對農民靈魂進行雙重性思考;具有復雜心態、集納諸多矛盾的農村干部形象的增多;農村現代人的形象及其哲理指向,等等。當然,最根本的還在保持現實主義精神,致力于民族靈魂的重鑄。”⑹我們不得不說,從夢幻般的“大別山系列”走出來的劉醒龍,扎根于他血液之中的鄉土情懷讓他找到了一條與他的靈魂真正相契合的文學之路。“我現在越來越偏向普通人,我覺得他們更可靠。”⑺在諸如孔太平、張英才、夏雪、吳豐等普通人的身上,劉醒龍找到了文學的價值所在。“一個小人物、尤其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類人,尤其是一類處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與生存狀態,從來就是一條貫穿我(劉醒龍)的全部小說的命定線索。”⑻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來自城市的蠱惑讓農村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沖擊和毀滅,農村人受到城市的吸引,紛紛離開農村去城市里討生活,鄉土意識漸漸地被城市文明覆蓋消亡,造成了鄉土文明的極大缺失。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很多作家選擇用文學敘述的鄉土想象來彌補現實的缺失,以想象中詩意的鄉土文明來抵抗現代文明。劉醒龍也選擇了這個文化母題來進行創作,但他卻選擇坦然面對鄉村文明所遭遇的每一次傷痛,每一道傷疤。他曾坦言不喜歡“知青情結”,甚至有些反感。《大樹還小》中,母親與歐陽,姐姐和白狗子、秦四爹與文蘭之間的感情讓我們感覺到的只是一種深刻的悲涼。他描寫鄉村,是為了孜孜不倦地從鄉土文明中尋找一種堅韌樸實、厚重無垢的精神,來抵抗被異化的城市文明。《生命是勞動與仁慈》這部小說表現得尤為明顯。操勞一輩子的陳老小,堅守勞動信念的陳東風與不再固守鄉土的段飛機、嫁給陳西風的方月之間不同的價值觀,象征著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之間的對峙。父輩們堅守的價值觀隨著鄉村一起凋敝了,而年輕一代的農民拋棄了看似“落后”的農村,拼命想擠進城市這個公共空間,然而城市文明卻并不接納他們。公然的欺辱、壓榨和歧視,使得城鄉之間形成了無法改變的二元對立體。當然,劉醒龍不是僅僅為了展示,他在清醒地面對這一切的同時,更多地指向了對傳統鄉土價值觀的回歸。所以陳東風最后回到了西河鎮,回到了讓他安心的家園。他的回歸,其實是對城市文明的一種無聲抵抗,是遵循了本心所做出的決定。與它有著相同文學意味的還有《白菜蘿卜》中重返鄉村的青年大河。如雷達所言:“應該看到,一些非審美化傾向正在嚴重困擾長篇創作——其實是整個文學的發展,卻并未引起我們足夠的注重。首先是,為了追求某些虛懸的目標,以文學性的大量流失為代價的現象。我發現,在不少被媒體叫好的長篇里,很難讀到雋永有味的細節,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同身受的濃郁氛圍,撲面而來的鮮活氣息……我們欠缺的仍然是思想的穿透性,但這種穿透不可能通過犧牲詩性來獲得。這種思想魄力并非西式觀念的中國式轉述,而應是扎根本土,飽蘊感性、靈魂和血肉,與中國當下的人文命題緊密結合的一種形象的力量。”⑼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從劉醒龍鄉土小說創作中所透射出的深邃光芒足以彌補這一缺憾。作家蘇童認為他的“血脈在鄉村這一側”,而“身體卻在城市的那一側”。劉醒龍用他與生俱來的鄉土情懷證明了這一點:“對于生命來說,勞動是物質的根本,仁慈是精神的根本。在此之上的生命才是有意義的。”在他的筆下,只有那“沒有浮華、虛偽和欺騙”的被遺落的鄉村和土地才能抵抗城市文明對人的侵蝕、變異。
劉醒龍在創作實踐中并沒有嚴格遵循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精神,而表現出一種突破和超越。從無距離的真實這一點來看,劉醒龍的現實主義創作與九十年代初所風行的新寫實小說并無不同,但他的視角已不再滿足于形而下的原生態呈現,不再是通過對一個小人物的日常瑣事來展示其生存境地和精神狀態,而是以更全面、更冷靜、也更求實的眼光來審視現實關系的復雜性,來關注某些尖銳的現實問題,甚至帶有更強烈的關注世事、著眼國計民生問題的色彩。他的作品不削平、淡化或回避社會關系和生活中出現的種種重大矛盾,把現實主義文學的領域拓展到一個新的層面和廣度。同時,劉醒龍的作品不再刻意地去追尋生活的意義,而更多的是去關注處于生存困境中的人們的生存方式與生存意識。劉醒龍遠離了所謂“消解激情”的寫作,他秉承自己獨有的創作理念,不遺余力地傾注了他的悲憫與良善之心,拋棄了以“零度情感”來反映現實的寫作模式。
以《分享艱難》這部小說為例,作者在談到這篇小說的創作動機時說道:“那時,從老家來的兩個青年干部正在上省委黨校,我經常去看他們,他們向我訴說了在基層的許多苦衷,其中包括為了擺脫貧困,不得不違反良心做了些事,不但別人罵他們,他們也罵自己無能,但現實又讓他們無法做出別的選擇。后來,我將這些捏在一起寫成《分享艱難》,當寫到孔太平為了公眾的利益,不得不放過強奸了自己表妹的洪塔山時,我的心有一種被人撕裂的感覺,最先讀到這部作品的編輯和評論家都說讀到這一節時他們不禁淚眼模糊。我也流過眼淚,擦干眼淚后,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如果自己面對這些又會怎么辦?我一遍遍地回答:誰敢這樣就宰了誰!可生活不是這樣選擇的,它默默地承受起這最讓人不能接受的艱難。生活又一次告訴我,僅靠情感是無法實現超越的,必須用自己的靈魂和血肉去作無情的祭奠。”⑽就這樣,作者在小說中把日益凸顯的金錢和道德、物質與精神,惡的手段與善的目的之間的矛盾,深化為一種社會、道德、政治性問題,而不僅僅是生活自身的呈現。作者立足于社會與時代的兩難課題,直面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會遇到的困境以及身在其中的中國人面對這些困境所必然會出現的種種精神狀態。何為“分享艱難”,在分享改革成果之前,必然先要分享的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正是因為有這樣理解和包容的胸懷,劉醒龍的作品才能讓讀者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生出一種無畏的勇氣。
二、為歷史正名
新世紀伊始,沉寂多年的劉醒龍便以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圣天門口》震驚文壇。這部時間跨度很大(從世紀初一直到六十年代)的長篇歷史小說,不管是從思想藝術內涵還是基本敘事模式來看,都充分證明著劉醒龍的確已經實現了某種堪以脫胎換骨稱之的艱難的思想藝術蛻變,進而使自己的小說創作步入了一種全新的最起碼臻于當代一流的思想藝術境界。
這種論斷并非夸大或粉飾,《圣天門口》的出版讓我們看到,劉醒龍在他多年的創作過程中已經具備了一個優秀作家所應該具備的超越現實表象直抵存在本質的深邃意識和眼光。“人的一切經驗都來自歷史,只有歷史才能給我們一雙看未來的明眸。我寫歷史目的就是為了更有效地認識現實。”⑾不可否認,一個優秀的作家只有能超越現實的拘囿,把視野拓展到更為深遠的本民族的全部歷史過程中,才可能對本民族所走過的獨特道路進行重新審視和深刻反思,才能夠最終升華出對當下社會現實的觀照更加通透的特殊能力。而史詩性的創作,則要求作家必須把目光投向更為宏大深邃的歷史空間,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以深沉而博大的胸懷理解歷史,才能使作品具備深厚的歷史內蘊和積極的現實意義。因此,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對作家來說就的確意味著一個極大的挑戰。而且,從歷史小說發展的過程來看,自1949年之后迄今已經六十多年時間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就先后出現過兩次影響巨大的歷史小說創作潮流:“十七年”期間的“革命歷史小說”與新時期的“新歷史小說”。當然,也還有諸多無法被納入這兩大創作潮流之中的散落于這兩大潮流之外的同樣不應該被忽略的其他歷史小說,比如“十七年”期間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李劼人的《大波》、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比如新時期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等。以上的這一系列事實就充分地說明,歷史小說的寫作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確實有過豐富異常的創作實踐過程。有了這樣的一種創作背景,批評家們對于《圣天門口》這部小說的出版,顯然只會帶著更為苛刻和挑剔的目光來進行審視。值得慶幸的是,當我們終于讀完這部長達百萬言的長篇歷史小說之后,終于不無驚喜地發現,劉醒龍在承繼傳統歷史敘事經驗的基礎上,確實找到了另一種更為獨特的敘述方式。
《圣天門口》是一部由諸多矛盾線索交錯混雜而成的結構相當復雜的長篇小說,在小說的前十二章亦即1949年之前的那個歷史階段,以傅朗西、杭九楓、阿彩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一派與以馬鷂子、王參議、馮旅長等為代表的國民黨一派之間的矛盾對立構成了小說的主要矛盾。而在小說的后三章,到1949年之后,執政后的共產黨內部的矛盾沖突以及執政者與廣大民眾之間的矛盾沖突取而代之,上升為小說的主要矛盾。除了以上兩個不同歷史階段各自不同的社會矛盾之外,小說中實際上還有另外兩種貫穿文本始終的矛盾線索存在。一條是天門口小鎮雪、杭兩大家族之間綿延長久的恩怨情仇以及彼此之間的消漲起落。而另一條更為潛隱然而也更為重要的卻是一種暴力文化與一種以仁慈、寬恕、博愛為根本內涵的或可稱之為基督文化之間的矛盾沖突。小說中的梅外婆、雪檸、董重里(轉變后的)等當然應被視作基督文化的突出代表,而在這個意義上看來,則無論是杭九楓還是馬鷂子,無論是傅朗西還是馮旅長,則都可被看作是暴力文化的體現與張揚者。以上我們只是從批評便利的角度出發,從《圣天門口》中梳理提取出了幾條主要矛盾線索,在文本的實際中,這些被我們所條分縷析出的矛盾線索,其實都是水乳交融般地互相交錯纏繞在一起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諸多交錯纏繞在一起的矛盾線索共同構成了現實生活本身的復雜性與日常性,我們所謂在“革命歷史小說”中被遮蔽了的歷史真實所指稱的,其實也正是現實生活的這種復雜性與日常性。應該注意到,在這個充分接近歷史真相的敘述過程中,作者的敘事立場其實站在了以梅外婆、雪檸她們為代表的帶有突出的仁慈、寬恕與博愛特征的基督文化這一邊。
在小說中,梅外婆、雪檸當然是歷史的當事人,她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了充滿殺戮與爭斗的歷史進程之中。但在另一個方面,我們卻又可以把她們看作是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種帶有突出超然意味的局外人。得出這一結論的關鍵原因在于,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演進過程中,梅外婆們始終沒有被某一狹隘的黨派立場或政治立場裹挾而去,她們總是能夠在超越種種復雜的利益紛爭之后堅持“用人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這正是梅外婆與雪檸終其一生都身體力行著的一種人生信條。正是依托于這樣的一種人生信條,小小年紀的雪檸才會如此地憎惡暴力:“天下的事有一萬萬種,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用暴力強行奪走他人的性命。再好的槍,只要不殺人,就是一文不值的廢鐵,一切為了殺人的手段,哪怕只要她拿出一根絲線,她也不會答應。這就是她的最大仇恨,也是她對仇恨的最大報復。”而慘遭日軍獸行蹂躪之后的梅外婆,也才會講出這樣一番令人格外震驚的話語來:“很多時候,寬容對別人的征服要遠遠大于懲罰,哪怕只有一點點的體現,也能改變大局,使我們越走越遠,越站越高。懲罰正好相反,只能使人的心眼一天天地變小,變成鼠目寸光。”這樣,在堅持著以一種寬容的非暴力的“人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的梅外婆們看來,一部20世紀的中國歷史其實正是一部黨派利益的紛爭史、殺戮史,是一部由種種殺戮與爭斗的暴力行為所必然導致的廣大民眾的受難史。也正因此,所以他們才忍辱負重拼盡全力地為消弭這種種紛爭與苦難做出自己全部的努力,這正如梅外婆所說:“一個人的能力救不了全部的人,那就救一部分人,再不行就救幾個人,實在救不了別人,那就救自己,人人都能救自己,不也是救了全部的人嗎?”
我們注意到,小說中曾經幾處借人物之口將“圣”字贈予到梅外婆與雪檸等雪家女人的身上,小說標題中的“圣”字很顯然也正來源于此。如果說小說的確借助于天門口這樣一個小鎮而濃縮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風云變幻的話,那么這個“圣”字則正意味著一種超然于黨派或政治立場之外的超越性視點的最終確立。前文曾經強調梅外婆們的以非暴力化為突出特征的所謂基督文化立場其實也正是劉醒龍的基本敘事立場所在,這樣,梅外婆們眼中作為一種黨派利益的紛爭史、殺戮史,作為一種廣大民眾的受難史而存在的20世紀中國歷史,實際上也正是劉醒龍意欲在《圣天門口》這部長篇歷史小說中所竭力還原表現出的歷史本相。如果我們承認出現在劉醒龍筆端的的確是一部黨派利益的紛爭史、殺戮史,是一部廣大民眾的受難史,那么同時也就必須承認以這樣一副面目呈現于讀者面前的20世紀中國歷史,的確與我們在“革命歷史小說”中所習見的由那樣一整套“階級斗爭、人民解放、偉大勝利、歷史必然、壯麗遠景”的歷史邏輯所支撐著的歷史狀貌有著大相徑庭的天壤之別。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劉醒龍所描畫勾勒出來的20世紀中國歷史圖景,與我們在既往的“革命歷史小說”中習見的歷史圖景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別,所以我們才斷言劉醒龍《圣天門口》的一大突出成就,正體現為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一種極為成功的消解與重構。更準確地說,劉醒龍通過自己的藝術努力所消解顛覆的,其實也只不過是在既往的“革命歷史小說”作品中業已完全固型化的,帶有鮮明意識形態特征的20世紀中國歷史的景觀而已。
可以說,劉醒龍在消解和重構歷史的同時,也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敘述話語。他曾說道:“在我用一百萬字寫了各種各樣的爭斗,卻沒有使用描寫那段歷史一貫使用的一個詞:敵人!一個民族間的內戰,不管是正義或者是非正義,都不應該再由后人來繼續互相稱呼為敵人。這種時候,寫作者的立場,應該是兒女們面對父母間糾紛時的立場。所謂家丑不可外揚,其實是讓人心里有一種恥辱感。在這種至關重要的細節上,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圣天門口》是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第一個吃螃蟹的。在小說中,我所寫的是人物,而不是階級;是對和諧社會和和平崛起的渴望,而不是歷史進程中暴力血腥和族群仇恨。”⑿這種對政治性、革命性的質疑與消解,之于劉醒龍重新建構歷史話語來說具有某種必然性,他在寫作之前就已經擺出這樣一個客觀的姿態——力圖回到歷史現場進行現實意義的描述。這樣,小說中人物的塑造自然也就帶有了某種特別的客觀性,他們不再讓讀者產生極端的憎恨或者熱愛,而是隨著歷史進程的不斷發展變化而成為了活生生的人。而歷史事件的再次演繹,也變得更為冷靜真實,從而使讀者獲得一種傳統歷史觀念消解式的閱讀。回溯20世紀的中國歷史,“革命”恐怕是最為重要的關鍵詞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歷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革命的歷史。因此,當劉醒龍意欲借助于《圣天門口》,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進行一種消解與重構的藝術性努力的時候,“革命”便成為他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如何理解、評價并敘述“革命”,實際上成為衡量《圣天門口》思想藝術成就如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圣天門口》思想藝術成就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正在于對于“革命”進行了相當深入透辟的質疑與反思。如果說“革命歷史小說”的確是在“講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講述革命在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之后,如何最終走向勝利”的過程。如果說“革命歷史小說”在某種意義上乃可以被理解為是對某種“革命”神話的創造過程的話,那么,劉醒龍《圣天門口》之值得注意處,則正在于對于這樣一種“革命”神話形成了強有力的消解與顛覆。如果說“革命歷史小說”所著力表現的是“革命”對于未來的人民解放與幸福的承諾,它所反復宣諭的一個絕對性真理便是,只有通過“革命”這樣一種方式,廣大民眾才有可能擺脫苦難,走向一種美好的幸福生活,那么到了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中,“革命”不僅沒有能夠成為廣大民眾的真正福祉,反而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殺戮與爭斗傾軋的代名詞,就小說所表現的實際情況來看,“革命”乃可以被視為20世紀歷史進程中廣大民眾苦難生活的重要成因之一。
在這一方面,小說結尾處關于傅朗西在文革中被批斗一節的描寫顯得格外意味深長。在樟樹凹,有一戶人家,家里的六個男人都先后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婆媳三代只剩下了四個寡婦。直到文革開始,她們方才醒悟到“她家的男人全都是受了傅朗西的騙”。于是,當傅朗西在文革中被押回天門口進行批斗的時候,這四個寡婦便上臺去控訴質問傅朗西。“你這個說話不算數的東西,你答應的幸福日子呢,你給我們帶來了嗎?”“為了保護你,我家男人都戰死了,你總說往后會有過不完的好日子,你要是沒瞎,就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就是我們的好日子,為了趕來斗爭你,我身上穿的褲子都是從別人家借的!”“老傅哇老傅,沒有你時,我家日子是很苦,可是,自從你來了,我們家的日子反而更苦。”也正是這些普通百姓樸素的真切追問,擊中了傅朗西的內心世界,促使他在離開人世之前對自己的一生行徑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對自己傾畢生心血從事著的“革命”產生了堪以幡然悔悟稱之的深刻認識:“這么多年,自己實在是錯誤地運用著理想,錯誤地編織著夢想,革命的確不是請客吃飯。紫玉離家之前說的那一番話真是太好了,革命可以是做文章,可以雅致,可以溫良恭儉讓,可以不用采取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傅朗西是《圣天門口》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終其一生都在致力于革命的事業,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革命家。然而,最后的傅朗西卻走向了自己終生事業的反面,完成了一種雖然痛苦但卻又必然的自我否定,可以說,在親身經歷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風云變幻,在親眼目睹并親身感受了帶有強烈的血腥和暴力意味的“革命”給廣袤的中國大地所造成的巨大災難之后,傅朗西最終徹底地否定了這種血腥暴力的“革命”,最終認可并皈依了梅外婆、雪檸她們那樣一種充滿了仁慈、寬恕與博愛的非暴力文化立場。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小說中所描寫的傅朗西最后的幡然悔悟,絕非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之舉,從劉醒龍的基本創作動機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整部《圣天門口》關于一部20世紀中國血腥暴力史的展示與敘述,其實都是一直在為小說終結時傅朗西的自我否定進行著鋪墊與準備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也就完全可以說,其實在傅朗西的自我否定背后,潛藏著的是劉醒龍自己同樣十分痛苦的對于“革命”所進行的質疑與反思過程。其實,這種質疑和反思不是突然發生的,在他90年代的創作中就已初見端倪。被人指責為丑化下鄉知識青年的《大樹還小》就是他對以往知青苦難、悲壯形象的一種消解和顛覆。他沒有參加到為那段歷史進行“立言”、“敘史”的隊伍中去,而是站在一個客觀自持的距離進行闡述,反思被話語中心遮蔽的歷史。另一部小說《彌天》則是對文革歷史的質疑和反思,比起回避、粉飾,他更愿意直面歷史的真相——人性的扭曲和毀滅,一次政治的荒誕事件的發生。文革其實是我們民族歷史進程中的一段悲劇,他的直面其實就是反思的起點。由此看來,到了《圣天門口》中,對革命歷史的反思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圣天門口》在全面地勾勒表現20世紀的中國歷史的同時,最終是要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作一種深入的挖掘與探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圣天門口》毫無疑問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首先,從文本的實際情形來看,劉醒龍的確從自己個人對歷史的理解角度出發,極有力地挖掘表現出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這就是說,在已經確立并認同了以梅外婆、雪檸她們為代表的一種以仁慈、寬恕、博愛為突出特征的非暴力文化立場的映照之下,出現在劉醒龍筆端的20世紀中國歷史,是一部黨派利益的紛爭史、殺戮史,是一部廣大民眾的受難史。對于呈示出如此面目的一部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作家劉醒龍的態度是批判、拒絕與否棄的。其次,是“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應該說,劉醒龍《圣天門口》的一大突出特征,便是時間跨度的巨大宏闊,主體故事時間從20世紀初一直延伸到了20世紀60年代,但更值得注意的卻是小說中對于漢族創世史詩《黑暗傳》的完整傳插。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黑暗傳》的適時而完整的傳插,更加明顯地拉長了《圣天門口》的時間維度。從空間跨度來看,雖然作家的筆力集中于天門口小鎮,借天門口小鎮而濃縮凝聚20世紀中國的歷史風云,小說的標題很顯然也正來源于此。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作家的筆墨其實還是經常游離于天門口小鎮之外,且不斷地延伸幅射至武漢、香港,甚至東京、巴黎這樣的地方的。如此看來,《圣天門口》中的空間跨度也就不可謂不宏闊了。此外,小說中人物的眾多與情節線索的紛繁復雜,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圣天門口》具有宏闊規模的一個突出表征所在。第三,是“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從本質上看,小說當然是一種虛構的文體,事實上我們所閱讀著的大多數小說都是純然的虛構作品。但是,從“史詩性”的角度來看,它就必然會要求有重大歷史事實的充分介入。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要求《圣天門口》,則《圣天門口》的“史詩性”同樣是當之無愧的。首先,在《圣天門口》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跨度內,我們所熟知的諸如土地革命、白色恐怖、肅反、中日戰爭、解放戰爭、國共的合作與破裂、土地改革乃至于大躍進、文革武斗這樣一些發生于20世紀中國的重要歷史事件,均在小說中得到了一種格外形象生動但卻又十分深入的藝術表現。而且,與那些凌空蹈虛的“新歷史小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小說中的傅朗西、杭九楓等人物都有著歷史上真實的人物原型。如此看來,說《圣天門口》中有著充分的“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便絕非妄言了。第四,則是“英雄形象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圣天門口》中當然有著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形象的創造,在這一方面首當其沖的便是杭九楓。更何況,作家劉醒龍對于這樣一位與朱老忠、周大勇、梁大牙們屬于同一英雄人物譜系的英雄形象的塑造,還顯得格外真實且別具一種人性的深度。然而,關鍵問題在于,我們不應該拘泥于的傳統英雄觀念而對英雄作出一種狹隘化的理解。從一種更為現代也更為寬泛的意義上看,如梅外婆、雪檸乃至于董重里、王參議這樣的人物形象,又何嘗不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更加本真的新型英雄形象呢?梅外婆與雪檸雖然自身飽受凌辱,但卻依然不改以“愛”的行跡拯救眾生與自我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董重里不惜擔當“叛徒”罪名而從革命隊伍中堅決出走;王參議在梅外婆的精神感召下日漸傾向于一種仁慈、博愛的情懷,并在抵御日軍的細菌戰時慘死。如此種種,在我看來,其實都可以被當作英雄行為加以理解看待的。如果我們承認,不僅僅杭九楓、傅朗西是英雄,梅外婆、雪檸、董重里、王參議他們同樣是英雄,而且還是更大的英雄,那么說《圣天門口》是一部沉淀交響著英雄主義基調的優秀長篇歷史小說也就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了。由以上論述可見,劉醒龍的《圣天門口》確實有著突出的“史詩性”藝術追求,而這,也充分說明在劉醒龍內心深處的確存在著一種強烈的重建“宏大敘事”的沖動與努力。
劉醒龍曾經明確強調:“對史詩的寫作歷來是每個作家的夢想……一部好的小說,理所當然是那個時代民間的心靈史。做到這一點,才是有靈魂的作家。我寫《圣天門口》,是要給后來者指一條通往歷史心靈的途徑。”⒀王又平認為,所謂的“史詩性”,“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最高級別的形容詞,稱道一部作品是史詩,也就是將這部作品置于最優秀的作品的行列。因此‘史詩風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作為一種文學理想一直為作家所企慕、所向往,形成了作家的‘史詩情結’。當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規模、豐富的歷史內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象、莊重崇高的風格等特點時,便可能被譽為‘史詩性’”。 ⒁與此同時,對于“宏大敘事”,王又平也發表了相當精辟的看法:“在利奧塔德看來,在現代社會,構成元話語或元敘事的,主要就是‘宏大敘事’。‘宏大敘事’又譯‘堂皇敘事’、‘偉大敘事’,這是由‘諸如精神辨證法、意義解釋學、理性或勞動主體解放、或財富創造的理論’等主題構成的敘事。”在王又平的理解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存在著不同的宏大敘事。現代西方曾以法、德兩國為代表分別形成了“解放型敘事”與“思辨性敘事”這樣兩種宏大敘事。而在當代中國,“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正史觀念中,也形成了一套宏大敘事,它們以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和正統性向人們承諾:階級斗爭、人民解放、偉大勝利、歷史必然、壯麗遠景等等都是絕對的真理,真實的歷史就是關于它們的敘述,反過來說,只有如此敘述歷史才能達到真實和真理……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述及敘述風格雖有變化,但從總體上說都本之于宏大敘事,它們也因此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眾多作品中居于‘正史’的地位”。⒂對于“史詩性”與“宏大敘事”,洪子誠的看法同樣值得注意,雖然他是將二者合二為一加以談論的。洪子誠認為:“史詩性是當代不少寫作長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評家用來評價一些長篇達到的思想藝術高度的重要標尺。這種創作追求,來源于當代小說作家那種充當‘社會歷史家’,再現社會事變的整體過程,把握‘時代精神’的欲望。中國現代小說的這種宏大敘事的藝術趨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這種藝術追求及具體的藝術經驗,則更多來自19世紀俄、法等國現實主義小說,和20世紀蘇聯表現革命運動和戰爭的長篇……‘史詩性’在當代的長篇小說中,主要表現為揭示‘歷史本質’的目標,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⒃可以發現,王又平與洪子誠對于“史詩性”內涵的理解幾乎達到了驚人一致的地步,他們的區別乃體現在對于“宏大敘事”的理解上。洪子誠基本上將“宏大敘事”等同于“史詩性”。而王又平則更多地援引利奧塔德,在一種元話語或元敘事的意義上歸結出了中國當代文學中一套“宏大敘事”的基本內涵與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王又平不僅只是對于“史詩性”與“宏大敘事”的基本內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而且他還更進一步談到了“史詩性”與“宏大敘事”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中逐漸式微的問題。“但是進入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的轉型,穩定和統一的文化語境出現了裂痕,僅僅根據元敘事或元話語來講述歷史再也不能使作者和讀者感到滿足,更何況由于正史總不免要掩蓋、隱藏、篩除或舍棄某些歷史材料(大到若干關涉到億萬人的重大歷史事件,小到歷史人物的個人動機和偶然的抉擇對歷史的影響),因此宏大敘事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開始受到懷疑”。⒄“但是在新時期,史詩或史詩性卻好像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在各種歷史敘述的沖擊下,史詩性已經不再是這個文學時期普遍的美學理想和美學標準,它已經成為‘古典’而從往昔的高位上跌落下來,失落了當年至尊的榮耀,也失去了對作家絕對的誘惑”。⒅從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演進過程來看,我們的確應該承認王又平的觀察與分析都是極其到位的。在一個王綱解鈕的解構主義時代,作家們的確已經不再具有以“史詩性”的追求構建“宏大敘事”的藝術雄心,他們的藝術興趣更多地集中在了對于歷史角落中的歷史碎片的尋繹與闡釋上。在這個意義上,則“新歷史小說”的應運而生,“新歷史小說”對于既往“革命歷史小說”的顛覆與消解,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我們在具體面對解讀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之前,首先需要面對的,就應該是橫亙于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毋庸置疑,劉醒龍這部歷六年之久而成的長篇巨制,當然應該被看作是劉醒龍小說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這樣一部重新恢復對于“史詩性”的藝術追求,并憑此而重建“宏大敘事”的長篇歷史小說,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站在了“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主義”的肩膀之上。但這并不意味著劉醒龍的寫作只是一種簡單的模擬和重復。的確,劉醒龍《圣天門口》的寫作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新歷史小說”,例如在一種新的歷史觀念方式的確立方面,在一種解構性寫作技法的運用方面,“新歷史小說”對于劉醒龍的寫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啟示與榜樣作用。我們的確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大量成功的“新歷史小說”作品的存在,還會不會有劉醒龍《圣天門口》在新世紀中國文壇的出現。但是,在承認“新歷史小說”對劉醒龍所產生的重要的滋養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充分地認識到二者之間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巨大差異的存在,極鮮明地凸顯出了劉醒龍《圣天門口》同樣重要的思想藝術價值。“新歷史小說”的一個根本特點在于它只“解構”,而不“建構”。如果說“新歷史小說”的根本缺陷之一正在于它只“解構”而不“建構”,那么,劉醒龍《圣天門口》的根本價值則正在于對于這一藝術缺陷的修正與彌補。具體來說,劉醒龍在他的這部長篇小說中一方面極有效地消解了“十七年”期間的“革命歷史小說”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固型化敘述,但在另一方面,他卻并沒有走向歷史的虛無主義,在消解歷史的同時,他也在積極地進行著一種艱難但卻十分重要的重構歷史的工作,或者說,他通過自己對于歷史的一種個性化的敘述過程,而最終成功確立了“自己終極的精神價值的問題”。“寫這部小說時,我懷有一種重建中國人的夢想的夢想。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覺得中國人有些夢想是要重建的,我們不應該繼續采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不能再崇尚以血還血以牙還牙。”⒆由此,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察覺到,劉醒龍在反思歷史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確定和肯定以梅外婆、雪檸、董重里等人物為代表的非暴力文化立場——即使這種確定和肯定是基于個人立場的一種道德重構。當劉醒龍成功地將在“革命歷史小說”中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矛盾置換為暴力與人性、人道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并以此來燭照20世紀中國的血腥暴力史的時候,我們便可以說,劉醒龍終于完成了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極為艱難的重構工作,他終于依憑于自己的藝術性努力在《圣天門口》中確立了“自己終極的精神價值”立場。從這個意義上看,就的確是“怎一個圣字了得”了。如果說小說中的天門口小鎮的確濃縮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風云變幻的話,那么正是依憑了這個“圣”字,劉醒龍在確立自身終極精神價值立場的同時也完成了對于“新歷史小說”的成功超越。同時,與“新歷史小說”觀念性的寫作特點相比,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中不僅有著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上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的藝術性表現,而且他筆下的一些人物,比如傅朗西、杭九楓等都是有人物原型的。既曰歷史小說,那么便應該有真實的歷史根據,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劉醒龍《圣天門口》與“新歷史小說”的根本差別所在。而這,也正是劉醒龍《圣天門口》對于“新歷史小說”實現藝術性超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事實上,也正是依憑著這種超越性,《圣天門口》才成為了當下中國小說界一部不容忽視的長篇歷史小說佳作。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劉醒龍的《圣天門口》是一部涵納融匯了“革命歷史小說”與“新歷史小說”的藝術優勢,然而同時卻又突出地體現著劉醒龍巨大創造性的歷史小說的集大成之作。
如果說對當下社會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劉醒龍創作的橫坐標,那么對歷史進程中人類普遍問題的透視就是其創作的縱坐標。從劉醒龍九十年代的新現實主義作品到新世紀《圣天門口》的出版,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恪守“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并且不斷地構建自己獨特的歷史意識和敘述模式——消解與重構。現實觀照與歷史意識是互相補璧的,對現實的觀照是一種橫向的時代的世界眼光,而歷史意識的產生則是一種縱向的歷史的眼光。一個優秀的作家只有站在現實與歷史的交匯點,才能具有一種宏觀的、整體的、博大的審美認識能力,使主體意識獲得一種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能力,進而擁有一種歷史的眼光和胸懷。因此,正是由于劉醒龍對既往的小說創作進行了不斷深入反思,在意識到自身所存在的思想藝術不足的前提之下,真正地突破了既往小說創作中那樣一種狹隘且不無簡單化嫌疑的現實主義寫作格局,“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將自己的藝術關注視野投射向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最終在《圣天門口》的創作過程中切實地實踐并確立了一種堪以博大深邃稱之的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不可否認的是,劉醒龍在自己幾十年的創作過程中,能夠帶給我們啟示的不只是一種經驗,一種視角,更多的是他對現實與歷史的吸納和重鑄,是他不斷尋求可靠的道德理想與精神支柱的理想,是他在反思中不斷重新構建新的人文精神的努力。
注釋:
⑴⑻⒆周新民、劉醒龍,《和諧:當代文學的精神再造——劉醒龍訪談錄》,《小說評論》,2007年第1期。
⑵王春林,《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消解與重構》,《小說評論》2005年第6期。
⑶⒃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333頁、9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版。
⑷蕭功秦,《走向新現實主義——轉型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變化》,《探索與爭鳴》,1995年第3期。
⑸李揚,《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23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年第一版。
⑹⑼雷達,《思潮與問題:20世紀末小說觀察》,75頁、6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⑺劉醒龍,《浪漫是希望的一種——答丁帆》,《小說評論》,1997年第3期。
⑽劉醒龍,《僅有熱愛是不夠的》,《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5期。
⑾⒀劉醒龍,《寫作史詩是我的夢想》,《新京報》,2005年7月10日。
⑿汪政、劉醒龍,《恢復現實主義的尊嚴——汪政、劉醒龍對話<圣天門口>》,《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8年6月第2期。
⒁⒂⒄⒅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版,380頁,329—330頁、330頁、3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