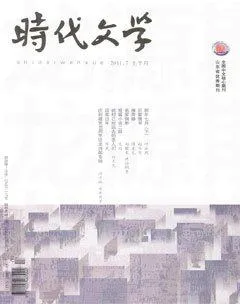彎刀
毛毛用小刀刮開桔樹皮,果然發現了樹干被蟲啃咬過的痕跡。
快瞧啊爸爸!毛毛興奮地叫起來。可是沒有人答應他。
毛毛抬頭一看,桔園里除了他自己,并沒有其他人。給桔樹治蟲的工具散亂地扔在草地上,爸爸不知道什么時候離開了。
毛毛跑到桔園中央的井臺上,踮起腳尖往桔園外望。只見爸爸兩手插在后腰上,站在桔園的籬笆旁跟人說話呢。爸爸面前站著一位又高又瘦的駝背老人,毛毛認出他是爸爸水泥廠看管倉庫的老廉,全廠的人都喊他老廉頭。老廉頭的雙手握在胸前,不停地揉搓著一頂藍布工作帽,正低著頭跟爸爸說著什么。他的背看上去似乎比以往更彎曲了一些。還有三位陌生的老人,站在距爸爸和老廉頭十來步遠的地方。和老廉頭相比,他們的個頭要矮小很多。此刻這三個老人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站著,像是互不相干的幾個人。他們都沒有說話,安靜地抽著卷得很粗大的旱煙。和老廉頭一樣,他們的身板都有些彎曲,雙肩微微下塌,看上去都十分溫順的樣子。
以前毛毛從來沒有見過老廉頭到家里來找爸爸,來找爸爸的往往都是副廠長、車間主任這樣的人,當然,偶爾也有采購員、供銷員。他們有時到家里來,跟爸爸商量生產、銷售和采購的事情。老廉頭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能跟爸爸說什么!老廉頭可以跟爸爸說的話,毛毛用腳趾頭都能想得到。每次毛毛跟著爸爸去水泥廠,走到倉庫那,老廉頭不管在做什么,他都會把手里的活兒放下來,站得端端正正地跟爸爸打招呼:“……廠長來了!”——回回都是這么句話。
老廉頭話不多,但他在水泥廠,在這周圍十里八鄉,都是一個十分出名的人,沒有人不認識老廉頭。早幾年,老廉頭的背還沒有這樣彎,他的力氣也還大得驚人,一個人能把一根碗口粗的椿樹連根拔起來。水泥廠的倉庫蓋得又高又大,倉庫里成包的水泥碼得像小山一樣,大卡車日夜不停地來拖,小山也很難變得再小一點,有時候即使它小下來,但用不了一個晚上它又會重新變大。老廉頭的兒子,曾是這倉庫的搬卸工,長得像是老廉頭的一個影子,力氣也同樣大得驚人,一百斤一包的水泥,他一次能搬三四包。幾年前一個夏天的中午,非常炎熱的一個中午,他爬到倉庫的水泥小山上,躺在一把吊扇下邊午休。后來,“嘀嘀嘀”的上工鈴聲一響,他忘了頭頂轉得呼呼作響的吊扇,“噌”一下從小山上坐起來,他的脖子當即被吊扇的葉片砍了個大口子。那時候老廉頭還不在倉庫工作,他在距水泥廠七八里地的小山村里種田。人們把他從熱烘烘的稻田里叫上來,他帶著兩腿的泥跑到水泥廠,看到他的被自己的血染紅的兒子時,老廉頭哼都沒有哼一聲,直愣愣像塊門板一樣“嘭”一聲倒了下去。等他再次站起來,人們發現他比原先竟然矮了許多——這些當然不是毛毛親眼所見。自從半年前毛毛跟著爸爸媽媽來到這里后,老廉頭的故事毛毛至少聽過八百遍。人們只要遠遠地見老廉頭走過,就會說:“喏,這就是老廉頭,這就是那個兒子被吊扇把脖子砍了的人!”廠里的工人,有時候下了班并不急著回家,他們會在倉庫前的小廣場上抽根煙,或是找老廉頭要杯水喝,他們一邊抽煙喝水,一邊聽那些外地來的卡車司機扯外面各處的奇聞逸事。作為回報,他們往往會把老廉頭兒子的事說給那些外鄉人聽。
“老廉頭,你說你兒子那脖子,只怕比牛脖子還粗些,怎么就叫吊扇葉子給弄了呢?”末了總有人不免要這樣問。
“命里的事嘛……”回回老廉頭都一臉平靜地答。
毛毛幾乎沒有見過老廉頭高興或是生氣的樣子,他從來沒有笑過,但是也好像沒有什么事情能讓他哭。只有一次例外,不過是在前兩天,鎮上那位在肩膀上紋著一只螃蟹的三哥,來水泥廠找爸爸要錢花。老廉頭等三哥走遠后,沖著他的背影啐了一口痰。
“要爛你到遠處去爛!”老廉頭帶著一絲怒氣道,“這樣的東西,沒有了才干凈……老天不長眼,竟讓這樣的東西活下來!”
現在毛毛看著老廉頭雙手揉搓著工作帽,低著頭小心翼翼地跟爸爸說著什么的樣子,不禁感到有些新鮮。
“也許是在告媽媽的狀呢。”毛毛想。
毛毛曾和媽媽一起陪著鎮上那個老得都快走不動了的神父去水泥廠給工人們送《圣經》——神父來到小鎮四十多年了,送出去的《圣經》可以堆成一座山——媽媽特地給老廉頭送去一本。當著媽媽的面,老廉頭恭恭敬敬接了過去,轉過身卻隨手墊在了暖水瓶底下。過了兩天,媽媽找了件爸爸的舊衣服拿給老廉頭,說話的空間,媽媽不動聲色地將那本《圣經》從暖水瓶底下抽出來,揩干凈放到了窗臺上。
老廉頭不喜歡別人動他的東西。
水泥廠倉庫的門廊下有一個小磅秤,很久以前它就被擺在了那兒,沒人能說得出它在倉庫有什么用場。老廉頭不管它有用沒用,每天都將它擦得很干凈。常常有工人有事沒事都要跳到那秤上去將自己稱上一稱。如果跳到稱上去的工人動靜大了一些,老廉頭就會很心疼地咒罵:“—— 你娘!卵事沒有,像個神父!”
毛毛覺得,頂頂不討老廉頭喜歡的人,除了三哥,就是神父。神父叫老廉頭“廉兄弟”,老廉頭卻從不答應他。
此時天近黃昏。
太陽從西邊的山嶺上照過來,毛毛眼前的一切都籠上了一層薄而柔軟的金紗。山腳下的小鎮看上去就像條灰色緞帶,顯得格外安詳。在小鎮西頭,水泥廠家屬區的對面,是神父的那座小小的尖頂教堂。此刻夕陽的余暉斜斜地照在小教堂尖尖的屋頂上,屋頂上高高矗立的十字架在教堂東邊的稻田里涂抹下厚重的陰影。毛毛站在井臺上,看到一個被拉長得走了樣的十字架將稻田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幾塊。桔園西邊的山嶺后就是水泥廠,平時它就像頭巨獸,躲在山后不停地噴著渾濁的熱氣。天氣好的時候,站在桔園里把頭一抬,就可以看見水泥廠上空飄來蕩去的灰白煙霧。現在呢,水泥廠躲在了夕陽后面,靜悄悄的,毛毛迎著光,什么也看不見。而近處那些袒露在陽光里的桔樹的葉子,像被傳說中神奇的金手指摸過,泛著亮而溫暖的光澤。在這光澤的下面,雜草、背光的樹葉和散發著香氣的果實卻潛入到樹下愈來愈深的黑暗里。看著眼前的一切,毛毛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那就是黑暗實際上并不是從天而降的,原來一切都來自泥土。黑暗就像霧氣一樣從腳下的土壤里鉆出來,它們順著草根、樹干一點點往上生長,在空中匯集,形成牢不可破的一個整體,然后步步為營,逼退陽光,最后抵達高遠的天空——黑夜就這樣降臨。這個發現使毛毛著急起來,如果黑暗長得再高一點,桔園里很快就什么也看不見了。他跳下井臺,急急忙忙奔回到那棵有蟲眼的桔樹下。
毛毛跪在柔軟而潮濕的地上,把一根細長的有著小小彎鉤的鐵絲輕輕伸進樹皮下的小洞里。
我在給你治病,你要忍著。毛毛對桔樹說。
掛滿果實的桔樹一動不動,仿佛聽懂了毛毛的話。毛毛學著爸爸的樣子用鐵絲在小洞里掏了掏,然后慢慢地往外抽動鐵絲,鐵絲帶著一些像面粉一樣細的木屑出來,木屑散發著好聞的香氣,飄飄灑灑地落到桔樹下的泥土里。毛毛屏住呼吸,把鐵絲抽出洞外,一只像粒白米飯一樣的蟲子在彎鉤上掙扎,它的頭和尾不停地一曲一伸,一副努力想要自己親吻自己的樣子,讓毛毛忍不住笑了。毛毛輕磕鐵絲,把蟲子裝入到一只玻璃瓶。
毛毛背著小包、抱著玻璃瓶子跟在爸爸身后來到小鎮街上。他回頭望了望桔園,老廉頭他們已經不見了,桔園變成了一片深黑色的厚重的云彩,懶懶地漂浮在山腰上。有一片亮亮的晚霞還停留在山頂,看上去像頂柔軟而溫暖的帽子。毛毛的鞋子上沾了一些桔園里潮濕的紅土,他停下來把腳伸到路邊的一叢蒿草上蹭了蹭,然后追上幾步跟在爸爸身后往家里趕。毛毛背上的小背包活潑地一下一下拍打著他的大腿。
這街是一條長街,從桔園下來一直往西走,會路過幾家雜貨鋪,兩家小酒館,一所小學校,街道中間是鄉政府和派出所,最西頭是水泥廠的家屬區。這是晚飯前的一段時光,從道路兩邊的房子里飄出來陣陣炒辣椒的嗆人的香氣。家家戶戶門前的梧桐樹灰撲撲的,有不少男人在樹下或蹲或站,個個都是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沿途不時有人跟爸爸打招呼,爸爸簡簡單單地回應一聲,腳步卻并不因此而慢下來。
毛毛跟在爸爸身后路過一家小酒館時,有個人從酒館里走出來招呼爸爸。毛毛認得他,是派出所的王所長。
王所長穿著件顏色暗污的藏青色T恤,一件警服松松垮垮地披在肩頭,渾身散發著刺鼻的酒氣。他一邊用牙簽剔著牙,一邊對爸爸說:“廠長,聽我們所里的小劉講,昨天你來報過案,是嗎?”
爸爸點點頭,道:“是的。”
王所長把嘴里的穢物吐到地上,笑了。
小酒館過去就是一家理發店,理發店門前的路燈下擺著兩張油漆斑駁的斯諾克球桌,有條桌腿不知何故短了一截,用幾塊青磚胡亂墊了起來。幾個頭發染得焦黃的十六七歲的少年坐在球桌上,有兩個少年手里還各握著一支被磕得長短不一的球桿。他們裸露在外的臂膀上,紋著和三哥肩膀上一樣的靛藍色螃蟹。以往這些少年總是給人十分無聊而又肆無忌憚的印象,他們圍坐在球桌上,旁若無人,高聲大語,不時還會吹出幾聲尖利的挑釁的口哨。今天他們默默地抽著煙,個個都有些不快地繃著臉,一副準備隨時跟人打一架的樣子。毛毛覺得這些少年很是神秘,時常很久都見不到他們,但是就在你快要忘掉他們的時候,冷不丁地他們又憑空冒了出來,三五成群地坐在這兩張球桌上,過不了幾天再次消失掉。鎮上的大人們見怪不怪,他們來來去去,從不多看那些少年一眼。他們和那些黃頭發的少年,就像是兩條方向不同的河流,彼此相安無事,卻也永無交匯。毛毛一只手抱著瓶子,一只手牽著爸爸的衣角,他倚在爸爸的腿邊,不住地張望那兩張球桌。他想球桌下一定有一個同樣神秘的管道,這些少年借助這個管道,在不同的世界里自由來往。
王所長笑著指點著那幫少年,道:“呵呵,就他們?”他伸出一只手拍拍爸爸的肩頭,有些輕佻地說,“廠長大人,莫怕莫怕!他們無非也就是要頓酒錢,等城里掃黃打黑風聲一過,你就是想見他們一面,只怕也難。”
爸爸似乎是不經意地往邊上略微挪了挪身子,王所長那只擱在爸爸肩頭的手滑了下來。爸爸看了看那群少年,冷笑一聲道:“不是有你嗎,我怕他們什么!我要是怕,就會給他……只是給了三哥,大哥、二哥、說不定還有四哥五哥,就都該來了!”
“呵呵!哪里會有這么多哥!”王所長訕訕地笑了。那只從爸爸肩頭滑下來的手,在空中不易察覺地停了一下,五指緊握著帶著些不快回到他的褲子一側的口袋里。王所長的眼皮垂下來,冷冷地道:“……多慮了。”
王所長從耳朵上取下支卷煙自顧自地抽起來。王所長道:“自古以來都是邪不壓正、白不畏黑。我可是知道的,以前老廠長,高興了也打發他們一點,但是要是膽敢找他要……”王所長話沒有說完,臉色一點點陰沉下來。他吐出一口煙霧,煙霧給他有些陰沉的臉戴上了一層面紗,使得他看上去就像桔園里的那口井,深淺莫明。
爸爸彎下腰來,摸摸毛毛的頭,十分溫和地說:“你先回去,告訴媽媽,爸爸和王伯伯說兩句話就回。”
毛毛抱著瓶子往家里走去。路過理發店時,一個像女人那樣在腦后扎著根馬尾的少年,伸出手里的球桿攔住了他。毛毛站定了,側過頭去看著那個少年道:“哥哥好!”少年愣了一下,遲疑著將球桿從毛毛胸前移開。
理發店里亮著燈,毛毛看見那個叫三哥的人臉沖著門外坐在一張人造革的椅子上理發,他把脖子以下的身體都埋在一塊發烏的白布里,聽任理發師擺布的樣子看上去特別溫順。但不知為什么,毛毛覺得三哥繃著臉一聲不吭看著門外的樣子,顯得有些心事重重。
毛毛回到家里,媽媽的晚飯已經做好了,飯菜都扣著盤子擺在了桌子上。媽媽沒有開燈,坐在窗前的暗影里擦拭著一把二胡。毛毛聽到了松香從馬尾上滑過時的絲一般的聲響,知道媽媽一定是在打理那只她不怎么舍得用的琴弓。這琴弓是爸爸托人從很遠的地方買回來的,淺栗色光潤的桿身上滿是深褐色的小圓點,毛毛到現在還能記得媽媽當時驚喜的表情。爸爸把琴弓從一只錦盒里取出來時,媽媽兩眼張得大大地叫起來:“天!湘妃竹的啊!”看到媽媽愛不釋手的樣子,爸爸十分得意地說:“馬尾是正宗的白馬尾毛哦,絕非漂染!”媽媽激動得臉都紅了:“你從哪里弄到的啊?”爸爸當時笑著瞧了媽媽半天,才答非所問地說:“謝謝你愿意帶著毛毛跟我來到這里……”毛毛聽不懂大人間那些莫名其妙的無趣的話,但他從此卻對那把琴弓著了迷,毛毛時常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摸摸它。每當他的手指觸摸到光滑柔韌的馬尾時,他都會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回回他都仿佛看見了一匹白馬,雄壯而又矯健的白馬,來自童話中和平而純美的國度,渾身像雪一樣白,像墻一樣厚實。它聽從了某種神秘的召喚,“嘚嘚嘚”地迎風疾跑而來。它在進小鎮的簡易公路上奔跑,身后揚起薄薄的塵沙,它穿過道路兩邊青翠的山嶺和清澈的流水,掠過果實累累的桔園,它奔跑著,雪白的馬尾高高地飄起來,簡直像道閃電一樣奪目……
毛毛跑到媽媽身邊,一只手抱著瓶子,伸出一只手去觸摸媽媽懷里的琴弓。媽媽輕輕拍了拍毛毛沾著泥土的小手,把琴弓放好,回過身來摸了摸毛毛的頭。毛毛把瓶子舉起來給媽媽看。媽媽并沒有看毛毛的瓶子,她站起來,微笑著擺了擺手,示意他把瓶子放到窗臺上。不知道為什么,毛毛覺得媽媽今天與以往有些不一樣,她看上去像三哥一樣心事重重。
不一會兒,爸爸回來了。毛毛聽到了爸爸“咚咚咚”的有力的腳步聲。爸爸進到屋里打開燈,燈光把爸爸的身影投射到他身后的墻上,這身影看上去異常龐大。墻的正中間掛著老廠長留下來的一把彎彎的短刀,爸爸站在那把短刀下,一只肩膀斜倚在墻上。爸爸看著媽媽笑著說:“你不知道他有多勇敢!長大一準是條好漢!”毛毛不知道爸爸在說誰,但爸爸臉上的表情看上去驕傲極了。媽媽的臉上浮起一個好看的微笑。
“你要知道,神父后來也路過那,他可是遠遠繞過球桌走的!”爸爸又說道。
媽媽對爸爸說:“你呀,知道什么!神父只是愛人,不是怕人。”
爸爸笑道:“神父愛人,所以怕人。”
媽媽回過頭去看著爸爸道:“你呢?愛人還是怕人?”
爸爸走到媽媽身邊,伸出雙手扶著媽媽的肩頭道:“我嘛,我只是愛人,不怕人。”
“不老實!你以為你是毛毛?”媽媽笑道。
爸爸也不由笑了。他歪著腦袋,裝出一副很認真的樣子道:“容我想一想……這樣吧,我且也先去做個惡人,好嗎?”
媽媽“撲哧”又笑了,道:“以后我就得叫你四哥嗎?”爸爸聞言也笑。
爸爸說:“做人真難啊!要不,這樣吧,遇到惡人做惡人,遇到愛人的且愛人?”
媽媽笑著搖搖頭,伸出一根手指,輕輕點在爸爸的嘴唇上。爸爸嘆了一口氣,安靜下來,不再跟媽媽爭辯什么。媽媽在裙子上擦了擦手,把扣在飯菜上的盤子一一揭去,屋子里一下子充滿了暖融融的飯菜的香氣。
“——廉師傅找你了。”媽媽吃著飯,有些遲疑地說道。工廠里的工人,媽媽都叫他們師傅。
毛毛聽到這句話,感到非常失望。他以為媽媽會像昨天一樣問他:“你學會了嗎?”如果媽媽這樣問,他就會告訴她,瓶子里的蟲子,有一條是他捉的。他還學著爸爸的樣子用注射器往蟲眼里擠藥水,然后把刮開的樹皮重新抿回去,并用稻草圍著樹干在打過藥的部位系了一個活結。他做得非常好,幾乎和爸爸做得一樣好。可是,媽媽沒有問。
毛毛把頭轉過去看著爸爸,他很希望爸爸告訴媽媽:“哈,我們的毛毛,今天干得真不錯!”但爸爸似乎也把這件事給忘了,這會兒他只是很專心地吃著飯,腮幫子鼓鼓地,慢慢地一下一下嚼動。爸爸把嘴里的飯菜咽下去后,說:“哦,老廉頭嘛,他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巴巴跑來說點維修倉庫的事。”一個說“廉師傅”,一個說“老廉頭”,乍一聽就像他們說的根本不是同一個人。
毛毛很奇怪地看了爸爸一眼。老廉頭根本沒有跟爸爸說維修倉庫的事,毛毛不知道爸爸為什么會這樣說。毛毛把桔樹包扎好后,把工具收拾好放進一個小背包里。他背著小背包,抱著玻璃瓶跑到爸爸身邊,聽到老廉頭對爸爸說:“……這樣的東西,沒有了干凈!”毛毛仰著小臉,把瓶子舉起來給爸爸看。毛毛說:“爸爸,瞧,我捉到了一只!”爸爸似乎沒有聽到毛毛的話,他皺著眉,對老廉頭說:“好了,你們回去吧,這事不成!”說完爸爸彎腰把毛毛抱起來往家走。老廉頭急急地跟上來,兩只大而骨節突兀的手在胸前撕扯著工作帽。老廉頭急促地說:“廠長!燒成車間里頭,石頭進去,還不是變成灰出來!你放寬心……”爸爸停下腳步,非常厭惡似地打斷他:“好了老廉頭,別說了!這件事,不成!”老廉頭把手捂在胸前,慢慢抬起頭來看著前方。老廉頭一字一句地說道:“要是老廠長在……”爸爸“噌”一下轉過身去,看著老廉頭很大聲地說道:“現在不是老廠長了!我再說一遍,不成!”不容老廉頭再啰嗦什么,爸爸說完這句話轉身就走,步子邁得又大又快。毛毛把下巴擱在爸爸的肩膀上,看見老廉頭的雙手無力地垂下來,顯得非常失望的樣子。那三個站在不遠處抽煙的老人走到老廉頭身邊,毛毛看到他們穿著和老廉頭腳上一模一樣的軍綠色膠底鞋,褲子都卷得高高的,露著蒼老而青筋暴突的小腿。他們問了老廉頭一句什么話后,把旱煙從嘴邊上移開,抬起頭齊齊地看向爸爸,滿臉都是鄙夷的神色。
毛毛也曾跟著爸爸去過水泥廠。翻過西邊的山嶺,就能看見水泥廠的廠房。毛毛不但知道水泥廠有燒成車間,還知道水泥廠有制成車間,烘干車間和包裝車間。從山里挖出來的石頭,在這幾個車間里挨個走一遭,就會完全失去自己原本堅硬的本性,變成風都能帶走的粉塵。不過,神奇的是,只要這些粉塵遇到水,就會重新變得堅硬,而且比原先的石頭更甚。
“爸爸,蟲子進到燒成車間,會不會變成灰出來?”毛毛問。
爸爸笑著摸了摸毛毛的頭,說:“快吃飯吧!”
“桔樹呢?”
“……”
“鐵絲呢?”
“……”
爸爸一直沒有吭聲。媽媽看了爸爸一眼,柔聲地代替爸爸答道:“可能會吧,爐子里的溫度太高了。”
“那有什么東西是不會變成灰的呢?”
“毛毛!吃飯的時候不要說那么多話好嗎?”爸爸的眉頭皺起來,有些不快地喝道。毛毛趕緊低頭吃飯。
毛毛覺得爸爸媽媽突然都變得有些不對頭,可能是提到了老廉頭的緣故。當然,也可能不是。是不是對毛毛來說都不重要,毛毛不再說話,飛快地把飯吃完。毛毛吃完飯,到廚房的自來水龍頭下洗了洗嘴巴,“噔噔噔”地跑到窗臺前去看那只玻璃瓶。毛毛跪在一張方凳上,看見那些蟲子都安安靜靜地躺在瓶底,似乎是先前那種一曲一伸的運動把它們累壞了,此刻它們都已沉入夢鄉。毛毛毫不費力地從它們中找到了屬于他的那只,現在它以一種特別的姿態躺在那,小小的身子中間有一道細微的被鐵絲弄出的傷口,沒有鮮血流出的傷口,這讓毛毛一眼就認出了它。
爸爸媽媽在他身后小聲說話。
爸爸對媽媽說:“要不,你們還是回到城里去住吧……”
毛毛一聽著急了,他猛地回過頭去喊道:“我不想回到城里去,我就要在這里嗎。”毛毛知道一回到城里他就要去那個四周都是鐵柵欄的幼兒園,天天把手背在背后,小身子坐得直直地跟老師念“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真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
媽媽對毛毛擠出一個安慰的笑,道:“爸爸逗你玩呢,你到院子里去,把蟲子都倒進雞食槽里吧。”毛毛把瓶子抱在懷里溜下凳子往門外跑去,聽到媽媽在身后對爸爸說:“瞧,他喜歡這里……都還是些孩子呢!能怎么樣呢?兔子還不吃窩邊草,老廠長一家,還不是在這住了十多年?”
“可是……”
毛毛借著從窗口淌出來的燈光,拍著瓶底把小蟲子都倒進雞食槽里。小雞聽到動靜在雞窩里撲騰起了翅膀。
“明天再吃吧!”毛毛對小雞說。
院子里有媽媽種的花花草草,紅紅黃黃地開了一大片。沒有月亮,燈光照不到的地方都黑漆漆的,是刀也劈不開的黑。毛毛站在燈光里,感覺就像站在一口開鑿在黑暗中的狹長的水井里。毛毛朝四周看了一眼,索然無味地回到屋內。爸爸皺著眉,若有所思地坐在桌子邊上。他的手里還攥著一塊軟布,正有一下沒一下地擦拭那把短刀。媽媽坐在窗前調試二胡,“多米多米,來索來索”,毛毛知道媽媽又要拉二胡了。爸爸把刀輕輕放到桌子上,伸出一根手指豎在嘴唇上,“噓——”爸爸沖毛毛打了個手勢,把毛毛摟過去讓他坐在自己腿上。毛毛把空空的玻璃瓶抱在懷里,瞪著眼睛看著門外濃濃夜色中的天空。有兩顆星星非常亮,這是個寧靜的晚上。很快,媽媽的琴聲引來了風,先不過是微風,嘆息一般在身邊繞來繞去。后來風越刮越大,裹挾著飛沙與嘶鳴的馬群,鞭子一樣呼嘯著從門外卷過。毛毛屏住呼吸,把眼睛瞪得大大地看著門外。毛毛渴望能從那些疾奔而來的馬群里看見一匹真正的白馬,屬于他的,閃電一樣迅捷的白馬……可是毛毛什么也沒有看見。狂風與紛沓而來的馬蹄踢騰起的陣陣塵沙,遮住了星星的光芒,毛毛一瞬間仿佛墜入了無邊的黑暗。毛毛坐在爸爸的腿上一動也不敢動,屏住呼吸把那只空空的玻璃瓶緊緊地摟在懷里。毛毛頭一次感覺到了恐懼,那些莫名的無人能免卻的恐懼,是那么真實、那么近……
琴聲終于停下來的時候,毛毛在爸爸溫暖的懷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就像剛剛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現在雨歇風停,毛毛重新回到了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