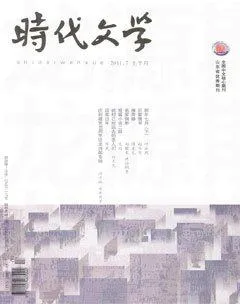艾瑪:剛強而溫和的慈悲
艾瑪的短篇小說《浮生記》,寫過這樣一個情節:學做屠夫的新米頭一回殺豬,不僅顯示了“令人叫絕”的好刀功,而且讓師傅看到:這個十六歲的少年“在溫和的外表下,有著刀一般的剛強和觀音一樣的……慈悲!”如此感受,得之于一個小小的細節:單薄的新米在“手起刀落、神情專注”地行使屠夫的本分時,還顧惜到了“躺在條凳上的豬無助地將頭后仰,它嗷嗷叫著,雙眼潮濕而驚恐”,所以,他未忘騰出一只手來,把豬的雙眼一一合上。這個不起眼的小動作讓老屠夫感動得潸然淚下,也讓他對死去的結拜兄弟——新米的父親——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在六七千字的篇幅中,艾瑪迂回綴合了兩代人的故事:他們或靠做活謀生,或為謀生而死,在生生死死恩怨交割之中各有各的情理因由,但不管生存條件如何冷酷,“剛強”的人們總能釋放出可以相濡以沫的“溫和”,最終攢下合適的溫度,從而達成和解。
從處女作《米線店》,到《浮生記》、《開滿鮮花的土地》、《小民還鄉》、《萬金尋師》等一系列以涔水鎮為背景的作品,艾瑪在敘事上有著一貫的從容淡定、不溫不火的自信與自覺,因此,她的小說素材雖然多為不起眼的凡俗瑣事,但是講出的故事卻能別有一番滋味。這滋味得益于質樸而節制的語言,得益于小說的敘事氛圍,當然更得益于艾瑪表現出的親和與包容,她好像總能夠在不經意間將你拉入到“涔水鎮”的語境中,讓讀者和小說人物共同充當故事的推手,從而使小說大大突破它的文本格局,獲得甚為廣闊的勢力范圍。她的小說常常就是這樣幾乎是悄無聲息地結束了一場追魂奪魄的搏殺。
本期同時刊發艾瑪的兩個短篇小說《一只叫得順的狗》和《彎刀》,依然遵行了她的“和解”路線,體現出剛強而溫和的慈悲。像《浮生記》那樣,艾瑪還是用簡短的文字講述了兩個并不曲折的故事,尤其是《彎刀》,甚至可以說近乎看不到故事,作者所做的,只是借助一個小孩子的有限視角,探察成人社會的重重隱秘。正如毛毛為桔樹治病一樣,他以為用鐵絲從樹洞里鉤出蟲子很值得驕傲,卻不明白爸爸、媽媽為何不以為意,他只覺得他們“有些不對頭”,他不知道大人們既要面對惡人,還要面對自己的內心。那把彎彎的短刀,原是可以壯膽的,在被爸爸擦拭之后,卻讓毛毛“頭一次感覺到了恐懼”——這“恐懼”很可能意味著童年的結束,讓一個孩子瞬間長大。小說結尾寫道:毛毛在爸爸溫暖的懷里,“重新回到了寧靜”。顯然,艾瑪的落腳點仍是和解。雖然爸爸也說“遇到惡人做惡人”,雖然他拿出了短刀,但作者早已用神父、《圣經》、愛人等溫暖的語匯阻止了他,屬于我們的,必然是狂風暴雨之后的一片寧靜。
《一只叫得順的狗》相對好看一些:寫的是一名酷愛食狗肉的警察,對細膩肥嫩的母狗肉尤為看重,他極其細心地飼養母狗,為的是好好地吃狗。但是,小說里的“阿黃”很走運——不僅沒被吃掉,還很長壽地活了二十多歲。原因不是那位狗肉警察改了食性,而是因為阿黃懷上狗崽子——當然,根本原因還是這名警察,若非他的“成全”,阿黃也不可能成其好事。僅只這些還不夠,關于該狗肉警察,重要的卻是另外一筆:他親手抓住的女毒犯在被處死前托他照顧一家老小,他由此對“一報還一報”的行刑產生了“厭惡”。正是那女犯的死,讓這位酷食狗的警察有了測隱之心,所以才有了阿黃后來的幸福時光……一條狗命,照見人心。在這篇小說中,艾瑪恐怕還是在揣度人心的柔韌度。善說鼓書的梁小來是一種,酷食狗肉的警察又是一種,當他們一致把阿黃叫成“得順”時,很可能,二人的心里都極其柔軟。
艾瑪是學法律的,她的小說也或多或少地可見其法學背景,但她從未生硬地強調法的力量,或者裝模作樣地以案說法。雖然她的小說常會有非正常死亡,會有殺戮、苦難,但她不去虛張聲勢地渲染某種宏旨大義,而是以一顆憐恤之心,去描繪生活的肌理。她關心阿黃,也歡喜得順;她欣賞說書人,也顧惜女毒犯。因此,她的文字剛強而溫和,她的小說像傾之不盡的大碗了一樣盛滿了安詳與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