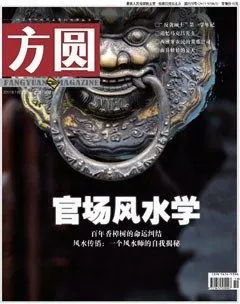官場風水記
2011-12-29 00:00:00邰筐
方圓 2011年13期



眼下的某些官員跟僧道活佛關系密切,信了這個信那個,說到底,其實什么都不信。他們之于佛道還有風水,無非是想找一點彼岸世界的助力,幫他們升官發財。這樣的信法,就是迷信
最近,網絡上兩則較為搶眼球的消息都跟風水有關:
一則是前文提到的鬧得沸沸揚揚的百年香樟樹事件,另一則是接連發生兩起學生命案的廣東高州市平山鎮中心小學“鬧鬼”事件,從校長到老師內心都很惶恐,認為是同處的祠堂里的“鬼魂”作祟。為保平安,先是前任校長請一位風水師作法“驅鬼”。受阻后,后任校長跟著又請來一位風水師查勘,得出學校大門方位不好,要修改校門方位“改運”。
在近年媒體不斷爆出的“風水事件”中,這兩件也許是最新的,但絕不是最離奇的,已有事例證明,一些高級官員,先后被某種“玄學”俘虜。
國家行政學院綜合教研部研究員程萍博士曾作過一項調查,在接受調查的900多名縣處級公務員中,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人數比例僅為12.2%,一半以上的縣處級公務員多少都存在相信迷信,相信風水的情況。
李真:越腐敗,越迷信
曾被視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國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李真就是其中一個極端的例子。曾經跟蹤采訪李真案四年的記者秀靈近日接受了《方圓》采訪,給記者講述了李真案件背后不為人知的細節。
“在李真獲悉中紀委要對他實行‘雙規’前,早在2000年2月29日下午,他就將金錢和護照都放在了車的后備廂里,做好了半夜里出逃的一切準備。但是,為什么沒有離開呢?是因為征求了一個大師的意見。在出逃之前,他給北京的大師打電話問:我近日有災禍嗎?大師切算后答:‘沒事,你有貴人相助的,你就放心地休息吧。’李真信以為真,就休息了。結果第二天李真就接到通知,讓他下午到省委‘開會’。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秀靈對此很感慨,“這件事對于一直信奉‘大師’,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寄托在‘大師’身上的李真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反諷。”
據秀靈透露,“除了信奉‘大師’,李真對數字‘8’也特別迷信。李真認為數字能夠給人帶來吉兇,而他的吉祥數字就是‘8’。所以,他開的車是‘38’號,手機號碼有‘8’,BP機號碼有‘8’,辦公室和住宅電話號碼也都有‘8’。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出事那年38歲,三十八,反被抓。”
以下的情節在《河北第一秘——李真盛衰記》里可以找到:李真剛當國稅局局長沒多久,就找到“大師”,讓他給自己算算多長時間能當封疆大吏。 “大師”說,“你長不過5年,短不過3年。”他一聽高興極了,從口袋里馬上拿出5000塊錢,甩給了這個“大師”。“大師”說你再加1000吧,我圖個順,沒想到李真又拿了3000給他,說我就圖個發。
秀靈還告訴記者,“圍繞李真常坐的轎車,還有好多迷信的細節。1992年,李真當上了省長秘書后,他駕駛著省政府的二號車,即冀A-00002 ,這時他既是省長的秘書又是司機;1993年他跟隨程維高進入省委成為第一秘后,他駕駛的車牌號改為冀A-11111,他的寓意是:我是天下第一秘,在河北我是老大,我說了算;1995 年他調到省國稅局當上了局長之后,他駕駛的車牌號改為冀A-00038 。李真找人算過,三十八,是個坎兒,闖過去,就能發達;如果他的車在三十八歲這一年被攔下超過八次的話,這個坎就過不去了,從此會前半生輝煌,后半生遭殃。因此,李真駕駛的冀A-00038 車,別人是不能阻攔的,攔住他的車就等于擋了他的前程,所以,對膽敢攔自己車的警察,李真從來都是毫不客氣的,非打即罵。”
“所以李真的車是從來不管紅燈綠燈,勇往直前的。久而久之,老警察都知道冀A-00038是李真的車,就當成沒看見。”
“有一天偏巧來了個新警察,李真的車闖紅燈以后,立即就趕上去。李真從鏡子里面一看這個警察跑過來了,就把車玻璃窗搖下來,然后擺了擺手,這個警察快走了幾步,正準備敬禮,結果李真就呸的一下,吐了這個警察一臉。而且還給一個領導打電話,‘把今天在這個崗樓執勤的警察,給我開了。’結果呢,這個警察在這個崗樓上再也沒出現。”
問題是并不是所有交警都吃李真這一套的,偏偏就有不信邪的交警和他較真。結果在李真三十八歲這年,即2000年3月1日前,他的紅旗高級轎車被警察攔下的次數超過了八次,三十八歲這個關他沒能通過,他迷信地認為:是自己的疏忽大意,同時也是警察給他帶來了災難和毀滅,心中因此充滿了憤恨。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李真被捕進入看守所后,依舊“癡心不改”,一天到晚翻來覆去用撲克牌為自己算命,夢想通過54張紙牌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如果算出來的就是好卦,他一天心情都會很好。算出來的如果是壞卦,他就會一天話都不說,情緒很低落。”秀靈說,“李真迷信幾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他被關押在2號院的2號監舍里,這在李真看來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因為2+2等于4,而4的諧音就是‘死’啊。”
“李真對自己的未來始終存有一份幻想。除了靠擺撲克牌給自己算命打發時光,他最有興趣的就是在監舍里給大家‘分官’,科級處級他一句話能分出去好幾個。他竟然對查監的李所長說:‘李所長,等我出去了,給你安排個公安局局長當當。‘李所長故意調侃他:‘那原來的局長怎么安排?’‘把他調走。’李真胸有成竹地說道。”
直至被執行死刑前,李真常常徹夜難眠,唉聲嘆氣對人說:“人的生和死原來是這么近啊。”
“李真在《悔過書》中這樣寫:‘人可以沒有金錢,但不能沒有信念。喪失信念,就會毀滅一生。’而他就是因為缺少信念才會迷信,迷信是盲目的信,其實是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才會無所畏懼,這是個很淺顯的道理。李真留給了我們一個血的教訓。”秀靈說。
官員為何迷信風水
除了李真,在媒體隔三岔五披露的落馬貪官中,愚昧迷信的并不少見:例如,重慶市委宣傳部原部長張宗海,不惜花費40萬元巨資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剎“爭”燒第一炷香。河北省原常務副省長叢福奎,信奉迷信到了癡迷的地步,在家中專設佛堂、供神臺,常常燒香拜神……
以上種種現象,不禁讓人感慨萬端。他們有的占卜算命,身后跟著“大師”的身影;有的求神拜佛,雙膝跪倒在泥菩薩面前;有的觀天看地,選擇“風水寶地”;有的大興土木,建造“極品活墓”,為自己安排“后事”;有的平時在臺上大談馬列主義,臺下卻對一些“大師”津津樂道,與之成了“知心朋友”或座上賓;有的官員每逢上任、紅白喜事等,都要“大師”或神靈指點迷津,甚至連出行也要看日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對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頗有感慨,“這些年來,總是聽到有人談起風水學正走俏官場,一些掌握一州一邑或者某一部門的官員不但遇佛拜佛,逢仙奉仙,也向一些風水師互通款曲,求其指點迷津。這種事情,最初是偶爾聽人口述,當做茶余飯后的談資,后來見媒體已時有披露,便知此風日盛,不再是個別現象。這種事知道多了,才意識到我們一些官員不知什么時候開始,把無神論擱置一邊,紛紛信起風水,難怪如今我們的社會‘大師’忽然多起來,各種‘妖孽’都順勢沉渣泛起,有了新的發財之道。”
“為什么有人青云直上,有人卻掉了烏紗帽?在一些官員看來,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王擇青說,“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諸鬼神,找寄托。而關于風水成功的各種傳說流言,當官員們處于換屆調整這樣的緊張時刻,就會給他們強烈的心理暗示。”
“一旦步入官場,除了不斷地升遷,很難用其他方式證明自身的價值,而升遷又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錯綜復雜的關系、無窮無盡的應酬、糖衣炮彈的誘惑、突發事件的打擊、媒體監督的曝光等等,目前大量的抑郁癥、自殺事件表明官員這個群體其實同樣面臨著巨大的職場壓力,因此訴諸風水、命運是一個精神依托和宣泄渠道,無非是想逢兇化吉,官運亨通,安頓心靈。”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馬特認為,“另外,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員,原本通過正當的努力就能夠獲得升遷,但為了增加‘保險系數’,也同時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不正當的投資。”
“仔細想來,國家官員信風水,原因也不都一樣。一種是某些官員基于讓自己主政下的建設工程更為完美,找人看看風水,這一個動機,雖說有迷信嫌疑,也還算說得過去;另一種是相信冥冥中有神秘力量操縱著個人命運,盼望善用風水學為自己的仕途前程增加機會,所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是也;還有一種是貪墨之士唯恐東窗事發,想借風水避災辟邪,與其信其無,不如信其有,把風水當做自己的護身符。”張建偉認為。
“不管哪一種情形,國家官員信風水,多少說明無神論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已經式微,他們已經在意識形態上向有神論輸誠。對于國家官員來說,如果他不是執政黨的一員也就罷了,如果是,起碼他的觀念已經背離了執政黨的宗旨,這種黨員干部要是還能坐得穩權力寶座,乃至平步青云,獲得高升,那實在是紀委監察部門對該人未盡明察之責。”
官場風水其實無關風水
“風水”是科學還是糟粕?前段時間,隨著風水申遺的提出曾引起長時間的質疑與爭議。
不可否認,一些與風水有關的意識中確實存在著反科學甚至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如果仔細論道的話,“風水”這一傳承自中國傳統文明的產物,卻并非完全是毫無道理的糟粕。用“封建迷信”一語來概括,顯然也有不加鑒識,全盤否定之嫌。
不難看出,“風水”之所以引發爭議,不過是因為“風水”二字的出身不好罷了,如果剔除其中封建迷信成分,將其更名為“建筑環境綜合科學”的話,想必反對之聲定會大為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既然不否認建筑、城市規劃有著與自然調和、與環境適應的天生需求的話,就不應否認“風水”存在的合理性。
相反,如果因為“風水”中曾經含有的封建迷信成分,便將其一棍子打死,使其不得不走入“地下”發展,倒反而促成了一些缺乏專業知識,卻打著“風水”旗號販賣封建迷信的江湖術士行騙發財。即便從防止風水成為江湖邪術這一視角出發,正視“風水”也遠比視而不見的避諱要強得多。
風水學很民間,堪輿學很學術。殊不知,在不同馬甲間變換的一樣東西,竟會產生迷信與科學的大爭辯,似乎一提及風水二字,社會上總免不了質疑與爭論。堪輿學,自然有科學的成分。
若沒有因地制宜、坐北朝南、中軸對稱、依山傍水、統籌規劃等原則,我國建筑史上也不會出現布達拉宮、中山陵等天人合一的經典建筑,更不會出現氣勢宏偉的帝王宮殿與陵墓。所以,堪輿學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1985年,在時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強力支持下,北京大學就正式開設了風水課,于希賢是主講人。
2008年,在新一輪的“風水熱潮”中,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在全國高校中率先開設“建筑與風水”課程,選修人數竟遠遠超過50-60人的平均水平,達到130余人,且70%以上為非建筑專業學生。
目前在國內,風水學課程,受到了市民的追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天津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安徽大學等高校也先后開設了與風水相關的課程,且多設在環境建筑系、哲學系和地理系等專業中。
據北京師范大學易學與建筑文化研究生課程班負責人介紹,該班每期招收的學員約為30-40名不等,要完成為期兩年的學習課程,學習包括《堪輿易學》、《易學與預測學》、《建筑風水學》、《家居易學》等內容,學員中80%都是來自房地產、建筑行業的從業人員,也有一部分是風水愛好者或專門的風水師。
“其實,官員迷信不是當代才有的新鮮事,而是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人性基礎的規律性的現象。單純依靠禁令、宣教、懲戒是很難真正奏效,因為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內心世界和整個官員任免制度改革,而與民間風俗方面的堪輿學關聯不大。大量相關事例的涌現,折射出的是公務員職業的不確定性和官員內心的不安全感。”馬特告訴記者。
“一言以蔽之,官場風水其實無關風水,頂多只能算是一塊讓官場丑劇欲蓋彌彰的遮羞布罷了,只不過這塊遮羞布其實更像是一面照妖鏡。官員的風水情結,官場對風水的膜拜,不過又是一出翻版的《官場現形記》。”
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神鬼傳統”而非“人的傳統”,即所謂“皇帝統治靠天,草民維權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個人都是弱者,他們甚至不得不將自己的成敗得失歸因于某些不可抗力。這種將自己與社會的命運寄托于神秘力量獲取拯救的心理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散發著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氣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鳴說,“風水先生可以通過‘看’,看出來,算命大師可以通過‘算’,算出來,而佛道和活佛,則可以通過各種更加神秘的法會、道場展示出來。大師無非是中介,是官員和神界之間的中間人。官員通過中間人,賄賂了神佛。官員們的迷信,跟他們在官場上的作為一樣,無非是私下操作,潛規則,走關系,塞包袱。”
官場風水折射信仰危機
“這些年來,佛道很風光,會看風水的人,生意也特別的好,名氣大一點的,每每賓客盈門。有權和有錢的人,似乎都好這一口。特別是有權人的熱衷,對這些人的生意,有極大的廣告效應。這些大師們,自我吹噓之時,一般都會提及他跟哪個領導關系如何如何。”張鳴告訴記者。
“哪個哪個大師,或者活佛,跟哪個領導過從甚密。這些事,我都無法考證,即使這樣的話出自號稱不打誑語的出家人之口,我也沒法信。現在道觀佛寺,盡管香煙繚繞,但卻有了太多的衙門氣和銅臭氣。”
“眼下的某些官員跟僧道活佛關系密切,信了這個信那個,說到底,其實什么都不信。他們之于佛道還有風水,無非是想找一點彼岸世界的助力,幫他們升官發財。這樣的信法,就是迷信。”張鳴認為,“佛教也罷,道教也罷,不僅有讓人尊奉的神佛體系,而且背后有相應的道德說教和信條。信徒守戒,就是要通過這種外在的約束,實現道德的凈化。但是,迷信佛道的官員們,守戒者一百個里面一個都沒有,根本也不在意宗教的道德信條。他們的信,就是讓宗教業者通過某種操作,給他們帶來福祉。當然,這需要付費,即使不付費,也要轉讓一點權力。所以,很多圍著領導轉的僧道活佛,都很能辦事,其本領,就是從領導那里讓渡過來的權力。實際上,官員們在意的是大師們的法術,一種正常人間世界沒有的功夫。”
“這樣極端性的功利信仰,跟中國人固有的宗教意識有關。或多或少,國人傳統的宗教信仰,確有功利性的一面。但是,即便如此,一般人的信仰之中,還是存在對宗教道德信條的敬畏。沒有太多的人相信,可以一邊做惡,一邊給神佛掏點香火錢,就可以平安無事,官運亨通。但是,官員們信,在他們看來,沒有權力運作和金錢運作做不通的事,只要有了權,就什么事都能辦成。這樣的極端,本質上是官員們在既有信仰崩塌之后的一種變態反應。在這個時代,如果真的有信仰危機的話,主要體現在某些官員身上。”張鳴說。
官場風水危害大
官場風水的現實危害,絕非危言聳聽。所以才有這樣一種說法,“民間信不信風水,是老百姓自個的事兒;官場信不信風水,是全中國的事兒。”
一個官員,往往承擔著社會事務管理者和協調人的角色,還掌握著許多政治、經濟資源。是相信迷信還是崇尚科學,實質上是世界觀的問題,而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官員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迷信的官員,在工作和生活中,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迷信思維滲透進來。
更為嚴重的是,官員迷信會產生不良的示范作用,污染社會風氣。一旦迷信武裝了官員的腦袋并且據此發號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員的特殊身份也決定了迷信的危害會從私域沖進公域,就像山東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只因為某大師說他“有副總理的命,只缺一座橋”,不惜將建設中的國道改線橫穿水庫,修上一座橋。
張建偉認為,“信術士,迷風水,多少讓人有一種聯想,那就是為君則為昏君,為官則為昏官。為官之道,各有心傳。在官僚體制之內,官員只要博上司之歡心,就有了步步高升的條件,但精明強干和政績卓著與前一個條件結合在一起,就更無往不利。在民主社會,主要官員須得選民支持,才能在一定時期掌握和維持權力,對民眾冷漠以對,不為民眾服務,無異于仕途自殺。這兩種情況,都與風水無關。迷信風水,也許就是昏庸的表現,這種人將自身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尤其是將私欲私利置于民眾利益之上。”
“風水腐敗”法律上難界定
現在官場人物迎僧訪道,講求風水,并不是少見的事情。但在一些法律人士眼里,這種潛規則已經觸犯刑律。
“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區分:一方面,官員作為個人,有沒有權利相信風水?這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如果僅是內心信仰,秘而不宣,實際上也無從懲戒,如果通過語言、行動表現出來,則是一個作風問題,為風紀所不容。”馬特認為,“另一方面,如果官員利用風水斂財,供養‘大仙’,或者濫用公權力,搞什么‘風水樓’、‘風水橋’,這才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的關鍵是限制官員手中的權力,把公權力處于法律制度和公共輿論的約束下,不能拿公共資源為官員的個人風水癖好買單。”
“如果是官員明確授意商人支付看風水的費用,那毫無疑問屬于行賄受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說,“但是,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鉆: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幫閑’,官員又推說自己只是聽聽朋友的建議,法律上就難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