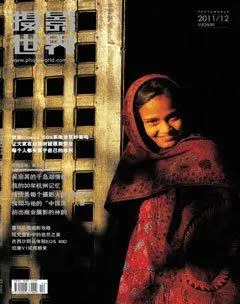影中人
2011-12-29 00:00:00沈伯韓
攝影世界 2011年12期


8月15日至27日,我在中非國家喀麥隆首都雅溫得工作了近兩個星期,拍攝有關“貧困”的專題報道。這種工作形式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實踐——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待一段時間,在較為寬泛的主題之下去挖掘各種表達的可能。
食品安全、艾滋病、瘧疾和TB(結核病)是目前非洲大陸上最嚴重的四大問題,我自己對艾滋病相關問題最感興趣,所以這是我確定下來的第一個大致拍攝的方向。另外,喀麥隆是非洲足球大國,全民愛球,是否可以把足球作為切入點來探討當地的貧困生活?最后,雅溫得有大小貧民窟(棚戶區)數十個,這些地方應該是發現故事的“金礦”。盡管這三個話題顯得有些“老套”,但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講述,對我而言未嘗不是一種挑戰。
8月16日至18日,我探訪了幾處當地的貧民窟,本想嘗試在街頭抓拍,卻遇到了困難。雅溫得的貧民窟有大大小小的負責人,一般都是當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家庭的成員,偶爾也會有黑幫勢力的滲入,在社區生活中起到一定的領導、核心作用。在貧民窟拍照,必須先去這些負責人家里“拜碼頭”,而且拍攝前也必須要征得被攝對象的同意。據當地記者介紹,早在喀麥隆共和國建國之初,為強化政府的某種權威,法律規定未獲得許可的人不得在公共場所拍照,幾十年來,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在街頭拍照,即便被拍攝對象對此無所謂,周圍的人也可能會來干擾。要抓拍到人的自然生活狀態基本不可能,于是我開始嘗試走入人們的家庭,用拼接全景的方式拍攝他們的房間內景,試圖去展現居民生活的細節、還原生活本態。
不過按照這種方式拍攝了幾個家庭后,我停了下來,因為這種被攝對象呆滯地直面鏡頭的肖像拍攝方式并不是我所喜歡的,過于模式化和簡單化,從照片中無法感受到更多人的活生生的氣息。而要用全景的方式去展現家庭生活的面貌,從技術上來說,抓拍到更有內容和意義的動作又很困難。同時,尋找有意思的場景和人物以及溝通所花費的時間成本過高,所以只好放棄。
8月19日,通過當地一個NGO的工作人員,我們找到了一個與艾滋病相關的 “希望與生命”協會。在開車前往這個協會辦公室的途中,我的腦海中蹦出了一句話“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是的,那些HIV病毒感染者不正是這種狀態嗎?他們為了生存,為了不被周圍的人、甚至是家人拋棄,不得不隱匿自己的病情和身份,如同生活在陰影中一般。是不是可以用影像來表現他們的這種狀態呢?拍攝HIV病毒感染者的生活環境肖像,將其面部隱匿在某種陰影之下,既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其隱私,畫面的形式又能契合主題;同時,畫面中的其他內容還能反映被攝對象的生活現狀。有了這些想法,我既興奮又忐忑——興奮的是,找到了一個自己感興趣的切入點以及表現形式,忐忑的是,真的有人愿意做我的拍攝對象,敞開他們的私人生活領域嗎?
在和“希望與生命”協會的負責人詳細闡述了我的想法后,她同意為我找十幾個會員,第二天一早在辦公室見面,由我來向他們解釋自己的工作內容,征得他們的同意就可以進行拍攝。回到辦公室,我在flickr上用“face”和“shadow”作為關鍵詞,搜索了一些能展示出我所想要拍攝圖片概貌的圖片樣例打印出來,準備第二天向那些HIV病毒感染者展示,消除他們的顧慮。
第二天,一切還算順利,來了13個人。在向他們詳細解釋了我拍攝這組圖片的目的、具體的操作方式并展示了圖片樣例后,有8個人答應了拍攝要求。從20日到24日,我一共見了23名HIV病毒感染者,為其中的15個人拍攝了環境肖像,同時對其生活景況進行了采訪并錄了音。
從一個人家到另一家,往往要開車一個小時甚至幾個小時。在見面之前,我不知道拍攝對象會是什么樣的人,曾有什么樣的遭遇和故事。要在短時間內了解他/她的背景情況,通過觀察并根據這些背景情況來大致了解這個人、感受他/她的氣質,再根據家中實際情況確定拍攝內容和方式,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每一次拍攝,都要避免在畫面構圖上與之前拍攝的照片重復,畫面內容還要契合拍攝對象的個人情況,要有所創新——自己給自己提的要求貫穿于拍攝的整個過程,也使我內心的焦慮不斷增加。但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壓力,才讓我盡一切所能去創造性地運用所能運用的所有條件和元素。也正是這種“糾結”才能激發出一個攝影師的潛能,有所收獲和提高。
在拍攝過程中,我也在進一步認識了“肖像”。那種被攝對象呆呆地盯著鏡頭的中畫幅肖像現在雖然很流行,但我覺得肖像不應只是那樣,呆板而毫無生氣。它應該有所變化,能反映出被攝對象的精神氣質。肖像雖然拍的是人,但用畫面本身而不只是圖片說明就應該能講“故事”。這里的“故事”可能不是具體的情節,但要有細節,并能用這些細節以及整體的氛圍來吸引和打動人。就像戴安·阿勃絲的作品,在畫面構成等方面看似簡單,讀來卻溝壑萬千、攝人心魄。
8月20日,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腳受傷的F女士躺在租住的小屋里和小貓玩耍。
43歲的F女士,2008年因做手術多次輸血感染HIV病毒。2010年,其丈夫知曉她的病情后隨即與其離婚。她生有4個孩子,全部感染HIV病毒。目前她帶著其中兩個孩子租住在小山坳里的一座小房子里,白天孩子們出去玩,只有一只小貓陪伴她。
F女士以前是一名秘書,現在偶爾打打零工,掙到的錢只能支付每個月13000非洲法郎(約合30美元)的房租。她沒錢支付CD4檢查費用,因此無法得到免費的藥物,但是孩子的學費她卻堅持支付。因為家人都不管她,她希望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維持生活,也希望將來孩子能贍養她。
8月22日,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O女士站在自家窗前,感受著胎兒的胎動。
36歲的O女士,2002年產前檢查時檢測出感染HIV病毒。
她生有1個孩子,未感染HIV病毒,所以她又滿懷信心地要了第二個孩子,目前已懷孕4個月。
她以前是酒店招待,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就放棄了工作。她盼望第二個孩子是健康的,希望大女兒長大后當醫生,給艾滋病患者治病,或者當個老師,教育孩子們預防艾滋病。
喀麥隆的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續上升,一度高達20%,但這一數字近年來持續下降,2009年為5.1%。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發布的統計數據,2009年喀麥隆全國共有61萬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歲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萬人。
8月23日,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發型師G女士頭戴假發,站在自家的小屋里。
28歲的G女士,2009年在進行例行檢查時檢測出感染HIV病毒,系工作時感染。她至今未婚,生有1個孩子。
目前她住在別人免費提供給她的一間小屋里,孩子則與其父親一起生活。她偶爾給居住地周圍的人做頭發,但收入不夠伙食費和醫藥費。她希望能重開理發店來獨立生活,她保證將格外注意安全,以避免把病毒傳染給他人。
8月21日,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K先生躺在自家的沙發上閱讀《圣經》。
42歲的K先生,2004年出國旅游例行檢查時檢測出感染HIV病毒。
他至今未婚,有3個孩子,目前與其中1個孩子一起生活,家人尚不知道他的病情。他以前是音樂人,現在靠種樹苗、在教堂樂隊打工維持生活,每月賣樹苗能掙6萬非洲法郎(約合136美元),可以支付孩子的學費和自己的醫藥費。他希望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待遇和治療條件能夠得到提高,公眾“不要拿艾滋患者當怪物”。
8月21日,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E女士在自家小屋里化妝,準備去教堂參加彌撒。
31歲的E女士,2004年檢測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寡居在娘家,其丈夫在他們結婚2年后就死于艾滋病。當她的病情被外人所知后,她丟了老師的工作。
目前她在一家小商店打工,每月賺25000非洲法郎(約合57美元),剛夠支付她的交通費和醫藥費。她希望能找到一個信教、善良的丈夫,即便知道她的病情也依然愛她、和她一起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