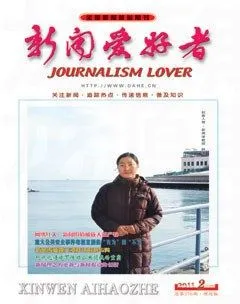豫西北西廂故事傳播管窺
摘要:元雜劇曾在河南西北地區廣為流傳,王實甫的代表作《西廂記》歷來被當地群眾喜愛。在今河南輝縣褚丘村和洛陽偃師石橋村,百年來流傳著關于《西廂記》的故事傳說。兩地都分別提出有力證據,證明自己是西廂故事的源頭所在,而非學界普遍認為的山西永濟。然而結合田野調查、地理方志等相關資料研究,上述兩地的西廂傳說應為元雜劇《西廂記》傳播過程中的衍生物。所得結論雖然駁斥了西廂源頭的說法,但當地的西廂故事傳說卻有著較高的傳播學研究價值。
關鍵詞:西廂故事 田野調查 傳播學
元雜劇《西廂記》作為中國古典戲劇的精品之作,歷來被學界所關注研究。其研究角度在文本分析、藝術鑒賞的基礎上,于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側重點:20世紀60年代,王季思、陳中凡先生曾就《西廂記》的作者問題進行激烈爭辯;七八十年代,蔣星煜先生針對《西廂記》的版本問題展開了深入探究;進入21世紀,受傳播學等鄰近學科影響,伏滌修、趙春寧等老師又從《西廂記》的傳播、接受角度進行探討。總結前人成果,不難發現《西廂記》的研究角度,正逐步從針對劇本本身的研究,而轉變為整體西廂故事流變的研究。這其中既牽涉到《西廂記》不同時期的版本,又涉及西廂故事的傳播與接受。豫西北作為元雜劇曾廣為流傳的地區,出土過大量戲曲文獻,對于探究戲曲原貌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其中在今河南省輝縣市褚丘村、洛陽偃師市石橋村,雜劇《西廂記》流傳情況尤為突出,群眾普遍認為當地應是西廂故事的源頭所在。
河南省輝縣市褚丘村西廂故事概說
輝縣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歷史悠久,遠古時期曾為共工氏部族居住地,明洪武元年后隸屬河南省布政使司衛輝府,《西廂記》廣為流傳的褚丘村位于輝縣市西。村北部有一普救寺,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褚丘萬柏山上,占地百余畝。然其初始位置實在村西,新中國成立后村民才把寺址搬遷至此。該寺始建年代不詳,但寺中碑文記載明嘉靖年間曾大規模修繕,因此寺史應較為久遠。當地群眾普遍認為這里應是《西廂記》的故事發源地:首先,普救寺的存在是一有力證據;其次,當地崔氏為一大姓,據族譜記載,唐時崔姓祖上也有人位居高官;再次,除普救寺外,當地還有白馬將軍碑,村東一公里上官莊村有鶯鶯墳,上八里鎮有李虎寨、炮臺嶺這些和《西廂記》有關的歷史遺跡;此外,村中有不唱西廂戲、女孩取名不叫鶯鶯等各種風俗。據當地群眾講述,當地西廂故事原貌是張生旅途中寄宿普救寺,與回歸故里的相國之女崔鶯鶯相遇。褚丘有一賊人名叫李虎,整日燒殺搶掠,當地因此有著“山西怕馬五,河南怕李虎”的傳言。李虎欲搶崔鶯鶯做壓寨夫人。張生見此情狀,喚來在附近駐扎的好友白馬將軍杜確,后者率兵解了普救寺之圍。其間二人雖早已私訂終身,并都希望老夫人能夠成全,但老夫人仍舊逼迫張生進京趕考,以拆散他們。張生第一年未能中舉,遂留在長安以備來年再考,其間娶妻生子;鶯鶯也因無張生半點音信,嫁給了鄭恒。
河南省偃師市石橋村西廂故事概說
cd036f811b83c3a79cbe153747fcb8ffbc7389e3eec3314cb93dad3ab2e13c9c 偃師位于古都洛陽東,伊河、洛河在此交匯,遠古時期孕育了二里頭文化,商都時期造就了“西亳”文明,同時這里也是文明使者玄奘的故里。戲曲方面,出土了宋丁都賽戲曲磚雕,刻畫的雜劇藝人丁都賽是我國戲曲史上迄今為止發現的第一位有形象傳世的女藝人;并且這里是豫劇豫西調、河南曲劇的發祥地,可謂戲曲資源極其豐富。石橋村位于偃師市西,古屬首陽驛,毗鄰洛陽,村因石橋得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偃師縣志》記載該橋:“□志在治西二十里,今石橋鎮西,故洛陽城東。《迦藍》記魏都城建春門一里余至東石橋;又云,石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靖四年,馬□造橋南節中朝牛馬市。”①與褚丘村相同,石橋村同樣有一普救寺,但比前者規模更為宏大,山門、天王殿、大佛殿、登天臺等佛教建筑十分齊全。寺中石碑數十通,詳細記載了寺廟的興衰過程。現存最早碑為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9年)立,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續河南通志》載普救寺:“偃師石橋保,孝昌三年(528年)張欽建。”②調查期間,當地提供了幾份證據:首先《西廂記》的源頭唐傳奇《鶯鶯傳》作者元稹,曾長時間生活在洛陽,十分熟悉這里的人文地貌;其次,當地有鶯鶯冢、和尚冢(據傳為張生冢)、紅娘墳,以及《西廂記》中提到的草橋等遺跡;尤為重要的是,在筆者調查過程中發現一通名為《大唐崔鶯鶯之墓》的墓碑,碑中記載:“崔氏鶯,東都□里人,父諱暟安公,鶯名□,善綴文□,絕匹之姿,不顧尊貴之門,圣貞專,縊死于草橋下,享□有七□。唐貞□□□年□□□立。”③當地流傳的西廂故事是張生與相國之女鶯鶯在此一見鐘情后私訂終身,但崔家素有不嫁白衣女婿之規,故張生不得不進京趕考。其間鶯鶯卻被老夫人逼婚,出于對張生的忠貞,她自縊于草橋下;紅娘也為免遭賊人凌辱,隨小姐而去。張生中舉歸來準備迎娶鶯鶯,然面對此情此景,遂決定出家為僧,死后被僧侶葬在鶯鶯冢旁。
比較兩地西廂故事原貌,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有以下幾個共同點:首先,故事主人公均為張生與崔鶯鶯,而并非學界普遍認為的元稹(崔鶯鶯原型爭議較大,在此不再論述)。同時,傳說的故事情節也相對比較完整。其次,普救寺不約而同地成為兩地西廂故事共同的物質載體,故事緊緊圍繞普救寺展開。再次,兩地都有和《西廂記》而非《鶯鶯傳》相近的歷史遺跡,如草橋、白馬將軍碑等。最后,兩地的西廂故事結尾,無論與《鶯鶯傳》還是《西廂記》都存在較大差距。
兩地西廂故事文化圈的構建
我們判斷兩地究竟是不是西廂故事源頭所在時,決不能孤立地看待所提證據。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輝縣褚丘村、偃師石橋村周邊地區,曾經出土過兩塊疑似與《西廂記》人物有關的墓碑。一塊是褚丘村東北六十公里鶴壁出土的唐秦貫所書《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④(以下簡稱《鄭崔合祔墓志銘》),另一塊則為石橋村西北十余里洛陽出土的《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崔公(暟)墓志》⑤(以下簡稱《崔暟墓志》)。
唐人秦貫所撰的《鄭崔合祔墓志銘》金元時期不曾記載,然明清之際卻在河南內黃、汲縣(今衛輝市)、鶴壁浚縣等地頻繁發掘,對于文中所載的鄭恒、博陵崔氏是否與《鶯鶯傳》中的鄭恒和鶯鶯存在關系歷來爭論不休。據伏滌修先生考證該墓志銘是唐人秦貫所書應不存疑,但由于在不同地區都有發掘,故其中應有偽造。因此鶴壁《鄭崔合祔墓志銘》是否可靠,還有待于進一步挖掘新的材料。此外,根據伏滌修先生的觀點,即使鶴壁出土的《鄭崔合祔墓志銘》為真,也不能證明碑文所載的鄭恒、博陵崔氏與褚丘村的西廂故事中人物有密切關系。⑥上文已有提及,褚丘東的上官莊村有一鶯鶯墳。既然鄭恒與崔鶯鶯是合葬,那為何存在兩人墓地相距100余里的情況,這顯然不合情理。但是,無論上述兩地有無關系,西廂故事在此地區曾廣泛流傳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甚至能夠以此勾勒出豫北地區西廂故事的大致傳播文化圈:應當就是今天的河南輝縣周邊地區。同時根據筆者調查,早年輝縣地方戲曲活動并不豐富,故人們接受《西廂記》的唯一方式應是雜劇演出。所以這個傳播范圍也應當就是元雜劇《西廂記》的流傳范圍。
《崔暟墓志》與其妻《王媛墓志》在上世紀20年代一同發掘,為潁陽徐珙所書,此二碑曾作為研究隋唐時期的儒釋道思想而為人關注。《全唐文》等史料中對崔暟記載不多,但其子崔沔曾為禮部侍郎,其孫崔佑甫曾加朝散大夫。《崔暟墓志》載崔暟卒于神龍元年(705年),享年74歲,應生于貞觀五年(631年);其妻王媛卒于開元九年(715年),享年74歲,故生于貞觀十五年(641年),碑中記載王媛13歲時嫁給崔暟。偃師石橋村出土的《大唐崔鶯鶯之墓》寫崔鶯鶯17歲自縊于草橋下,但落款為唐貞□。假如鶯鶯是貞觀時期人,以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最后一年為亡期倒推17年,為貞觀六年(632年),崔暟在一歲時生下鶯鶯顯然不合情理;又假如鶯鶯生活在貞元時期,在貞元元年(785年)卒,則崔暟在死后63年生下鶯鶯,也不合理。故此碑存在較大硬傷,有后人附會、偽造之嫌疑,或者碑中所載“崔暟”與《崔暟墓志》中所載“崔暟”并非一人。所以,《大唐崔鶯鶯之墓》中所載“崔暟”與《崔暟墓志》中的“崔暟”一種可能是沒有關系,二者只是名字上的巧合;另外一種是后人借崔暟偽造崔鶯鶯身世,但卻犯了低級錯誤。不過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兩種“可能”最終都造成了一個共同結果,使得石橋西廂故事源頭說惟妙惟肖,并形成了又一個西廂故事傳播圈。
綜上所述,輝縣、偃師兩地歷史上的確存在西廂故事的廣泛傳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西廂故事文化圈,并且支撐著兩地的西廂故事源頭說。
褚丘石橋西廂故事源頭辨偽
王實甫元雜劇《西廂記》的源頭,學界基本認為應是中唐作家元稹以自己為原型所撰寫的唐傳奇《鶯鶯傳》。據《鶯鶯傳》描寫,故事發生地為河中府蒲州,張生游玩至此,在普救寺巧遇路過于此欲回長安的前朝相國遺孀崔氏母女。崔張雖有過一段熱戀,但最終卻以始亂終棄的悲劇收場。后來又經過宋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改編,到金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二人愛情才以大團圓收場。到了元代,王實甫又極大地豐富了故事情節,才使《西廂記》成為元雜劇的經典劇目。因此西廂故事的完整情節并非在開始的《鶯鶯傳》中就已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變化過程。因此,我們研究西廂故事原貌,探究西廂故事源頭,就必須從元稹生平切入,從唐傳奇《鶯鶯傳》著手。
元稹生于大歷十三年(778年),卒于大和五年(831年),撰寫《鶯鶯傳》時大概為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早年主要生活在長安、河南府、河中府等地,故其不可能來到位于衛輝府的褚丘,僅此一條就可否定褚丘村不可能是西廂故事源頭。然偃師緊挨洛陽,有沒有可能元稹年輕時聽說張生、崔鶯鶯的故事,而后自身經過文學創作而進行改編?這種可能不能說一定沒有,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元稹為張生的原型歷來是學界無可爭議的事實。鑒于《鶯鶯傳》中張生的經歷與元稹有著驚人的相似,因此張生、崔鶯鶯應還是文學作品中的兩個人物形象,而并非現實生活中的人。故當兩地不約而同地把故事主人指向小說人物張生、崔鶯鶯時,就顯得十分突兀了。此外,針對兩地的西廂故事與唐傳奇《鶯鶯傳》的內容進行對比,我們也發現存在著較大出入,但它們與元雜劇《西廂記》故事情節卻較為接近。例如在《鶯鶯傳》中,是沒有《西廂記》中的“白馬將軍解叛軍之圍”的劇情,也沒有“草橋驚夢”這一出。然而在褚丘村卻出現了白馬將軍廟,偃師石橋也出現了草橋等遺跡,這不得不令人懷疑事情的原委。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重視,為什么出現了兩地西廂故事結尾,與《鶯鶯傳》、《西廂記》都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筆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方面,起基礎性作用的是下層民眾對西廂故事的審美傾向:《鶯鶯傳》始亂終棄的結尾遭到民眾唾棄,因此石橋村的西廂故事結尾就傾向于二人對忠貞愛情的維護,最終他們都為情而死;張生與崔鶯鶯追求自由愛情雖本無可厚非,但在封建社會二人的私自茍合也是社會所不容。因此,褚丘村的西廂故事改變《西廂記》崔張結合的結尾,使鶯鶯與鄭恒結婚,這樣的結果更合乎倫理法度。另一方面,兩地區客觀上不得不依靠為數不多的“素材”進行故事拼湊。兩方面原因共同導致了一個“四不像”的故事結果。
結合褚丘、石橋兩地的出土文獻,以及元稹生平、《鶯鶯傳》,我們基本可以判斷兩地不應是《西廂記》的原始發生地,而應是《西廂記》在傳播過程中后人的附會形成。兩地“西廂故事源頭說”是在雙方都擁有普救寺,這一承載唐傳奇《鶯鶯傳》與元雜劇《西廂記》的實體的基礎上,把本地素材同與之有可能相關的材料進行拼湊而杜撰形成。經過論證,兩地雖然都不是西廂故事源頭所在,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證實了元雜劇《西廂記》的廣泛影響力。正所謂:“舊雜劇,新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⑦
西廂故事的傳播學思考
西廂故事在近一千年的傳播過程中,隨著作品的不斷豐富與完善,傳播過程體現出一種由上而下的層次性、由點及面的推廣性。首先,作者元稹一生仕途順利,生活放蕩不羈,經常游走于燈紅酒綠之中。在《鶯鶯傳》中,他擬定的作品接受對象就是和他一樣生活在社會上層,喜好玩弄感情的文人士大夫。因此,當元稹在作品中污蔑鶯鶯為“尤物”,感慨“女人是禍水”,并對自己“善補過”進行褒獎時,上層社會對此也基本“認可”。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鶯鶯傳》的傳播影響范圍,因為廣大民眾對于這種行為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傳播也受到了交通、自然條件的限制。發展到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作者第一次采用大團圓結尾,改變了作品“始亂終棄”的結果,使崔張愛情最終修成正果,這就迎合了廣大群眾的審美趣味。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相比《鶯鶯傳》的純文學作品,諸宮調作為一種講唱文學形式,它直接面對廣大市民。民眾通過聲情并茂的“新型傳媒”方式來欣賞作品,這就形成了西廂故事的第一次大規模傳播。緊接著王實甫把西廂故事搬上戲劇舞臺,成為經久不衰的常演劇目。到此完成了西廂故事由上流社會至下層百姓的傳播過程。但元雜劇的影響范圍終究有限,僅限于現在的河南、山西等地,這就局限了西廂故事在面上的傳播。隨著明清時期南戲、傳奇的興起,李日華、陸采等人編寫《南西廂》,使這一經典以嶄新面貌呈現在長江以南地區,完成了西廂故事的最后推廣。(基金項目: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項目“中原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生態研究”,項目編號:2009-ZD-009;國家級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基金項目“豫西北戲曲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調查與保護對策研究”,項目編號:091047609)
注釋:
①湯毓倬、孫星衍纂修:《偃師縣志》,清乾隆五十四年影印本,卷二,地理志下,第7頁。
②阿思哈纂修:《續河南通志》,清乾隆三十二年影印本,卷十七,寺觀,第18頁。
③該碑文拓片現保存于河南洛陽偃師祁永安先生處,碑文不清處用□代替。
④周紹良:《全唐文新編》,第四部,第二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531頁。
⑤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2~1803頁。
⑥伏滌修:《秦貫撰〈鄭崔合祔墓志銘〉真偽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4)。
⑦李漢秋、朱世滋、金寧芬主編:《古典詩歌精華·歷代名曲千首》(上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頁。
(作者單位:梁帥,河南大學河南地方戲研究所;馬亞超,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