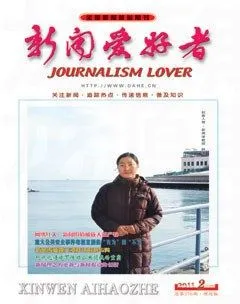媒介迷思
摘要:媒介迷思在每一種新媒介誕生初期都會出現,常表現為兩種認知取向:烏托邦式的樂觀認識與批判性的悲觀認識,內容主要集中在對歷史、空間以及政治的終結等相關論題的探討上。如何理解這種具有歷史循環性的媒介迷思化建構,如何正確對待這種媒介迷思現象呢?這便成為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關鍵詞:迷思 媒介迷思
從媒介發展史上看,每一種新媒介的誕生,同時也伴隨著對其烏托邦認識與批判性認識的相互交織。然而,隨著這種新媒介的日漸成型、普及,這些蘊涵著傾向性色彩的迷霧漸漸消退,媒介的實際特性以及用途的關注日益明顯,如互聯網研究也經歷了三個階段:誕生時的烏托邦批判、用途研究和網絡代表的新的社會邏輯引發的社會學思考。①不難發現,這些對媒介烏托邦或批判的認識是一種迷思(Myth,即神話)化的建構,是媒介與其發展的歷史相割裂、與所處社會相孤立的產物。然而,這種迷思化建構在每種新媒介誕生時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現,這種現象的反復出現不得不讓人們發出這樣的疑問:何為媒介迷思?如何看待這種媒介的迷思?
媒介迷思
圣·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描述了上帝和人交流的場景,給當下傳播帶來了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想象出一個不在場的實體,讓一個在時間、空間和程度上相距遙遠的受眾覺得,這個實體存在是真實可信的。②而媒介的發展也正是沿著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而不斷地發展,技術(媒介)幫助我們跨越、克服因缺席出現的不足,通過使缺場可視化,讓其成為符號性的在場,技術媒介變成在場的技術。新媒介這種對時空結構的影響將最終延伸到對社會的影響上,新媒介技術的產生會形成新的空間和新的時間,新的時間與空間將形成全新的社會形態。法國學者埃里克·麥格雷更進一步指出,這些對媒介的言論“應許一個以互動為基礎的透明的未來,相信更優良的技術(民調、影像、計算機)將庇護眾生免受誤解之苦,這實際上是理性主義焦慮的補充,其源頭也在啟蒙精神:社會信息化之所以被推崇,是因為它被看做是知識革命、個體自主的同義詞,因此也就是回到了更負責、更開放的契約社會(但是并不大眾化)。”③另外,對新媒介的產生與社會道德敗壞之間存在種種關系的認識,總是與媒介認識的樂觀論調相伴而生的。從媒介的發展歷史來看,“每一種抵制新型傳播媒介的危險的運動,總是能夠找到理由,認為其斗爭對象是特別危險的。19世紀,廉價驚險小說是特別腐朽的,因為它們是讀者唯一能夠買得起的文學作品。20世紀初,電影有了大熒幕,也帶來了‘威脅道德的黑暗’。連環畫報可以在私下里‘聚精會神地閱讀’幾個小時。電視特別有害,因為人們可以在自己家里輕松地觀看。現在,錄像帶有嚴重的危險,因為孩子們也會控制如何觀看。”④這種對新媒介的刻板認識,形成了一種對媒介持悲觀論調的傳統,“有一個明顯的循環,伴隨著新媒介的引入產生的道德危機,總是與人們怕上癮的恐懼聯系在一起的。”⑤而且,每一種新媒體的問世,每一項信息傳輸新技術的誕生,都會引發恐懼和擔憂。⑥
迷思。迷思(Myth),也即神話。羅蘭·巴特從意義構成的角度分析神話,認為:“神話是一個奇特的系統,它從一個比它早存在的符號學鏈上被建構:它是一個第二秩序的符號學系統,那是在第一系統中的一個符號(也就是一個概念和一個意象相連的整體),在第二系統中變成一個能指。”⑦“迷思”作為一種意義的建構,意指符號本身最為直觀的意義被當做另一種符號的能指,將意指符號重新語境化,這個過程賦予了所意指符號全新的意義,于是新意義的生成便帶有了意識形態的色彩。在談及迷思的作用時,羅蘭·巴特并沒有完全否認“迷思”的作用,他指出:“迷思沒有否認什么事物,相反,它的功能是要談論這些事物。簡單地說,它使之凈化,使他們變得清白無辜,賦予它們一種自然的和永恒的正當性,一種不是源自解釋而是事實陳述的明確性。”⑧
“迷思”是一種純粹虛構性的敘事,通常涉及超自然的人物、行動或事件,體現了一些與自然或歷史現象有關的流行觀念。對“迷思”的批判有助于打亂和顛覆傳統的頑固意義和常識的沉淀物,因為“迷思”本身就是一種使對象自然化的過程;“迷思”也能夠排除政治,能夠將話語去政治化,話語借助貌似客觀敘事的形式,傳達著含有意識形態的內容,羅蘭·巴特等人對意義建構的分析,對迷思的解惑,將使人獲得對這種話語權利的認識,有助于打開通向修復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門。
媒介迷思。媒介迷思,意指基于對媒介基本功能的認識,而又超越這種現象層次的認識,形成一種與特定的認知傾向或意識形態相聯系的取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認為新媒介能夠跨越時間、空間以及社會屬性之間的區隔,形成自由、開放、平等而又充滿希望的新社會;二是認為新媒介強化了社會固有的不平等性,將帶來社會秩序的紊亂,并常常把道德敗壞與新媒介的產生相關聯。
媒介迷思有助于對媒介社會的認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媒介迷思也使得人們對媒介的效果產生片面的認識,或一味地批判新媒介將給社會帶來道德的紊亂,或認為新媒介是未來希望的代名詞。而導致媒介迷思存在片面性的原因在于:缺乏將媒介與社會相聯系的考量;缺乏將媒介放置于歷史的大背景中做長時段的分析。法國學者埃里克·麥格雷雖沒有具體論及媒介迷思這一問題,但其對傳播的結構性想象的剖析,給人們進一步認識媒介迷思以有益的啟發,他指出:“關于傳播的結構性想象隨處可見,不是盲目樂觀,就是太過于悲觀,其根源在于有數千年歷史。隨啟蒙而再度勃興的理性與技術的對立,也在于19世紀隨著民主發展而誕生的‘大眾’所遭遇的污名化。”⑨在媒介研究領域,這種技術與理性的對立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認為媒介(技術)的發展是對人文精神的侵蝕,如尼爾·波茲曼認為,電視媒介不僅導致了童年的消逝,也使美國的歷史、政治、新聞甚至宗教帶有娛樂化的傾向,并認為電視媒介是對民主社會基石——理性的侵蝕。政治意識在質量上的降格(從邏輯判斷轉向審美判斷,以直觀感覺代替延遲的理性),代表了新媒介偏向和舊媒介偏見之間的矛盾沖突,如喬治·康茨認為,電子媒介已經廢除了《人權法案》。⑩其二,認為技術的發展將促進人類理性的全面實現,理性的潛力借助技術這一工具將得到進一步彰顯,如保羅·來文森認為技術是處于理性與實踐之間的中介環境,作為一種認知性技術的媒介將使人更容易認識世界。所以,媒介迷思既體現著對技術與理性之間相互關系的偏頗性認識,也體現著將導致社會眾多積極或消極現象的原因解釋為脫離具體歷史與現實的媒介作用的結果。
媒介迷思的傳統。媒介迷思,在每一種新媒介產生之時都會呈現,而且有著相類似的表達、相類似的生成機制。文森特·莫斯可在論述媒介迷思這種循環性時,指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有線電視在把人們聯合起來方面具有其他技術所無法比擬的潛力。它將帶來無所不在的雙向溝通,并有可能開創一個由電子民主控制的連線的社會。……令人驚訝的是,多年來有關新技術的各種預言的變化是如此之小。正如人們曾經開啟了電報時代、電力時代、電話時代、廣播時代一樣,如今人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電腦的時代。”
媒介迷思的傳統,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其一,主導媒介形成的媒介文化形態上,美國環境學派的眾多學者,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考察媒介的發展,并認為媒介是文化、社會以及歷史等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而且,在對各種媒介文化之間變遷的認識著迷思化的表述,根源在于這樣一種媒介認識論:新媒介的出現不僅改變了既有的認知模式、感知形式,也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于是,媒介環境學派便對新媒介、新媒介文化的認識有了迷思的傾向。其二,具體媒介的發展史上,每次新媒介的出現,歷史上都會出現對這種媒介迷思的表述,如電報。在電報剛剛問世不久,1849年,文學家維多克·雨果對其帶來的驚人效果寫道:“人們是怎樣接觸的呀!他們間的距離是多么靠近呀!靠近,這是兄弟般博愛的開始……不過多久,人們就會像荷馬描寫的諸神一樣游逛于地球之上。再過幾年,和諧的電報將環繞擁抱世界。”
媒介迷思的表現
對嶄新世界的預言,常常是建立于各種終結論的假設之上的,“每一次包括信息和傳播媒介在內的新技術浪潮,都會帶來關于終結的預言。……關于技術的確存在著一種引人注目的,幾乎是有意的歷史健忘癥,尤其與傳播和信息技術相關的時候更是如此。”這些終結的預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終結。歷史終結的迷思宣布,我們與時間的關系發生了轉變,它斷然結束了我們關于歷史消逝的傳統經驗,并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用加拿大學者伊尼斯的話來說,隨著偏向空間傳播的電子媒介的發展,人們更多地關注共時性信息,而偏向時間的歷史經驗將逐漸萎縮,如電報的出現最初被形容為“偉大的時間和空間的消滅者”,因為電報的出現改變了人以及借助于自然或物理工具所傳遞信息的速度,人的經驗構成將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遠距離事件的影響,這種全球化的意識將成為人們經驗組成的新成分。但是,尼爾·波茲曼在論述電視媒介對“歷史”的影響時,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我們不是拒絕記憶,也沒有認為歷史不值得記憶,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們已經被改造得不會記憶了。”
地理的終結。伊索爾·索勒·普爾用“自由的技術”來表示現代技術,因為技術具有跨越地理邊界的能量,這種表述同樣適合于媒介技術。媒介跨越空間距離的特性,使身處世界各地的人們有種相聚一堂的感覺,很容易滋生地理距離終結的迷思。地理終結的迷思認為,我們與空間和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種迷思日趨流行,因為信息電子化、數字化的發展,當下的媒介一步步實現了一場超越空間障礙的革命,在歷史上這種障礙曾經限制了信息的流動,從而終結了地理。然而,“地理的終結不只是意味著疆界的變化,它同時也指的是空間在組織內部,尤其是在商業公司內部的消亡。但對迷思而言,還遠不止于這些疆域性和結構性的轉變。距離的消亡也包含了社會空間,即那些標著社會分野的邊界的滅絕,在歷史上,正是這些分野把世界上的人們分割開來。”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隨著網絡的普及,不僅消除了人們在地理上的距離障礙,更重要的是將使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種種限制性的關系得到消除,這將改變社會組織的形態和結構,形成一種嶄新的網絡社會。
政治的終結。在新的通信基礎設施的支持下,政治終結的迷思創造出新型的公民和新型的社會關系。同時,它也播下了自己不朽的種子,進一步把自己確立為唯一合法的交易方式。在報紙出現初期,被人認為是觀點自由碰撞、交流的公共場所,是保障自由言論與真理實現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維系民主、自由的重要形式。這種對民主、自由向往的愿望,在電話誕生時也曾出現,認為電話雙向交流的特性能夠改變傳播的非均衡現狀,而這種話語表達機會的獲取將大大提高人們民主參與的可能。對這種關于政治將終結的觀點,阿爾溫·托夫勒表達了自己相反的意見,他認為:“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和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人的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達到權力和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
具體就網絡媒介而言,因為信息技術誘導著我們的思想,使我們認為能夠從信息的維度看待一切事物,并且最終把信息作為這個世界的建構基礎來分析,而網絡媒介在互聯網中進一步放大了信息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將信息傳達到網絡所能觸及的各個領域、各個地方。
對媒介迷思的思考
針對當下有關各種媒介決定論的論點,如網絡社會,法國學者埃里克·麥格雷剖析了這一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強調:“它是社會進程融入自身的構建物,它使社會進程得以發生并決定其效率,而社會科學一直借口技術不能被歸入人的范疇,因而無視技術。這種分割一度是必要的,但它引起了對客體的現實及其現實的秩序的誤解,將技術的‘內在’益處理想化,或盲目批評,批評技術‘本性上的’異常。”麥格雷不僅分析了這種如本文所認為的媒介迷思的現象及其原因,而且還進一步要求,要回歸客體,就必須從關于客體的互動(而不是客體的影響)的民主視角出發,而不是簡單地研究某個未經加工或隱蔽的自然。
此外,人們往往沉浸在對媒介巨大社會影響的關注上,以致將這種對媒介迷思化的認識作為媒介自身的本屬特性,否認了媒介自身發展變化的事實,割裂了媒介與社會的聯系,然而有學者指出,新技術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出現在它們的迷思性階段,即當它們因為能夠帶來世界和平、社區復興,或者終結貧乏、歷史、地理或政治而受到熱情歡呼的時候;相反,當技術變得稀松平常的時候——真正地(例如,電力)或者象征性地成為尋常之物,它們的社會影響力卻達到了頂峰。赫爾曼·鮑辛格爾也指出:“對媒介有種非理性的不信任——在所謂‘新’媒介引發的爭論中,伴隨著許多雄辯的批評論據,這種不信任肯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他指出,媒介也帶來權力解放的可能,如遙控器可以迅速切換頻道等,但是鮑辛格爾卻認為,這只是我們看到的人與技術(媒介)關系的表象,重要的是要關注“這些和技術交往的方式凸顯出的日常生活過程的真正本質:自然化”。所以,我們應將注意力放在媒介去迷思后的實際影響上,而非一味地徘徊于媒介迷思的爭論之中;而且,應該以一種歷史的眼光正確地對待這種帶有循環性的媒介迷思現象。
對媒介迷思的認識,不僅使我們能正確對待各種對新媒介產生后出現的種種預言般的表述,厘清各種關于媒介迷思背后的邏輯,也可以使我們在面對將來的過程中理性地看待各種新媒介,這也是本文的追求所在。
注 釋:
①③⑨埃里克·麥格雷[法]著,劉芳譯:《傳播學理論——一種社會學的視角》,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頁,第6頁,第3頁。
②彼德斯[美]著,何道寬譯:《交流的無奈》,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頁。
④戴維·巴勒特[英]著,趙伯英等譯:《媒介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19頁。
⑤羅杰·西爾弗斯通[英]著,陶慶梅譯:《電視與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
⑥門羅·E·普萊斯[美]著,麻爭旗譯:《媒介主權——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對國家權力的挑戰》,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
⑦羅蘭·巴爾特[法]著,許薔薔等譯:《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頁。
⑧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The Noonday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