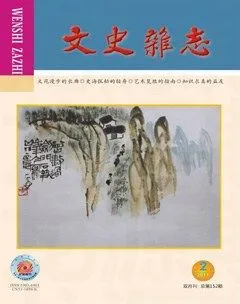《中國文學》的歷史與文化價值
2011-12-29 00:00:00何琳趙新宇
文史雜志 2011年2期


中國譯介活動源遠流長。晚清以降,中國譯介活動經歷兩次主潮:一是在“五四運動”前后,一是“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與這兩次主潮中,中國作家、翻譯家迻譯大量國外文學著作,即所謂“拿來主義”相較,中國優秀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在同時期向國外讀者的譯介,即所謂“送去主義”,無論從質、量,還是從影響力上,均難望前者項背。從這個意義講,中國與國外雙邊或多邊文學文化交流活動多有失衡。如果說,20世紀中國譯介活動的兩次主潮均出現“外譯中”的一邊倒局面,有其特定歷史條件下深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動因,尚可理解;那么,時值21世紀初,中國在與世界日益頻繁的雙邊、多邊文學、文化交往互動中,這種不對稱的境況仍未得到顯著改觀,則頗發人深省。
《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大陸(香港有《譯叢》RENDITIONS)唯一主要面向國外讀者,及時、系統地翻譯、介紹新中國文學(兼及中國古典文學與其它藝術形式、文藝動態)的多語種(英、法語版,國內、國外均有發行)國家級刊物。《中國文學》自1951年創刊,于2001年停刊,歷經新中國50年滄桑,為初步扭轉上述失衡現象做出了卓越貢獻。本文在梳理、回顧《中國文學》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基礎上,指出其主要在翻譯實績、促動跨文化交流和積累辦刊經驗三方面的重要歷史貢獻,并陳明其在中國翻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獨特的文化價值,以期對《中國文學》展開深入而系統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之用。
一、《中國文學》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
l.創刊與成長期(1951年一1965年)
1951年10月,由時任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局長、著名劇作家洪深倡議,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支持下,由剛從英倫歸國的知名作家、翻譯家葉君健負責具體籌辦,翻譯家楊憲益及夫人戴乃迭(Gladys),和美國友人沙博理(SidneyShapiro)一道參與,創辦《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第一期。刊物裝幀和版式模仿《蘇聯文學》[1]。
《中國文學》起初由中國文學雜志社出版,外文局是其主管單位;后中國文學出版社成立,統歸出版社負責。其刊名雖為《中國文學》,但實含文學和藝術(刊內還有古今繪畫等)兩部分,又以文學為主。文學部分既譯介中國現、當代優秀文學作品,亦譯載自《詩經》以來的古代作品,其中尤以當代作品為主;此外亦刊載選自國內報刊和書籍的文藝評論和文藝短訊,顯透著時代氣息。
《中國文學》從創刊到1953年,為不定期出版。1954年,《中國文學》改為季刊出版。時任中國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茅盾出任主編,葉君健為執行編輯。1958年,中國作協派何路與葉君健一道經辦《中國文學》,在業務上形成外文局和作協對《中國文學》的共同領導。同年,《中國文學》改為雙月刊,次年改為月刊。1964年首次推出《中國文學》法文版(季刊)。此間,楊憲益、戴乃迭、沙博理、唐笙、喻璠琴等為主要譯者,翻譯選材以新中國成立前北方解放區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為主。
2.波折與停滯期(1966年-1979年)
“文革”期間,茅盾、葉君健、楊憲益被迫離開中國文學出版社。此間,《中國文學》雖在運轉,但已成為那個時代的“傳聲筒”,主要依靠毛澤東詩詞、魯迅文章、革命回憶錄、樣板戲和以大寨、大慶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以及個別小說,如《艷陽天》,個別電影劇本,如《小兵張嘎》得以維持。同時,也刊載了諸多荒唐文章。“譬如在著名作家老舍蒙冤去世不久,便刊登了批判老舍諷刺小說《貓城記》的文章;又如把中國古代作家分為儒家和法家,以反映反動和進步;再如攻訐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扭曲作者原意等等。”[2]《中國文學》這個當時唯一的對外文學、文化傳播窗口雖存,但受到“文革”極“左”思潮的嚴重損害,其發展停滯不前。
3.繁榮發展與成熟期(1979年-2001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20世紀中國文學譯介史上第二次高潮。從極左思潮中擺脫出來的中國讀者強烈渴望重見世界文學殿堂。十年“文革”中備受摧殘的中國翻譯工作者更是滿懷熱忱地投入到自己熱愛的翻譯事業中;加之文化政策上“雙百方針”的重新提出,從而為《中國文學》的復興創造了契機。
1979年茅盾出任《中國文學》新編輯委員會主編,直至1981年3月去世。1981年至1987年楊憲益歷任《中國文學》執行主編、主編和顧問。在任期間,他對《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均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國文學》面貌為之一新。除了恢復適量選擇現代和古代的優秀作品外,《中國文學》主要譯載反映新時期中國人民真實心聲的文學作品,尤其重視呈現中國新時期普通人生活和命運的變化,力圖展現新時期中國文壇藝術手法、創作樣式等多方面的創新。此間,《中國文學》法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于1982年、1984年由月刊改季刊。此外,1981年,在楊憲益倡議下,還出版了“熊貓”(Panda)叢書,主要用英、法兩種文字推出中國當代、現代和古代的優秀作品,也推出過少量的德、日等文版。“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進入了黃金時期,達到了頂峰,英、法兩個文版的總印數在6萬份以上。”[3]
楊憲益卸任后,王蒙、賀敬之、唐家龍、凌原先后主持《中國文學》工作。《中國文學》緊扣新時代脈搏,力圖呈現中國當代文壇的主脈。20世紀末,《中國文學》的發行量從數萬冊銳減到3000冊左右。[4]為了扭轉被動局面,《中國文學》于2000年第6期全面改版,由英文版改為中英對照版。新版推出后,各方反響較好。盡管如此,由于種種原因,《中國文學》還是于2001年年初停刊。
二、《中國文學》的貢獻
1.譯介實績輝煌
50年間,中國文學出版社共出版了《中國文學》雜志近400期(英文版),“熊貓”叢書近200種,迻譯文學作品3200余篇,介紹不同時代作家、藝術家2000余人次。
此間譯介主要代表作家包括:屈原、陶淵明、謝脁、張若虛、杜甫、李白、王維、裴鉶、蘇軾、歸有光、袁枚、袁宏道、李汝珍、蒲松齡、曹雪芹、劉鶚、魯迅、李劼人、茅盾、巴金、老舍、冰心、葉圣陶、沈從文、丁玲、郁達夫、吳組緗、戴望舒、李廣田、聞一多、艾青、艾蕪、孫犁、蕭紅、蕭乾、施蟄存、馬烽、葉君健、趙樹理、劉紹棠、茹志娟、陸文夫、王蒙、瑪拉沁夫、蔣子龍、諶容、宗璞、張賢亮、張承志、梁曉聲、鄧友梅、古華、汪曾祺、高曉聲、王安憶、馮驥才、賈平凹、張潔、韓少功、霍達、方方、池莉、凌力、鐵凝、劉恒、舒婷、犁青、益希丹增、扎西達娃、劉震云、程乃姍、聶鑫森、陳建功、航鷹、周大新、阿成、林希、劉醒龍、史鐵生、余秋雨、馬麗華等。
譯介作品中,特別值得一書的,首先是由楊憲益、戴乃迭自辦刊之初便陸續譯出的《魯迅選集》(4卷),和同樣是他們夫婦合譯的《紅樓夢》(Dreamof the Red Chamber)節選(見《中國文學》1964年No.6、No.7、No.8)。以此為契機,英譯《紅樓夢》(3卷)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引起中外轟動。其次,便是由沙博理譯《水滸》(1959年No.12,譯名為Outlaws of the Marshes,1963年No.10譯名改為Heroes of the Marshes)節選。1981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獲得授權,出版《水滸》全譯本(2卷),引發海外漢學界廣泛好評。
2.促動跨文化交流
《中國文學》作為溝通中外文學、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促動中外跨文化交流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是極大地激發和滿足了國外讀者閱讀、理解、體味中國文學、文化的訴求,使一個真實而富有時代感的中國得以呈現。其次是一批中外譯者集結在《中國文學》之下,相互切磋、相互砥礪、相互推動,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氛圍,進而保證了譯作境界的不斷攀升。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文學》發展黃金期,刊物行銷150多個國家和地區,遍布歐洲(如英國、芬蘭、法國、比利時、丹麥、德國、荷蘭、冰島、意大利、瑞士、瑞典等)、亞洲(如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以色列等)、非洲(如烏干達、蘇丹等)、南北美洲(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美國等)、大洋洲(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根據1986年統計,《中國文學》(英文版)在美國訂戶為1731戶,在芬蘭為1195戶,法文版僅巴黎訂戶便有1026戶。[5]
美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回顧自己研習漢語之路,曾提到中美“竹幕”緊閉時代,他所能讀到的中國文學英譯幾乎均出自楊、戴譯筆,而這些譯作絕大部分正是刊發于《中國文學》。《中國文學》選譯的新時期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沙狐》等20余篇小說被美國出版的《國際短篇小說選》選載,更有大量詩歌、寓言為泰國、印度、俄羅斯等國轉譯。在英美諸多知名大學圖書館,《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保存得相當齊全、完整。遍布世界的《中國文學》讀者關注著它的發展,同時他們也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著對它的關懷。“《中國文學》的最初刊頭,就是由一位德國讀者設計完成的。”[6]
1951年至1954年,楊憲益、戴乃迭和沙博理是《中國文學》僅有的三位譯者。此后,《中國文學》的中外譯者隊伍不斷壯大,林戊蓀、熊振儒、胡志揮、王明杰、燕漢生、劉方、唐家龍、章思英、陳海燕、張永昭等一批精通西文,更有良好中國文學修養的國內譯者,和Howard Goldblatt、W.J.Jenner、AlexYoung、DonJ.Cohn、Christopher Smith、Chad Phelan、Mark kruger、Simon Johnstone等母語為非漢語,兼有一定中國文學、文化修養的國外專家加盟《中國文學》。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因相同的志趣集結在《中國文學》周圍,相互研討切磋、互通有無、優勢互補,為《中國文學》穩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更為可靠的保證。當年諸多供職于《中國文學》的外國專家譬如詹納爾(W.J.Jenner)、白霞(Patricia Mirrlees)等,今日依然活躍在海外漢學界,為播揚中國文學、文化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3.積累重要辦刊經驗
《中國文學》作為專業雜志,在50年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諸多重要辦刊經驗,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文學》編輯部分工明確,工作流程組織科學、嚴謹。編輯部分中文部和外文部。前者主要負責選稿和組稿;后者又分為英文部和法文部,主要負責翻譯、文字潤色、核定、校對、打字等工作。兩個部門協力合作,一絲不茍。外國專家在改譯稿時,對一些生硬的語句進行潤色,使之符合國外讀者的閱讀習慣。
其次,翻譯選材豐富,凸顯鮮明的時代感和民族特色。除現、當代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節選、詩歌、散文、戲劇劇本外,《中國文學》對諸如民間寓言、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游記、回憶錄、電影劇本和中國傳統戲曲,諸如京劇、評劇以及各種地方戲、相聲等的譯介亦不遺余力。同時,大量中國作家、藝術家訪談、側記、印象和中國文學、文藝最新動態、訊息亦穿插其中。
第三,積極主動與國外讀者溝通,重視國外讀者反饋意見,重視讀者群的培養與擴大。《中國文學》欄目設置注重考慮國外讀者接受。譬如,在楊憲益任執行主編期間,《中國文學》增設“致讀者”(To Our Readers)一欄,主要包括:譯作簡介、欄目和版面更新變化說明等,以最大限度便捷外國讀者統覽全刊。
早在1955年,《中國文學》便設計了自己的讀者問卷調查,隨刊物一同發行。其間設計問題諸如:“您是否為長期訂戶?您為什么閱讀《中國文學》?是因為朋友推薦?是您見到了它的廣告宣傳?還是它對您工作有幫助?您注意到今年這期有什么新意了嗎?如果有,是哪些呢?您最喜歡本刊的哪些內容?不喜歡哪些內容?您對本刊插畫怎么看?”[7]此外,刊物還特別注明,對于訂戶周圍的朋友,只要他們對中國文學、藝術感興趣,都可獲贈一冊刊物。此后,《中國文學》經常做不定期讀者問卷調查,對進一步提升刊物水平與擴大受眾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中國文學》外文部還有專人負責通聯工作,閱讀大量讀者來信并及時復信,并將其中有價值的來信翻譯成中文,定期匯編成冊,呈交相關領導、編輯、譯者和作者等傳閱。這種良性互動,大大調動了《中國文學》編輯部各部門、各環節的工作熱情,為譯介質量和效果的不斷攀升,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三、《中國文學》的文化價值
以《中國文學》為研究對象,其獨特的文化價值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在漢籍外譯史、中外文學、文化交流史方面,其二是在翻譯批評和翻譯理論方面。
《中國文學》自新中國成立初期誕生,“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從創刊到停刊歷時50載,盡管它的身上留下種種歷史烙印,存在諸多缺憾,但其譯作整體,無論從數量、質量和海外影響力上,都達到了漢籍外譯史上新的高峰。毫無疑問,它是漢籍外譯史和中外文學、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全面、深入、系統地梳理、分析、評價《中國文學》在不同歷史階段諸方面發展狀況,考察其在不同歷史時期辦刊方略上的得失,無疑將對后來者起到極大的借鑒與啟示作用。
另一方面,以《中國文學》譯作為個案,諸多翻譯批評、翻譯理論均可有的放矢地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文學》已成為諸多翻譯理論和翻譯批評的“試金石”。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中國文學》歷經新中國建立之初、十年浩劫、新時期文藝轉型與建設,以及市場經濟沖擊下的20世紀后10年,是新中國文學翻譯、翻譯文學,以及對外文化交流傳播事業的直接參與者,故而從翻譯理論的文化研究視野出發,對《中國文學》在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形態、合作機制等方面展開研究,將進一步拓深和拓展我們對當前國際學術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的認知與理解。
《中國文學》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唯一主要面向國外讀者,譯介中國文學、文化的多語種刊物,向世界讀者提供了有別于新聞報道和一般宣傳材料的,深層次了解、感知中國社會面貌、觸摸中國普通人物情感世界的空間,為新中國漢籍外譯事業發展奠定了扎實、豐厚的基礎。它使中國新文學圖景翔實、生動地展示在國外讀者面前,為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語境做出了卓越貢獻,其意義與價值將是深遠而持久的。
注釋:
[1]《蘇聯文學》(SOVIET LITERATURE)是蘇聯作家協會出版月刊,有英、德、波蘭和西班牙語版。
[2]楊憲益:Thirty Years of“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