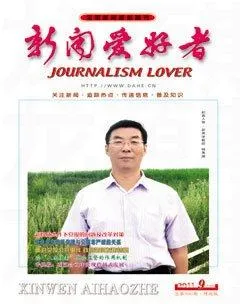兩性性靈詩說的“和而不同”
性靈詩說是清代四大詩說之一。現在學界大都從袁枚的詩學觀來認識性靈說的內涵、價值與意義。事實上,清代女性對性靈說也作出了一定貢獻,既有相通之處,也存在性別差異,應成為性靈詩說的一部分。所以,要客觀全
面識評性靈說,應從雙性視野出發。
兩性性靈詩說的同聲相應。袁枚“性靈”論一出,“從游者若鶩若蟻”①,形成“袁枚現象”②,繼王士禛后獨領文壇風騷。在大量追隨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約60人的隨園女弟子身影,緊承其后的碧城閨秀詩群規模相當,相繼形成一個在聲氣相通、唱酬角勝中走向繁榮的兩性詩學網絡,女詩人也當之無愧為性靈生力軍。
現代學界對袁枚“性靈”的詮釋不盡相同,還原當時語境去了解應屬捷徑。他說:“詩者,人之性情也。”確定性情是詩歌的本源與靈魂。第二,主張獨創性,如《答蘭垞論詩書》曰:“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作詩須體現獨特的“這一個”,無須執著于宗唐、宗宋。第三,創作時強調有“才”與“靈機”。如《蔣心余蕺園詩序》有曰:“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第四,語言自然簡潔。“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淡不宜濃,然必須濃后之淡。”綜上,性靈詩論應包含率真的性情、鮮明的個性、奇妙的靈感與本色的語言。大部分女詩人以性靈為指導,并在創作中呼應此說。如被袁枚譽為“詩冠本朝”的席佩蘭《長真閣集》中的十數首論詩,揭橥的正是性靈詩說:“始知絕妙傳神句,不在辭華在性靈”③;金逸的“格律何如主性靈”也以性靈為旨歸。汪端、沈善寶、歸懋儀、宗粲、吳靜、劉琬懷等一致贊同詩歌內容要真實:“詩本天籟,情真景真皆為佳作。”④吳靜《自題集后》云:“一瓣清香何所得,敢夸真率不夸奇。”創作個性上,沈善寶《名媛詩話》中女詩人屢屢認同“未經人道語”的新穎而自然之作為好詩,如“(郭)笙愉詩皆性靈結撰,無堆砌斧鑿之痕,為可貴也”。對即便不合格律而秀韻天成之作也充分肯定:“安邱李婉遇幼而敏慧,性耽吟詠,雖不甚講求格律,而往往出口成章,自然秀逸。”
兩性性靈詩說的疏離。清代女詩家從性別視角切入文本關注詩學的性別差異,表現出不同于男性對女性文學的關注特色。于是,兩性詩學在相互依存的同時,也出現了相互疏離的一面。主要體現在:
1.認同原因不同。袁枚性靈論起于“神韻”、“格調”、“肌理”以及形形色色羈縛才思、窒息性情的詩觀念、詩批評、詩創作現象已捆緊詩文化近百年,而且愈捆愈緊之時。袁枚承繼前代特別是明中葉公安詩學與趙執信等的論詩精義,破唐宋界限與門戶家數,試圖挽救詩歌的生命,成為封建名教的破壞者。而絕大部分女性認同性靈說的原因則是“第二性”地位。因為無論身處何種階層,女性整體屬弱勢群體,創作心理與創作條件與男性迥異。就前者而言,創作的超功利性目的是女性以性靈為主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同性別的人對詩歌創作帶來的社會意義、人生意義的理解不同。男性以詩歌作為通往仕途的工具,達與不遇之間的多樣化人生影響著他們詩歌創作與詩學觀的多樣化發展,已為多家所論證。女詩家則不同,社會邊緣的生存狀態、苦悶與無奈的精神壓抑以及生性的柔弱和仁忍使她們始終無法擺脫“弱者”的印記,也因此決定了她們創作的主導心態是弱者的心態。在她們眼中,文學不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可能僅僅是生活中一種美麗的裝飾。靠了它在虛幻的世界建立一些意義,人生才不至于顯得太蒼白太空虛。沒有了傳統文學觀中過于沉重的政治負荷后,詩歌的價值也還原到人生本身,這應是女性選擇性靈詩說的重要原因。“吳中十子”中的多人在以任兆麟為師后又轉投袁枚門下固然有好名的因素在,但也不排除性靈說對女性的特別吸引力。同時,道家思想與道教也對女性求真性情造成一定影響。道家尚“真”。《莊子》一書共有66個“真”字。清代信奉道教的女詩人甚多,“真”也就自然成為悟道、悟人生的審美要求。
2.具體內涵有差異。第一,示真的尺度不同。男女性靈詩人均崇尚率真的性情。不過,男性詩人抒寫的真性情主要針對封建名教,具有叛逆的特點,多放膽直言之真。而女性詩中少有這種異端色彩,即便是書寫男女之情,也基本符合儒家禮教。圍繞自身的春怨秋愁、離愁別恨。如《名媛詩歸》序云:“故夫今人今士之詩,胸中先有曹劉溫李,而后擬為之者。若夫古今名媛,則發乎情,根乎性,未嘗擬作,亦不知派,無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女性缺乏吟詩屬文的嚴格訓練,反而保持了詩的感性特征;被隔離的處境也使她們在精神、情感上的單純、純凈,更能接近“真性靈”的境界。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嚴迪昌也曾有論:“她們在訴述感情生活以及身世遭遇時的真的成分要比搖筆即來的男性文人多得多。細膩與纖巧往往只是一紙之隔,這差距的關鍵每在于‘真’與否。”?譽?訛第二,詩格的纖俗與雅正有別。當宗法某種理論主張或創作實踐時,在將積極因素發揮到淋漓盡致時,消極的東西也一起被推向極端。袁枚提出的性靈詩說確實給清詩壇注入一針強心劑,但性靈論本身的問題與性靈末流的不濟也漸漸給詩壇帶來消極影響,這也是袁枚生前身后遭遇非議的重要原因。時事的變遷與詩歌自身發展規律均促使詩人對乾隆盛世風花雪月的詩歌理論與創作風氣進行批判與反思。作為性靈詩說的建構者、實踐者與傳播者,女詩家也主動參與到性靈詩論的充實與修正中來,為清代詩壇詩風轉變作出了一定貢獻。汪端曾毫不客氣地指出袁枚的消極影響:“吾鄉文體士習,隨園實始敗之。”?譾?訛她還追根溯源對性靈先驅公安、竟陵進行批評:在《明三十家詩選》中,公安竟陵派詩人詩歌一首未選,且評價甚低:“三袁之佻仄,鐘譚之幽詭,則人所共知,毋庸深論。”究其原因,公安末流淺率化的弊端與竟陵派幽深奇僻的藝術境界與汪端提倡的雅正審美理想不相容。如何改良性靈詩論來挽救詩歌生命呢?女詩家認為在追求風雅之懷、真摯之情、閑適之趣的同時,要摒棄男性性靈派的狂放之性,而要抒寫“雅正”之音,即符合“忠孝義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如張印在《學詩》中要求自己“不淫不傷旨,默與《關雎》會”。曹錫淑《燈下課大兒錫熊古詩拈示一絕》曰:“漢魏遺風還近古,休教墮入野狐禪。”教導兒子避免滑入性靈的鄙俗。對語言的干凈要求與李清照反對“詞語塵下”一脈相承,是女性面對男性性靈詩人出現弊端時提出的一個修正辦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古體詩的生命。同時,以不悖于儒家的倫理道德和詩教為皈依,也流露出她們思想意識上相對保守的一面,與袁、趙的激進有一定距離。從中正可看出男女兩性不同的社會壓力。第三,審美情感的多向性與單一性有別。男性筆下的詩歌審美情感豐富而變動不居。有兼濟天下的壯志豪情,有憂國傷民的慷慨悲歌,有終老林泉的避世情懷,也有云卷云舒的婉媚柔情,甚至紅塵香艷的野趣俗情。而女性大多過著多愁多病、壓抑苦悶的人生,所以墨痕中常和著斑斑血淚,“愁”成為女性詩歌的情感內核,傾訴生命悲苦成為女性的群體特征。如江珠《讀周硯云女史詩稿題此寄慰》曰“一卷冰雪文,字與血淚并”、李媺的《題梁溪孫旭英〈峽猿集〉》:“花落江城水亂流,繡馀一卷獨悲秋”。
總之,女性性靈論與“真”、“愁”、“清”、“雅”關系密切。“真”是對詩歌內容的最基本要求,要求抒發真情實感;而“愁”是“真”的具化,關涉女性的審美情感取向;“清”是在“真”、“愁”的基礎上形成的詩歌審美趣味;“雅”則是對“清”的深化,指向性情之正,與俚俗相對,與作家的主體人格精神相關。四者之中,“真”為詩之骨,“清”乃詩之神,“愁”為詩之魂,“雅”為詩之格。以此四者為特色的女性性靈詩說有著顯著的性別因素,對男性性靈說是一種補充與修正,二者和而不同。
女性詩學受限于時代與性別局限,無法完全獨立,只能在通過對男性詩學的或贊同,或質疑,或顛覆,或平衡中,以女性特有的體驗建立一個詩學的特殊空間。或許,這正是一代女性對清代詩學的獨特貢獻。而且,互識互惠的“性別詩學”是文學觀照中有趣而重要的維度,女詩家的這一空間開啟將有永恒的參照與啟示意義。[本文為湖南省高等學校科學研究資助項目(09C608)的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②劉世南:《清詩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③席佩蘭《胡智珠夫人香端〈抱月樓稿〉題詞,《長真閣集(卷七)》,掃葉山房,民國九年石印。
④沈善寶:《名媛詩話(卷七)》,清光緒鴻雪樓刻本。
⑤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頁。
⑥汪端:《論詩示蘇孫侄》,《自然好學齋詩鈔(卷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作者為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副教授)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