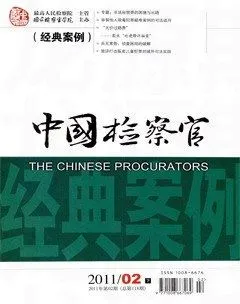對非法經營罪罪狀的限縮解釋
非法經營罪淪為“口袋罪”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脫序行為日益嚴重與經濟規制手段單一、措施落后之間的矛盾日漸凸顯的過程。當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手段不能(乃至不想)形成對經濟脫序行為的有效規制時,刑罰就會像“法寶”一樣被祭起,以為如此便能彈壓、威嚇經濟脫序行為。對經濟犯罪應持嚴格(而非嚴厲)的刑事政策,這本無可厚非,然而以法制脫序行為來應對經濟脫序行為,則顯然得不償失,因為如此會喪失公眾對法治的信賴,更可能導致司法權的不當運用乃至濫用。任何不遵從現行法律、濫用法律賦予權力的行為都屬于法制脫序行為。對非法經營罪的過度運用,即是法制脫序行為的表現。為使非法經營罪的適用重回法制的正軌。在現行《刑法》第225條未作新調整的情況下,應通過對非法經營罪的罪狀進行合理而必要的限縮解釋,將非法經營罪的適用限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內。以《刑法》第225條的規定為根據,對非法經營罪的罪狀應作如下限縮解釋:
一、“國家規定”應指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規定的行政措施等中確定的禁止性規范,且違反這一規范會引起具體的法律責任
對“違反國家規定”的界定,實際上也就劃出非法經營罪的最大懲罰范圍。根據《刑法》第96條規定,“本法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以該條規定為根據,屬于“國家規定”的規范性文件的立法主體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各部委制定的規章、發布的命令、決定等均不屬于“國家規定”,各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更不在其列。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屬于狹義的法律,形式上表現為“XX法”的規范性文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如果屬于規范性文件,實質上就是法律,只不過形式上稱謂是“決定”,例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套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如果認為某一經營行為違反的“國家規定”是法律(包括名稱為“決定”的法律),而這類法律屬于帶有經濟性內容的行政法律,那么,必須確切地指明違反該法律的具體條款。進言之,當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時,該行為應當首先判斷該行為是否為某一行政性(包括帶有經濟規制納入的行政性)法律中規定的法律規范所禁止,其違反這一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該法律明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甚至可能引起刑事法律責任的法律表述,如“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法律只是單純性的加以禁止或者命令從事一定的行為,但并沒有相應的有關法律責任的規定,則應將這種情形排除于《刑法》第225條“違反國家規定”的范圍之外。其理由在于:對于沒有規定法律責任的行為事實,根本不能稱其為違法行為。即便將這種情形理解為“廣義的違法行為”,但從比例性原則看,對于這種行為,既然行政法律尚且不設置懲罰條款,刑法自然毫無處罰的必要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包括由國務院直接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也包括由于國務院有關部委制定,但經國務院批準并以國務院名義發布的。《刑法》第96條之所以將國務院制定的這類規范性文件納入到“國家規定”之中,其根據是《憲法》第89條第1款,即“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同時,考慮到《立法法》第56條有關國務院有權制定行政法規事項的規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應有明確的憲法和法律根據,并以憲法和法律確定的法律規范為依歸。就國民經濟問題而言,憲法只是就基本經濟制度作出規定,而對基本經濟秩序及相關制度的確定,則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來完成。如此分析,可以發現,“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應有明確的法律根據。屬于《刑法》第225條“國家規定”的行政法規、行政政策、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也應屬于禁止性規范。且該規范有明確的法律根據,而違反這類禁止性規范,也應具有相應的法律責任規定,一般而言,行政法規中應有明確的刑事責任的規定,例如《彩票管理條例》第38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擅自發行、銷售彩票,或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行、銷售境外彩票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違反國家規定”。即是違反上述規范性文件中規定的禁止性規范。且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設若,某項經營行為雖然可能干擾既有的正常經濟活動,但上述國家規定沒有加以禁止,或者雖然禁止該項經營行為,但未設定法律責任條款,則不屬于《刑法》第225條的“違反國家規定”。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國家規定,應是具體的法律規范,即明確了一般人不得從事某項活動的義務,且設定了相關機關對該項活動的主管權限。如果某一規范性文件只是抽象、一般地提出。不得從事某類經營行為。但是一般人應如何不為一定的行為的內容并不明確,且沒有賦予相關機關以具體化的權限來管理這類行為,則這種規范性文件不屬于《刑法》第225條的“國家規定”。如上結論的理由在于:對于公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而言,只有法律予以禁止且禁止內容明確的,才能形成法律規定的義務;反之,如果法律沒有明確禁止,或者法律規范模糊不清無法指引如何活動的,則不能形成法律規定的義務,當然也無從引起法律責任。
二、“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違法性判斷應與《刑法》第225條前三項規定相當
對《刑法》第225條前三項進行分析,很容易地會發現,這三項所規定的非法經營行為都與行政許可有關,其中第1項、第2項直接違反了行政許可制度而從事了特定的經營行為。一言以蔽之,《刑法》第225條前三項都與特定市場經濟行為的行政許可有關。《關于懲治騙購外匯、套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第4條規定:“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該條規定的非法經營行為,實質上也可以看作是對行政許可制度的違反,因為只有經行政許可的金融機構才能買賣外匯,其他人并不能買賣外匯。因而,從《刑法》第225條的立法目的看,設定非法經營罪,意在維護國家對特定經營活動的行政許可制度。《行政許可法》第12條對可以設定行政許可的范圍作出明確規定,其第13條則對不設定行政許可的情形作出規定。從《行政許可法》規定的內容看,行政許可制度的建立,其目的之一即在于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秩序。該法第14條還規定“設定行政許可的根據,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規。”設立非法經營罪的正當性,即表現為其對市場經濟中基本秩序的破壞,而這些秩序與國民經濟安全、民生問題等緊密聯系在一起。從現有法制看,法律和行政法規恰恰是通過設定行政許可制度來規制這類經濟行為的。可見,雖然說,非法經營罪侵犯的客體可以認為是“國家對市場的管理秩序”,但從形式上看,非法經營行為首先且直接侵犯了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管理的行政許可制度。
需要強調的是,實踐中,不能僅以行為人從事經營行為未事先進行工商登記來作為判斷該行為“非法”的根據。對工商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登記制度,其目的在于進行有效的管理,但工商企業、個體工商戶從事行業廣泛,且并非都與基本經濟秩序相關,因而僅僅是未進行工商登記而從事經營活動的行為,不能以非法經營罪定罪。
三、對“情節嚴重”的判斷應當充分考慮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實質侵犯程度
實踐中在處理一些非法經營案件時,辦理機關只是片面地強調非法經營數額,如此判斷“情節嚴重”是缺少說服力的。考慮到非法經營行為違反國家規定的內容不同,在判斷“情節嚴重”時也應區別情形,綜合其他相關因素予以判斷。對于指向國家經濟安全的,如非法買賣外匯,可以非法經營數額作為判斷“情節嚴重”的因素,因為在這種情形下,非法買賣數額越大,則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傷害越大,潛在的危險也越大。對于涉及市場準入方面,則不僅要考慮違法經營數額,還要看對合法企業造成的實質損害程度。而對于涉及民生方面,則還應考慮對人們生活的實質影響程度。總之,行為人違反不同內容的行政許可制度,形成對不同內容的具體經濟關系的侵犯,因而就要求對不同情形非法經營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做不同情形的綜合考量。而不應僅以違法經營數額作為唯一的判斷根據。倘若行為人的經營行為確屬違法,且形成一定的數額,但并未危及國家經濟安全等重要經濟秩序,也沒有損害其他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更沒有損害到民眾的實際利益,對于這種情形,則不宜認定為“情節嚴重”,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很難說這種行為具有社會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