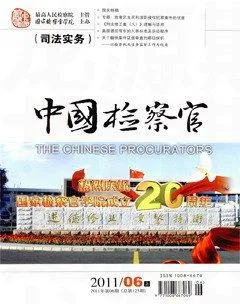論憲法與刑罰的關系
所謂刑罰權,指的是將某種行為定為犯罪,并對違反者科以刑罰的權力。因此,作為限制人權的公權力,其成立的基礎與適用范圍。都必須從憲法角度闡明。在近代立憲主義下,如法國學者西耶斯所言,所有國家權力,均為憲法設置的權力,都必須以憲法為基礎,在憲法規定的條件下行使。特別是對人權進行限制的權力,從人權的不可侵犯性與人權保障的目的來看,則是憲法所允許的例外情形。
一、憲法與刑罰權
從日本國憲法規定來看,刑罰權是由國家行使的。日本國憲法第18條規定,除因犯罪而受處罰者外。任何人不得違反其意志,使其服苦役。日本國憲法第31條規定,任何人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罰。這些條款明確以刑罰的可能性作為前提。
一方面,刑罰屬于對人權的強力制約,因此憲法對刑罰權的行使,設置了許多限制。特別是關于科以刑罰的程序方面,憲法的立場非常嚴格。如前述憲法第31條、第33條,關于刑事手續與刑事裁判,從比較憲法的角度來看,日本國憲法的規定也是相當詳細的。日本國憲法關于刑事手續與刑事裁判的條款規定,接近占據日本國憲法上人權條款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對刑罰的內容或是實體相關的憲法規定,也不在少數。日本國憲法第36條規定,絕對禁止殘虐的刑罰,第18條與第39條,也明文規定了刑罰權的實體界限。
當然,未經憲法明文規定的。其他憲法關于刑罰權的實體決定,并非基本委由刑法等立法。如后所述,關于刑罰權的實體在憲法上的界限,也引發了諸多爭議。作為人權制約手段的刑罰,因其重大性,必須由憲法予以說明。
雖然,長久以來,日本法學者對刑罰的根據與適當范圍的研究,是由刑法學進行的。對刑罰權的根據與目的、刑罰的實體相關規則,也是各國刑法學的重要課題。但是從憲法角度來分析刑罰權則為數不多。本文則希望通過考察日本國學說關于憲法與刑罰權的關系。以思考公權力對人權限制的界限所在。
二、實體正當
日本國憲法關于刑罰權的實體的憲法規定,即第31條,任何人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罰。日本學界通說認為該條款規定了法定正當程序,同時也內含對實體正當的要求。若是刑罰法規的實體不為正當,即使科以刑罰的程序屬于正當,也可能造成對人權保障的不充分。這種理論是以日本國憲法第31條的模版,即美國憲法中的正當程序條款要求程序與實體的正當作為解釋依據。學者認為所謂第31條的正當,不僅包括罪刑法定主義,還包括實體正當意義下的刑罰規定明確性、罪刑均衡性、刑罰抑制主義等。
但是,日本有學者認為,實體正當的要求,并非一定要由第31條推導而出。若是刑罰法規違反了實體正當的要求,這實際上就是侵犯人權,這直接就被視為侵犯憲法上人權規定而進行處理。另外。即使憲法第31條不包含實體正當,刑罰實體正當所要求的刑罰規定的明確性、罪刑均衡、刑罰抑制主義等,并非就不能在憲法上找到依據。刑罰規定的明確性也可以作為罪刑法定主義的內容之一,無論是在實體法定還是在程序正當,都能占有一席之地。對犯罪不能科以失去均衡的刑罰。也是可以從憲法36條殘虐刑罰禁止中解讀出來的,同時也可以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中進行思考。
本文則認為,作為法制裁的一種,刑罰屬于對人權非常重大的制約手段。如死刑刑罰,首先將罪犯的人身自由進行制約。在刑事程序中,強制性的調查與身體強制也是必要的。即使實際上并不一定科以刑罰,但是這些限制到人身自由的行為,其震懾力很強,往往存在社會制裁的因素。因此考慮到刑罰制裁的特殊性,程序正當與實體正當,都有必要在憲法上獲得特殊考量。故而在這種情形下,與刑罰相關的實體正當,在日本國憲法第31條內尋求規范依據是妥當的。
三、憲法與刑罰
對刑罰權的根據與適當范圍的研究,長久以來都是刑法學的領域所作。雖然刑罰權的發動屬于公權力的行為,但是如何發動刑罰權則是刑法學的獨門研究。日本有刑法學者指出,刑罰法規的多項原則,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憲法不能使之停止。傳統的日本法,也有“憲法與刑罰法規區分”理論,認為除了罪刑法定之外,刑法與憲法不存在關聯。
不可否認,刑罰本身先于近代憲法而存在。為何刑罰存在,這是憲法之上的問題。更多意義上是社會與歷史的問題。但是雖然歷史與社會與刑罰存在緊密聯系,但是隨著憲法原理的變化,刑罰權則應該從憲法角度進行分析。有學者也指出。在日本國憲法制定之后,刑法的目的從保護國家自身與倫理秩序,轉變為保護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與財產。在價值觀出現轉變之際,對刑罰權的研究更有必要從憲法出發。刑罰權的淵源雖然可以從作為政治的、社會的事實出發,但是正當的刑罰權,其依據則必須從憲法出發。實體的刑罰權則是基于權力正當化原理的憲法的具體規定而受到調整的。這種調整即表現在刑罰權必須基于國民意思。必須基于人性尊嚴,必須考慮到自由與生存。因此,實體刑法的合理性要求的實質,在于尊重憲法上的人權。
具體到日本國憲法中,即將憲法第13條以下的人權規定,把握為實體正當的要求,正是憲法第31條的內容所在。
四、實體正當與刑罰權的界限
如前所述,刑法的目的并非在于保障國家自身與倫理秩序,而是要保護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與財產,即市民安全。憲法則賦予人民在權利受到侵害之際要求國家予以保護的權利。在此也科以國家以保護義務。國家于此的保護義務,存在多種形態,但是并不包括制約力度很大的刑罰權的發動。只有在憲法沒有禁止的范圍內,并且符合實體正當與程序正當的原則下,刑罰權才能被允許發動。但是刑罰權的界限為何,則是問題所在。
從日本國憲法的條款出發,對人權制約的明文根據。即憲法第13條的公共福祉。具體到如何基于公共福祉,刑罰權得以發動的場合下。從刑罰制裁的特殊性出發,必要性最小限度則要求在最嚴格意義上實施。這意味著,刑罰權,只有在必須對犯罪進行刑罰才能抑制制止的情形下,才得以發動。原則上是對人權產生了重大侵害的情形下,并且這種行為具有反社會的強度,以及在無法通過其他手段來抑制制止這種侵害行為的情形下。才能允許刑罰權的發動。
因此,謹慎發動刑罰或是刑罰的自我抑制性。可謂是實體正當的重要因素。另外。從必要性最小限度出發,所科以的刑罰的程度,也應該停留在對罪犯侵害的必要最小限度之內。這也是罪刑均衡的要求所在。關于刑罰權的其他實體上的界限,也可以從必要最小限度的原則進行解讀。
五、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目前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之際,建設法治國家更是我國人民的期待。而法治國家的價值理念,即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以限制國家權力為己任,以保障國民的人權與自由為目的,以促進人全面發展為方向。而刑罰權只是管理社會的一種非必要的手段,它的破壞性告誡我們啟用它要慎重和理智。
社會發展到今天,隨著人類文明化程度不斷提高,國家管理和調控社會的形式多樣化,即使法律本身也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種手段,刑事手段作為國家最后啟用的一種合法手段,它的運用受到刑事法治理念、人權保障意識、司法成本、刑法謙抑性、自身強制性和破壞性的影響和限制。
尤其是在刑罰權的懲罰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打擊犯罪的單一取向轉變為限制刑事法律活動的范圍和保障國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人權雙重價值取向下,刑罰權存在界限,刑罰權應該更加人道,充滿人性關懷。
尤其是當今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際,在社會的發展中,更多的是靠民事等非暴力的手段來解決沖突或矛盾,只有當構成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價值和基本秩序受到不可容忍的侵犯和否定,且沒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予以保護時。刑罰才被迫現身,并且其選擇的手段應是在必要最小限度下進行,而且應該盡可能慎重。刑罰權的發動之所以這么謹小慎微,并不是刑法功能的退化和地位的下降,這是法治國家建設以人為本的題中之義,更是憲政國家權力分立與人權保障的必然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