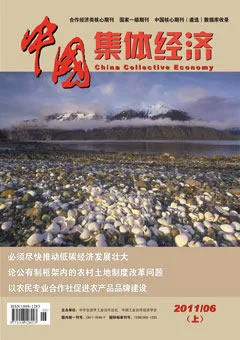古代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淺談
摘要:文章對古代農業的兩種形式——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現象進行分析,涉及到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形成發展,以及經濟間的交流,對古代社會文化的影響。
關鍵詞:農耕經濟;游牧經濟
一、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形成
無論是農耕經濟還是游牧經濟,都存在著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產生了種植業與畜牧業的萌芽,在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就產生了原始的農業,特別是在進入父系氏族制之后,農業已經發展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主要部門,男子在社會生活中占主導的地位,通過改進農具,革新耕作技術,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基本上形成了男耕女織的分工,農耕經濟在此時已經基本形成。雖然畜牧業也是萌芽于舊石器時代晚期,但在農耕經濟形成時,游牧經濟還沒有形成,而是在農業經濟有了相當長時間的發展之后,游牧經濟隨著游牧部落的形成而發展起來。這是因為除了直接為狩獵生活服務的若干牲畜外,作為食物來源重要部分的牲畜的馴化,往往要在種植業生產以后所提供的相對安定的環境中才能最后完成,而游牧經濟的形成更是以畜牧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基礎的。游牧人并非完全不需要農產品,在其內部基本上脫離了種植業的游牧部落,要以外部農業部落的存在、因而能通過交換或其他方式獲得必要的農產品為其存在的條件,所以只有整個社會的農業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才有可能分化出游牧部落來。
二、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發展
從總體上來看,古代中國經濟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農耕經濟,但從自然環境的角度來看,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帶,因此,這些地區也就成為了以草原畜牧業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認為,自我國東北大興安嶺東麓-遼河上游-陰山山脈-鄂爾多斯高原東緣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廣大地區,都屬于歷史上傳統的游牧經濟分布地區。而在此界線以南和以東則屬于傳統的農耕經濟分布地區。從一定程度上講,我國的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歷史上的整個西域地區,都屬于歷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因此,宏觀地說,也屬于傳統的以游牧經濟為主要特色的區域。在歷史上,農耕地區和游牧地區存在著各自擴散的過程。
(一)農耕經濟的向南擴散
首先,由于中央政權向南侵略而把農耕經濟帶到了處于落后的南方地區。三國時期,在今天的云南地區,貴州西部,四川南部的地方,南中大姓崛起,抗拒蜀漢,諸葛亮七擒孟獲征服南中,并在南中采取措施加強統治,在經濟方面,把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到了南中,諸葛亮提倡廣開屯田,以牛耕代鋤耕,使不少土著民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在西南的各少數民族中至今仍留傳著諸葛亮傳授水稻、牛耕的先進技術的傳說。因此,可以看出諸葛亮南征推進了該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是對農耕經濟的傳播。在東吳,孫權曾派船到夷洲(今臺灣)的時候,夷洲的社會尚處于原始社會階段,當地百姓已經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也從事漁獵經濟,但生產力水平很低,生產工具大部分為石磨器。孫權的這一舉動加強了夷洲與內地的了解和來往,促進了夷洲經濟發展,把農耕經濟帶到了夷洲。
其次,游牧民族經常的南下,侵擾了北方人民的生活。東晉以后,中原為少數民族占領,大批農耕居民潮水般涌向南方,出現“北人避胡多在南”的情形。當時僅編戶南渡人口就達八九十萬,其主要遷居地為皖南、江浙、湖北、廣東、福建等。據《晉書·地理志》、《宋史·州郡志》等資料估計,劉宋時有戶籍的南遷人口約占西晉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占劉宋時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此外還有大量未被統計的脫籍人口。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大移民,南渡人民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技術。他們利用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發展農業生產,加快了這一遼闊區域的開發過程。生產規模迅速擴大,糧食產量明顯提高。隨之而來,南北經濟地位發生變化,南方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
(二)游牧經濟的南下
游牧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南下,向中原擴張。我們不能把游牧民族的擴張簡單看成是軍事上的侵略,從更深的層次上分析,主要是游牧民族與外界接觸以尋求自身存在與發展的內在動力。游牧民族主要從事于畜牧業,長期過著逐水草而遷徙的游牧生活,這就使他們的經濟生活受著自然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嚴重制約,“他雖然成功地征服了這種可怕的環境,這個環境卻也在暗中把他變成了奴隸”。游牧民族的主要食物都是獵物,或牛馬羊等,這些畜牧產品不如糧食谷物易于保存,所以游牧民族往往缺乏農耕民族那種頑強的抗災能力,當災荒發生,饑餓、死亡便接踵而至,經濟文化均面臨著崩潰的危機。避開災害因素不談,單純游牧本身也不能滿足因人口增加而不斷擴大的對生活資料的需求,于是糧食、布帛等農產品就成為畜牧產品的必要補充,而這只能從中原農耕圈中獲得。在漢代,長城以北的匈奴不斷入關,獲得財物以滿足生產和生活的各種需求是其重要動機,文帝時,晁錯說:“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當時著名的和親政策之所以能減少邊患,就是由于漢朝的"絮、繒、酒、米、食物"的誘惑,故武帝初年“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雖然自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漢匈發生戰爭,匈奴與漢朝停止和親,但仍然不愿放棄關市貿易。繼匈奴之后千余年興起的蒙古帝國,更多的是出于其民族的好戰性,而發動了南下擴張的戰爭。
游牧部落的南下是游牧文明對農業文明的沖擊,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不斷地喚醒農耕民族日漸消沉的斗志。當農耕民族在豐沃大地的滋養下安土樂天,沉緬于豐衣足食的安逸時,游牧民族的侵擾使得他們不得不拿起武器自衛。每一個優秀的民族都是在戰爭的錘煉下進步的。生存作為第一需要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活力,優勝劣敗是自然的法則,農耕民族在心志上的健全,不能說沒有游牧民族的功勞。二是對“往來轉徙,時至時去”的游牧民族,單靠局部防御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因而必須聯合起來。因此,農耕文明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不能說沒有這一因素的作用。所以,長城作為大一統的象征,堅定地拒絕游牧民族侵擾的同時,也框定了中國大一統的格局。
游牧民族不僅南下向中原地帶擴張,而且在古代,我國的西域南疆廣大地區也主要是有游牧民族統治的。如漢代的匈奴對南疆及西域其他地區的統治、鐵勒、突厥對南疆的統治、蒙古族對南疆的統治等等。也就是說,北方的游牧民族對南疆的影響較大。真正對西域實現統治的中原農耕民族王朝主要是兩漢和唐朝,而在其他大部分時期內,以游牧民族的統治居多。
三、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交流形式
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表現為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矛盾,但是,兩種經濟之間一直存在著經濟交流。在古代社會,馬匹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既是農耕生產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獵、交通、騎射、戰爭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往往與國勢盛衰聯系在一起。歷代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視馬政,將擁有數量充足的馬匹看成富國強兵的重要標志。從區域生產的特點和分工來看,中原農耕地區一般缺少足夠的馬匹,而邊疆游牧地區則以畜牧業為主,牧養著數量可觀的馬匹。與此同時,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農耕民族所生產的糧食、布帛和金屬工具。這樣,中原馬匹的獲得,主要提高貢賜貿易與絹馬貿易來實現。
歷史上互市的出現,對于貿易雙方的民族來說,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我國古代中原農耕地區與西北周邊游牧民族之間的貿易,一般記載都是“進貢”與“賞賜”,即各政權或民族帶來本地區的土產方物,中原王朝則回贈絲帛等物。當時的這種進貢與賞賜滿足了雙方的需要:進貢者謀求政治上的依托與援助,并獲得物質利益;賞賜者將這種貿易看成一種政治需求大于經濟利益的手段,就其作為安撫邊境,結好各政權及各民族的基本國策。尤其一提的是,當時的這種民族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原王朝“天朝上國”的心理需要。歷史上的這種貢賜貿易,對于西北游牧民族來說是一種有厚利可圖的生意,故一些商人往往或隨同使節一同前來,或冒充使節前來貿易,以此獲得較一般正常的貿易更加有大的利潤。
隨著中原王朝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與農耕區的逐漸固定,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貢賜貿易也就發展演變為絹馬貿易。絹是對中原農耕民族所生產的絲織品的總稱,因其受自然條件及加工技術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產絲織品,而游牧民族的上層就其視為高級奢侈品,其消費只能靠馬匹及其畜產品與中原民族的的交換來滿足,隨著游牧民族對絲織品需求和中原王朝對于馬匹用量的不斷增加,絹馬貿易相應擴大。發展到唐代,就開始出現了馬價絹。一匹馬換取40匹絹,是當時回紇與唐朝絹馬貿易中的標準價。當然,當時的這種絹馬貿易是不公平的,具有政治色彩,馬價過高,已經成為唐王朝沉重的財政負擔之一。
雖然存在經濟交流,但兩者一直沒有融合起來,沒有能夠形成農牧結合的經濟形式。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自然環境所導致的氣候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種經濟的分布,長城以北的廣闊的內蒙古草原,西域地區的青藏高原都是草原地帶,只適于進行游牧經濟,而如果進行農耕則會破壞自然環境,土地會沙漠化。而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這種差異,導致了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出現,各個民族之間由于習俗文化差異而存在矛盾,經常發生戰爭,戰爭加劇了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形式的隔閡,使兩種經濟的分離狀態一直存在。歷史上的重農抑商政策對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之間的關系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使得農耕經濟地區的畜牧業生產受到了遏制,農耕經濟實際上變成了幾乎單一的種植業經濟,少量的畜牧業也僅僅是一種家庭副業,即“雞豚狗彘之畜”。抑商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正常的經濟交流,因而也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了各種非正常的商品貿易交流形式:貢賜、官方互市以及戰爭和掠奪。這種狀況反過來又加劇了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對壘和隔閡。
四、農耕經濟與與游牧經濟交流對兩大經濟區文化的影響
這種經濟交流,雖然沒有改變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格局,但相互的激勵與促進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影響著生活習俗以及文化。
漢民族就是這種經濟交流所形成的。北方的居民原本都是華夏族的,但隨著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地區的經濟交流,有相當一部分的游牧人口到中原定居。眾多的少數民族融入了華夏族,構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漢族。由于北方漢人融入了少數民族成分,故其文化形態,生活方式都和華夏傳統有著明顯的差異。最著名的就是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東漢時,盡管北方游牧時時攻掠,但文化交融仍很明顯,如漢靈帝“好胡服、胡賬、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筱、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竟為也”。唐朝的空前繁榮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結果,其時長安盛行胡衣、胡帽、胡食、胡床,《舊唐書·輿服志》:“開元以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供胡食,士女盡胡衣胡食”。蒙古對中原的統治并不長久,然其影響卻很深遠,北方不少漢人改用“胡服”、“胡語”、“胡姓”,盡管明政府嚴加禁止,但直到15世紀中葉,“韃妝”仍較唐服為盛。游牧文化一方面消弱了儒家傳統對中原地區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為北方漢人注入了強悍、樸實的獨特氣質。夏竦《論幽燕諸州》云:“幽燕山后諸州人,性勁悍,習于戎馬,敦尚氣節,可以義動”,《新安縣志》稱:“其人多剛介慷慨尚樸略,而少文華,純厚之風相沿成俗”,《舊宣鎮志》:“山高水深,風勁氣寒,人性勇健,喜敦信義,故多貞烈之節”,都形象生動地反映了游牧文化對北方漢人的影響。
通過經濟交流,在游牧民族影響漢人文化的同時,漢人也影響著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從農耕民族先進的物質生產中汲取了先進的物質與制度文明。通過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文化上的交融,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
參考文獻:
1、江應梁.中國民族史[M].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