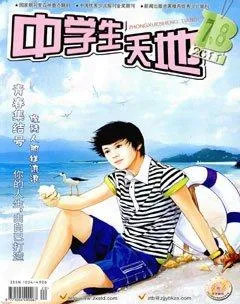日本游學散記
3月11日下午,驚聞日本地震的消息,第一反應就是聯系在早稻田大學留學的兩個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文章里的沫沫),接著又給兩位日本友人發了郵件,均收到了平安的回復。從此每天總會上網看看日本的相關新聞,對于這個一衣帶水的鄰國,我有著一份美好的中學記憶……
初來貴地
清晨的陽光暖融融地懸掛在雪白的機翼上,明亮,但不刺眼。又一次登上飛機,感受卻是不同的。我以一種最舒服的姿態靠在座位上,看著窗外熟悉的風景,等待起飛。
身邊坐著高大的王磊,他一邊吃著套餐,一邊關心飛機的行駛狀況。我則一邊笑他,一邊看窗外,浮云像棉花糖一樣絮軟。突然想到那本橙色的小書,江國香織的《芳香日日》,里面有篇非常短的小說,叫做《棉花糖》。我在淡淡的香甜氣息中閉上了眼睛。
醒來時,飛機正準備降落在東京成田機場。我已經看見了軌道,銀練一樣,筆直地伸向遠方。身邊的王磊同學,長出一口氣。然而僅僅幾秒鐘,飛機突然筆直地拉起,直沖九天。大家的臉色全變了……各種語言開始向乘客解釋,因為強風的緣故,飛機要在空中盤旋一會兒。大約七八分鐘吧,飛機再次降落。當我們終于站在大地上的時候,驚魂未定,每個人的表情都慘不忍睹。
坐車去了千葉,一個美麗得如同童話的小鎮,道路兩側是望也望不盡的綠色,如夢如幻。低矮的房屋色彩典雅,幽深而古樸,將天空映襯得十分高遠。我問沫沫和小萌,你們感覺如何?她倆異口同聲吐了一個字——耶!而我,不由得又要聯想。這次,是安房直子的童話,尤其是《花香小鎮》。
這里的街道就像是宣紙,輕薄柔軟,以至我們的腳步都變得很輕,生怕不經意的一點聲響,就驚動了它的靜謐。沒有看到櫻花,我用磕磕絆絆的英語問日本朋友,Where is the SAKULA?
他告訴我,這個季節櫻花已經開過了。看到我遺憾的樣子,他找出幾張櫻花的相片送給了我。
我的接待家庭
泡過溫泉,美美地睡了一覺,第二天趕往新宿。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建筑物一下子高大雄壯起來,不再是漫畫里那些火柴盒般的玩具小屋。街道也充實起來,行人車輛流過,像一片片靈動的光影。輕柔的風里,竟也有了一些磅礴的味道。
大家坐在一家麥當勞里休息時,我和陸陽跑去附近的郵局看郵票。當然,我們也不是什么集郵者,我們相中的盡是些動漫郵票,像是寵物小精靈、鐵臂阿童木或者機器貓。可惜標價奇高,我趴在玻璃柜臺上和花花綠綠的它們對視了好久,寬慰自己,看一看也是享受。出了郵局,只買了一瓶飲料,一條鑰匙鏈,一頁貼紙,竟花掉500多日元,心都快碎了。
這里的麥當勞,一包薯條相當人民幣幾十元,無奈,只好坐在倍感親切的香氣中忍受煎熬。還是聊天吧,或許能緩解一點兒食欲。
沫沫說,日本人八個有九個英語講不好。如果我的home stay果真如沫沫所說的那樣,豈不是要在日本的家庭留下一段無聲的記憶?
傍晚,乘坐新干線到了長野。一出車站,就看見上田西高校(日本“高校”相當我們的高中)的同學舉著花束迎接我們,每一個人都清澈明媚,笑容燦爛。
上田西高校校舍非常普通,除了干凈整潔,遠遠不及我們的學校寬闊氣派。
我們一行6人就像孤兒一樣等著被認領。我的home stay的爸爸媽媽已經等在那里,手里拿著大大的牌子,上面用中文寫著我的名字。我從翻譯那里了解到,這家姓甲藤,媽媽就是上田西高校的老師,家里有一個上大學的女兒,叫恭子。
興高采烈地跟著我的日本爸媽上了車。
大街上流光溢彩,燈火晃眼。我禁不住感嘆一句:How beautiful it is!
我的日本爸媽互相看看,只是笑,不說話。
我又指指窗外:It looks very well!
他們又互相看看,只是笑,不說話。
慘了。我的心猛地一沉。此后的交流恐怕得依靠肢體動作了。
到了家,爸爸媽媽第一件事就是找來紙和筆,寫給我的第一個詞是:夕食。我想了一下,明白了,就是我們的晚飯。我連忙說了好幾個Ok,靠中午那點食物捱到現在,的確不容易。他們大概是向我描述晚飯吃些什么,我只聽懂了一個詞,咖喱。呵呵,我最喜歡的口味。
大學生甲藤恭子回來了,英語水平比我想象得要差。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千萬別像在國內一樣,一開口先琢磨語法,在這里,你說得越是正規,人家越是聽不懂,像我這樣考試經常出現語法丟分的英語,剛好符合日本人的習慣。
恭子的性格非常開朗,還唱日本歌給我聽,我也回唱了兩首,不好意思,都是通俗歌曲。本來很想唱首《茉莉花》什么的,但歌詞記不完整,只好放棄了。恭子手舞足蹈地給我講日本的民俗,比如辟邪,插花,茶道,櫻花盛會什么的,還有漫畫。去年冬天我心血來潮,曾經在學校選修過一段時間的日語課,所以聽了個一知半解,有時也能用日語回她。聽不懂時,我就瞪大了眼睛問:“What?”。再不成,就在紙上寫寫畫畫。交流雖有些障礙,但同時也蠻有趣的。
再說晚飯。一家人也是分餐制。我看看自己的盤子,能叫出名字的,除了咖喱飯,就是沙拉了。我慶幸他們沒有給我吃生魚片之類的食物。
恭子送了我一件和服,暗紫色的花,杏黃色的腰帶,還有粉色的蝴蝶結。可惜,穿起來實在太麻煩了。
晚上,用恭子的電腦給家里發了一封郵件。我告訴媽媽,這兩天在日本,我使用最頻繁的一個詞,就是——What。
上田西高校見聞
吃過早點,甲藤媽媽開車把我送到上田西高校。
我的partner是一個臺灣女孩,英文名字叫Grace,高三,中文自不必說,日文說得也很流利,我便幸運的有了一個形影不離的翻譯。沫沫她們都很羨慕我,后來,她們的羨慕就變成了感嘆,因為Grace為人特別善良熱情,不論誰的交流出現障礙,她都樂呵呵地跑去“傳道、授業,解惑”。
女學生化妝在日本高中很普遍,染發,穿耳洞,美甲的比比皆是。每次我們去衛生間,總能看到幾個美眉拿著口紅或者胭脂在一絲不茍地裝扮自己。她們大多很開朗,很時尚,反正不是我們傳統印象里那種邁著碎步、弱風扶柳的樣子。
第一節課是日本學生的國語課。班主任首先讓我到前面做自我介紹。擺脫了時態、語態、還有單復數的羈絆,我可謂侃侃而談,一氣呵成。我想,能蒙倒多少算多少吧。教室里掌聲一片,盡管每個人的表情多少有些茫然。真沒想到,在日本,我對我的英文水平,居然產生了天才般的得意。
沒法很好地描述日本中學生的國語課,因為我完全聽不懂。想來和我們的語文課差不多吧,也要抑揚頓挫地讀課文,分析思想內容,講解歷史背景。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學生上課很隨便,可以離開座位走動,嚼泡泡糖,自由提問,也可以互相探討。所以,很快,我就由最初的中規中矩變得有點肆無忌憚。我小聲地問Grace,你們班的帥哥在哪里?她指給我,我立馬扭過頭去看,直到把人家看毛為止。
接下來就有趣多了——花道課和茶道課。
插花看著不難,做起來也不難,難的是,盡管我們都充分發揮了各自的聰明才智,但作品卻怎么看都像是孿生。其實插花起源于中國,隋唐時期傳入日本,后來在日本發展起來,二戰之后,反而是日本插花走向了世界。
日本的茶道同樣源于中國,講究典雅、禮儀,使用的茶具也是精挑細選,品茶時還配以甜品,日本人視之為一種培養情操的方式。我有模有樣地泡了一壺茶,至于茶的味道,真的是苦不堪言,好在有甜點中和一下,將就著把茶道課完成了。
雖說高三(5)班的同學相當友好,但上課對我來說還是有些枯燥,要么聽不懂,要么簡單到了無趣。他們的英文教材非常簡單,他們的一堂數學考試,我們飛快地完成了。但最后的得分,卻令我們瞠目結舌。7分!(滿分10分)原因嘛,是我們覺得過于簡單,許多題直接寫出結果,而日本教學極為重視演算過程,一步一步,一絲不茍。
晚上,甲藤媽媽和恭子帶我去了百元商店。在這里,我總算過足了消費癮,買了很多精美可愛的禮物帶給我的好友。想起5月有母親節,便買了兩件禮品,一件帶回給我媽媽,一件送給日本媽媽。她不要。我的英語水平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心情,只好將同樣的一句話說了兩遍——This is for
- 中學生天地(B版)的其它文章
- 你知道嗎
- 聲音
- 我們這一班
- 夏天來點兒“冷笑話”
- 微博也搞笑
- 新型石墨烯晶體管研制成功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