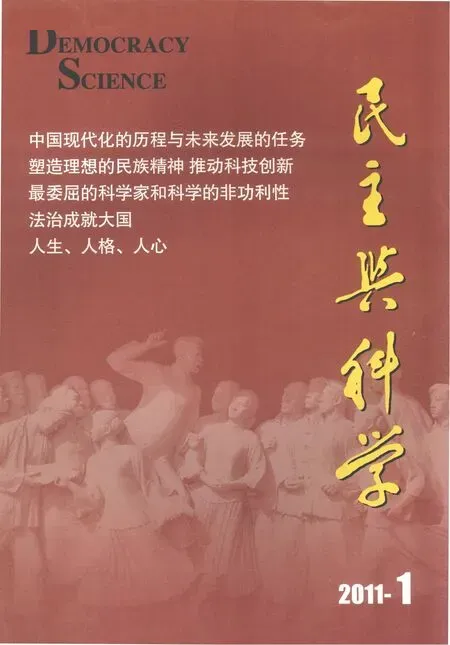2010年中國法治的進步與局限
■張千帆
2010年中國法治的進步與局限
■張千帆
2010年,中國制定了《社會保險法》和《人民調解法》,修改了《保密法》、《國家賠償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法律,同時出臺了不少規章和規定。總的來說,這些法律規定的主要亮點在于技術細節方面的完善,其程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
以新制定的《社會保險法》為例,這部法律的一大進步是實現了養老和醫療保險的“異地漫游”;對于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個人,其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關系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這一規定為養老和醫療保險的全國聯網提供了法律基礎,也為勞動者跨地區工作清除了不必要的障礙。在網絡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建立這樣的全國聯網系統顯然不是一件難事。但同時不能不看到的是,技術進步并沒有解決這部法律解決不了的實體困難,那就是養老和醫療保險覆蓋范圍有限、保障程度過低。目前大多數人都不可能靠養老金過活,醫療保險也只管小病,大病對于許多家庭來說仍然是滅頂之災。要讓《社會保險法》真正發揮作用,國家今后還得投入比現在多得多的財政,增加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和力度。
《保密法》修改的主要亮點也在于技術細節,譬如以往中國只注重保密,而不知道解密的重要性;如果已經超過保密時效的事項仍然被保密,人民的知情權自然就遭到剝奪。因此,此次修改規定了兩種解密制度:一是自動解密制度,保密期限已滿的國家秘密自動解密;二是主動審查制度,要求有關單位“定期審核”所確定的國家秘密,不需要繼續保密的應當及時解密。更重要的是,修改后的《保密法》有限度地上收了定密權。以前由于有權定密的政府單位過多,定密程序十分隨意,造成“國家秘密滿天飛”的現象,嚴重限制了公民知情權。現在縣級以下的單位不再擁有定密權,而且規定了定密責任人制度:單位負責人及其指定的人員為定密責任人,負責本機關、本單位的國家秘密確定、變更和解除。新法對定密主體的限定和程序的完善有助于糾正國家秘密范圍過寬的現狀,但這種改善是有限的。嚴格來說,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資格確定國家秘密,因為國家秘密應嚴格限定于國防、軍事以及某些敏感的特殊外交事務等專屬中央政府的事項,其余都屬于必須向社會公開的政府信息,因而只有中央有關部門才有權決定什么是“國家秘密”,地方政府僅有權執行中央規定。這里涉及一個基本的治國理念——既然地方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內部治理,有什么地方事務是不能或不應該向老百姓公開的呢?即便是公安偵破等當時不宜公開的信息,也屬于信息公開的例外,而非嚴格意義的“國家秘密”,而我們一直將兩者混為一談,從而極大擴張了“國家秘密”的范圍。現在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都有權確定國家秘密,因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秘密滿天飛”。今后需要進一步上收定密權,將其嚴格限于中央有關部門,并使之接受全國人大有關專業委員會的監督。
《村委會組織法》的修改經過激烈爭議,最后頂住各級官員的普遍壓力,保留了任期三年的規定,有利于村民自治不受上級干預,因而這種不修改也未嘗不是一種“進步”。新法進一步規范了委托投票,有助于治理選舉舞弊。另一方面,新法沒有對選舉細節進行適當規定,例如沒有規定當場記票制度,從而為選舉舞弊留下空間。對于作用越來越重要的村民代表會議,新法也沒有實質性地規范其選舉和組成,成為今后村民自治的一大隱患。總的來說,新法對技術細節的改良不足以在整體上改善村委會選舉質量,而自上而下的領導方式有所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村民自治的前景面臨諸多變數。
《國家賠償法》自1995年施行后,由于賠償范圍小、標準低、程序復雜而備受詬病,甚至被戲稱為“國家不賠償法”。這次修改除了賠償程序有所改進、賠償時間有所限定之外,還擴大了賠償范圍,明確規定了獲得精神賠償的權利以及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賠償責任,將監管人員虐待或放縱他人實施毆打、虐待等行為納入賠償范圍。這類明顯違法行為在許多國家被界定為工作人員的“個人行為”,國家并不承擔直接責任,國家替代個人賠償被認為有縱容個人犯法之嫌,甚至被認為是慷納稅人之慨以彌補政府管教不力的過失。從受害人權利保障出發,由于肇事者很可能賠償能力有限,國家確有必要保證賠償;但是從政府法治、責罰分明、提升威懾的角度來看,國家有必要在賠償之后對明顯的個人過錯加大追償力度。不可忽視的是,目前掌握公權力的某些人之所以肆無忌憚地侵犯公民權利,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正是因為法律責任太小;對于那些無法無天的公職人員,傾家蕩產的罰款或許是最有效的震懾,而國家賠償的目的顯然不是為肇事者提供“保護傘”,而是為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濟。由于新法關于追償力度和精神賠償幅度的規定存在極大彈性,今后的司法實踐有必要適當把握,在為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濟的同時適當追究肇事者的個人責任。
調解本來可以是解決糾紛的有效機制,只不過這套民間機制不太適合法院,反而容易混淆司法職能并加劇司法政治化。《人民調解法》明確規定了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有助于將民間調解機制規范化和制度化,進而有望厘清調解和司法職能的分界。調解應該在法庭外進行,調解不成的案件進入庭內訴訟;對于調解達成的協議,法院的主要職能限于協議的解釋和執行。只有這樣,才能將屬于司法的(訴訟)還給司法,屬于民間的(調解)還給民間。
最后,程序性規定的作用當然未必僅限于形式,而是可能產生實質性效果。國家安監總局出臺的《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企業領導帶班下井及監督檢查暫行規定》將領導帶班下井制擴展到所有礦山,要求每個班次至少有1名領導在井下現場帶班,并與工人同時下井、同時升井。另外,礦山“領導”明確為礦山企業的主要負責人、領導班子成員和副總工程師。如果礦山企業沒有領導帶班下井,從業人員有權拒絕下井作業;如果從業人員發現并確認帶班下井領導無故提前升井,經向班組長或者隊長說明后有權提前升井。雖然這些規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打折扣,但是讓礦山領導“陪死”確實有助于促使他們重視礦山安全,從珍愛自己的生命出發加強礦山安全保障,從而讓廣大礦工也能搭上安全保障的“便車”。和所有其它規定一樣,這條規定的關鍵也重在落實。讓領導和礦工“同生死”當然好,而目前將監督實施主要交給礦工自己,但是礦工是否敢堅持要求領導下礦?礦工自己是否有意識堅持這條要求?如果缺乏具體的監督措施,只有等到礦難發生后才發現領導沒有下井,那么任何處罰都為時已晚。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