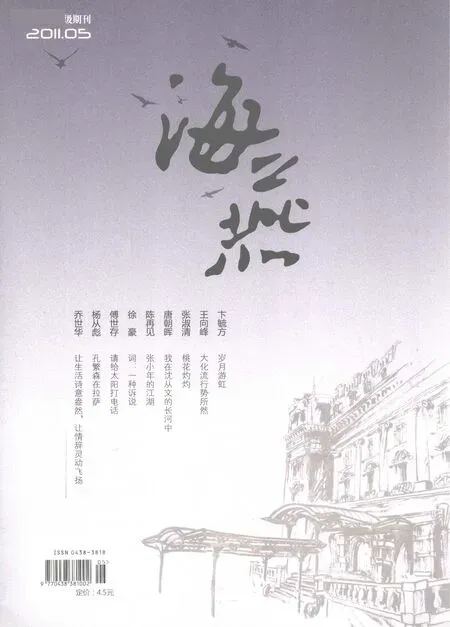我在沈從文的長河中
唐朝暉
我在沈從文的長河中
唐朝暉

唐朝暉
1971年出生,湖南湘鄉人,現居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心靈物語》、《一個人的工廠》、《勾引與抗拒》等書。散文作品上榜“ 當代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 ,曾獲冰心散文獎。作品散見于《大家》、《花城》、《美文》、《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學》等報刊。作品入選多種選本。
每個月都會有那么幾天感覺到自己沒有著落,漂著,浮著,也不是有什么悲傷的事情,更不是那種矯情的憂郁,就是無所事事,而,同時,又有一大堆的事情等著我去處理。當時只是強烈地感覺到生活:不應該這樣!至于該怎樣?就沒想清楚過,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加,漸漸明白——生活肯定不應該是現在這種模樣。
像很多人一樣,我好像在做一番事業,其實,我們都只是落在一個井里,只是在勤奮地不斷把井給掘寬些,至于多寬,終究不過井而已。
我們每個人都在用力,而力都用在對外的物質上、身體上、肉身上,都用在虛華的其他人的認同上。好像是為了證明給某個人,或者某小群人看,證明自己可以做好某件事情,可以把某些事情做得風生水起。風有多大?水有多深?與井底之蛙無異。
風——生,經過樹林,吹動那些細碎的枝葉,搖曳著,要不了多久,所有的動作就停止了,樹林還是樹林,還站在那里。到了我退休的那天,生活還是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更多的年輕人用其他武器和工具走在我們認為那是一條奮斗之路上,重復著我和上輩的生活之路。
一切,似乎與自己的本質、生活的本質沒有太大關系,有限的時間煙灰堙沒于生命遙遠的地方,無聲無息,明知為一種浪費,而無能為力,而冠以風生水起之名。
如果能夠破碎成花也好。
最奢望的是:長槍出擊、戰旗繞長風,這些,真就只是一種奢望。
對于太多事情我無法給予良好的判斷,做出讓自己徹底欣慰的事情。
只有一點:閱讀。閱讀是純凈和全能的,可以給至清的水增加無限的深度,可以讓渾濁的水靜下來。可以讓徹底滿溢的事物,空出一個回旋的空洞,深入或擴延,植物在空出來的地方蓬勃生長,綠色開始綻放,水在空出來的地方流動。
在綿綿的時空里,閱讀幫助我脫離無力的抗爭。
在每一個一百年里,都有數百種不同地域的文明,留下幾位大師的作品,舒展成闊遠的大地,供我自由行走,并享用。
我羨慕那些遠行于大地上的知行合一者,他們用故鄉的血滋養著自己,用生活中的坎坷,用身體來閱讀陌生的、熟悉的大地。感謝他們用文字記錄下這些,讓我得以與他們深切交流,讓我傾聽和妄想,他們的身體力行和文字成為我的泉水,滋養著我四分五裂的精神和干涸的河流。
沈從文就是其中一位大師。
他樸實至憨,他的文字是泥土隨意捏出來的,文字的世界,泥土的世界,土的氣味把我從瘋癲的奔跑中喚醒,讓我止語,讓我停止,讓我傾聽山在水里的聲音,水繞山的綿長。
從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開始,我一次次懷揣著沈從文的文字,行走在那山重水復的湘西,那里有繁雜的人群和靜謐的叢山。
我出生于湖南,在湖南生活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湘西的那些河流和重重疊疊的群山,那些隱藏于樹林和灌木里的小路,我每年都會有不同的機會去游歷。那個時候的我,整個身體和心理都處于警覺狀態,沒有放松過,肩膀、胳膊、腰、頭、頸、膝蓋、腳趾等主要部位都繃緊著,應對著各種人和事,沒有輕松隨意地面對大自然,也就無法如水般流淌在沈從文的波瀾之地,去感受和呼吸他生命的混合之音。
來北京后的數年里,都會經常打開《湘行散記》、《長河》和《邊城》,那片我曾經游歷過的土地,在文字的召喚下,在我的身體里復蘇,蓬勃而有生機。神奇的土地復活我的記憶,讓我無數次醉行其間。
雖久居城市,但一幅幅畫面固執地停留在我的頭腦里:迂回百轉的沅水河,兩岸叢山之中,三人撐舟而行,沈從文先生在船上,觀村看景,更多的是感慨時態,記憶中的燈火,圍柴火而坐的閑談,火光照亮的那些人影和臉……
1934年冬天,因母親病重,沈從文從北京回到湖南,乘車到達武陵,即現在的湖南常德。在河邊碼頭,他租了一條小船,沿著屈原和陶淵明曾走過的沅水溯流而上,二十多天的時間里,沈從文全部在這條船上度過,他每天以書信的形式,告訴新婚的妻子張兆和,他在千里沅水及支流上看到了什么。聽到了什么。又想起了什么過往之事。他隨性地與張兆和敘說著當時的心境,沈從文也知道,信到張兆和手上的時間,最快也在十天之后,所以,文字隱約之中多了一種自語的成分,想念著妻子,喜歡著這些山山水水,與曾經熟悉的人見了面,有的只有驚嘆。船上雖有流動的重疊的千山萬水,但更多的還是作者的孤獨和寂寞。
在寫給張兆和這些信件的基礎上改寫和梳理,1936年結成一部系列散文集《湘行散記》,成為現代散文的名作,共由十一篇作品構成。
湘西是沈從文的故鄉,常德亦屬于大湘西概念之中,20世紀20年代初,沈從文離鄉出走,十多年后再返故里,舊時的那些人與往事,一一重現于激情的現在。
《湘行散記》頭篇是《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
沈從文由常德去桃源坐船之前,坐的是一輛公共汽車,由這位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陪著,這是位懂人情而有趣味的朋友,也是位風流的主,對畫有些了解,他是專程來陪沈從文走一段路程的。
沈從文的作品是立體的,不是單純的游記和風情,有他自己的影子,有回來數十年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經歷,有湘西特有的人文情境,語言也是湘西的味道,不是純正的普通話。他筆下的那些水是輕靈的,山是重的,生長著枝繁葉茂的古樹。
他用文字隨意地營造著或空曠或幽暗的時空,蕩蕩回回,從現在的公車汽車,回到十三年前的那個小鎮。
他的每一篇作品中,基本都有一位個性鮮明的與他有過數次交往的朋友。每次都會出現在他觸手可及的視野中,或者是可視的虛空之間。
沈從文在朋友的幫助下,在桃源河街附近的船碼頭上,與人講好價格,船總寫好了保單,一切就緒,第二天就出發,開始他的船上生活。每個時代各有自己的規矩行市和路數。
常德、桃源于我太熟悉不過,這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的妻子就是常德臨澧人,我孩子的童年時光就是在常德度過的。1931年沈從文與丁玲營救胡也頻沒有成功之后,沈從文護送丁玲母子回的就是湖南臨澧縣,現在每次回湖南臨澧,總會經過丁玲公園,也會在丁玲廣場上轉轉。
因為我太執迷于沈從文的語言和他所寫的作品,無數次夢想著跟隨從文先生文字去他曾經到過的任何一個地方,用文字回應他,告訴他,三五十年后的湘西的模樣。《湘行散記》的魅力,船,成為我用行動跟隨沈從文的一種方式之一。船,隨他的文字走一遭。從河流到城鎮,沈從文在湖南的飄蕩、游歷所經之地,我都繪成了地圖,隨時準備租船而重游。回去了幾次,探聽到河道上建了幾個水壩,修建了幾個光榮的水電站之后,沈從文親歷過的幾個小鎮、山水碼頭和風景,如青浪灘、寡婦灘等諸多村鎮、風景都已經沉沒于水庫深處。
遺憾沉痛,但我依舊深愛這條河流,這是一條詩歌的河流,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之一。屈原曾生活于這河邊,也曾乘舟于這沅水之上,河聲也回響在《楚辭》里。沈從文在《湘行散記》的《桃源與沅州》篇中寫道:
在這條河里在這種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見于記載的一人,應當是那瘋瘋癲癲的楚逐臣屈原……估想他當年或許就坐了這種小船,溯流而上,到過出產香花香草的沅州。
沈從文以寫流浪軍人,湘西底層勞動人,以及求生存的性情妓女為主,寫花草不多,而在這里有一小段對香草香花細致入微靈動的描寫, “長葉飄拂,花朵下垂成一長串,風致楚楚。”文字一改那種“土”和至樸,而以細微、雅致亮相。
包括陶淵明的退隱,也在這條河流上。
在那些土得掉渣的文字里,文化的厚重與輕靈渾然一體,尤為重要的是作為作家的思考和反省不動聲色地融于其中,農民抗爭的鮮血,雜草的湮沒,四十多位犧牲者被拋入屈原所稱道的河流中,這一切,被流動的水永遠存封。沈從文說,本地人大致把這件事也慢慢地忘掉了。
作家不玩文字的,作家的靈魂的眼睛是應當明亮的,暗而復明,黑而復亮,是循環著的,不應當只是沉迷于山水的險奇峻峭,沈從文的深度和激情深含于文字中,不外露。
船到沅州,水手們上岸買些煙絲,對話和場景,都真實可摸。
從文先生喜歡這些底層活生生的水手和生意人,遠勝那些尋幽訪勝的知識分子,底層生活的豐富性,遠勝那些編造的戲劇效果。
在《鴨窠圍的夜》,沈從文的船在河上行了五天。下雪了,南方的冬天寒冷徹骨,何況是在河上航行,冷的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是我走這條水路,萬不會是冬天去的。夏天再熱,因為有水上的涼風,倒是另有種享受的。
在冬天的河流上行進,做生意的、運貨物的、接送客人的船,冷的夜,讓水手更加孤獨。大大小小三四只船,擁擠著停泊,到這樣一個有人情味的小鎮碼頭,水手們紛紛上岸尋找些特殊的女人,吃“葷煙”,更多的只是去烤烤火。那些屋子里的主人,大有背景和歷史,有退伍的軍人,有運氣不好的老水手,有寡婦等等。
那時烤火的方式,是典型的南方鄉里烤火的方式。
我很小的時候,家里就是這樣烤火的。在屋子中間淺淺地刨一個小坑,在上面架些樹根樹塊,柴火的溫度遠勝過所有的取暖方式,鄉里人常說,柴火溫度上身快,可以驅除濕氣。
沈從文的過人之處在于:突然之間,在虛虛實實的場景中,把一個人、一群人,更多的是一代人、一類人的不可思議的生死和生存環境細細地梳理成章。這些烤火屋里的主人不會有名字,河兩邊碼頭鎮里的人們也沒有名字,但成百個不同人物的命運都會浮現出來。
文章中寫到一些美麗的有想法的女孩,因懷上外鄉人的孩子,被沉潭。這事件發生的過程中,審判的族長、圍觀的鄉人、推她下潭的人,都是主角,讓人說不出一句話,只有看和沉重的份。

我們再回到這烤火的屋子,里面有些小細節,屋子的木板墻壁上,會有大大小小、紅紅白白的軍人、團總、催租吏、木排商人等頭銜的名片,我想到現在一些有小情調的酒吧,也是名片和隨意的簽名留言,制造些文化的氛圍。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這是唯一一篇以時間為標題的作品。因為這天,船將到達沈從文充滿了濃郁感情的辰州。
他在離辰州約有三十里水路的船上醒來,他是被一個極熟悉的聲音喊醒的,人醒了,那聲音還在耳邊,原來是辰州的河水,足見辰州在沈從文心中的重量,非一般文字可說的。
他寫到另一條擱淺的船上的水手,跳進水中,試圖用肩之力讓船離開沙灘,但浪咆哮著卷走了水手,其他人在岸上追幾步,人便不見了,一個生命在水中消失,于水手而已,這是常事。因為太平常,而震撼人。這樣的險灘與長長的激流,較多。
船過了灘和激流,進到平靜之處,沈從文坐在日光里,他離開辰州十多年,這是他的第二故鄉。
沈從文離開家鄉之后,就停頓在這碼頭上,他熟悉辰州的每一條街和每一個店鋪。
他溫暖地愛著這條河里的船和船里的人,那些日夜流著的水,和沉于水中的小石子,還是那樣細碎,他的開悟和智慧,都源于這里。
沈從文寫的就是他的生活,生活中就有那么巧的事情。在多篇文章里,他都會筆墨較多地寫到一個人。
《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文如其名。第二天清早,沈從文的船準備出發了,他的目光和心思落在一個叫牛保的水手上。這些水手待船一靠岸,就有一部分人上吊腳樓與相好的婦人去睡一個晚上。他們感情復雜,說是露水恩情也可以,說柔情萬種也對,從這些婦人身上,可以依稀從今天的湘西女人身上找到。沈從文眼中的這些婦人,沒有半點臟的感覺,有的,只是分別和快樂。牛保的陽剛之氣和靦腆之情,留于紙上。沈從文給了牛保四個蘋果,他又再次跑回閣樓給那婦人,其間感情和分享的愛意躍于聯想中。
這一天,沈從文的船全部在上灘,他欣賞著船舷邊奔涌的白浪。船,下午在一個叫楊家岨的地方停靠,這里不像其他地方停靠的船多,好像就他們一條船,沈從文有些擔心船上的水手下黑手把自己給黑了。不久,后面來了一郵船,與一小伙相識,在岸上一人家里烤火,突然進來一位讓沈從文驚艷的婦人,名為夭夭,夭夭打聽著牛保的消息,也對沈從文這位京城里的人有些羨慕。
沈從文在不經意間,把生活中的雜質在文字的河中洗滌掉,留些相關聯的事件,用文字串起來,就有那么巧的事,而遠比那些發生在影視里的喜劇效果來得有趣。
其實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只是被太多的瑣事所遮蔽。
沈從文幾百字描寫夭夭婦人,一個水靈靈的夭夭就落在紙上,尤其夭夭在文章結尾唱的那首《十想郎》,是給誰聽的?牛保?沈從文?或者是天性的愛唱和打鬧而已,都可以想象。
十天了,沈從文一直坐船而上,他也比較集中地寫了這些將與他共同度過二十多天的水手們。他知道那年齡較大的掌舵者是八分錢一天,攔頭的水手是一角三分,那個學徒小伙計一分二厘一天。這條河上有十多萬人這樣過日子,可見那時的河流,以及兩岸是何等的繁華。
沈從文的豐富在于他進入了身邊人的世界,從水手大伙計的過去,到現在的憨實,讀來生動。
在船艙里,我與沈從文一起等著黃昏的到來,觸及傷感的向晚,看陽光幽淡。沒有辰河上的奇異光彩,沒有人生的沉浮顛覆,就不會有《九歌》的驚魂。同樣,沒有至樸的水手和吊腳樓里的鄉親和婦人,也就無從有沈從文那波瀾不驚的《湘西散行》。
十二月七號,沈從文來到他十五年以前來過的箱子巖。那些曾經的記憶,依舊縈繞于樹林和叢山之中。看著那些剛下水的船,他要水手們把船停泊在十五年前待過的地方,在一家小飯鋪里,他與一群正直的鄉下人一起烤火,談他們的生活,他才感覺到自己真正回來了。說這里是“小飯鋪”,用這樣的名詞表述,應該只有湖南南方才有。那些可以吃點飯的地方,只賣點小小的生活用品,如小酒、小煙、鹽和味精的小店子,就叫小飯鋪。有些也指可以住宿的地方,共同點是,來往的人多為附近鄉鄰,經過這里喝喝茶,聊聊天,烤烤火,說說閑話,順便買點家里需要的小東西。這樣的小飯鋪,遍布湘西的各個小小的交通點。基本是不會有外地人。人們坐在一起,每次都會不約而同地談到某一件事,或以一個人為主要話題,所有的褒和貶,都不是惡意的,最多的是在調侃中帶些羨慕和批判。鄉村的很多道德也是這里的一些強勢人說出來的。
沈從文那次看到了跛腳什長,出現在小飯鋪里,這是一個鄉村居民的靈魂性人物,戰爭、殘疾、生意、倒賣、煙、玩花姑娘,都是他的關鍵詞。沈從文就在這些親歷中,用湘西的口語寫活一個個湘西大山里的人。似小說,而不是。似傳奇,也不是,都是生活中的大活人,真真實實。沈從文深切的感情濃濃郁郁地懷抱著湘西的綠色。
政治、軍閥、反抗、民風,沈從文一一寫到。
在之后創作的長篇小說《長河》的“題記”中,沈從文的船一入辰河,他就感覺到一切變了,一切在變化中墮落,山里人正直樸素的人情味幾近消逝,人們的敬畏之心隨著破鬼神的動作而消亡,現代的文明膚淺地在這里如碼頭的垃圾,漂浮水面。也有一些公子哥們花著祖宗的錢,在外面游樂,享受現實的腐朽部分。深刻的思想和學習,是沒有的。
批判中更多的是痛惜。
責任編輯張明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