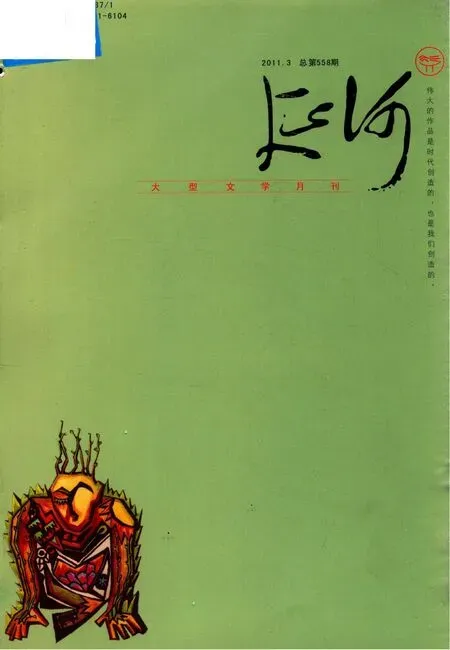中國出了個晃晃叫李更
中國出了個晃晃叫李更
一
我與李更相識已有三十余年。記得1980年春天,湖北省作家協會在我的故鄉英山縣桃花沖林場招待所舉辦一個小說筆會。參加者有鄢國培、祖慰、周冀南、王維洲、王繼等人。組織這次活動的,是當時省作協駐會副主席李建綱。桃花沖處萬山叢中,離縣城六十余公里。縣城每日有一趟班車到達一個名叫紅花嘴的小鎮,自此進入桃花沖還有十五公里,雖有簡易公路,卻無班車可通。一日午飯過后,李建綱忽然對我說:“我兒子今天從縣城搭早班車來桃花沖,按理應該到了,怎么不見人影?”一干作家,只有我是當地人,于是自告奮勇沿簡易公路去尋找。當時的青年作家王繼陪同前往,因為只有他認識李公子。沿林場招待所下行大約五公里左右,忽見一位瘦若麻桿的少年正對著路側一處山洞出神。王繼喊了他一句,麻桿少年沖著他一笑,說:“這洞內有泉水流出,還有燕子飛。”樣子稚氣,卻滿臉興奮如科考工作者。
這位麻桿少年就是李更。
從那以后,就算認識了李更。但來往不多。其因是他太小,還是一位高中生,但與他父親李建綱卻過從甚密。建綱是著名小說家,代表作有《三個李》、《坐火車玩兒》等,文風樸實而幽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湖北文壇,占有重要的一席。
說實話,認識李更的時候,只把他作為李建綱的兒子看待,并未意識到這麻桿少年日后會成為一個特立獨行的文人。
記憶中,李更大學畢業就去了珠海,在《珠海特區報》謀了一份編輯的差事,并且一干就是二十五年。論資歷是元老級的人物,論職位還是一名普通編輯。在別人看來,他這際遇似乎有點蹭蹬。但人各有命,豈可一概而論。不必美譽他“安貧若素”,也不必說他“不求聞達于諸侯”,只能說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作家的造詣,相比于他的小說家的父親,完全可以說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二
李更開始寫文章,大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其時正是我文運蹇滯下海經商的時期。我那時不讀任何文學類的報刊雜志。所以,對李更早期的文章知之甚少。記得有一次,一位作家老朋友地我說:“你還記得李建綱的那個兒子李更嗎?那家伙可是文學界的一根刺兒,看誰不順眼就扎誰,大家都躲著他。”聽到這番評論,我心存疑惑:難道當年那個站在山洞前一臉興奮的麻桿少年,竟成了牛二式的潑皮?
三年前,我與《文學自由談》的主編任芙康先生同時擔任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賞讀入選作品之余,常得暇聊天,有一次他問我:“你認識李更嗎?”我立刻想到關于“刺兒”的評論,便回答:“李更的爸爸是我老同事,老朋友,聽說李更文章寫得犀利。”任芙康說:“李更經常給《文學自由談》投稿,他的文章從不趨炎附勢,有自己的見地。”聽到這番評價,我內心高興。因為芙康自己就是一個不趨炎附勢的人物,他的評價可謂惺惺相惜。
去年,我在《文學自由談》三月號上讀到李更的文章《大聲公》,第一段就把我吸引住了:
那天在鳳凰衛視的竇文濤節目里看見德國的漢學家顧彬,他果然是敢于說話的。但是我在他身上沒有看到德國人的嚴謹,倒很有一點當年黨衛軍的嚴厲和戰敗國的憂慮。
果然犀利,果然潑辣,果然無所顧忌。在好好先生大行其道的當下文壇,李更果然是一根“刺兒”,但他并不是逮著誰就咬誰的瘋狗,而是有的放矢、對當下文壇的不正之風始終保持著批判意識的獨行俠。
三
李更的雜文,在讀者中影響廣泛,仇者仇之,親者親之,不用我更多的繞舌。但是,作為詩人的李更,對熟悉李更的讀者來說,恐怕是個新鮮的稱呼。日前,我收到李更寄來的他將要出版的詩集,附上不到一百個字的便條說:“你看看這些詩值不值得你寫幾句,如覺得不夠格,就不勉強。”
在李更的內心中,有親情而無權威。他不大看地位、名頭,但絕對要看交往的“舒適度”。讀了便條,我隨手翻開他詩集的打印稿,只見以下這些句子:
哪一天自己也會像他們那樣
白發蒼蒼坐在那里
固執地把交易所
當自己的養老院
《悲壯》
在中國房價
像長征火箭一樣升天的時候……
買
還是不買
這不是一個
哈姆萊特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像買自己的棺材那樣
趕快作出決定
《海倫堡》
四十八年以前
在這個叫蔣家墩的地方
呼爾嗨喲
中國出了個晃晃叫李更
《紅鋼城》
我們已經比不了官大官小
也比不了錢多錢少
我們只有比誰比誰能熬
《我們終于熬過了2008年》
其實
小人是有素質的
你如果
不具備那種素質
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花錢
都做不了小人
哪怕裝也裝不像
《小人是天生的》
我們認真活下去
已經不是為了享受生活
而是為了看到一種結果
想知道結果離真相有多遠
《自言自語》
四
讀到以上這些詩句,相信讀者會有一個判斷:詩人李更還是那位雜文家李更,同樣的調侃,同樣的冷峻。
雜文詩在中國素有傳統,古人不說,單是新中國成立后,雜文詩就出過不少名篇。如袁水柏先生的《馬凡陀山歌》,趙樸初先生的《某公三哭》,聶紺努先生更是雜文詩大家。有句俗語說“嬉笑怒罵,堪成文章”,移植到雜文詩中,便是“嬉笑怒罵,皆成詩趣。”但是,近二十年來,寫雜文詩的人已越來越少了。不是社會上值得批判的東西大為減少,而是文學批判社會的功能大為減弱。李更僻居珠海,卻是“位卑示敢忘憂國”,說憂國太大,憂時可也。瀏覽詩集中的作品,沒有士大夫的優雅,也沒有小文人的閑適。處處流溢的,既有草根階層生活的窘迫,也有對庸俗生活的譏諷。即便是懷舊,也是“苦惱人的笑”;即便是向前看,他也認為“把世界交給陌生人”有點讓人擔心。
李更詩作中的妙處,在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以,我只是想引導讀者來讀讀這本詩集,至于評判,還是那句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更在詩中自嘲地說:“中國出了個晃晃叫李更”。晃晃是武漢的新方言,有無所事事,管管閑事,做不了正經事,無事找事等諸多意義。當然,上述種種還不能概括“晃晃”之妙。在日常生活中,晃晃為貶義,說某某人是晃晃,大家就會對他敬而遠之。李更自稱是晃晃,依我看,這是對那些“正人君子”的巨大反諷。就像他的這些詩作,不能登上被一些“大師”們控制的“大雅之堂”,但是,置于另冊,相信還是有不少讀者會喜歡它。
2011年元月1日于閑廬
責任編輯: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