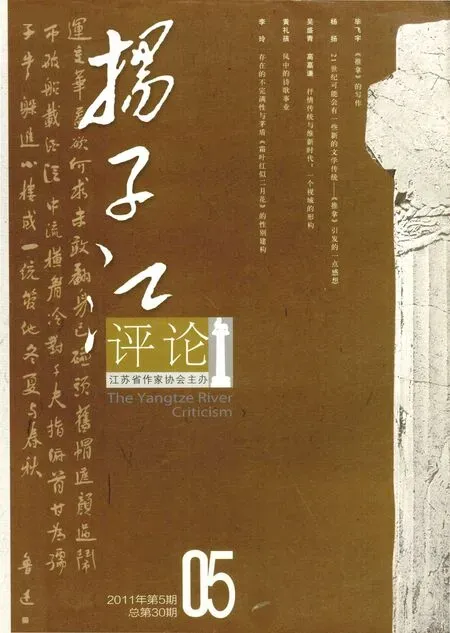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一個視域的形構
吳盛青 高嘉謙
古典詩詞與現代文學史視域
1923年,同光體詩歌的代言人陳衍,在《近代詩鈔》刊行之際,作五言古詩六首,抒發心情。其中第二首如此寫道:
漢魏至唐宋,大家詩已多。李杜韓白蘇,不廢皆江河。而必鈔近人,將毋好所阿。陵谷且變遷,萬態若層波。情志生景物,今昔紛殊料。染采出閑色,淺深千綺羅。接木而移花,種樣變剎那。愛古必薄今,吾意之所訶。親切于事情,按之無差訛。①
詩中表達了愛古人也不薄今人的態度,詩歌的歷史就像陵谷變遷,綺羅染采,今人通過移花接木的轉化努力,可抵達種樣剎變、脫胎換骨之境界。陳衍編輯《近代詩鈔》所展現的與時俱進、不因循守舊的姿態,意味著他對近人詩歌有披沙揀金的評判眼界,也在詩教的承傳上彰顯個人見識。盡管這部收有五千余首,從咸豐到民初369位詩人,共24冊的《近代詩鈔》順利問世,但詩的寫作和發展的環境已分崩離析,詩的核心精神遭逢文學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的抗逆,一種惘惘的威脅籠罩在詩的生產和傳播空間,讓近代以來的古典詩詞②和詩人都逐漸走向了歷史的邊緣和暗角。在標榜時代精神的現代文學史敘述中,他們自然地被束置高閣,甚至被刻意遺忘。
長時期以來,以“五四”為源頭的新舊嬗遞成為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唯一的范式。帶上“歷史的眼光”,意味著學者握有一把刻度清晰、單線進化的計算尺來勘探文學演進的過程。③這個過程甚至成為了政治歷史的另一翻版,1919年、1949年也由此成為文學史上大寫的日子。④在此類刻舟求劍式的文學史的表述中,舊文學要么在“五四”的高歌猛進中潰不成軍,要么將它在現代的持續存在視作是舊文學的負隅頑抗。舊形式在新時代,透過現代性的鏡片,被先驗地被涂抹上保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些都昭示了我們批評視域里長期因意識形態的作祟而形成認知的封閉系統。同時,這類表述也經由將文學史長期用作教材的方式,影響了幾代人的文學教育。陳思和在九十年代初曾生動地描繪過文學史的寫作狀況:“像變戲法似的隨著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編造文學史的神話。”⑤
當文學革命風起云涌,白話文運動替“五四”新文學建立典范之際,胡適卻坦言詩的堡壘是他號召的文學革命中最難攻下的一役。他挑明古典詩學的語言問題是必須被征服的對象,文學必須選擇一套可以表述“當前的時代”經驗結構的思維,等同換一口腔調來重新表達自己、認同自我。新文學與現代性的關系由此更為緊密。“五四”一代人對古典文學的重新評價,改變著文學史的價值觀,也重寫了文學典律。⑥在此語境下,以白話文為主導性的現代文學史幾乎遮蔽了20世紀的傳統詩詞的寫作。⑦隨著文學革命的發展態勢,古典詩詞作為文類被推向邊緣化,但那些被視為舊派或傳統文人群體的持續寫作,依然在民初以后的文學場里占據難以忽視的位置。古典文學,從廣義的“文”的概念中分化出來,獨立成為文學學科,更在現代學院體制的創設中登堂入室,詩與詞建立各自傳承的學術譜系。⑧隨著詩社的普遍成立,以及遜清遺民避居租界而形成圈內人的聚集和交流,文人雅集賡續不斷。相對新文學運動的各種社團與流派主張,這些寫作古典詩詞的文人,卻在傳統的詩社活動與讀者圈里找到延續文學生命的渠道。對日抗戰開始,詩社團體也紛紛成立,雅集活動并不中止。無論抒情言志,表現民族氣節,或刻畫亂離苦難,古典詩詞在形式意義上,契合了憂患意識與文化民族情感。民初以降古典詩詞寫作的生生不息,顯然拋出更為嚴肅的議題。詩人以詩為志,甚至安身立命于其中,暗示了古典詩詞的文學儲備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文人養成,形塑了其自我圓融飽滿的美感經驗的表征模式,當然這類模式在離亂的時代里亦遭遇表達的危機。換言之,古典詩詞在現代情境內隱然展示著其不可輕易替代的文類意識與功能,其豐厚積累的文化資本,不可能是一場文學革命就能消耗殆盡的。這提醒了我們在現代文學史視域下重新審視古典詩詞的寫作與生產,成了重要議題。
針對現代歷史語境與詩歌文本之間的互動,在方法學上我們有如下的考慮:首先,牽念于一個歷史時間點、事件或是單獨的文本作細部的描繪。近年來陳平原提倡“回到歷史現場”的治學方法,投身歷史的情景去把握在特定的語境下文學與文化事件的意義,以期對宏大學術話語進行糾偏。⑨堅持從文本、事件、細節而不是從固有的觀念出發,注重的是將文本作歷史化的處理。其次,歷史的具體細節與文學史描述體系該如何做一個銜接?我們的每一次細部的述說都只是在接近本體論上“真實”的歷史現場邁進的一小步,我們穿不過歷史時間的隧道。“時間距離”是意義產生的場域。⑩史海鉤沉,讓這些被人遺忘了的記憶浮出地表,并不是為現存文學史拾遺補缺,填補空白。而是通過重建歷史現場的多音復義,去思考舊文學的負隅頑抗是否可以撼動現存的文學史詮釋框架。甚至可以考慮說,是否一定要拼出一塊新舊更替,有終極目的的文學歷史圖景。歷史演進的淵源與線索往往多元并置,回旋往復,一部線索清晰的“進步”的文學歷史,往往消弭了異質的聲音,遮蔽大塊斑駁的色澤、時代的錯誤(anachronism),還有匪夷所思的基因突變。
歷史是一種敘述,這類說法如今頗為流行。這個說法提醒我們對史的敘事性的特征保持清醒的認識。歷史作為敘事,并不是在漠視鉤沉索隱的材料功夫,而是強調歷史文本的真實性,文本與文本之間的聯系框架,以及文本與歷史學家譬喻性的語言描述之間的關系。?宣判文言死刑,仿佛一夜之間就催生出新的事物,誕生與死亡互為因果。在此類我們熟悉的文學史敘述中,新與舊一刀兩斷,毅然決然,但是這個故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在講述,缺少血脈精髓、五臟生氣,更有敘述者一廂情愿的主觀臆想。講一個生動的歷史故事,我們需要在材料的局部的真實性與闡釋視角的豐富性之間找到有機的平衡,描畫它的千頭萬緒,它的起伏跌宕,尤其關注其間被壓抑的聲音與反抗的實踐。一個世紀之后,當我們在對伴隨現代性而至的歷史暴力了然于心的前提之下,這些當下情境中的歷史的哀音,模棱兩可的思想,文學形式的靡麗艱深化,是否同樣可以進入我們文學歷史寫作的范疇?在新/現代文學史與現代性幾乎劃上等號的同時,我們該如何去描述沒有現代性的、反現代性的或是在現代性的大框架里左支右絀的抒情實踐?
作為文學歷史的研究者,我們每一個個體都有闡釋的權力,撰寫的是屬于個人的文學史。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舊體詩詞能否被寫入現代文學史的命題是一個偽命題。如果純粹將現代文學史視為現代性文學經典生成的歷史,以此拒斥和忽視文言寫作的位置,那么這個定義的理論預設——白話文學等同于現代性,大有可商榷之處。同時,本書的一個目標即是勾勒傳統抒情文類或隱或顯地與現代性進行辯證的線索。此外,我們亦無意提倡刻意去書寫“另類”(alternative)的文學史,在新文學史之外再形塑一種文學歷史的描述體系。“另類”作為概念的局限性在于它已隱含了對正宗的確認。本書的作者達成的共識,旨在超越“五四”論述框架之后,描畫文學變化的多重軌跡,共同關注在現代性發生的環節中,新與舊的交織角力,乃至共生同謀的關系。面對浩瀚如煙、亟待整理的近現代詩文,“從歷史出發一部分一部分地對待一個事物”,?細究各部分交互扣聯,是我們切入文學史秉持的基本方法。
詩與維新時代
本書的框架建立在1870年延續到共和國初年,集中辛亥鼎革前后的文學寫作,尤其以古典詩詞為大宗,廣義的抒情文類為主要的考察對象。這是我們界定的歷史研究領域?,而這個預設顯然有明確的意義指向。王德威在其影響深遠的《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本書正是順接這樣的思路,跳出“五四”作為現代文學濫觴的論述框架。王德威將現代性的發生在時間表上向晚清的推進,并不是簡單的對歷史事實——現代性的源點的操作,而是希望通過對近代小說多聲喧嘩的狀態重新描畫,來勾勒文學現代性迂回曲折的道路。換言之,此說法的內涵不在于斷然否定“五四”典范的“變”與“新”,而是提醒已典律化的“五四”文學、文化和精神,可能在一個“起源”或“起點”的意義上簡化或窄化了民國初年種種的文學生產背后對知識、正義、欲望和價值的重新定義和追求。?而我們將視域拉回到晚清,不過是正視晚清文人如何調動傳統資源以應對和解釋他們所面對的新時代,并為創造意義而做的種種實驗。
“維新”一詞,典出《詩經·大雅》,經由近代日本,始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變革圖強之意。本書的“維新時代”從廣義上涵括晚清尤其戊戌變法以降,中國社會激進變革,中西思潮相擊蕩的時代。晚清以追求啟蒙、新知為尚的主旋律,在后續的“五四”運動、革命文學中繼續生發張揚,成為主導現代中國的精神結構。以詩歌為主體的抒情傳統與追求現代化的精神氣質相呼應,晚清與民國詩文是當下境遇、歷史模范與個人內在心境互動激蕩下的產物。維新時代帶動改革的激情,從國族到個體被迫積極向現代轉化,卻同時有著歷史的反諷與困頓。知識分子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變的不僅是國家局勢,更是文化根本。他們經驗時代的喪亂和暴力,個體意識一再遭逢日常性災難和斷裂,以致書寫的形式和內容,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感時憂國”和“涕淚交零”的集體氛圍。詩歌在捕捉到了時代風云變幻的同時,更有力見證了創傷性的文化經驗,呈現了一個強行植入的現代性所帶來的種種痛苦的癥狀。陳三立有云,“遭際極艱而情蹙”,正是極艱的歷史情境給舊體詩創作帶來了嶄新的駁雜色澤、銳利的生命體驗。無論是驚心動魄的文化裂變的感受,還是家國淪覆之痛、兒女切切之情,詩歌中呈現了前所未有的歷史的糾結與復雜的現世心態與情緒。直面歷史時刻時主體經驗頓挫有力的回應,文人的滄桑心境,都成為建構復雜的現代主體性不可或缺的環節。
當我們觀察詩面對浩劫創傷的處理,“詩史”的敘事傳統難免誘惑詩人去象征性的表述災難。他們或由此進入“詩史”的語言系統,又或透過抒情主體介入巨變所選擇的視角,以帶有悲劇性氛圍的自傷、流亡、哀情來面對歷史,呈現災難背后主體與巨變的情境交織認同的審美姿態。我們由此改變了對詩的圓融和諧的象征精神的認知而隨著詩人深入巨變災難的內部,理解陳述主體的惶恐不安,以及處身歷史當下碎片狀的存在感。因此我們更能掌握“震驚”?如何成為詩的現代性特質,透過“震驚”深刻顯示了詩如何走入革命歷史、悲劇氛圍,招魂或復古式的懷舊。詩作為一種手段和載體,更清晰紀錄著詩人存世的矛盾和沖突,并精準勾勒在時局的轉化和危機中,詩人如何表現抒情自我體驗的幽暗情懷。我們思考的出發點并不是傳統的“以詩證史”,而是堅定地要將詩歌中呈現的震驚、猶豫、悲劇、反諷、歷史脅迫的力量等寫入現代性的歷史中。?
與此同時,舊體詩詞作為維新時代的古典文學遺產,構成一種格式化的古典文化氛圍。詩人在歷史當下追憶“古典”時代,意圖在日常生活的缺罅和斷裂之間,藉由詩“填補圍繞在殘存碎片四周的空白”。?所有在帝國崩毀、新文化運動后被棄置及一再改變的經驗及記憶,在抒情詩的安穩結構里找到了棲身之所。如此說來,傳統詩教的言志抒情,可興可觀,提示了詩人處身在除魅與暴力相間的現代文明世界的根本意義。
在維新時代里討論詩教,不能忽視黃節的獨到見識:“詩之所教,入人最深,獨于此時,學者求詩若饑渴。”?近代知識分子肩負詩的使命,或以詩救人心,展現詩教從最純粹的詩歌鑒賞與表意實踐,導向召喚民族的文化心靈作為寫作的倫理和歷史心志。由此就不難理解,堅守詩的堡壘,尤其成為遜清遺民追懷傳統的媒介與對象。他們藉由詩將自己投射到文化長河,以解救現代意識內的精神危機。而在遺民之外的廣大士紳群體,他們經由自身的傳統教養所延續與建構的文化道統,仍以詩的生產與傳播,清楚表現出強烈的文化意識。詩由此深入為生活的組成部份,在復雜的政治糾葛與文化想象之間,他們以身教和著述試圖采集古典文化“光暈”(aura),重新辯證與重建傳統文化的存在意識。我們或以本雅明筆下“歷史的天使”視之,看他們站在時代暴力的面前,伸手觸及堆積的歷史殘骸之際,卻隨時被現代性的風暴吹得七零八落,或卷向不知名的未來。
以上種種面向強調了詩與維新時代的復雜關系,相對現代新詩必須重建其表意格式和審美經驗,舊體詩的文類意識卻接近于一種詩與魂結合的形式,表征民族心靈與文化美學的集體想象。藉此我們可以再度審視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的辯證意義。抒情傳統作為一個現代學術情境下建構的一套話語,更由此提供給我們一個文學史視域的觀照。
抒情傳統與文學史
20世紀70年代以來,陳世驤教授以《中國的抒情傳統》及系列文章,揭示和命名了“抒情傳統”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詮釋概念與認知框架。接著高友工教授從西方語言哲學的概念語匯,在中國文化史的基礎上,進一步界定了一個占據主導意識型態的“中國抒情精神”,并從文論、詩律、樂論、書論、畫論等層面提出“抒情美典”的辨識與歷史面貌。如此一來,“抒情傳統”經由系統的知識化處理,奠定了宏大的理論架構與知識空間,更擴大為中國抒情美學體系的研究路向,成為東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相繼投入與深耕的重要論題。學者們分別在不同的研究面向對“抒情傳統”做出深刻的演繹和思辨,由此展開的對話、重構與衍伸,建立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版圖內具有強大解釋效力的一套抒情論述和學術傳統。
70年代末以降的三十年間,抒情論述的大量研究成果,分別從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學史的角度衍生出各類議題,并從不同文類、源流辯證和論證“抒情傳統”的存續和意義。在古典文學方面,包括臺灣學者蔡英俊、龔鵬程、張淑香等人對重要古典詩學觀念的清理和解讀,厘清“抒情傳統”概括的內涵和具體作用;同時又深入本體論、發生學角度思考美感經驗、抒情本體,抒情自我的構成,對應“抒情傳統”展現的一種現象學意義的自覺。另外,對“抒情傳統”的回應,還包括站在現代文學立場,思考現代情境下對“抒情傳統”的“召喚”與“發明”,如何成就中國文學現代性——現代主體的多重面貌,以及此一傳統元素的角色與功能。包括陳平原、王德威、陳國球、黃錦樹等學者都注意到了“抒情傳統”的延續、轉化及其構成的文化邏輯,顯現了其在現代語境內的辯證潛力。因此,“抒情傳統”作為中國文學有效的詮釋框架,以及這套抒情論述和典范的產生,在文學史的觀照下就有了理論梳理和反省的意義。
不論抒情是文類概念,還是一種情感結構、史觀,甚至是一套思維方式和詩學規范,抒情“話語”的建構提示了我們在現代情境中對中國文學史觀的洞見與盲點。因此,我們對“抒情傳統”的思索,可以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為“抒情的文學史”的理論視域。這一概念本身,旨在展示并探究抒情“話語”如何與文學史對話,抒情是否被后設為一套表述文學史的機制?“抒情傳統”生成的歷史條件為何?同時重新檢視抒情“話語”運用的情境脈絡和有效范疇,在跨領域的多元視域內為“抒情傳統”探索出可能匯通經學、史傳、思想史等領域的發展路向,以及探討現代文學系統內中國“抒情傳統”如何展現其美學和政治的向度,為中國現代性提出繁復的辯證意義。尤其當我們將抒情傳統的觀照放在近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那是小說地位已大幅躍升、文類結構重新洗牌的時代,透過抒情傳統的切入和考察十九世紀末以降文學史各環節之間的關鍵性轉折,可以有效展示抒情傳統在現代流變的豐富差異。在本書關懷的晚清至民國時段,“抒情的文學史”因此是一次省思和架構抒情論述的新起點。
現代性觀照下的抒情主體與形式
王德威是近年努力探討“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議題的重要學者。在一篇有著導論意義的重要論文《“有情”的歷史》中,他明確提議在革命、啟蒙兩大話語之外,將抒情作為現代主體建構的另一重要面向。他提到:“抒情傳統的關照對于我們持續思考中國現代文學,以及中國文學所呈現的現代性問題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主軸。”?現代性一詞,涵蓋廣闊甚至歧義紛出,詹姆遜近年提倡將之視為一種“敘述范疇”(a narrative category),局限于審美領域,可以用來敘述現代性的不同情境。?在西潮拍岸的晚清,本土的抒情傳統在新舊秩序的更替中面臨沖擊和變動。其間的成功轉化,其間的偃蹇困頓,藏而不露的現代性線索,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文學演進的螺旋往復、錯綜矛盾的狀態。文人對現代性的掘發和辯證,既有選擇地調動傳統資源,亦對他們所處的時代創造意義和解釋。這種種的努力探索,恰恰構成我們與世界對話的重要面向,且豐富和提供了我們探索文學現代性的多種可能。本書中所有的文章都從不同的側面直接或間接地敘述了個案中的現代性議題,勾勒出現代性視野觀照下的“傳統”抒情主體與形式的多重面貌。
當詩人直逼現代歷史時間,而陷入內部自我的抒情時刻,抒情詩因此生發了其作為詩人存續與自我證成的邏輯。抒情自我的主體性如何在現代情境中被表征和呈現,文人寫作如何利用傳統資源,安頓自身的處境,進而創造個人在此時代際遇中的意義,顯然都值得深究探析。這指出了文人的古典詩詞寫作響應、延續和轉化了他們創作意識內的抒情詩美典,重新鑄造他們在此現代情境下文學意義內的美感經驗。尤其舊體詩詞賴以存續的語言表達模式(無論格律、修辭和語言的合法性)被文學革命炮轟,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檢視古典文學的現代生產,意味著此抒情文類也正檢視著其生產的意義如何發生效用,抑或辯證和自我證成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言下之意,在傳統文化落幕的維新時代,以舊體詩詞為骨干的抒情傳統所持續堅守的寫作態度和立場,且以頑強的生命力在新文學發展的不同階段,展現了舊形式的誘惑。這是一個“啟蒙”視域下頗有時空錯位的文學景觀,卻也是詩與維新時代的辯證。這是抒情詩/抒情傳統觀照下的提示:文人的主體性如何在廣義的抒情文類,自古延續以降的古典傳統中展示此一抒情自我/主體性在現代情境下書寫的脈絡和意義。我們以抒情作為切入這些古典文學生產的觀察視角,提出了兩個值得省思的面向:首先,舊體詩詞在現代情境的持續書寫,帶出文人浸淫和共享的抒情傳統的實踐方案和現象,其在背后反思和反芻的傳統資源,顯示了創造出其依存和寄托的民族精神和中國文化邏輯的企圖以及歧義紛出的實踐。這種現象不但暗示了文學革命劃分的新詩時代,遭遇到功能與形式的瓶頸,而且同時提醒我們舊體詩詞總能自尋出路,在不同環節展現其蠢蠢欲動的文類意識。舊體詩詞背后藏有的另一層文化編碼,昭告了一個審美意涵上文化共同體的想象。再者,抒情的主體如何去辯證和轉化出自身的文學力量以及美學經驗?寫作舊體詩詞的文人的審美趣味,他們對當下情境的處理和創造,以及他們試圖確立的審美現代性,如何在一個宣揚啟蒙與革命的維新時代找到生活實踐和論述對話的方式?細究抒情的實踐與形式在面向世變時所作大小不一的調適或不適,誠如胡曉明表達過的,古典的詩學因而“才具有了古代不具有的思想意義和價值緊張”?。
在考察晚清與民國詩人面對時代變局時,尤要關注文本內部及其語言形式的特質,以及形式與表述心境、生存體檢之間形成的張力。?一方面我們反對將詩歌研究作非歷史化或時間性的處理,而另一方面當我們以現代性的一套理論話語來觀照抒情傳統,必須考慮抒情文類的因為形式而帶來的一些特殊性。延續了兩千年的古典詩詞傳統,絕對承載龐大的美學經驗,熟爛格式與定型化的文字表述形式,如“感時書憤、陳古刺今、述懷明志、懷舊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說禪慕逸”等構成“情感內容的相似性與連貫性”?。千篇一律的抒情言志、使事用典,或許已經符碼化,但是在異代異時,在迥異的文化語境里,可以被移花而接木,化陳腐為新奇。也就是說,一樣的吟風弄月,一樣的偎紅刻翠,我們必須思考在不同歷史語境中催生的新意,以及對讀者產生的不同意味。即便形式與情感的內容改變甚微,但社會與文化語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動。文言在晚清到民初的興盛是時空錯置的大展演,彰顯的恰恰是舊形式在新時代的再生產意義。而這類“相似性與連貫性”在一個轉型的時代,對那些擁有儒學教養與抒情資源的人來說,恰恰意義深刻。詩人往書寫傳統回歸,將自身鑲入古典抒情序列,用典故與熟練套路來應對、模擬眼前困境,為自我作為歷史主人公的當下,延續或獨創一個屬于自己的古典詩格局。抒情詩人正是藉由古典詩詞走入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成就自我在當下的意義。
再則,抒情詩歌,有別于敘事文類,呈現更多地對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抵抗。當我們堅持不懈要在舊體詩歌中尋找時代新內容時,不可否認它常與現代社會發展步調不一致甚至毫無瓜葛。超越、永恒、崇高等字眼,在當代“后”字當頭的研究理路中幾乎成為了敏感詞而被輕易屏蔽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說法,也早已深入人心。維新時代的詩歌中固然留下了許多易于辨識的時代標記與風格,但是不可漠視的是,古典詩歌作為一種高度形式化與風格化的寫作,有其穩定規范的特征,常常與歷史當下的物質現實不直接建立起指涉關系,或是說這種關涉必然要經過長久積淀下來的文本傳統的過濾。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對泰戈爾的研究或許有參考意義。他指出,如果用發展階段論來審視泰戈爾的詩歌,就會發現其作品缺乏政治性,無甚新意。浸染民族主義思想的泰戈爾在文學創造性的活動中有勞力分工,典型的孟加拉村莊,在其小說與詩歌創作中呈現出兩種矛盾的形象。他在詩中堅持描繪豐饒和平的農村景象,顯示現實主義的缺席與政治的疏離。查克拉巴蒂鄭重指出,“詩歌的功用在于在歷史時間中創造停頓,將我們帶入超越歷史的空間。此另一空間就是泰戈爾所謂的永恒。”?這個說法聽上去或許并不新鮮,但是放在舶來品的現代性與殖民地文化相沖擊的論述框架中則意義顯明。泰戈爾的例子提醒我們,守成與新變在一位作家身上亦可以有多重曖昧呈現。而在新文學作家中,無論是“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還是以“骸骨迷戀者”自稱的郁達夫,都在舊體詩中寄托別樣的生命隱喻,更是眾所周知的例子。抒情詩歌對歷史化有顯豁的抗拒,但是這類抗拒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條件下的文學行為,我們亦可以從中搭出另一種歷史暗潮洶涌的脈搏。
有關文學形式與內容的話題,中外前輩學者有大量的理論表述,實非一兩句話可清楚厘析,在此不再展開,僅想提倡關注文學形式的中介意義,表與里的湊泊。一個維新的大時代里,文學的風格與類型,師法的對象與文學的美典,新語匯的嘗試或排斥等等,呈繁復多樣的形貌,其中既可以有對形式的精心守護甚至變本加厲的運用,也可以有對形式與經典的小心翼翼的修正乃至激進反叛。晚清的詩歌在實踐上(如新媒體的利用)與詩學理想的表述上(如詩界革命的觀點),都有大張旗鼓的新變。但詩藝本身所帶來的變化往往是極其微妙的,引用寇志銘的說法,所謂的“微妙的革命”?。在形式與語言的縫隙中,滲透進了一些需要細心辨識的現代性的質地。這些細微的差別,或許喻示了詩歌傳承轉化的某些軌跡與契機,值得今天的學者重視與玩味。
柯慶明曾指出,在文學歷史的論述中,學者往往偏好發掘其中的新穎與變化的美感知覺,將之視為那個時代的成就與代表,而忽略了那些臻于圓融完美的重復“仿古”之作,其實亦大有可觀之處。?新異與故常是流動而相對的概念,古人喜從形式的角度來談詩歌“生”與“熟”的矛盾統一,詩家顯示的是“熟后求生,密后求疏,巧后求拙”的追新心理。?現代文學研究者高舉現代性的大纛,自覺地求新求變是現代性的本質特征。此類嗜新之癖幾乎在所難免,但是至少我們需要對我們的偏見保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援引了詹姆遜的說法,現代性是情境中的“敘述范疇”。摒棄“新”眼光,甚至可以說,晚清與民國年代的古典詩詞,作為一種在被迅速邊緣化(或是說將被重新定義)的文類,在退幕前帶著鐐銬舞出了美侖美奐的卓約風姿。同時代的俄國白銀時代的杰出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曾以其天才的敏銳,嘲笑過詩歌中的“進步”的概念,認為“詩歌的進程是一種不間斷、不可逆轉的失去。失去的秘密多得像創新。”套用他的話,或許有些偏激,這座錯彩鏤金的詩歌的七寶樓臺,或是句度的參差、平仄的配置,“使所有關于藝術中的進步的扯談變得毫無意義。”?
本書收錄的專文,主要落實在幾個不同面向的觀察。作者群橫跨歐美漢學界,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的華語研究學界,都屬近現代文學領域耕耘的學者,呈現中西觀點之間的交集與差異。書中設定的五個單元,紛呈不同的議題和論點,希望開啟不同論述視域間的多元對話與越界潛能。以下將針對書中的五個單元的議題稍作說明。
(一)媒體、社團與文化生產
在歐美文學研究界曾占主導地位的是文學文本研究,而近年來書籍史、文學社會學的流行顯示的是對這類封閉的文本研究的反動。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著名的“文學場”的概念,指一個由多種能動者與各類機構組成的鏖戰之地,以及體現他們各自文學意向與審美趣味的緊張空間。他深刻闡釋活躍的文學場域中的權力關系及其消長過程,年輕文化人在文學場域中要策略性地找到自己的定位,通過社團建立人脈關系,通過期刊提供的平臺,積累自己的社會與文化資本。文學生產/再生產是一個由出版商、編輯、作者、讀者、評論家等組成的生產鏈,其中兩個主要生產場域,即文學社團與雜志,是生產鏈的關鍵。?這個理論為我們研究現代文學社團與媒體提供了意義深刻的方法論參照。賀麥曉首開其端,將之運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的研究,并在中國語境中對此作過很多修改。賀麥曉在研究思路上的特點,即是對體制(institution)的重視,尤為重視文學出版物在一個群體的文化產出上的重要性。他在《文學社團的職業化:以南社為例子》一文中,認為十九世紀后期的新式文學社團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特征是比政治化更為重要的趨勢,而職業化最為顯著地反映在文學社團對出版行業的介入與利用。該文指出從19世紀晚期開始,文人親身參與并承擔書籍的定期出版,許多成員本身亦是編輯或出版人,同時文學活動和出版物也呈現了更為自治與專業化的特點。學界對于處于新舊蛻變轉型期的南社的研究,成果豐碩,相關討論大多側重突出這個社團的愛國熱情、革命情懷。?賀麥曉的研究關注體制內的章程確立、定期出版物的刊行、詩文雅集,以及圍繞柳亞子而形成的文化人圈子。這些見解為我們提供了理解1910年代文壇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全國性文學群體的鎖鑰之一。
從廣義上說,布爾迪厄的理論對于文學研究有兩個基本的方法論上的提示,即文本研究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對歷史情境的深度描繪(thick description)。?其“文學場”的概念是建立在對文學自主性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的,而這個理論運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在于,它不能涵蓋現代作家感時憂國的文化關懷,文學與政治的糾纏互動。吳盛青的《風雅難追攀》采用別的取徑,關注易代之際的“有情的共同體”的形成,友朋間的相濡以沫以及個體的文化理想的訴求。該文考掘了民國時期文人三月三的修禊情況,簡要勾勒了兩個在滬的遺民詩社——超社與晨風廬唱和集團的雅集情況。民國修禊展示了民初士人對蘭亭禊集與文學美典魔咒般的迷戀,而在撫今追昔中體嘗的是時間與文化斷裂的憤悱之情。該文對詩歌文本的討論側重在時空的軸向上展開,面對現代時間的不可逆轉性,都市生存場景的大轉換,民國遺民在詩歌中構建起一個封閉的帝國魅影,銘刻惘惘而不甘的文化招魂的姿態。這些身心錯置的憂傷書寫,是對歷史加速度的自衛性的心理回應,其間亦有抒情主體介入歷史的自我證成,以及延續斯文的文化擔當。
張暉與魏泉的文章關注傳統詩詞在公共領域與現代傳媒的互動,體現的亦是將文學研究帶回到生產現場的努力。他們在關注作品發表的語境的同時,關注雜志的發刊詞、插圖、欄目、作品間的關系以及廣告、發行渠道等,強調一個文本與同期刊登的所謂的“副文本”之間的空間關系。?張暉以前期的《小說月報》的《文苑》欄目與不定期增設的欄目《最錄》為研討對象,這是1910年代最大規模發表舊體文學的陣地。魏泉一文選擇了三十年代舊文人群體的在滬的同人刊物《青鶴》。兩篇文章的共同之處在于:首先,兩文都考察了主編王蘊章與陳灨一的核心作用,以及編輯活動背后所寄寓的文化理想。張文指出《小說月報》能夠吸引并刊登大量詩詞體現了文化人對“風流末歇”的一種文化焦慮,而陳灨一更是表達了“學術盛衰之變遷,誠國家存亡之關鍵”的認識,顯示出兩位文化人在舊學垂絕之際以道自重,以挽頹瀾。其次,兩位主編都利用其廣闊的人脈,匯集了清末民初一批重要的文人墨客,利用學養背景、世誼或姻親等,建立起私誼甚篤的文化人圈子。如果說1910年代的文言寫作是濃墨華彩的夕陽燦暉,儲備豐富,那么到了三十年代陳灨一是嘔心瀝血,艱難持續,因而也更有了薪火相遞的文化意味。這兩份雜志在相距了近二十年之后,稿件來源竟有頗多重合之處,表明舊文化生產鏈的頑強延續。鬻文賣字的舊文人,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依然擁有象征資本與文化資本。此外,受陳衍、朱祖謀等老輩提攜且成就大業者如龍榆生,同時期在滬刊行《詞學季刊》,表明耆宿相繼凋零之后,學養上新舊相參的年輕文人已經接上地氣,強韌地維護并志在開拓舊文學的生態環境。龍榆生如此看待他這一輩倚聲者應盡的責任:“不在繼往而在開來,不在守缺抱殘,而在發揚光大。”?
(二)離散與跨太平洋的詩學想象
十九世紀末以降,士大夫與平民百姓的跨境出國已成常態,尤其以謀生為主的群體遷徙,似乎說明晚清以來的中國正進入大離散的時代氛圍。在此脈絡下重新討論詩的寫作,除了凸顯詩的境外書寫已成為遷徙者在流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文學實踐,同時亦清晰勾勒出中國精粹的文學形式,必然遭遇的海外異質世界與文明體驗,以及衍生面對文類形式守成與改造等等的修辭手段與內容表征議題。如此一個遷徙流動的情境,一個主動與被迫的現代境遇,無形中預告了傳統文人最熟悉的古典詩詞寫作,勢必進入到一個現代情境世界的書寫。透過文人的漢詩寫作,及漢詩表征的境外視域:殖民地、城市空間、文化沖擊、離散際遇、雙鄉體驗、民族和語言的裂變及融合,漢詩面對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現代巨變,深化了我們理解這個古典文類遭遇的現代元素刺激可能的改變與不變。換言之,詩遭遇了現代性,以及離散境遇改變了詩的世界與眼界。
我們重新看待古典詩詞的現代書寫,似乎不能輕易略過一個更直接處理現代體驗的時空現場。因此,從中國離境后,直下南海,或跨太平洋的遷徙路線,都見證了不同的漢詩書寫脈絡,可以整合為一個離散詩學的視域。
距離當代最近的1949年,一個劃時代的兩岸政治分水嶺,國民政府的渡臺,開啟了我們重新反思離散書寫的核心內涵。什么樣的時空動蕩與文人心事,成功在詩的世界造成轉化。王德威的《國家不幸書家幸》處理了臺靜農的渡臺。臺靜農是隨國民黨政府遷臺的學者和書法家。喪亂作為那一代人的命運,臺靜農從文學到書法,展現了一種獨特的“書寫”政治學與美學。他難以壓抑的詩情和政治胸懷,寄存于書法的字墨行間,展示了絕境逢生的抒情特質和生命形式,書法成了中國現代性最特殊的抒情見證。
而境外寫作與離散敘事的密切關聯,呈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境外”與“離境”框架。在此議題下,黃錦樹的《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敷衍一個流動的文學與文化史論述。黃錦樹以南洋的星馬為據點,討論晚清南來使節左秉隆、黃遵憲,以及流亡詩人康有為如何以各自的文化資本,擘畫南洋的境外詩學。甚至二戰時期南來的郁達夫,以特殊的肉身經驗和死亡,透過詩的寫作形成一個巨大的象征遺產。從以上個案的簡要討論,他試圖透過“境外中文”的框架,將這些流寓者或南來者的文學實踐,或建立的文學象征,放入一個流動的文學史論述。在此基礎上,作為中原境外的南洋,可以視其為“華人的另類租借”。境外的離散與流動,成為馬華文學更早的際遇,它的起點不在新文學,而是晚清。
同樣是對南來詩人的觀照,高嘉謙針對兩位晚清嶺南的著名詩家丘逢甲和康有為,探討他們南來的短暫歲月里,他們的行蹤與漢詩創作如何改變了南來文學的傳統格局,替南洋詩學形塑了迥異的風貌。丘逢甲的漢詩寫作與當地孔教復興作了一種民族主義式的結合,他的保種保教和民間立場激揚的漢詩精神引起陣陣回響。相對于此,康有為亡命之際彰顯的詩學底蘊,就是孤臣的身心悲愴,以及內嵌的帝國視景。在引人注目的政治光譜之外,流亡者的詩學是康有為替南洋形塑的一道漢詩風景。在傳統文化塌陷,遺民大流亡的前夕,康有為落難南洋賦誦楚騷──憂患的漢詩欲望,頗具象征意義的內化為南洋華人移民史的一個部分。
在南洋之外,香港是觀察流寓詩人另一個重要的據點。從晚清的動蕩局勢到辛亥鼎革,避居和南遷港澳的廣東文人不在少數,由此開啟了香港文學的發展格局。黃坤堯和程中山的論文分別處理了陳步墀和潘飛聲這兩個文人個案。陳步墀獨力編印《繡詩樓叢書》,雖以個人及家族的詩文著作為主,但也輯錄了大量師友朋儕間的詩文墨寶,保存了珍貴的晚清史料及鄉邦文獻。顯然香港的斯文存續,在避難南來的文人身上獲得見證。潘飛聲在晚清時期移居香港,昌詩論文,成為當時香港的詩學大家。他撰述的《在山泉詩話》更是香港第一本詩學批評著作,而居港時期撰述完成的詩集──《香海集》,則是程文探析的焦點,揭示了潘飛聲的香港寫作在近代詩壇上別樹一幟的風格。在離散詩學的譜系里,香港另有值得關注的傳承視野。
十九世紀以降由移民和淘金客開啟的跨太平洋移動路線,掀開了一個重整漢詩譜系的新世界局面。黃運特的《詩意的錯誤》探討了無名詩人留在美國舊金山天使島上的詩篇。這批經后世學者以《埃侖詩集》成冊的早期離散詩學文本,呈現的不是詩的精粹飽滿,而是以充斥生命刻痕的具體形式賦形了遷徙流動生涯中錯置的真實人生。黃運特的研究則試圖提醒我們天使島的“題壁詩”該作為歷史紀錄,還是文學文本來理解?其可能的詮釋視域何在?尤其在經典化過程中,天使島詩歌內容的簡樸和錯譯,卻反諷地揭露出離散文本的書寫有其歷史因素呈顯的獨特形式。黃運特在其英文近著中提出“跨太平洋的想象”這一概念,將“太平洋”理解為多元、矛盾的地理與隱喻性的空間。他指出邊緣化、反詩學的文化實踐,可以用來抵御普世經驗、國族國家的疆界,從而為星球想象創造可能。?以上種種議題都可視為離散詩學范疇內的探討,從南海到太平洋彼岸,離散漢詩描述了一個我們探究漢詩的新界面,也為晚近興起的研究領域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探討提供了新話題。
(三)抒情與性別的政治
性別作為一個分析的概念,已成為一全球性的學術趨勢,廣泛運用于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包括單個的女性形象塑造的探討、寫作與閱讀主體的性別建構、文學中的換裝與擬仿、男作家的女性意識等等。在老一代學者如胡文楷、譚正璧等人開疆拓土的基礎上,明清文學與女性主義的研究在近二十年中蔚成聲勢。1993年在耶魯大學召開的明清婦女與文學的會議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九十年代后期晚清女性文化與文學的研究有追趕之勢頭。關于女性文化的兩種定性論述,在近一時期的研究得到廣泛質疑與修正:首先,生活在傳統父系制下的女性,在“五四”時期被建構成作為被壓迫、被凌辱的空洞的能指;近年來通過學者共同的努力,顛覆這一女性沉默失語的印象,展示帝國后期女性的主體性在書寫中的自我呈現,在網羅桎梏的縫隙中的自我抗爭。其次,十九世紀中后期以降,女性的寫作與女性自身的解放往往被置于國族主義的大話語之下;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中順勢提升女性社會地位的同時,賢妻良母成為了建構性別化的國族想象的重要資源。而近年學界關注女性如何與現代女權、民族主義運動互為利用的復雜關系,強調女性在國族與婦女解放運動中借勢成就個性價值,凸顯性別的主體性。
魏愛蓮、方秀潔、胡曉真的三篇論文均以新材料,梳理晚清新語境里的閨秀詩詞寫作與新興媒體之間的關系。從歷史時間段來看,她們處理的女性作家,承接明清閨襜詩書之澤,并成為新文學女作家的前身。魏愛蓮多年致力于明清婦女文學的研究,尤為關注女性文學社群的形成與互動,十九世紀的女性與媒體的關系。《1870年代以降“精通媒體”的閨秀》一文認為,晚清閨秀的從私人間詩歌酬唱、書信傳播到積極利用新的印刷媒體的轉變在1870年代即已現端倪。通過對四種文學期刊上女性發表詩作的情況的調查,展示了舊式閨秀文化在新媒體的催生下在向新的方向發展。該文集中討論了兩位鮮為人知的女性作家王慶棣與張慶松的投稿情況,細繹其間的變化,以及男性友人與讀者在其間可能扮演的推手角色。方秀潔在其英文近著中集中探討了17世紀早期到19世紀中葉,江南地區的女性寫作情況,細致爬梳了實際與想象的女性寫作社群的構成,尤其強調女性是如何將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學類型轉化為女性主體的自我呈現與自我銘刻的媒介。?本書收入的《激進化的詩學觀》,以《女子世界》(1904-1907)為中心,考察女性詩歌在清末的嬗變軌跡,涉及作者的性別、舊形式在新時代的意義、女性作家的主觀能動性等議題。魏愛蓮與方秀潔的文章均提出了晚清時期男作家偽裝成女性在女性刊物上發表作品的文化現象,包括周作人在內的文學扮裝。方秀潔指出,男性作者的托名游戲,一與文人借香草美人而言志的書寫傳統有關,二是緣于男性作家策略性的運用筆名,以期在競爭激烈的出版市場勝出。方文進一步指出女性詩歌中豪放風格的模仿與嫻熟運用以及新語匯和新概念的使用,顛覆了傳統的文學女性慣常的吟風弄月、摛藻揚芬。
胡曉真對于17世紀以降女性的彈詞文化研究成績斐然。?收入本書的論文在時間上順接方秀潔一文,到達晚清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混沌地帶,以王蘊章主編的《婦女雜志》為討論重點。《女子世界》與《婦女雜志》,均設有“文苑”一欄,而《婦女雜志》為“文苑”專列一欄,以“文苑”來重新定義女性文學。胡曉真認為,此舉“預設女性文學成為經典的可能”。同時“文苑”欄目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詩詞歌賦,出現了新的文類如散文甚至白話小說的嘗試。她以施淑儀刊登照片、在文中現身說法等形式來例示當時代閨秀在世變中的自我調適與表現,向往革命思潮的新姿態。這三篇論文勾勒了“五四”前女性文學的景觀,描畫了浸潤詩書之澤的晚清才媛如何開始偏離明清才媛文化的軌道,從不自覺的新媒體的投稿者到積極的參與者甚至弄潮兒的變化歷程,體現了創造的能動性(creative agency)。而這三篇論文涉及的共同課題,也在晚清女性文學研究中頗具代表性,即女性與新媒體提供的公共空間之間的關系、性別(閨秀)與文類(詩詞)的關系,以及男性名士的獎挹的角色或躊躇的立場。這幾篇論文彼此呼應,共同呈現女性活躍于晚清文化舞臺的風姿,展示了性別理論關照下的文學社會學與歷史敘述的多重關照。
呂文翠的文章代表了近時期蔚成風潮的近代“上海學”與海派都市文學的研究。其近著《海上傾城》以開拓的視野,細致描畫了19世紀后期上海洋場才子文化圈子的形成,長篇小說情感主體的建塑與當時迅速商業化的多元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收入本書的《情色烏托邦的回歸與消解》一文正是顯示了傳統的言情書寫模式在近代衍生的變異,認為《海上花列傳》正式終結了《紅樓夢》續貂之作中重復呈現的哀感頑艷的傳統審美情緒。該文對備受“五四”評論家批評的該小說后半段里的官家花園——一笠園的描繪作了重新詮釋,認為韓邦慶將傳統名士、仕女花園的寫作嫁接到新舊糅雜的商業社會中,對文學典律既有“趨進”,更有“消解”,“勾繪出城市商業文明中成熟成形的女性文化與現代性之隱喻結構”。韓邦慶小說中的酒令詩詞與《紅樓夢》里的詩詞預言人物命運的寫法不同,無甚深意,呂文翠由此提出一個新穎的見解,即他在無深度的堆砌辭藻與操作表演中達到對才子佳人言情模式的違逆與反諷。該文為我們的抒情討論帶來的新議題,即傳統詩詞中的風花雪月或忠貞不渝的情感套路,在新的物質文明與情感關系世俗化的過程中,遭逢峻切的挑戰,成為了諷喻或戲仿的對象。
近時期的性別研究超越了早期本質主義或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關注再現(representation)、話語(discourse),尤其是語言媒介在性別關系與性別形象塑造中幽微曲折的意義。此外,曾在文學史上失蹤的女詩人,風華絕代的呂碧城、薛紹徽,在晚近引起學界以及文學大眾的注目。打撈這些文學史上的遺珍散珠,或可免去其蒙塵之憾,但是我們更期待在女性詩歌文本分析上有進一步的拓展,從而重新建構仍以男作家為發言主體的二十世紀文學經典。
(四)遺民詩詞與歷史記憶
綜觀民國以后投入古典詩詞寫作的文人群體,遜清遺民是其中的堅實班底。這一批從亡清過渡到民國的人物,在自我認同與身份標簽上,締造了政治與文化交錯的人格類型。他們或許有政治理想,或許依戀舊朝,但新生活的經驗裂變卻曝顯出他們無所適從及文化懷舊的生存癥狀。這理應從一種超越政治、王朝的文化眼光,著眼于他們安身立命的價值:一種對傳統生活、穩定秩序的企盼。作為追憶古典時光的文化采珠者,他們賴以存身的終極價值是對上層精致文化的眷戀,相應也成了他們產生舊朝情結的部分根源。?舊朝情結與文化懷舊因而有著交融互涉的模糊地帶。相對“五四”以降新興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與進步信仰,遺民遁入歷史潮流的暗角,呈現出悲觀、荒涼、憂患、頹靡、破碎的生命情調與時代景觀。
相對“五四”新文學作為時代的主旋律,遺民文人的古典詩詞生產顯得邊緣和守舊。然而,我們卻無法忽略這些舊體詩詞在民初的文學場域占有重要的位置和文化資本。文人聚集組社,特定的期刊報紙依然保留古典詩詞發表園地。這方面的議題已在前述單元介紹處理。但值得我們探究的是,遺民的詩詞寫作如何響應和解釋他們的歷史記憶?詩人如何對詩的審美意義重新認知,舊體詩詞又如何構成文化遺民的根柢?詩的抒情技藝如何成為遺民的生存及自我想象文化母體及生存倫理證成的手段?
以上種種問題在林立和胡曉明的論文中,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處理。林立的《泡露事、水云身》著眼的是詞的文類,凸顯其作為清遺民群體中負載歷史記憶的關鍵媒介,討論遺民詞人之間的唱和活動,如何藉詞作來喚發、維系和鞏固他們的忠清意識,以達到彼此認同的目的,進而在詞人面對歷史記憶的共同表述中,建構遺民詞人群體的特征。林立還在另一篇近作中,通過對天津的須社與詩集《煙沽漁唱》的分析,進一步闡發集體唱酬在維系、強化清遺民群體的記憶與身份過程中的作用。同調同題所形成的微妙的互文關系,更是從藝術形式上強化彼此間的聲氣相通, 鞏固遺民文化身份的認同。?
胡曉明的《陳三立陳寅恪海棠詩箋證》則以一對父子,又是兩個世代的重要詩人和學者,他們在不同時間創作的海棠詩展開探究。父子二人個別遭遇了各自的時代風暴,海棠詩的寫作反而見證了各屬的父親認同,且突出了詩作為精神對話和心靈相守的載體。這可以看做詩學傳統的重新發明,也賦予二十世紀古典詩現代內涵。
在中原境內的遺民群體之外,1895年的乙未割臺令臺灣率先進入殖民地境遇。面對地域的割裂,島民成為天朝棄民,清朝正統未亡,他們卻開始有了遺民感覺;新文化運動還未揭幕,他們卻有了文化焦慮。從乙未割臺開始,自殖民地臺灣出走或留下的文人,他們以遺民自稱的吊詭身份,讓遺民情結跳脫出傳統朝代更迭范疇,成了一種癥狀。他們流連中原,在帝國疆域內尋求機會;或流放海外,尋找其他謀生可能。當然還有茍活、避居臺灣島內,周旋在殖民者的誘惑與壓力之間,導致認同的游移。在棄民的集體流亡意識中,他們寫作大量古典詩詞,試圖描述自我處境,傳達與古人共感的飄零情懷,或以詩詞記載流離域外的地理空間意識的改變。
施淑和黃美娥都是長期耕耘臺灣文學和臺灣古典詩學領域的著名學者。施淑的《臺灣詩人洪棄生的文化意識及身份認同》以避居島內的詩人洪棄生為例,從其數量龐大的古典詩詞作品中,探究在艱困的殖民地境遇里,洪棄生以詩作為文化象征和抵抗,堅守遺民志向,不忘中華原鄉。他的詩作記錄臺灣淪亡大事、批判殖民體制,強化他在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性死亡,更加深他的自我異化。這些詩作見證了詩人啟動傳統資源以建立自我完整的遺民形象,卻也在臺灣漢詩版圖奠定了其光彩奪目且屹立不搖的位置。
日本殖民臺灣五十年間,詩社發展蓬勃,漢詩寫作從未斷續。黃美娥的《日、臺間的漢文關系》勾勒了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論形構。該論文著眼日本、臺灣漢文接觸后引起的諸多問題,聚焦于日本、臺灣間的漢詩跨界流動,及其所帶來的文學知識生產,提示日本漢詩在殖民臺灣的關鍵時期,如何被引用、挪用或拉扯、抗拒,尤其這些來自異域的知識如何轉化成自我的范疇,而安置在臺人的古典詩歌知識系統。以上種種問題呈現了一個迥異于中原地域的古典詩詞發展譜系,同時凸顯了20世紀另一個復雜的古典詩詞生產場域。
(五)漢詩形式與文體變遷
這一組文章從更為開闊的視野下看世變中的文類、文學形式本身的守成與變遷,穩定的形式與巨變的內容之間的齟齬、磨合或突變。在文化研究依然大行其道的學界風氣里,文學文本常淪于意識形態的注腳。在此我們強調的是在理論關照下的文本研究,第一手材料的梳理,和對文學形式與美感的辯證。如果說以上單元關懷的主題都是詩詞文本與抒情傳統實踐,跟晚清民國的歷史現實的相激蕩,從而衍生出的種種新變;那么這一部分的討論除了以十九世紀末以降漢語詩歌形式的變異和轉化為焦點,還擴展至其他抒情形式,關注審美與技藝的豐富性。
胡志德在八十年代后期發表過兩篇重要論文,對十九世紀的文學潮流與思想作過系統梳理與深入辨析,影響深遠。在《從書寫到文學》一文中,他通過對十九世紀桐城派與文選派的研究,細繹寫作的角色在知識體系中的嬗變軌跡,認為“古文”與“文”的復興顯示了道德關懷滲透進了寫作領域,社會文化的危機意識在文學層面上的展演,并指出“文”地位在此一時期的升遷為1895年后“文學”概念的重新整合做了有效鋪墊。?收入本書的《新的書寫方式》一文,在時間上承接前文,深入剖析“轉型時代”的散文理論,寫什么與如何書寫成為晚清知識分子縈懷于心的關鍵議題。該文指出,原本內涵豐富、意義寬泛的“文學”概念與狹義純粹的文學概念相互糾纏,使得文學成為二十世紀文化領域中“充滿張力的競技場所”。胡志德將吳汝綸對雅潔風格的守衛看做是對西方觀念的搖擺不定的抵抗,并認為文選派中,劉師培通過對阮元的“文”概念的張揚,為“文”劃定疆域,反對雜糅的文風,從而將“文”提升成為一種有效的、抽象的“國粹”。胡志德在《將世界帶回家》一書中繼續發揮這個議題,進而指出,在外來文化觀念與本土文化的鋒刃相交中,“新小說”最終脫穎而出,承擔起維新救亡的重任。這一系列文章揭露出晚清士人面對西潮欲拒還迎的復雜心態,伴隨而至的深重的文化危機以及彼此激揚生發的軌跡。在把中國帶入現代世界體系的自覺努力過程中,晚清知識分子試圖拋卻歷史包袱的同時,又認定文學將在其間扮演確證國族、文化身份特征的關鍵角色。“對其本身的多元性,采取矛盾的立場”,成為了那一個時代的征兆。?
在桐城派與文選派的研究中,注重對其文學理論與思想的邏輯脈絡的梳理,戴沙迪的《辛亥之際文論的承前啟后》另辟蹊徑,借鏡布爾迪厄的“位置制造”(position making)理論,關注社會制度的變化與理論、方法之間的互動,顯豁文化行動者(agent)如林紓與劉師培等人的具體文化實踐。該文采用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兩個視角,來探討林紓與劉師培各自的古文教學、閱讀的實踐,詮釋這些實踐背后的動機以及他們在文化場域中的種種斡旋,進而論證其成為新文學效仿對象的緣由。頗具吊詭的是,所謂的“桐城謬種,文選妖孽”以及20世紀初的傳統文學話語,成為了催生新文學必不可少的歷史條件,進一步論證了“二十世紀初傳統文學話語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多元的辯證空間”。胡志德與戴沙迪兩文之間的交集,為讀者進一步追索晚清文論提供了不同的思索維度。
面對時危國難,古典詩詞負載了巨大的文化期待。晚清“詩界革命”,呼吁在詩歌中反映新內容、新思想,成為詩歌變革的契機,同時也遭遇挫折,而面對形式的變異和轉型,詩人們在親近新世界時有所自覺地進行實驗并努力嘗試不同的寫作方案。詩人在熟悉的古典詩歌傳統中調動典故成詞、創造新語匯,甚至放棄格律,既為詩尋找出路,也在定位和改造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黃遵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鄭毓瑜近年的研究著眼于古典文學傳統中的“感知模式”和“語言系統”在面對經驗、記憶和知識,所產生的語言調度和替換,擴大和具體陳述了抒情的文學傳統的意義認定模式。?她的《舊詩語的地理尺度》進而將時空拉近到十九世紀末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檢視了遭遇異地文明的詩人必然從爛熟的舊典傳統中,調動古典辭藻和意象去傳譯他所描述的明治維新世界。鄭毓瑜指出“詩、注并存;舊詩語、新事物并置”的相互撞擊和磨合現象,其離合和參照的意義脈絡,正是我們觀察晚清以降古典詩詞展示的自我認同的外部視域和世界。換言之,我們看到了晚清以后古典詩詞的變異舉步維艱,卻又毅然自信地走進的新世界觀。此觀點試探性地陳述了漢詩的舊與新不是文學價值范疇的定義,而是在意義闡釋過程中體現其曲折反復的“現代”見證和效應。邁入二十世紀的舊體詩,接棒走上同樣的路。
寇致銘的《論陳衍、陳三立、鄭孝胥和“同光體”詩》討論了近代詩學范疇內不能回避的同光體詩人群。他從詩人的境遇驗證了詩風的變異,彰顯了經驗世界的土崩瓦解,以及自我的懷疑和生存危機。這些見證時局的舊體詩詞,以支離破碎和殘敗的意象重新組裝了詩的感覺結構,并準確把握了局勢動蕩與文化衰頹的精神狀態。這是詩人特殊的時代感,同時也是詩的現代性體驗。寇致銘在專著《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里對此議題有更深入的開展,并指出舊體詩詞對時代微妙而復雜的反應,顯示出詩人們在歷史體驗和個人感受之間所建立的美學距離,進而形塑和構成了我們討論古典文學形式的現代性特征的重要路徑。
而最直接表現詩的抒情美學與現代性結合的個案,當屬楊昊昇《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處理的郭沫若和毛澤東三十余年的舊體詩詞唱和。從詩人的浪漫主義轉向張揚政治抒情,進而投入紅色革命的抒情浪潮,郭毛二人的舊體詩唱和,見證了中國的政治進程,卻同時暗示了舊體詩詞在文學革命后最具爆發力的展示,反而是政治的抒情主義。楊文對郭毛詩詞唱和的分析論證,指出了在政治浪漫想象的視域里,必然突出彰顯的抒情主體,構成了二十世紀舊體詩詞寫作最具體的現代性特征。在抒情跟政治密不可分的時代語境內,舊體詩詞生生不息的活力,卻狡黠地體現在郭毛的時代唱和。這恐怕是當年胡適企圖推倒舊體詩堡壘時未曾料到的發展,但也說明了古典詩詞內蘊的抒情傳統力道與政治文化一拍即合,后勁不容小覷。
于是,我們可以重新檢視詩界革命以來,對漢詩形式變革的呼吁,所衍生的對文體/文類疆界的種種糾葛和反思。張宏生《詩界革命:詞體的“缺席”與“在場”》從詞體的獨特性出發,客觀地評述了由于常州詞派比興寄托的審美定勢與詞體“要眇宜修”的文類特征,形成詞在時代新變中的局促應對、捍格難容的境地。該文再次提醒我們,思境與藝術形式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熔鑄新思想又要兼顧詞體之美是那一代詞人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四”戰。在艱難融合新理想、新詞語與舊風格之途上,“五四”新文化運動者高揚革命旌幟,以一種激進的姿態顛覆窠臼,另起爐灶。奚密的《詩的新向度: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一文,深入分析了古典詩歌與白話新詩在形式、意象、感性等方面的根本性的分野以及現代漢語詩歌裂變背后的“不可控制的力量”。首先,該文指出古典詩歌是建立在有共同教養的“同質”的讀者群體之中,而在新詩的詩人與讀者間則不具備這樣的同質的教育背景,共享穩定的詩歌語匯,以及預設的整體文化價值體系。同時,該文以朱光潛等為例,簡扼地討論了現代漢詩所呈現的革命性轉變的哲學與文學的意義。“什么是詩?”“詩人對誰說話?”“為什么寫詩?”等這些命題劃出新/舊詩歌的文類疆域,成為建構新詩的本體觀與現代性的關捩。
這本《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論文集孜孜矻矻思考的命題之一,即抒情傳統在現代語境中的發明或演化。但是需要澄清的是,我們并非在理論上預設從傳統到現代的絕對的延續性,或是說一個活躍了千年的形式就必然要在現代得以承繼。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從許多個案中發現新詩的雖新猶舊,與舊詩的藕斷絲連,但是總體而言,新詩作為全新的反形式的詩歌形式,是在“斷裂”的大前提下,在審美空白的空間中,開掘獨特的表現力與想象力的自由維度。?在1910年代,如果說同光體與常州詞派是盤根錯節的千年古木,那么新詩是些移植來的細細嫩枝,但是這些嫩枝在二十世紀將遭逢催生茁長的機緣。奚密還在另外一篇重要論文《中國式的后現代?——現代漢詩的文化政治》中,以高度的自覺,駁斥了對新詩的質疑,反思新詩在世界視野中的自我定位與文化認同的焦慮。該文對于我們的醒示意義在于,當代對抒情傳統的重新發掘研討,并不是要抑此揚彼,退守古典主義或本土主義的立場,執紅牙檀板,悵惘若失于走遠了的曉風殘月之景;也不是要從抒情傳統中去尋繹、去建構一種一成不變的、本質化的“中華性”(Chineseness),以期獲得一本國際旅行的通行護照。陳世驤、高友工等前輩學者張揚抒情傳統,雖有其特定的西方漢學語境,但抒情傳統作為一套“傳統之發明和轉化”的話語系統?,可以有效展示中文抒情文類在現代世變語境中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或以王德威所提醒的另一個關注面向:我們如何透過中國傳統文論的檢視和反思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問題,或對相同問題的不同解答路徑和方法,建立和設定自己的議題范圍。?我們無意強調全球視域下在現代化道路上中國文化的特異性,旨在展示傳統在流變中無可爭議、不容簡化的豐富形貌。本書關注古典詩詞及廣義的抒情文類、話語如何在傳統的裂變和融攝中生長與衍異,期望為晚清民國詩學與文化研究推波助瀾,引發更多的相關探討與論辯。本書安排的各單元均涉及一些錯綜復雜的問題,我們毋寧希望借此提出一些粗略的觀察,起拋磚引玉之效。
【注釋】
①陳衍:《近代詩鈔刊成雜題六首》,見氏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3頁。
②本書對十九世紀以降的抒情文類探討,交替使用了幾個常見的詞匯,包括古典詩詞、舊體詩詞、漢詩、抒情詩等。相關詞匯的概念并沒有太大歧異,仍指向傳統詩詞形式的寫作。交替使用主要是針對不同語境脈絡方便凸顯其參照和辯證意義。舊體詩詞乃對立新詩而言,凸顯新文學革命性的態勢。漢詩是過去學界已漸進使用的詞匯,可概括為漢語詩歌。當然,其過去習慣使用的范疇乃指在域外與漢字文化圈生產的漢語詩歌。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學界開始提倡表征現代經驗的“現代漢詩”概念,奚密專著也以“現代漢詩”為題,標榜1917年以后的新詩書寫。現代漢詩既表征現代意識與時代精神,反襯出晚清以降的古典詩,似應正名為“古典漢詩”。本書使用漢詩,既響應一個相對“中性”的漢語詩歌概稱,也同時關注域外離散詩學。至于抒情詩,則泛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以抒情文類是尚的詩學體式和范疇,而詩詞仍屬其核心文類。尤其當古典詩詞作為晚清以來文人之間交際和抒情媒介,其追求的價值精神與文化秩序,表征了古典抒情詩的審美想象,與文化共同體的追求。
③見王汎森對線性的歷史觀對近代史研究的檢討。詳氏著《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49-108頁。
④宇文所安:《過去的終結:民國初年對文學史的重寫》,《他山石頭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頁。
⑤陳思和:《一本文學史的構想》,收入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51頁。同時參見該書中陳國球的導言,詳氏著《導言:文學史的探索》,第1-14頁。
⑥宇文所安:《過去的終結:民國初年對文學史的重寫》,第306-335頁。
⑦其中當然有例外,如錢基博的成于1930年代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對近代詩詞及文章變革均有精彩的論述。關于白話文對文學史寫作的主導,詳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⑧關于學科體制下的中國文學的現代研究和文學史建構,研究成果不少。可參考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⑨陳平原:《導言》,《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1-7頁。
⑩見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中“時間距離的闡釋學意義”一節。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385頁。
?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 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chap.3,esp.pp.94-95.深受語言學研究影響,歷史學家懷特認為歷史的真實是通過歷史學家所運用的譬喻性的語言與文本之間建立的關系而獲得的。
?見德里達在中國的演講記錄,闡述其尋求差異性的解構學思路(第68頁)。轉引自陳曉明《現代性與當代文學史敘述》,《文藝爭鳴》2007年11月,第63-72頁。陳文對文學史的寫作與現代性等議題有深入討論。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間斷限乃是我們編輯權宜下擇取的歷史研究的時間范疇,此處無意涉入界定莫衷一是的關于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分期的討論。
?王德威近期對中國現代性的考察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參考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72-73頁。
?這是本雅明詮釋機械時代的現代性體驗的關鍵主題。這種震驚體驗成為詩人潛意識的一環,賦予詩的精神結構。詳本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版。
?參見Dipesh Charkrarbarty,Provincializ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2000),p.43.迪皮什·查克拉巴指一種歷史寫作,要特別彰顯在“現代”的普世原則下的“壓抑的策略與實踐”。
?宇文所安認為中國古典詩歌有一個追憶的機制,為詩歌提供養料。詳氏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3頁。
?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自敘》,氏著《曹子建詩注(外三種)阮步兵詠懷詩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07頁。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首刊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第77-137頁;后收錄入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3-65頁。
?Fredric Jam eson,A Singular M odernity: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New York:Verso,2002),p.40,p.57.書中討論了現代性的四種準則(pp.15-96).
?胡曉明:《二十世紀中國詩學史小言》,《社會科學家》2003年5月,第126頁。
?關于晚清文言、白話和方言以及文學形式的深入討論,參見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語言與形式”,第59-132頁。
?劉納:《最后一位古典詩人》,劉納編《陳三立》(傳記、作品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
?Dipesh Charkrarbarty,Provincializ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p.149-179;引文見p.171.
?Jon Eugene von Kow allis,The Subtle Revolution:Poets of the“Old Schools”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C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6).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 200-201頁。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47頁。關于這一點的深入討論,見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版,第46-48頁。
?[俄]曼德爾施坦姆:《論當代詩歌》,收入黃燦然等譯:《曼德爾施塔姆隨筆選》,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
?主要參見布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對兩岸三地的南社研究成果的綜述,見林香伶《南社文學綜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版,第17-36頁。
?Michel Hockx,“Theory as Practice:M 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Bourdieu,”p.236.
?“副文本”(paratext)定義見,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
?龍榆生:《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頁。
?Yunte Huang,Transpacific Imaginations:History,Literature,Counterpoetics(Cam 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0.
?Grace S.Fong,Herself an Author:Gender,Agency,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 ai’iPress,2008).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年版。
?葛兆光對沈曾植的個案討論,引導出文化遺民的價值觀念與情感特質。詳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讀書》1995年第9期,第68-69頁。
?林立:《群體身份與記憶的建構: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1年1月第52期,第205-245頁。
?Theodore Huters,“From W riting to Literature:The Developm ent of Late Qing Theories of Pro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7,no.1(June,1987):51-96.
?Theodore Huters,Bringing the W orld Hom e:Appropriating the W 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 ai’i Press,2005),pp.100-122;pp.19-20.
?鄭毓瑜就此議題所發表的論文,詳鄭毓瑜:《類與物:古典詩文的“物”背景》,《清華學報》新41卷第1期(2011年3月),第3-37頁。鄭毓瑜:《替代與類推:“感知模式”與上古文學傳統》,《漢學研究》2010年3月第28卷第1期,第35-67頁。
?見臧棣對新詩現代性的討論。詳氏著:《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文藝爭鳴》1998年第3期,第48-52頁。
?黃錦樹:《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中外文學》2005年7月第34卷第2期,第157-185頁。
?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第 74-7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