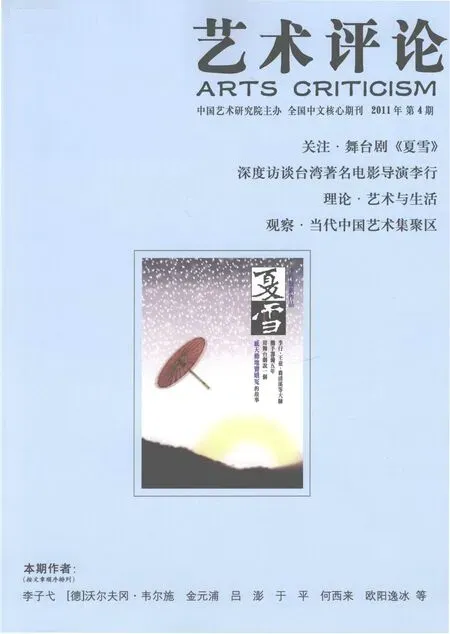藝術如何改善了我們的生活?
[德]沃爾夫岡·韋爾施 王卓斐 譯
藝術如何改善了我們的生活?
[德]沃爾夫岡·韋爾施 王卓斐 譯[1]
能夠參加“文化、藝術與人類發展的中國國際論壇”,并借此良機了解中國的美育思想,對我是莫大的榮幸與樂事。在接下來的闡述中,我自身的觀點將難免遵循西方的視角,然而,你們將看到,這樣的視角與你們偉大的傳統其實是一致的。

一、總論: 審美與倫理的一致性
從西方兩千多年的美學傳統中,我得到的教誨是:藝術活動并非只與藝術有關、甚至不以之為重心,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正確的生活方式。在此,審美與倫理緊密相連,二者如孿生兒般難分彼此——藝術品及相關活動應幫助人們過上更美好、更人性化的生活。
當然,既然置身藝術領域,那么藝術不可不談——只有滿足了審美標準,藝術作品才有成功可言。但歸根結底,審美標準與成功的生活形式是一致的。[2]
誠然,在過去二百五十年里,西方出現了使審美脫離倫理、將藝術視為自律的趨向。眾所周知的事實,便是19世紀喊出的“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的口號。然而,在整個西方傳統中(亞洲傳統亦是如此),占主導地位的信念卻是:藝術應為更美好的生活貢獻力量。
(一)范例
可以發現,表示“美的”希臘詞“kaló n”同時也有“善的”含義。在古典時期,這樣的關系通常是不言而喻的——真正的美不僅意味著審美的成功,同時也表示道德的完善。在中世紀,這種關系依然存在,即所謂的“美善合一”(pulchrum et bonum convertuntur)。到了近代,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重新提出,藝術的最終目標不是塑造藝術品,而是推動“生活藝術”(Lebenskunst)的發展。[3]藝術幫助人們過上更好的、真正的人類生活。席勒繪制了雄心勃勃的“審美教育”(sthetische Erziehung)藍圖,其任務與旨歸,在于使人們首先成為“完整的人”——這不僅指個體的生活方式,同時還包括社會與政治的存在(在文章結尾,我將再談這一論點)。
20世紀一再出現的情況是:藝術(從蒙特·韋里塔到約瑟夫·博伊斯)的動力不是源于自身,而是來自生活;藝術為了生活而追求超越。“生活的藝術”取代了“藝術的藝術”,該口號意味著藝術乃是生活的手段。在賴內·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看來,經過對古典雕像的沉思,典型的結果就是產生了警句“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Du musst dein Lebenndern)[4]。此外,在1987年的諾貝爾演講中,俄羅斯詩人、異議人士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強調了審美與倫理的魚水關聯,甚至在此稱審美為“倫理之母”[5]。[6]
(二)特例?
誠然,也有表面反對審美與倫理聯姻的藝術流派和藝術理論。但如果進一步審視,便會發現,它們之所以這樣做,恰恰是同樣堅信,審美活動應預示美好的生活,甚至或許應在某種程度上去實現它,而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規范在它們看來是完全錯誤的,并似乎恰恰妨礙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正是出于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對相關藝術使命的捍衛,它們才同這種道德規范展開抗爭。對此,19世紀的“為藝術而藝術”運動堪稱典范。[7]
二、為何審美與倫理是一致的
現在,根據這些歷史線索,讓我們系統地思考一下:為什么審美與倫理的一致性是西方美學的基本主題與永恒信念?——當然,對亞洲美學同樣如此(無論儒家還是道家,皆有這樣的特點)。
(一)古人類學研究: 作為社會黏合劑的藝術
第一種原因是歷史性的。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藝術首先是為了形成或增強社會凝聚力而出現的。古人類學告訴我們,儀式與手工制品最初是用來加強社會團結的形式。于是,從遠古時代開始,藝術便銘刻著與人類社會有關的內容。審美與倫理的姐妹情誼,屬于美學染色體組的構成要素。
(二)審美與倫理目標實現的結構相似性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審美與倫理目標的實現要求上,二者有著明顯的結構相似性。
1、倫理整體主義
按照倫理標準,個人不應通過對抗社會或犧牲群體利益的形式實現自我,而應首先為集體的成功做出貢獻——以這樣的方式,其自身也將取得極大的進步。促進社會的安康對謀取個人幸福同屬最佳的策略。
亞里士多德
作為西方傳統的早期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著作《政治學》(Politik)中明確闡述了這種倫理政治原則。他在此指出,政體領導者應關注他們所受托的集體福祉,而不是單單注重一己之利。在后一種情況下,領導者將破壞政體,并最終危害自身。但是,如果他們首先為集體利益而奮斗,那么作為集體的一分子,其自身的事業也將蓬勃發展。這就像船長一樣,他必須保證整艘船處于良好的行駛狀態,也就是說,使一切(alle)順利進展——以這樣的方式,他本人也將迅捷、安全地抵達目的地。“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乃是更務實成功(無疑也是更好、更恰當)的箴言。[8]
道家思想
對亞洲傳統來講,這種(倫理政治)原則是從道家那里學到的。[9]《道德經》第七章這樣寫道:“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10]。一個人不應自私自利,而應與社會和諧共處,從社會的角度審時度勢。這實際是一種著眼于整體的行為策略。不是從自身出發,而是立足“大道”理解“我”;“我”成為“道”在這兒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在這個地方,“道”是以“我”的形象出現的。如果“我”意識到自身的實際構成并相應地采取行動,就會完全做到依“道”而行,從而也就不再依照一己之利行事。然后,“道”將在“我”這里獲得其最佳的形式,而“我”也將為此受益無窮。
2、審美整體主義
(擁有與上述)相似的結構乃是審美成功的關鍵。比如,繪畫要素必須彼此協調,個別要素必須有益于整體,并根據在這方面的表現得到合理的評價。再如,交響樂的篇章必須相互協調,最終形成連貫的整體,使了解整部作品的人幾乎在任何位置(在不同的細節中)都能感受到一致的整體效果(某種程度上講,差不多處處都一樣)[11];又如,在芭蕾舞表演中,舞者的各種動作應始終產生整體的形象效果,并在整個劇情的發展中形成連貫的姿態。總之,同倫理的成功一樣,實現審美目標的關鍵亦在于,個別的要素并非僅指涉自身,而是有助于整體的表現。恰恰是整體中的要素(Momente)生成了整體本身。關于這一點,在古典美學中是通過連貫(Kohrenz)、和諧(Harmonie)或協調(Stimmigkeit)的要求體現出來的。
這種審美與倫理目標實現的結構相似性使人不難理解,藝術品同時也能預示正確的生活——就像此前所說的,審美標準本身與正確的生活形式是一致的。[12]
3、有機性—自由—自組織
現在,根據所描繪的審美與倫理目標的實現特點,我想詳細探討一下部分與整體、個別與普遍的關系。在有機物領域,我們發現了這種關系的原型,因為有機物的特點是:在此,部分不是脫離整體獨立存在的,而是通常只作為且只能作為整體中的部分出現;反之,整體也受制于部分的運作。這就像人的心臟不是以某種方式從外部置入體內、而是作為身體的一部分生長的;但是,身體同樣也對心臟有依賴關系:一旦心臟停止了跳動,那么身體的存活也將走向終結。有機物的部分與整體是同呼吸、共命運的:部分之間相互扶持,因而也需要整體,而同時,整體同樣離不開部分的運作。
因此,代表審美與倫理目標實現特征的部分—整體關系,是以有機物為藍本的。與此相應的是,指涉審美目標實現的眾多術語也源自有機物領域。所以,部分與整體真正實現互動的藝術品證明是有“生命力”(Lebendigkeit)[13]的;或者說,作品是有“靈魂”(Seele)的;或者說,人們提到的“力的自由互動”(Freies Zusammenspiel der Krfte)乃至“自由”(Freiheit)等各種術語,顯然實際上不是來自美學,而是從有機物本體論那里借鑒的。
讓我們進一步地思考——體現于有機物并以美的形態呈現的物理學原理是自組織原理。近幾年的美學研究愈益認識到,審美成功意識的首要依據在于——我們所體察的形態形成于自組織的過程。[14]對此,人們可以在有機物領域找到明顯的例證——從松果鱗片的螺旋形生長紋路到孔雀屏的眼睛圖案組合。不過,自組織是超越有機界、乃至回溯到無機界的原理,是自然界藉此形成有序結構的一般(generelle)定律——想想各種星系的情況吧!
(三)本體論背景
這樣一來,我們的探討已超越了審美與倫理成功標準的一致性,觸及了普遍的、物理學層面的宇宙原理,而這是產生一切成功形態的基礎。自組織是宇宙萬物(自大爆炸開始)的一般構成原理,是基本的本體論定律。它生成了有著內在和諧結構的事物(其中,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是協調一致的)。同時,這種和諧關系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否則生存便無從談起。以太陽系為例——它作為一種系統,一面對各種引力關系做出完美的協調,一面對運行軌道與運行速度進行出色的調整。太陽系在約45億年前的自組織過程中形成并穩定下來,由于其協調的精確性與不斷的細微調整,從而得以在極為漫長的年代里存在下來。
如果審美與倫理的一致性依據的是更深層的原理——涉及自組織的本體論或宇宙學定律,那么便意味著,審美與倫理的正確性反映了世界的基本秩序。這樣一來,那種認為審美是倫理之母的觀點就是錯誤的(就像布羅茨基所認為的),反過來,將倫理視為審美之母的見解也是有問題的,毋寧說,審美與倫理皆是世界基本秩序的衍生物。至少這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審美與倫理原則完全是人類的造物;可能有時看上去如此,但這卻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它們更多地體現了宇宙的基本原理(無論如何,審美與倫理本身是宇宙的組成部分)。——審美與倫理反映世界秩序的觀點對亞洲思想并不陌生,并很有希望在西方思想中再度盛行(在現代時期,這樣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思想家遺忘了)。
(四)依據深層原理的倫理與藝術活動
這同時表明,倫理與審美活動不是絕對自主的;它們無法獨自隨意制定規則、安排活動,而是必須以本體論原則為依托。
在倫理領域,這一點是通過道德戒律得到體現的:人們不應把自身意志強加于世界,而應通過行動推動自然的進程。至少在道家學者眼中,這樣的見解是合理的。《道德經》第64章這樣寫道:“(圣人)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15]——這便是“無為”(Tatloses Tun)的內涵所在。它指的是促進萬物的發展,而不是進行規約與掌控。
另外,藝術家以各種方式指出,他們無意充當獨立的創作者,而更愿把自己視為作品問世的助產師或媒介。[16]這樣的觀點也許在東方更為盛行,而在西方同樣可以找到蹤跡。比如,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曾提到,他“不過是受宇宙支配的工具”[17];他越來越清楚:“人不是塑造者,而是被塑造者”[18]。與馬勒類似的藝術家渴望忘掉意向與技藝,為的是像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所說的那樣,“僅成為感覺的容器……或儲存器”:“馬勒全力追求著內心的平靜。他必須平息所有的偏見,忘卻、忘卻,平定下來,成為完美的回音”[19]。在中國美學界,彭鋒的觀點與之頗為相似:“藝術家只有一并忘卻其創作意圖、技藝、慣例,也許甚至還有創造力,方能塑造出杰出的作品”[20]。爐火純青的藝術摒棄了一切刻意雕琢的痕跡,就像嚴羽(約1180-1235)的那個著名比喻——“羚羊掛角,無跡可求”[21]。
三、美與藝術的獨特價值
現在談談美與藝術的獨特性。
(一)美使人體驗宇宙的原理
美是這樣一種現象:在此,自組織與連貫性——即宇宙的基本法則變得生動可感(sinnenfllig),而美的獨特性則由此而來。一切在世間出現并存在的事物均具有自組織與連貫性的特點。因此,上述自組織與連貫性也同樣是成功行為的特征。不過,在審美領域、在美的現象中,這種普遍法則是可以感知的,因而也就更容易把握、更加清晰明了,較之其他場景更易令人體驗。
柏拉圖早已認識到這一點:在他看來,美是“最燦爛、最迷人的東西”(ekphané staton kai erasmi ó taton)[22]。他是想說,盡管觀念的東西在現象界一般以隱晦的面貌存在,但有一種觀念形態卻在此光芒四射,這就是美的理念。某種意義上講,它是最為持久的觀念,能夠使我們脫離現象界的漩渦,向理念的王國飛升,由此凸現它的寶貴作用。[23]
(二)藝術:表達與多樣性
那么,藝術的特色何在呢?
不同于自然的形態,藝術作品中部分與整體的相互依存性是刻意塑造的(eigens gestaltet),從而也就格外可觸可感(besonders erfahrbar)。部分與整體的連貫性是藝術品形成的首要法則。創作過程的每個環節都是圍繞現有成分與創作意圖展開的。這樣,每個成分都參與了其它成分的形成。因此,在藝術品中,部分成為名副其實的要素(Momente):它們造就了其它部分的形式與意義,并與源于自身的整體構成了依附關系。(比方說,這就是為何同樣的音符,隨著此前樂曲的行進和其它音符的躍動,可呈現出不同的音質)在完成的作品中,人們仍可以感受到這種貫穿創作過程的部分與整體的動態交互創造關系(即使它在繪畫中是以靜態的形象存在的),這體現在所有要素之不可思議的極度協調性和作品綻放出的勃勃生機。在時間藝術中,比方說音樂,這種部分與整體的相互糾葛無疑占的比重更大,而且在一切瞬間鮮明地顯露出來。
在藝術作品中,不僅是連貫性(源于進程之中,即不是從外部植入,而是內在生成的)、就連自組織因素也得到了清晰地呈現。優秀的藝術品不是某種預設程式(“理念”)的簡單復制,而是始終有自己的軌跡,可以說,它創造了自身——不是依照外部的成規,而是憑借自身生成的邏輯。(“在行走中創造道路”"Laying down a path in walking"可謂是對藝術之旅的恰當描述)。
如此說來,成功的藝術之作還始終體現著自由;要素的結合不是來自外部的強制力量,而是自覺自愿的。作品存在方式的特征不是屈從,而是相互制約。——順便說一下,弗里德里希·席勒率先表達了這個見解:在審美領域,每個要素都被視為目的本身;它與其它所有要素是平等的;不得被強行納入整體之中,而必須是自愿地行動。[24]從這個意義出發,席勒把“美”界定為自由的顯現。[25]
最終,藝術帶來了多樣性,因為它以斑斕的形態(in unterschiedlichen Formen)教人體驗自組織與連貫性。由于這些原理在自然界有著各種不同的現實形態——星系顯然不同于貝納爾對流(Bé nard-Reaktion)、DNA螺旋結構或激光束——因此,它們在藝術中也有著迥然各異的實現方式。藝術不單摹仿自然界中人們熟知的形態,還能憑借無窮的風格與范式彰顯宇宙的形式法則。[26]同時,這種多樣性還向我們揭示了世界的某些奧秘,這一方面指宇宙法則的無止無休,另一方面指表面各異的種種形態的共通性,即哲學中的“多樣統一”。[27]
于是,藝術經驗能夠教人體會多樣性的內涵。在藝術中,我們認識到,相同的原理如何可以形成繽紛多彩的現實形態,而且它們的地位是平等的。這樣說來,藝術經驗也可以傳授生活事務。它喚醒并培育我們的感知力、我們的理解力以及我們對各種世界觀和生活構想的包容力。我們開始懂得,不同的形態結構不僅存在于物理與藝術的層面,同時也存在于生活事務的領域——雖說通向幸福的道路千姿百態,然而卻都是等價的。在我看來,闡明這個問題,乃是審美教育的一項重要使命。
四、塑造政治生活的結論
按照此前所說,我在文章結尾將再次回顧席勒對藝術活動與政治生活關系的見解。席勒創造了“政治藝術家”這一術語,其核心觀點在于,政治也是有意識的塑造活動——甚至是最明確地以塑造生活為目標的活動。現在,如果部分與整體的協調是一切成功塑造行為的準則,那么顯然,政治的塑造活動也必須考慮到部分與整體的自由互動關系。席勒指出,匠人與藝術家[28]無需顧及所加工的質料。相反,“致力于教育和政治事業的藝術家”,即教師與政治家,由于所面對的對象不是死氣沉沉的材料,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也就必須格外慎重地對待與尊重。席勒甚至認為,在教育和政治活動中,整體必須為部分服務,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才應當、乃至可以聽從整體的召喚。[29]這就是說,席勒的要求是,整體的政治代表必須關注個體的權利,就像個體理應服從整體的要求一樣。[30](席勒的這個例子顯然不同于西方的個人主義模式。)他的政治目標在于實現部分和整體的唇齒相依,而這也正是我前面描繪的成功的審美形態與自由形態——或許,在這種部分與整體的相互尊重中,你們也能看到自己的社會與政治生活模式。
注釋:
[1]本文譯自韋爾施先生在“文化、藝術與人類發展的中國國際論壇”(2010年5月23-25日,北京)演講稿的德文版“Warum kann die Kunst zu einen gelingenden beitragen?”,為保證表達的流暢性,在翻譯過程中同時參考了英文版“How can art improve our lives?”的部分措辭(比如文章的標題)。
[2]此前,我曾探討過該話題的某些方面,請參閱拙文《美學的倫理內涵及影響》(沃爾夫岡·韋爾施:《美學的拓疆》,斯圖加特:雷克拉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34頁)。
[3]弗里德里希·席勒:《美育書簡》(1795年),載自《席勒全集》(卷五),戈哈特·弗里克、赫伯特·G·蓋卜弗特 主編,慕尼黑:漢瑟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669頁,此為第618頁。
[4]萊納·馬利亞·里爾克:《古老的阿波羅軀像》,1908年。
[5]約瑟夫·布羅茨基:《異樣的面孔》,載自《悲痛與理智》,紐約:法拉·斯特勞斯·吉魯克斯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8頁,此為第49頁。
[6]仍是在反向的形式中——在特定藝術流派受到批判的地方,西方傳統的倫理立場不時占了主導:這些藝術形態之所以遭到批駁,是因為它們背離了生活的真正目標。典型的例子便是柏拉圖對模仿藝術和戲劇藝術的批判。他認為,這些藝術形式不是強化理性的本質,而是通過展示感官與情感要素,誤導了人的認知與情感。(請參閱柏拉圖的《理想國》,第595-608頁。)另外,這種抵制模式跨越了數個世紀:經過本哈德·馮·克萊沃克斯對羅馬式雕塑的批判(因為依照其觀點,與其說神圣之物受人敬仰,不如說美艷之物更令人驚嘆。請參閱:“S.伯納蒂院長:向S.威廉·蒂歐得里希院長致歉”,載自米涅:《拉丁神父全集》CLXXXII,第 914-916頁),直到瓦爾特·塞德邁爾的《中心的喪失》(1948年)。
[7]在象征“為藝術而藝術”的實際宣言——《莫班小姐》(1834年)“序言”中,戈蒂埃抨擊了新聞道德衛士關于藝術應促進“道德重建”的無稽之言——這些人是從這一前提出發看待情色禁忌問題的。戈蒂埃反對這種將審美教化功能化的做法,并把美與無用性等同起來:“唯無用之物才真正有美;一切有用之物皆為丑,因為它們是需求的體現”。(詳閱艾克哈特?霍夫特里希:“何謂為藝術而藝術?”,載自《十九世紀末:世紀之交的文學藝術》,霍格·鮑爾等主編,法蘭克福:美茵茨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9頁。)后來的觀點仍是這樣:對自律性的強調批判了藝術功能化的謬論并摒棄了目的性。藝術自律性應服務于關鍵性目標,即形象地展現(并促進)正確的生活。到了阿多諾仍秉承這樣的理念,他認為,自律藝術提供了極端自我的范例,從而能對異化社會的虛假性做出批判。藝術“由于處于社會的對立面而有了社會性,這種對立的姿態僅在其成為自律物時方會存在。通過凝結成自為的實體,而不是因循現存的社會規范并憑借其‘社會效用’謀取合格的憑證,藝術只通過自身的存在對社會進行批判,而各類教派清教徒的攻擊即在于此。作為純粹的、遵循內在法則的建構物,它(藝術)對貶抑之詞做出無言的批判,所依據的狀況便是趨向于整體性的交換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切只為他者而存在——藝術的這種社會性偏離是對特定社會的特定否定”(西奧多.W.阿多諾:《美學理論》,載自《阿多諾全集》(卷七),法蘭克福:蘇爾坎普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頁)。詳閱合理性領域(認知的、倫理的、美學的等等)的區分與交織關系:沃爾夫岡?韋爾施:《理性:當代理性批判與橫向理性的構想》,法蘭克福:蘇爾坎普出版社1995年版,2007年第4版,第461-540頁。
[8]原句為“Nicht Eigennutz, sondern Ganzheitssorge ist die pragmatisch erfolgreichere Maxime”,在此,譯者借用中國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名句譯釋此句的部分語詞。
[9]不過,儒家學說(另一支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美學影響深遠的力量)同樣從道德立場出發,不僅闡明了正確行動的條件,而且還認清了優秀藝術創作的前提條件。
[10]老子:《道德經》第7章。
[11]我認為,貝多芬第六交響曲可謂典范之作。
[12]因此,一幅作品可以同時揭示出理想的社會,盡管表面看來它只關乎審美力量的平衡,并以完全抽象的方式略去所有的內容、特別是這種社會性的內容。蒙德里安的作品就是個典型。因為他的平衡藝術不僅涉及了繪畫因素,同時還對生活重量的平衡具有示范作用,這種平衡不僅在所有個體生活中發揮作用,而且對社會結構也有重要的意義。只有在懂得它們挺進到實踐維面的情況下,人們才會意識到蒙德里安靜穆、樸實的作品是完全真實的。蒙德里安本人也把它們視為平衡社會力量的典型,認為它們對民主社會是不可或缺的。同樣,人們也可以把蒙德里安的靜物畫當作隱藏的社會圖式。作品對象的排列顯然涉及了家庭關系。人們在此領會了等級、接觸、恐懼、自我主張、逃避、對照、結合。蒙德里安是立足宏觀社會學進行藝術創作的,而莫蘭迪則對微觀社會學情有獨鐘。
[13]“生”正是道家美學的一個基本范疇。請參閱卜松山(Karl-Heinz Pohl):《象外之象——中國美學史概述》,載自彼得.M.庫夫斯主編:《中國:歷史的維度》,圖賓根:嘗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243頁,此為第230頁。
[14]請參閱沃爾夫岡·韋爾施:《美的普遍欣賞》,載自《國際美學年刊》2008年第12卷,第6-32頁。
[15]老子:《道德經》第64章。
[16]關于造物主的激情與創作的模式問題,請參閱沃爾夫岡·韋爾施:《在創造的零點》,載自《國際美學年刊》2010年第14卷,第199-212頁。
[17]古斯塔夫·馬勒:《給安娜·馮·米登伯格的書信》(1896年6月或7月),載自《古斯塔夫·馬勒書信集》,維也納:澤爾奈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頁。
[18]古斯塔夫·科利安主編:《納塔利·保爾-萊希納追思古斯塔夫·馬勒》,漢堡:音樂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頁。
[19]P.M.多蘭主編:《與塞尚對話》,巴黎:馬庫拉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頁。同時,請參考約翰·凱奇的觀點“進步有可能意味著支配自然,而藝術則仿佛聽從自然的召喚”,載自理查德·柯斯特蘭尼茲:《約翰·凱奇談音樂、藝術與我們時代的精神問題》,科隆:杜芒特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頁。
[20]彭鋒:《論中國美學的現代性》(由英文名譯出),載自佐佐木健一主編:《亞洲美學》,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154頁,此為第144頁。
[21]請參閱卜松山(Karl-Heinz Pohl):《象外之象——中國美學史概述》,載自彼得.M.庫夫斯主編:《中國:歷史的維度》,圖賓根:嘗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頁。再提一下該觀點的道家思想背景——“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經》第9章)。譯者注:關于嚴羽的這個比喻,原文以闡釋性的語句做了描述。為使譯文顯得更加凝練,譯者在此略做調整,直接引用了嚴羽的原句。
[22]柏拉圖:《斐多篇》,250 d 7 - e 1。
[23]美雖然不是至高的理念,然而卻是將我們從自己的墮落狀態中有力拯救出來的最有效觀念。
[24]“美,或更確切地說是趣味,將一切視為目的本身,絕不允許一方把另一方當成工具或套上枷鎖。在審美領域,任何自然物皆為與至尊之物擁有同等權利的自由公民,不是為了整體意志被迫為之,而是根本上必須與所有事物保持協調。”(弗里德里希.席勒“論美”,載自《席勒全集》卷五,格哈德.弗里克與赫伯特.克.蓋卜弗特主編,慕尼黑:漢瑟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433頁,此為第421頁)。
[25]同上,第400頁。
[26]因此,西方藝術史明顯有承繼范式轉換的特點,在現代時期,這種轉換速度再次大大加快。
[27]當然,在藝術中,除了使自組織與協調性變得可感的目標以外,其他目標也能成為中心。目標的多元化同樣是藝術范式多元化的內容。但按照我的設想,自組織與協調性卻是藝術至為深刻的原理——任何直接和表面受到追捧的范式根本上都要對它負責并遵循它。
[28]按照席勒的術語,即“機械的藝術家”與“美的藝術家”。
[29]如果機械藝術家的手摸到尚未成形的質料,目的是把自身意圖的形態賦予它,那么他會毫無顧忌地施加威力:因為經過其處理的自然物并未受到他自己的尊重,他不是為了部分而關心整體,而是為了整體去留意部分。如果美的藝術家的手觸到上述質料,那么他同樣會施加威力而少有顧忌,只不過他會避免暴露這樣的威力。對于所加工的質料,他不會比機械的藝術家多一分敬意;但是,他會試圖通過某種反對相同做法的表面遷就,以欺騙捍衛材料自由的目光。獻身于教育與政治事業、以人作為材料與使命的藝術家則截然不同。在此,目的回歸了質料本身,同時,僅是由于整體為部分服務,因此部分才應聽從整體的召喚。與美的藝術家在物質面前偽裝出的尊重不同,從國家出發的藝術家必須貼近對象,但這不是單從主觀立場出發并追求欺騙性的感官效果,而應是珍惜個性與氣質,立足客觀視角并顯示出探索內在本質的趨向。參閱席勒:《審美教育書簡》(第四封信),載自《席勒全集》(卷五),戈哈特?弗里克、赫伯特·G·蓋卜弗特主編,慕尼黑:漢瑟出版社1980年版,第578頁。
[30]但正是為此,由于國家應是依靠自身、為了自身而發展的組織機構,于是,部分與整體的理念是協調一致的,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才能成為現實的存在。由于國家擔當了公民心目中純粹客觀人性的代表,因此,它必須立足于與公民相對的立場審視同樣的關系,而在這樣的關系中,公民是對自己負責的。只有在向客觀人性提升之后,主觀人性才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如果人的內心世界與外在行動是一致的,那么他也將在行動最大普遍化之際拯救其個性。此外,國家將僅是闡釋其美的天性,并更明確地表述其內心構想的法規(同上)。沃爾夫岡·韋爾施: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學哲學院理論哲學教授、當代著名美學家
責任編輯:李 雷
王卓斐: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