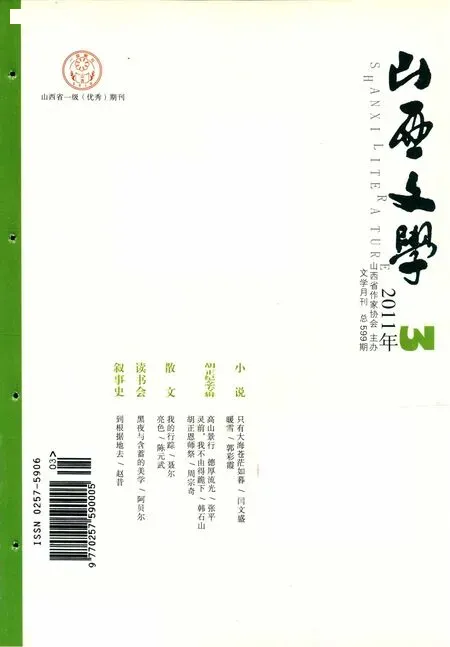到根據地去
趙 昔
到根據地去
趙 昔
這里記錄的人和事、時間和地點都是真實的。
1942年我還在北平女二中讀高中時,有幸認識了地下工作者姚繼鳴先生。我向他多次請求幫我逃出敵占區的北平去參加抗日。開始他否認有這種能力,后經多次的請求才答應了,說了一句“等機會吧”。以后的一年時間里,我一直和他有聯系。這期間有他對我的教育,也有對我的決心和勇氣的考驗。記得有一次他問我:“你敢從拿著刺刀的日本兵前面走過去嗎?”我當時很幼稚地想,我天天都看到日本兵在街上走來走去,他們也沒對我怎么樣啊,于是毫不猶豫地說“敢”。他問我這話時看來是有準備的,于是順手交給我一件女上衣,叫我到西單某胡同交給一位姓王的女老師,并囑咐我要繞開日本人的崗哨。倘若遇到臨時有檢查崗,要設法拐進附近的胡同,要拐得自然,別慌張。我接過衣服就走了。臨走時他又囑咐了一句“千萬別丟了衣服”。我一路不僅沒緊張,還有些得意地想這件衣服可能有什么秘密。
1943年6月,高中畢業考試結束后,姚先生約我6月18日去見他。這一天,我如約準時到了他在西城北溝沿按院胡同17號的家。當時他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和一個背朝外的人聊天。我走進一看有點吃驚,那個背朝外的人原來是他家的男仆王順,因為當時的社會根本不可能主仆平起平坐地一起聊天。姚先生雖覺察到了我的吃驚,卻沒做任何解釋,只和我說“你明天和他一起走,一切都聽他的”,說完就走開了。我見過王順多次,可從來沒說過話,無論什么客人來了,他只送上一杯茶就轉身走開,所以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男仆。今天他和我面對面說起了正經事,沒什么寒暄,開始就談起了離開北平的事:“明天下午四點前我們在前門火車站見面。除了最簡單的換洗衣服和兩本《升學指導》,其余的東西都不要帶。到了火車站,咱們必須裝作互不認識。進站時你跟著我走就行了。上了火車也不坐在一起,但彼此看得見。”頓了一下接著說:“萬一我遇到什么事你別慌,到了安陽下車后立即買一張回北平的車票去見姚先生就行了。”隨后他交給我一張火車票說:“你現在就回去做準備,這事對誰都不能說,也不要和任何人告別。”臨出門時他又加重語氣說:“一定要按時到站,誤了這趟車就走不成了。”當時我以為這些話只是一般囑咐,事后好長時間才悟到這里有多少重要的含義。

1942年攝于北平女二中體育室窗前,前排左一為作者
1943年6月19日下午4點,我準時到達前門火車站,看到王順已排在進站的行列里了。火車上的一切都比我們預想的順利,到了安陽已是20日的清晨,下了車我緊跟王順夾在人群中進了城。王順帶我走進一家小旅店,我被店主安排在兩間屋的里間休息,店主和王順在外間說話,聲音很小,我出于好奇側耳傾聽,很多話我都聽不清,但隱約聽到的意思是某邊的路斷了,另一條路困難多,危險也大,不過已經安排好了,一定要按預先的規定走,時間上也要嚴格遵守。還有幾句似乎和我有關,而王順肯定地說“沒問題”。
過了兩個多小時,王順叫我出來吃飯說:“一定要多吃點,因為今晚要趕路,要走很遠的路呢!”
下午3點,我們離開了小旅店,店主話不多,只把我們送到大門外招一下手就回去了,隨后我跟著王順走過地面上的鐵路線一直向西走,約走了兩個小時,來到一個掛有紅燈標志的派出所。當時的俗稱叫它巡警痞子,是個讓人厭惡的地方,老百姓說它是狗窩,而王順一如到小旅店時一樣自然地就進去了。這里的警察也很自然地各忙自己的事,好像根本沒看到我們。王順和我進入一間沒人的小屋坐下休息,緊接著一個警察送來兩杯水說:“喝吧,前面可沒喝水的地方,今晚我送你們過路。路上的動作要輕,不要說話,也別咳嗽,只要跟著我走就行了。”到了七點鐘,天還沒黑,警察帶我們走出派出所。王順在前我緊跟在后,一路上三個人只是低頭默默地走,沒任何聲音。四周安靜得如無人之境,忘了時間和地點,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不覺走到一條大溝邊了,憑感覺此時已是深夜。警察示意我們停下來,他獨自往前走了一段,再回來時多了一個穿偽軍制服的人,手里拿著一個鑰匙一樣的東西。兩人帶著我們順著溝往左走了約五六分鐘,到了溝邊的一塊平地上,只見對面橫過來一塊大木板。此刻警察已經不見了,偽軍在前,我和王順緊跟在后,輕輕地、快速地走過木板到了大溝的對面。我出于好奇借星光往上一看,這次可真嚇了一跳,原來我們是從日本崗樓下邊走過來的。這一瞬間,偽軍也已消失在夜幕中,只留下王順帶著我迅速地向前走。走了約十多分鐘,王順的腳步稍放慢了一點,我才意識到我們已把當時有名的平漢線上的封鎖溝甩在身后了。在那最緊張的一刻,最擔心的應該是王順、警察和那位身上背著壞名聲的偽軍,從此我不僅改變了對警察的看法,而且也對那些身不由己的偽軍多了些同情,而這位為我們放下吊橋的偽軍,我雖不知他是什么人,但在以后的“肅反”中我曾默默地為他祝福。
離開護送我們的警察和偽軍以后,王順和我依然無聲地前行,一直走到一個破敗的小村邊上,王順在一戶人家的外墻上敲了幾下,頓時左側的小木門從里面打開了,走出一位低著頭的駝背老人,把我們領進一間地上鋪了麥秸的小土房,暗示我們在此休息。王順立即坐下來,靠著墻閉上眼睛作睡眠狀,并指著地向我暗示,叫我也這樣休息。
這是我第一次走這么多路,確實覺得很累,但根本不能入睡,因為這一天實在太豐富了,我經歷了無限驚奇和神秘。我坐在松軟清香的麥秸上感到無限欣喜和滿足,當聽到一遍又一遍的雞叫聲時,我知道已經是6月21日的清晨了。此時,駝背老人悄無聲息地走進來了,沒說話只指了指門外,王順和我很快就又上路了。這次是老人走在前面,王順和我緊跟,走著走著東方已經發白了。駝背老人轉過身拉了一下王順的手,指了指正前方,即刻向后轉身消失在晨曦中,我甚至沒看清老人的容貌,他就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而他的身影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離開小村莊,我們一如昨天仍不敢說話,不敢有大的動作,仍是快步向前走。直到太陽升出了地平線,走到一個小山坡前面,一路上一直沒開口的王順才如釋重負地說了一句:“很快你就會看到第一個八路軍了。”此時此刻,我不僅放松了一直緊縮著的心,而且好像從一個殼子中跳了出來,這種感覺在以后的經歷中再也沒有過。隨后我們繞過這個小山坡走向一條很窄的碎石路,不遠處就是山,只見山前一塊巨石上站著一位身著草綠軍裝,手托上了刺刀的長槍的軍人,王順上前行了一個軍禮說了幾句什么,又隨手遞過一張紙條。對方立刻還了一個軍禮,放下槍,笑著說了一句什么,意思是放我們通行進山。
進入山區很快來到一個農家院,還沒進門就聽到了人們的說笑聲,進門以后只見院子里站滿了身著白粗布襯衫、綠色粗布褲子的年輕軍人,他們手端著搪瓷小碗正在吃早飯。當他們看到進來兩個穿便服的老百姓時先是一愣,但很快就有人認出了王順,大聲喊著“陳參謀回來了,陳參謀回來了”。隨即有人把我們領進一間打掃得很干凈的土墻土地的小屋,并送來兩份早餐(全麥饅頭和小米粥)。飯后一個很文雅的小兵送來一張表格,王順填完又叫我填,我看到姓名欄里王填的是陳志新,意識到這才是他的真實姓名,而王順是他地下工作的化名。王順邊吃飯邊和進來的幾個人聊天,他們毫無顧忌,暢所欲言,亂開玩笑,一切都是我從未遇到過的。這些年輕的小八路不僅對打日本充滿了信心,而且整個生活中都是陽光。我感到生活在這樣的群體中,才是真的幸福。看著這些幸福的人我只是心感神秘,沒有可以表達的語言。王順覺察出了我的心態,立即大聲說了一句:“你已經進入太行山的根據地了,現在自由了,可以隨便說隨便笑隨便喊打倒小日本了。”這一刻,我的心情很難用語言說清楚,有興奮和驚奇,更多的是高興,甚至還有點不敢相信我已到了另一個世界。因為從離開敵占區到目前的自由世界還不到三天,短短的兩天半時間里換了天、換了地、換了一切,整個地獄換了人間。這是在北平時夢寐以求的,如今已成了事實。
飯后戰士們都各自走向崗位,王順說帶我到村邊轉轉,放松一下昨夜的緊張,可我不敢去,因為我身上穿的還是北平的學生制服。王順說:“這里是進入根據地的大門,大部分從北平出來的學生都經過這里的,戰士和老百姓都看習慣了,而且只有到了總部才能發給你軍裝。”
我們在這個連村名都不知道的小村莊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離開時的告別聲是格外的熱情和親切。
我和王順漸漸走向太行山深處,一路上是巨石綠樹,還伴有花椒樹的清香,又看到不少村莊都有簡易的籃球場。說它簡易,因為只是在一塊不平整的土地上豎著一根木桿,上面掛了一個鐵圈。王順告訴我這是戰士們自己動手修建的操場,早晨出操,中午和晚上打球都在這里。凡有這個設置的村莊就都有八路軍駐扎,只要是公家人都可以在此住宿。
第四天我們走進一個較大的村莊,房屋也較整齊,看得出來,這是個敵人沒來過的村莊。當晚我們就在這個村莊住下了。臨睡前,王順帶著幾個穿細布軍裝的人說笑著進來了。王順說:“首長來看你了。”進來的這幾位穿細布軍裝的人照樣地平易親和,又隨便問了幾句敵占區和過封鎖線的情況,臨走時他們說了一句話是:“看來咱們平漢線的工作已經做到敵人的心臟了。”還順口夸了我過封鎖線時的勇敢。其實我根本不是勇敢,而是在不懂、不知的情況下走過來的。真正勇敢的是王順和一個警察、一個偽軍,而后兩個人身份的真假,對我來說這一輩子都是一個找不到謎底的謎。
第二天走在路上時,王順告訴我昨天的村莊叫王堡,一二九師的師部就在這里,昨晚來看我的一群人中就有劉伯承師長。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劉伯承的名字。
在此后的幾天行途中,除了青山、綠樹、巨石和清香的氣味外,還不時聽到遠處飄來的“我們在太行山上,我們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也壯”的歌聲,這歌聲使我這個剛從敵占區過來的年輕人感到十分新鮮生動,且鼓舞人心。對這里新鮮的人和事,我心中大有應接不暇之感,不僅忘了敵占區的壓抑苦悶,幾乎也忘了饑渴。
過兩天,又聽到了新內容的歌,是民歌形式的“老鄉老鄉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的吟頌,稍低沉,仿佛訴說著對親人的思念。又是王順告訴我,這是太行山上的群眾懷念今年5月大掃蕩中犧牲的左權將軍的歌。左權這個名字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日后回憶起這些經歷,我真覺得我當時就是一個盲人,對身處的環境十分無知。
在歌聲伴隨中我們又走了一天半,來到一個很大的村莊。王順說:“咱們到家了,這是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所在地的麻田村。”進村后,王順帶著我直奔一個農家大院,立即有一位皮膚白皙身穿軍裝的女同志迎上來說:“小陳一定辛苦了。”王順走向前握了手說:“林一同志,我又給你帶來一個人。”隨后從衣袋里掏出一個小玻璃瓶交給她,又對我說:“這是林一同志!我把你交給她了。”此時沒容我們多說什么,林一就說:“小陳快去休息吧。”這句話像命令一樣,王順轉身走了,我沒料到這一別竟是永訣。
后來得知,真名陳志新的王順,是陜西人,地下工作交通員,不久后犧牲在日本人的屠刀下。
林一是前總情報局局長,是姚繼鳴先生的直接領導。這位情報局長身材苗條,臉形秀麗,膚色白皙,說話也輕聲慢語,儼然一個大家閨秀,穿一身戎裝顯得格外有風度,完全看不出是整天出入在戰火紛飛的深山密林中的情報人員,我頓時產生一種由衷的欽佩和敬仰。
林一把王順打發走以后,我心里有些茫然和失落,因為是他帶我離開北平的,一路的驚險都是在我不知底細的情況下由他承擔的,且沿途中告訴我許多我不曾聽說過的事,他是我進入八路軍的第二個導師,是我的啟蒙老師。本想到了駐地后好好跟他聊聊,再向他請教沿途中的許多疑慮,在感謝聲中向他告別。豈料就這么匆匆地分手了,這是我心中的一大遺憾。
和王順分手的當晚我留在了總部,以后的一切都是林一親手安排直至奔赴延安。
當天林一把我安排在一個軍屬家住下來,告訴我:“這是一家十分可靠的基本群眾,但也不要和他們聊北平的情況;村里也有壞人或特務,不要隨便到處走動;不管什么人問你什么,你只說聽不懂他們的話什么也別回答,明天換上軍裝,我會叫送飯的小鬼把衣服一齊送過來。”
晚飯是一個小八路送來的,還帶來一套草綠色土布軍裝。我第一次穿上軍裝時又是一陣難以言傳的興奮和喜悅。這些所有的第一次,這些喜悅和激動,驚奇和興奮,都被我收藏為永久的記憶,深藏在心靈的寶庫里了。
我在麻田村住了一個多月,似乎又是在等待什么時機。在這段日子里,除了體驗了兩周太行山上的師生生活外,其余的時間都是在麻田村度過的。我參加了七月一號的慶祝會和豐盛的會餐,見識了用洗臉盆盛菜和用高粱稈作筷子的新鮮事。這些在八路軍隊伍中的平常事,對我來說都是第一次,所以覺得既新奇又有趣。
在麻田村的日子里,有件最讓我難以忘懷的事。一天晚飯后林一帶我到村邊散步,我們走在田埂上,看看四周的山和眼前掛滿黃瓜的瓜架以及還沒成熟的西紅柿,呼吸著菜地里的濕潤空氣,享受著農村獨有的溫馨香味。當我們漫步到另一個田埂邊時,只見幾個小八路正在渠邊澆水,埂上稍突起的土包上,坐了幾個人正邊說笑邊吃著剛摘下的黃瓜。林一和一位年齡較大的人邊打招呼邊說:“老總,我這兒來了一個剛從北平過來的女學生。”對方立即轉過臉來笑著說:“小鬼出來幾天了?過來嘗嘗我們親手種的黃瓜吧。”并隨手遞過來一條鮮嫩的黃瓜,林一也接過一根,大家一邊吃一邊聊天。被稱老總的那一位又接著說:“北平的日本人都在搞什么強化治安運動,這是針對我們的,你知道嗎?”我搖了搖頭。他又說:“敵人還說我們是土匪,說我們到處殺人放火,你不怕嗎?”我說:“北平的中國人都不相信他們的鬼話,而且很多學生都想參加抗日,就是苦于找不到門路,我認識的姚先生也不許我告訴別人。”林一立刻說:“這是紀律,是工作的需要。”緊接著又說:“我帶你到別處再轉轉吧。”路上林一問我:“你知道叫你吃黃瓜的人是誰嗎?”我說:“除了你和王順,我一個人也不認識。”她說:“親手給你黃瓜的人,是我們八路軍讓日本鬼子聞聲喪膽的彭德懷老總。”彭德懷這個名字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回村的路上,林一又帶我去看了滕代遠參謀長的住處。他的住處是一間農民的房子,室內只有一張用門板架的床,上面鋪了一條軍毯、一條薄薄的粗布棉被,地上放了一個小木桌、一個木凳,墻上掛著一件日本軍大衣。林一風趣地說:“軍大衣和軍毯都是日本鬼子給我們送來的禮物(戰爭中繳獲的勝利品)。”滕代遠這個名字,自然毫不例外也是第一次聽到。
這一天——1943年6月下旬的傍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而姚繼鳴先生,交通員王順,安陽小旅店店主,一個偽警察,一個偽軍,駝背老人,前總情報局長林一,以及八路軍的副老總,這些平凡而又偉大的人物從此都珍藏在我的記憶中,成為我最大的精神財富,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永遠給我鼓舞,給我力量,促我前行。
附:作者簡歷
趙昔,女,1924年出生,漢族。1937年入北平女二中,1943年高中畢業。當年6月經北平地下黨介紹到達太行區八路軍總部,隨之到達延安,在魯迅文學藝術學院學習。1945年隨華北文藝工作團到前方張家口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工作兩年,內戰爆發,隨學校輾轉于華北農村冀中一帶工作。1947年底石家莊解放,參加支援新解放城市工作,到石家莊女中任教。1949年全國解放后,先后在北京女三中、北京女十二中、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中央美術學院任教。1978年“文革”結束,任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院長辦公室主任、共同課教研室主任,兼任文學課教學工作。1987年離休。
照片由作者提供 責任編輯/朱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