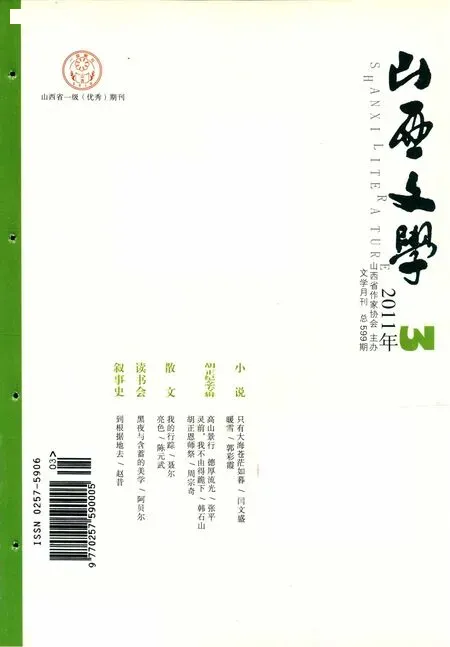胡正恩師祭
周宗奇
胡正恩師祭
周宗奇

1999年9月作者與胡正在作協機關大院
六天前,就是元月12號,我在博客上發過一篇配有照片的小文《歲月真無情》,很短,如下:
忽然翻出這么一張老照片什么意思?
這是幾年前與胡正老師在機關大院的一張合影。你看,“五戰友”碩果僅存的他是多么精神矍鑠,可今天下午當我們來到他病床前時,情景又叫人多么痛心、難過,那樣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漢,被病魔啃咬得面目全非。我的心在顫抖!
當年,是他和馬烽、西戎三位老作家,親自下去把我從煤礦里挖出來,走上一條文學之路;剛作了半年小說編輯,又是他代表作協黨組與我談話,要我出任《山西文學》編輯部副主任;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無聲的細流》是他作的序;我升任《山西文學》副主編、主編,成為當時全國省級文學期刊最年輕的主編,他都是最主要的推手之一;即便后來我的文學追求與他們的“山藥蛋派”漸行漸遠,他總以博大的胸懷和豪爽的笑聲將我包容……他和馬烽先生、西戎先生、孫謙先生一樣,都是有大恩于我的人生老師、文學父母。
今天這是怎么了?下午3點我和王東滿去吊唁一位謝世者,我的大學同學,他的通家故交,心情本來就很沉重。剛回來占平兄就電話告我說,胡老住院了,狀態很不好。于是我們倆又加上張石山、陳為人,直奔省人民醫院,看到的場面足可叫人徹夜難眠……
固然,生命總有盡頭。可你來得太突然,太不近人情啊!上個月胡正先生還和我們一道出席盛會——《山西文學》創刊60周年紀念活動,他還是那樣的談笑風生……現在這傷心的一幕,卻讓我們如何接受?我們四條漢子只好忍著淚說:胡老師,你會好起來的!
拙博文的反響還有點,有評論,有收藏,有留言……其中有人說,“一直沒見過胡老,這次算了了一樁心事,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復”;有人說,“我向太陽許個愿,愿太陽為胡正先生及時送去溫暖”;更多的人則是“為胡老祈福”、“為前輩祈福”、“祝福胡老師快好起來”……最叫我動心動情的是這樣一位博友,他有感于圖文,說:“他像你父親!”
我自幼喪父。父親于我是一種聲音:“到了,別睡了。”后來我追問母親,她說這可能在西安時,夏天去你老舅八里莊別墅路上的事吧。這就是我僅有的父愛。11歲離開家,離開母親,到外面上高小,上中學,上大學,暑假打工掙學費,頂著個“資本家兼地主”的家庭成分踏上人生苦旅。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了,卻被打發到人間最底層——下礦井挖煤去。無限少年繽紛夢,盡付東逝水,知向誰邊?這一種失落,屬于永遠的心痛。總不甘沉淪,便氣鼓鼓地開始寫小說,先后在《解放軍文藝》、《光明日報》、《山西日報》等報刊發表了近10篇(部)中短篇小說之后,依然難以出山(老實說,當時拼命寫作,就是為了改變處境,絕無什么“兩為”覺悟),那時我真的徹底絕望了。
也就在這時,馬烽、西戎、胡正三位先生出現了。他們不知為什么事來到臨汾,問文聯主席鄭懷禮有沒有發現“好苗子”。胖乎乎的可愛的鄭老頭后來告訴我,他說霍礦有個娃寫得不錯。他第一個就推薦了我。于是乎,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三位先生面前,算面試吧。北返時我們同車。胡正先生問我:“想去太原工作嗎?”我的心狂跳不已,我說想去,其實我想說的是,這不是做夢吧!車到辛置站,我不得不下來,望著北去太原的火車,我禁不住熱淚長流……這么多年來,有的只是歧視、壓制、傷害與冷漠,哪有過這樣父親般的溫暖與關愛?
1979年,我發表了新作——短篇小說《新麥》。不料引出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河南等省先后有幾位縣太爺告“御狀”,說《新麥》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應追究作者責任(有的告到中央組織部,一位姓高的大學同學在那兒工作,事后講給我聽的)。省內也有一位縣太爺找上門來說事。又多虧當家的父輩們替我遮風擋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胡正先生特別約我說:你該出個集子了,別忘了把《新麥》鬧上。我來寫序。他在序中寫道:“周宗奇是一位富有熱情而又勤于思索的青年作家。”“他在保持前幾年創作的特色,即飽含激情描繪善良的普通人的同時,開始了較深的探索。”“《新麥》是一篇有著較大社會影響的佳作。他寫了‘四害’橫行時一個縣委書記為了邀功而虛報產量,使得全縣人民挨餓,他卻高升……的故事。揭示了直到今天或者以后都值得深思的問題。”“每當他的小說發表時,就以其真摯的感情,使人感奮的力量,和他所著力塑造的一些感人的人物形象,以及發人深思的社會現象吸引著我,以至在這本小說集出版前我又重讀他的作品時仍不減興味,這就是我所以喜歡他的作品的緣故。”
還有什么比這種帶著父輩關愛的鼓勵與支持更有力量的?
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我又“開始了較深的探索”。我把關注農民問題改為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把對人的生活現狀的描繪改為對其靈魂的掃描,把已然失重的小說形式改為批判色彩的紀實手法,而且選中了一個填補歷史空白、然而注定不會帶來好果子吃的課題——中國文字獄……我完全忽略了自己是在一個父輩們視為生命所在的“山藥蛋派”的大本營,這里是演繹農民正劇和喜劇的標桿舞臺,唯一的宗旨就是為黨寫農民。
當然,我有我的思索。“三農”問題固然事關國運民脈,頭等重要,可知識分子問題就是二等重要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沒有一支一流的知識分子隊伍能行嗎?他們應該“不趨炎附勢,不迷信權威,不貪戀財富,不屈服于恫嚇”,具有最先進的社會理想和獨立社會人格,他們應該像蘇格拉底一樣公開質疑權力設定的價值標準,不惜丟掉寶貴生命;應該像索爾仁尼琴一樣,誰搞暴政殘害人民就把唾沫吐在誰臉上;應該像托爾斯泰一樣,面對沙皇政府的血腥暴政而寫下《我不能沉默》的正義篇章;應該像我們的山西前賢楊深秀一樣,為了改革大業甘愿舍生取義……他們沒有一點私心,這樣做完全是對社會罪惡的憤怒,對人民苦難的敏感和同情,對一名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格尊嚴的愛惜與敬畏。
然而你去反觀一下我們的知識分子同類,先秦以降兩千多年來,有幾個這樣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在多有的是臣服權力,迷戀官場,爭功邀寵,變賣靈魂……精神侏儒化愈演愈烈,文化軟骨病日甚一日,唯有在圍剿自己的同類時,才表現出意外兇悍的戰斗力,因為洞悉同類的弱點與羞處,往往一擊中的,見血封喉。一部血淋淋中國文禍史,就是代代犬儒知識分子們的狂歡與敗亡。
為此,讓他們像農民一樣覺醒、反思、振奮,把自己人頭按在自己項上,把自己靈魂裝回自己胸腔,重塑一個具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不屈操守的知識分子自由身,難道不是一件于國于民于己都很有意義的事兒嗎?
我父輩的作家們,馬烽先生,西戎先生,孫謙先生,當然還有胡正先生,能理解我的思索嗎?從他們的眼神中,神態中,話語中,沉默中……我明白了代溝的含義。但是,他們是偉大的父輩,胸懷博大,仁慈善良,我不喜歡但我不反對,非我門派卻也容納,我不放心把家業傳承于你這個兒子,可我也會讓你吃飽穿暖,想干啥盡管干,能成就一番功業我照樣高興,證明你錯了你再回來也不算晚。尤其胡正先生最為開明,見面總會關切地問:文字獄寫到哪兒了?有什么困難沒有?要寫就寫完,別半途而廢;出版不了別氣別急,放一放,慢慢會好的……就在前不久,我把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的《清代文字獄》送給他時,故意開玩笑說,胡老師,以前我送過你了,這一版的就算了吧?他立馬一陣陳為人先生認證的“胡正式”哈哈大笑:“要,要,這一碼是一碼呀。”在“五戰友”中,如果說那幾位父輩更多一種“黨員老作家”的威嚴的話,胡正先生則別具一種民間文人的平和、親和勁兒。
而今,“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眾多博友的祝福祝愿,抵不過趙壹這《秦客詩》,胡正父輩終于沒能好起來,趕在春節前駕鶴西行,要與馬烽先生、西戎先生、孫謙先生、束為先生歡會于高天祥云之上,把酒笑談之間,再續“五戰友”前世未了情緣。
只是,這遽爾降臨的天地造化,讓我們活著的后來者不能承受之重,滿腹痛悼之情又如何倉促成篇?哀哀之中,唯愿胡正先生及其他父輩英靈,遨游九天之余,莫忘繼續關愛你們的后代子孫;魂歸大美之日,再將東四條的文學事業做大做強。
胡正父輩,你永駐我心!
責任編輯/白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