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shī)歌筆記
孫文波
詩(shī)歌筆記
孫文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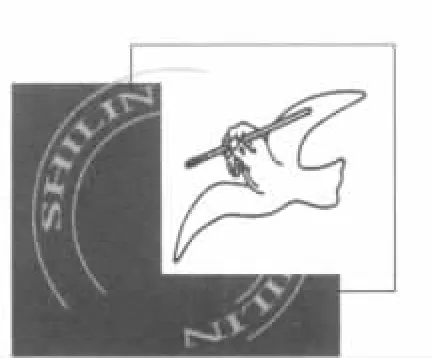
1
如果問(wèn)正在寫作的詩(shī)人:“你寫的什么詩(shī)?”他很可能不假思索,會(huì)脫口而出告訴問(wèn)他的人,“我寫的當(dāng)然是當(dāng)代詩(shī)了”。但如果又問(wèn):“你真能確定自己寫的是當(dāng)代詩(shī)嗎?”可能他會(huì)認(rèn)為這樣的追問(wèn)是在開(kāi)玩笑。在很多詩(shī)人的意識(shí)里,自己寫作的東西天然的就是當(dāng)代詩(shī),如果不是,還會(huì)是什么?也許他們從來(lái)沒(méi)有想過(guò),問(wèn)題并非那么順理成章,而是其中隱含著寫作意識(shí)與當(dāng)代社會(huì)關(guān)系這樣的,帶有認(rèn)識(shí)論色彩的對(duì)世界的理解。由此我們才會(huì)說(shuō):一切正在進(jìn)行的詩(shī)寫作是不是當(dāng)代詩(shī),問(wèn)題的關(guān)鍵不是別的,是寫作意識(shí)的確定,即寫作是在什么樣的對(duì)社會(huì)的認(rèn)知上展開(kāi)的。要真正理清這一問(wèn)題并不簡(jiǎn)單。就中國(guó)目前的社會(huì)狀況,以及文化思想狀況,要從中辨識(shí)出什么樣的認(rèn)識(shí)落實(shí)到詩(shī)上具有當(dāng)代性,以及這一當(dāng)代性又是怎樣與寫作契合而完整呈現(xiàn)出來(lái),需要我們有更為全面的文化把握能力。不然的話很難說(shuō)清楚。就像今天的人們一般都把朦朧詩(shī)的出現(xiàn)看做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的發(fā)韌,因此才會(huì)有“當(dāng)代詩(shī)三十年“這樣的涵定。不可否認(rèn),如果將朦朧詩(shī)作為開(kāi)端看待,它的確與之前的詩(shī)歌有很大區(qū)別,不再與意識(shí)形態(tài)宣傳聯(lián)系的那么緊密,而是在尋求詩(shī)的“自主性”的前提下展開(kāi)。但是,如果僅把“自主性”看做當(dāng)代詩(shī)的支撐,很顯然是不夠的。因?yàn)榫臀膶W(xué)的基本存在意義而言,“自主性”是它的必須要求。所以,我們不能簡(jiǎn)單地以此來(lái)論定當(dāng)代詩(shī)的獲得是由此一指標(biāo)的出現(xiàn)而成立的。如果用更完全的,譬如當(dāng)代文化意識(shí)、政治意識(shí),以及當(dāng)代生活對(duì)于人的生命的意義,當(dāng)代生活與未來(lái)生活的關(guān)系等觀念來(lái)考量,也許我們甚至可以認(rèn)為朦朧詩(shī)的當(dāng)代性其實(shí)也是并不完全成立的。在不少朦朧詩(shī)中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基于古典倫理觀念支撐的詩(shī)學(xué)認(rèn)知。雖然可以說(shuō)這里面包含著某種變動(dòng)不居的人類理念,但是,應(yīng)該看到的是,由于人類生活到了今天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復(fù)雜性,并由此改變了很多人類關(guān)于世界、關(guān)于自我的認(rèn)識(shí),因此如果沒(méi)有重新獲得的、與之相應(yīng)的認(rèn)知,我們便很難真正在寫作中做到完全的呼應(yīng),并呈現(xiàn)出能夠說(shuō)明其意涵的文學(xué)答案。
2
如果我們還要在越來(lái)越無(wú)望的生活中尋找意義,或者我們以為自己能夠在人生的跋涉中,劈荊斬棘找到一條出路,這說(shuō)明了什么?是不是說(shuō)明我們實(shí)際上對(duì)死亡還有畏懼?在今天這個(gè)混亂的世界上生活,有時(shí)候我感受的是:不得不生活。用一句時(shí)髦話說(shuō)是,“被生活”生活著。但是,誰(shuí)又不懼怕死亡?我聽(tīng)到過(guò)很多人談?wù)撟约合胨劳觯詈笫菦](méi)有勇氣去死亡而仍然選擇了活下去。好多年前,當(dāng)我閱讀那些中西古代圣賢的著作,常常被他們的言論搞得內(nèi)心戰(zhàn)栗。那時(shí)候我驚訝于他們關(guān)于死亡能說(shuō)出那么多頭頭是道的話來(lái),覺(jué)得他們真是有大智慧,把一個(gè)絕對(duì)問(wèn)題搞得如此透徹。現(xiàn)在我理解到了,當(dāng)他們?nèi)绱苏務(wù)摃r(shí),實(shí)際上不過(guò)是在抵抗死亡,或者說(shuō)抵抗內(nèi)心中對(duì)死亡的畏懼。但是“逝者如斯夫”。一切都是沒(méi)有用的。他們誰(shuí)不是被時(shí)間帶到了死亡的深處,留下的一切與他們有何關(guān)系?而說(shuō)到“死亡的深處”,這樣的詞實(shí)際上是修辭化了的。到如今,我知道我過(guò)的不過(guò)是一種修辭的生活。我每天糾纏不休的,是用語(yǔ)言為自己制造一種幻覺(jué),即:通過(guò)使用它,我能夠到達(dá)自己的身體無(wú)力到達(dá)的地方。有人說(shuō)這是一種傳達(dá)。姑且承認(rèn)這種說(shuō)法。但是從更深的理解來(lái)看,我知道任何傳達(dá)都是與自己最終無(wú)關(guān)的。也許真正的悲哀便來(lái)自于此。我,以及那些和我一樣想要通過(guò)寫作來(lái)對(duì)抗死亡的人,不過(guò)是在進(jìn)行著注定要失敗的徒然的勞作。
3
對(duì)于閱讀而言,“重新”二字永遠(yuǎn)有效。尤其是對(duì)與自己同時(shí)寫作的人的作品的重新閱讀。譬如二十年前,當(dāng)我讀到一位有交道的同行的某首詩(shī)時(shí),產(chǎn)生過(guò)震動(dòng)的閱讀感,于是便一直在心里對(duì)那首詩(shī)的評(píng)價(jià)很好,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段談?wù)摰剿鼤r(shí),也是給予贊揚(yáng)的言辭。但實(shí)際上真實(shí)的情況則可能不是這樣的,那首詩(shī)并沒(méi)有那么好,當(dāng)初之所以在閱讀它時(shí)產(chǎn)生了那樣的震動(dòng)感,是由于自己對(duì)詩(shī)的認(rèn)識(shí)或者還沒(méi)有達(dá)到真正的深入,或者是在某種具體的閱讀氛圍中被具體的東西所牽扯。現(xiàn)在我已不再相信自己二十年前對(duì)某些詩(shī)的閱讀印象,如果還要談?wù)撨@些詩(shī),我總是讓自己重新閱讀它們,如果閱讀的過(guò)程中仍然能夠讓我認(rèn)為所讀作品不錯(cuò),那么我才真正的認(rèn)為它是一首好詩(shī)。用這樣的方法近段時(shí)間我已經(jīng)否定了不少詩(shī)過(guò)去留在我記憶中的印象。
4
“煙花三月下?lián)P州”,這句詩(shī)大名鼎鼎。一直被后來(lái)人看做是寫江南的最形象的句子之一,也一直引發(fā)人們對(duì)江南的想象。其實(shí),不止是這句詩(shī)了,關(guān)于江南艷麗的談?wù)撘讯嗳缗C=希诓簧偃说男睦镌缇褪菬熁ǚ笔⒅兀侥抢锶ィ欢〞?huì)目睹數(shù)不清的風(fēng)月之事,并享受到某種意義上的最奢靡的生活。我大概也是受了這種東西的影響,到了杭州后,一直在觀看哪里有可以被稱之為體現(xiàn)古意的繁華之景。但結(jié)果不免失望。如今杭州的生活情態(tài),與我在中國(guó)其他城市看到的生活并沒(méi)有兩樣,它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同樣是當(dāng)代中國(guó)典型的城市生活。也就是說(shuō):中國(guó)生活。當(dāng)然了,就風(fēng)景而言,杭州以西湖為中心的周邊地區(qū),仍然是中國(guó)城市最美的。這一大片區(qū)域,植物長(zhǎng)得茂盛,種類也多,并且打理得很好。在這一區(qū)域游逛,讓人感到視覺(jué)上舒服,尤其是傍晚時(shí)分,常常會(huì)因?yàn)槁飞蠠o(wú)人,享受到靜。現(xiàn)代都市喧鬧,能夠在城市中享受靜,是很奢侈的事。僅這一點(diǎn),已經(jīng)讓人心里產(chǎn)生諸多感慨:要是中國(guó)的城市都能夠像西湖地區(qū)一樣,無(wú)論從人自然生活的角度,還是從社會(huì)生活的角度讓人獲得滿足,可能就不至于像現(xiàn)在,到處都是乖戾之氣橫行。以至于有時(shí)候我不得不這樣想:也許正是環(huán)境的原因,才使得當(dāng)代中國(guó)人精神上陷入混亂。有一段時(shí)間,我傾向于批判混亂。但是現(xiàn)在這種批判的勁頭明顯小了,因?yàn)槲铱床怀鏊墓τ煤卧冢D(zhuǎn)而同情的想法占據(jù)了我的內(nèi)心。我覺(jué)得在那么多人需要活下去的地方,為了生存,不得不想盡法子,困難又大的情況下,乖戾的行為出現(xiàn)也算正常。因此,我已不再像過(guò)去,一說(shuō)到無(wú)論什么事,便一股抱怨之氣。相反,我已經(jīng)能夠用比較平靜的心態(tài)接受自己所處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而從另一個(gè)角度講,有時(shí)候我實(shí)際上在內(nèi)心深處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混亂抱有一種幸臨之的心態(tài),覺(jué)得從寫作的角度看,混亂能夠給我?guī)?lái)可資談?wù)摰脑掝}。古人云:國(guó)家不幸詩(shī)家幸。所謂文學(xué)需要的沖突,在激變中生成的悲劇感,如果沒(méi)有從混亂中提煉的先在條件,怎么能夠產(chǎn)生呢?雖然,這有點(diǎn)要詩(shī)而不顧現(xiàn)實(shí)生活帶給人的普遍的痛苦了。但是人類的命運(yùn)中不可能有完善的存在,當(dāng)它在此呈現(xiàn)得非常充分的情況下,為什么又不承認(rèn)它呢?
5
前天晚上在柏樺家喝酒,見(jiàn)到搞德國(guó)文學(xué)翻譯的林克,他送給我他翻譯的荷爾德林詩(shī)選《追憶》,和特拉克爾詩(shī)選《夢(mèng)中的塞巴斯蒂安》。昨天和今天我將這兩本詩(shī)選翻了翻。這兩位德語(yǔ)文學(xué)人物,我早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就讀過(guò)他們的一些詩(shī)作,對(duì)他們還算熟悉。只是時(shí)間過(guò)去二十年左右,這次重新讀到林克的翻譯,感到特拉克爾不是像八十年代讀時(shí)那么吸引我了,但荷爾德林則讓我對(duì)之有一種重新的認(rèn)識(shí)。
德語(yǔ)文學(xué)重理性,講道理,因此很多詩(shī)歌,包括歌德的作品,都給人說(shuō)理的印象。荷爾德林作為一個(gè)被稱為德語(yǔ)詩(shī)人僅次于歌德的大詩(shī)人,盡管也在不停地說(shuō)理,但他的很多詩(shī)充滿了細(xì)節(jié)的描述。這次讀他,讓我一再想到華滋華斯。像《漫游》這樣的詩(shī)與華滋華斯的《丁登寺賦》太一致了,都是通過(guò)對(duì)鄉(xiāng)村景象的述說(shuō),表達(dá)一種情懷。也許是林克翻譯的原因,甚至語(yǔ)調(diào)都讓我感到特別像。
華滋華斯是我一直很喜歡的詩(shī)人,在他的詩(shī)中有一種非常干凈的東西。如果把這種東西稱為色彩,那么就是藍(lán),如果將之稱為聲音,則像山中泉水流過(guò)石澗。這次讀荷爾德林的詩(shī),讓我感到同樣的東西。
當(dāng)然,他們還是有不同,在荷爾德林那里,始終有對(duì)神的敬畏,和對(duì)神性護(hù)佑的祈盼。正是這一點(diǎn),使得他的詩(shī)一直是向上舉的。如此一來(lái),就音調(diào)而言,荷爾德林的詩(shī)里一直有一種響亮的、面對(duì)著天空發(fā)聲的調(diào)調(diào)。因此,當(dāng)他做得最到位時(shí),我感到詩(shī)中出現(xiàn)了寬闊的東西。的確,這次讀荷爾德林,給我的最重要的印象,即是他的寬闊。
偉大的詩(shī)人必須是寬闊的詩(shī)人,這一點(diǎn)應(yīng)該是毫無(wú)疑問(wèn)的。而荷爾德林帶來(lái)的這種寬闊當(dāng)然不是僅僅上面說(shuō)到的那一點(diǎn),還在于對(duì)終極問(wèn)題的追尋。荷爾德林在德語(yǔ)中被稱之為哲學(xué)詩(shī)人,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還在于他始終在詩(shī)中探究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以及人的命運(yùn)的實(shí)質(zhì)。更為關(guān)鍵的是他總是把這種探究與“祖國(guó)”這樣的民族身份聯(lián)系在一起。我覺(jué)得德國(guó)人之所以那么喜愛(ài)他,應(yīng)該和這一點(diǎn)有很大關(guān)系。
近來(lái),我一直在想“絕對(duì)”這個(gè)概念與詩(shī)的關(guān)系的問(wèn)題。盡管我在九十年代提出過(guò)“在相對(duì)性中寫作”這樣的理念。但其實(shí)我亦并不是對(duì)“絕對(duì)”沒(méi)有思考過(guò)。我發(fā)現(xiàn)成就一個(gè)詩(shī)人偉大的重要點(diǎn)之一在于:他必須對(duì)“絕對(duì)”有所觸及。從這個(gè)意義上講,荷爾德林的確是一個(gè)不斷糾纏于“絕對(duì)”問(wèn)題的詩(shī)人,他的詩(shī)幾乎都可以看做是對(duì)人類終極問(wèn)題的觸動(dòng)。
就今天的意識(shí)形態(tài)而言,我當(dāng)然不會(huì)認(rèn)為他談?wù)摰哪且徽讍?wèn)題,對(duì)我是有效的。不過(guò)我欣賞他由此在詩(shī)中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圖景。我認(rèn)為正是這種將自己與偉大事物聯(lián)系起來(lái)的方式,使得語(yǔ)言獲得了一種干凈的特質(zhì)。聯(lián)想到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為什么很多時(shí)候總是讓人感到語(yǔ)言的質(zhì)地太雜蕪,可能真的與寫作者僅僅在細(xì)節(jié)與俗事上糾纏有關(guān)。
當(dāng)然,獲得談?wù)摗敖^對(duì)”這樣的問(wèn)題的前提并非那么容易,它肯定是一種對(duì)世界的深刻認(rèn)識(shí)帶來(lái)的理解力。譬如談?wù)摗八劳觥保務(wù)摪ā疤摕o(wú)”這樣的問(wèn)題,如果沒(méi)有獲得對(duì)之的真正認(rèn)識(shí),并在這種認(rèn)識(shí)中找到一種談?wù)摰姆椒ǎ敲聪胍務(wù)摰淖屓烁械接辛Γ械揭?jiàn)識(shí)高邁,幾乎不可能。說(shuō)到底,仍然與智慧深入事物內(nèi)核的程度有關(guā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