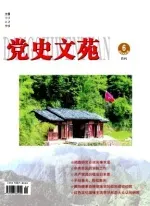使用歷史檔案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熊軼欣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 江西省井岡山 343600)
使用歷史檔案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熊軼欣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 江西省井岡山 343600)
在歷史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要依靠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為中介,進行相關的挖掘和應用。本文對使用歷史檔案要注意的全面性、真實性、邏輯一致性、關鍵問題完整性等幾個問題進行了論述。
歷史檔案 使用說明 全面性 真實性 邏輯一致性 關鍵問題完整性
歷史是社會前進的基礎,是開創未來的啟示,也是人類的最好的教師。胡錦濤總書記說:“歷史是一面映照現實的明鏡,也是一本最富有哲理的教科書。”[1]歷史科學具有教育、認知、借鑒、資政等社會功能,能為黨和政府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歷史依據,增強決策的科學性,減少行動的盲目性。檔案是最重要的史料,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原料。歷史工作者在寫作歷史論著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要依靠眾多反映以往歷史的史料為中介,研究歷史和認識歷史。現在研究歷史的同志很多,對歷史檔案的挖掘和應用也有了新的突破,但在歷史檔案的使用過程中,還存在很多不當之處,以下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高度注意。
一、使用歷史檔案要注意全面完整
檔案資料是歷史論著的血肉,是構成歷史論著的最主要構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善為文者必善積累資料。只有完整的占有歷史檔案資料,才能更好地發掘文獻中包含的事實、思想,才擁有學術發言權,這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歷史研究工作避免片面性、實現科學性的基礎和保證。司馬遷寫作《史記》,考證了大量的資料,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與取材廣泛、資料完整是分不開的。馬克思著述的《資本論》,白壽彝著述的《中國通史》,都是史料豐富完整的名作。
使用檔案史料的全面性、完整性要從多方面得到體現,既要注意縱向的全面性,也要重視橫向的全面性,還要注意史料類型的全面性。注意縱向的完整性,就是說使用的文獻檔案從頭到尾、來龍去脈都要清楚,要能首尾銜接。注意橫向的全面性,就是文獻檔案的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都要齊全,不能出現空白。使用文獻檔案類型的全面性,是指要善于使用各種類型的文獻檔案,印刷型、手寫型、視聽型、零次文獻、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原始文獻、傳抄文獻、撰述文獻,等等,均要使用,不能偏廢。運用各種文獻檔案,要如同網狀的結構,經緯分明,翔實全面,才能形成統一有序的整體。比如“文革”期間,曾經批判劉少奇1949年4月前后的“天津講話”鼓吹“剝削有功”、“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要建立資本主義社會”。“文革”結束后,黨中央對“天津講話”作了重新評價,而重新評價的基礎就是把“天津講話”的全部內容搞清楚,把劉少奇在17次不同場合的講話、插話的全部會議記錄稿都搜集整理出來,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得出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科學結論。[2]P150—151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一些歷史問題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重新評價。
二、使用歷史檔案要注意檔案材料的真實有效
歷史檔案貴在真實。要尊重歷史,從客觀歷史出發,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歷史檔案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客觀歷史形成什么文獻資料,客觀歷史存在什么文獻資料,就搜集使用什么。沒有形成的文獻資料,客觀上不存在的文獻資料,絕不能在搜集過程中編造,更不能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臆造。搜集使用歷史文獻檔案資料,要在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指導下,運用各種科學的方法和手段,采用各種令人信服的證據,辨別證明文獻檔案的真偽,并以此奠定歷史論述的研究基礎。
考證辨別歷史文獻檔案的真偽,要從5個方面努力:一是考證文獻檔案的版本。有些檔案史料有多個版本,每個版本記述都不盡相同,真偽難定,這就需要考證。署明版本的印刷型文獻檔案,通常比沒有署明版本的手寫型文獻檔案的真實性高一些;官方認定的版本,通常比民間流傳的版本真實性高一些。二是考證文獻檔案的作者。無名、偽托作者的文獻檔案,其真實性要低一些;署名的文獻檔案,真實性相對高一些;特定作者,比如事件的親歷者,真實性相對還可以高一些。但作者不是認定檔案真實性的標準,作者的立場,有時候也會影響真實性。如國民黨反動派曾于1932年2月中、下旬在上海各大報上連續登出偽造的所謂“伍豪啟事”,對周恩來進行誣陷。這種文獻檔案就不能亂使用。一些事件的親歷者,有時候因為保護自身的原因,也會隱瞞一些事實,這時候就要通過其他檔案資料來佐證。三是考證文獻檔案的形成時間。一般來說,形成越早的檔案資料可靠性越高,形成晚的資料往往都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加工,而傳播和加工的過程常常造成事實的訛誤。在戰爭時期我黨的一些歷史資料,日期不明,有的只有發表時間,沒有制作時間,甚至是假托時間,這就要花很多功夫來考證。四是考證文獻檔案的史實。這是難度很高和非常關鍵的部分。我們在收集使用文獻檔案的時候,一定要把來源、背景、形成與流轉情況搞清楚,這對于考證文獻檔案的真偽有很重要的作用。司馬遷著述《史記》,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這些做法值得我們肯定。但《史記》也有不少謬誤,比如關于秦王子嬰的身份,《秦始皇本紀》記載為“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3]P194,《六國年表》記載為“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3]P631,《李斯列傳》記載為“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繼位…”[3]P1993。一本書有 3 種說法,司馬遷自己也搞不清楚子嬰的身份,現在很多文學和影視作品將子嬰說成是秦始皇長子扶蘇的兒子,這都是在沒有考證歷史真偽的情況下亂下結論的錯誤做法。五是考證文獻檔案的文字。古代文獻經常使用通假字,這個問題應加以注意。文獻檔案的文字錯誤也是常見的,必須對文獻檔案的人名、地名、物名、書名等進行細致的校勘。另外由于古代和現代對詞語結構的運用有所不同,對引用的文獻檔案的詞語也要進行一定的校勘。
三、使用歷史檔案要注意各文獻檔案間的邏輯一致
研究歷史,必須對已經搜集到的文獻檔案資料進行挑選,也就是選材。使用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要注意各文獻檔案間的聯系性,用辯證的觀點來審視文獻檔案。事物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聯系,文獻檔案在一定條件下也互相聯系。在歷史論著寫作過程中,使用的各種文獻檔案一定要切題,要圍繞文章的觀點或主題來論述,千萬不能自相矛盾,甚至引用的資料之間互相沖突。我們知道,歷史檔案材料不外來源有二:文獻和口述。兩類材料,應以文獻為主,口述為輔;在使用口述材料時,最好和文獻互相印證。作者親身經歷的回憶材料固然可貴,但因事過境遷,或因記憶衰退,或因角度不同,往往多人回憶一事,互有出入。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來說,13名參加者,除早期犧牲的烈士外,差不多都有相關的回憶。但從這些材料來看,不僅不同人的回憶不相一致,就是一個人的不同時間的回憶也前后互有差異。我們在使用這些歷史檔案的時候,如果不注重這些當事人口述歷史的一致性,引用多人對同一件事情的回憶,就會出現互相矛盾和邏輯混亂。
總的說來,注意使用的文獻檔案間的邏輯一致,要把握以下環節。一是文獻史料在時間上要邏輯一致。同一個人所做的事前后銜接有序,不能出現時間上的倒置;同一件事必須發生于同一時間,不能前后提到同一件事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人、不同事件也要按照時間上的邏輯來安排資料,不能出現時間順序上的混亂。二是文獻史料在內容上要邏輯一致。選取用來佐證觀點的文獻史料要有思想和實體內容上的相容性,彼此之間可以無縫鏈接,看上去過渡自然,合乎一體。三是文獻史料在論點上要邏輯一致。文章寫得好,是因為主題明確,立意鮮明。如果前后使用的文獻史料觀點不一致,甚至發生沖突,讀者看起來覺得后面的觀點像是要推翻前面的觀點,那就是失敗之作。
四、使用歷史檔案不能在關鍵問題上斷章取義
歷史檔案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依據。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從這個社會生長出來的革命人物和發生的歷史事件,也必然有著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有些史實,我們不應回避,而是要去科學地說明。歷史學家楊天石認為,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真實地再現歷史本來面目,然后才有可能正確解釋和說明歷史。很多歷史工作者在寫作歷史論文的時候,專門挑選對自己的論點有利的史料或觀點,對自己要論述的觀點不利的內容則摒棄不用,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特別是引用一些權威著作的時候,斷章取義比使用不真實的檔案材料危害性還要嚴重。人民日報1978年3月12日轉載了《江西大學學報》登載黃少群的一篇文章《請不要在歷史文件上濫施刀斧》,對一些歷史研究者對史料進行“技術性處理”做了抨擊,作者在文中痛心疾首地說道:“文化大革命后,有的地方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在‘黨的創立時期’部分里,除了黨成立后的幾個文件外,只收了一篇毛澤東同志的《民眾的大聯合》,不但沒有陳獨秀的文章,連李大釗、蔡和森等黨的卓越創始人的文章也一篇不見。”“歷史是客觀存在,難道這樣一刪,李大釗同志就不是黨的創始人之一,黨的第一任總書記就不是陳獨秀嗎?這不僅是對歷史文件態度的極不嚴肅,而且是有意對黨的歷史戲弄和嘲諷。”[4]有的文集編者,在刪節了原文后,連刪節號都不保留。歷史問題是可以從歷史上說得清楚的。有些問題,不是什么錯誤觀點,只不過是客觀史實而已。例如,李大釗在1918年所寫的著名論文 《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中,在列寧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在以后的一些版本中,托洛茨基的名字就被刪除了。[4]又比如,2004年8月10日 《光明日報》登載 《列寧評價王安石的一個誤引》,對列寧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的說法提出質疑,指出這句話只是列寧在1906年所作 《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一文的一個注釋。列寧在論述自己的觀點時提出:“農民在其反對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對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爭中,通過自己的先進代表,必然要提出并且已經提出了廢除全部土地私有制的要求。”“農民中現在極其廣泛地流行著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這是絲毫不容置疑的。而且,盡管農民愚昧無知,盡管他們的愿望含有許多反動空想成分,但整個來說,這種思想帶有革命民主主義的性質,這也同樣是沒有疑問的。”在這兩段話之下,便是注釋②:“普列漢諾夫同志在 《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國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轍(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5]P226顯然,所謂“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只是普列漢諾夫提出“論據”的一個說明。這既不是列寧本人的觀點,甚至也不是普列漢諾夫對王安石的肯定性評價。一些歷史工作者將列寧的注釋作為列寧的評價加以引用,這種做法明顯是錯誤的。
總之,歷史研究是一項非常嚴謹的科學活動,不能有半點馬虎,更不能生搬硬造。歷史論文的寫作,既要繼承古典史學“四長(德、才、學、識)”,又要掌握和運用辯證法原理和唯物史觀,做到理論聯系實際,讓事實本身說話。只有在熟悉通史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運用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加強其內在邏輯性和聯系性,才能使文章有血有肉,有骨有魂,才能真正發揮歷史資政育人的作用,進而實現讓歷史告訴現在、讓歷史啟迪未來的目的。
[1]王恬、呂巖松、馬劍報道:胡錦濤在會見俄羅斯老戰士代表時強調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N].人民日報,2005—5—9.
[2]周一平編著:中共黨史文獻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
[4]黃少群:請不要在歷史文件上濫施刀斧[J].江西大學學報,1978(4).
[5]列寧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熊軼欣(1977—),男,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檔案館員、經濟師、碩士。研究方向:黨史黨建。
責任編輯 張榮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