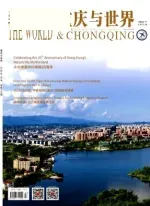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給中國生態城市建設的啟示
牟麗環,鐘家玉
(1.山東科技大學,山東青島 266590;2.榮昌縣人民法院,重慶榮昌 402460)
一、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概述
整體污染控制制度最重要的特點在于它用整體考察環境的方法取代了單一環境因素進行污染控制的方法[1]。
英國早期的環境污染控制立法僅是在污染問題凸顯時的一種被動回應,具有碎片化的特點。隨著環境問題的出現,一系列單行的立法也相應地隨之制定出來,相應的監管機構也就根據不同的規制對象而設立起來。因此,這樣做的結果是,根本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環境保護概念。環境污染控制立法就像是救火隊,哪里失火哪里去,沒有把環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沒有考慮對一種污染的控制可能會產生與之相關的另一種污染。比如嚴格污水排放標準,可能會促使行為人向其他環境介質中排放,比如燃燒或填埋(污染空氣或土地)。大量設立相應的環境管理機構,還導致了行政效率低下,職能重疊性沖突,缺乏管理的責任心和透明度。英國環境法是在經歷了上述立法和管理的覆轍之后,逐漸形成了環境整體污染控制的理念和方法,并通過立法付諸實施的。
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的核心規則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不至于產生過多成本的最佳可利用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Not Entailing Excessive Costs,BATNEEC)原則,用來預防或者減少規定的物質向媒介排放,以至讓那些規定的排放物或者沒有規定但可能引起環境損害的物質不產生危害;最佳可行環境選擇(BPEO)是當一個工序有可能包含一種以上的媒介排放污染物時,要進行考慮和衡量對環境整體產生最小的影響;清潔技術,主要包括在源頭減少、產品交換、過程改變、重新利用、現場回收和非現場回收。
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為評判一個整體工序對環境整體的影響提供了一種機制和法律基礎。該制度采用一種整體的方法確保那些不可避免要排放到環境中的物質,對環境的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該制度體現了預防好于治理的風險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也稱謹慎原則),遵循“預防—減量化—無害化”的污染防治理念;而且,它改變了傳統的分部門、分領域和集中于末端排放控制的缺陷。針對工業生產過程中向空氣、水和土地排放的廢水、廢氣和廢物進行一體化控制,也包括其他環境影響的管理;該制度鼓勵技術創新,平衡經濟成本和環境收益。
英國的整體污染控制制度在注重環境整體性、環境管理一體化及避免法律政策碎片化方面,值得學習和借鑒[2]。
整體污染控制制度綜合考慮包括污染排放在內的各種環境影響。該制度的設計思路除適用于環境的污染排放之外,還適用于更寬泛的研究空間,包括我國當下正努力實現的生態城市建設。
二、我國主要生態城市建設現狀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第一次給出“可持續發展”的定義以來,世界各國都在探索和堅持可持續的發展理念[3]。毋庸置疑,中國是世界上率先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國家之一,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全局性和指導性戰略納入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體系。中國通過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了生態城市的建設。
1993年,大連市率先開始生態城市建設。市委、市政府把城市生態環境建設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創造性地開展工作。1993年開始,大連先后對63個大氣污染項目進行限期整治,完成了80項廢水治理項目;1994年,大連對地處繁華區內耗能高、污染重、效益差的企業實施搬遷改造;1995年開始,大連市政府規劃了主城區綠化基本框架,建設了濱海路綠化帶第4條“綠化長龍”棒棰島等4個重點區域;“十五”時期,大連市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政府投入資金,實施了引英入連二期供水工程,全面搬遷改造污染企業,整合原有的工業格局,重新構筑城市框架與功能,優化配置土地資源,提高集中供熱率,推廣尾氣凈化技術,搬遷改造污染企業,削減工業污染物總量,控制污染源,凈化大氣環境;“十一五”時期,大連市著力抓好重點領域的節能,推廣應用節能、節水新技術與新產品,實施十大節能、節水示范工程,推進水源熱泵等節能項目,擴大污水處理再利用和雨水利用范圍,加快重污染企業搬遷改造及淘汰,嚴格控制新增污染物總量,加快建設各污水處理廠及配套工程,建設城市生活垃圾焚燒廠[4]。
天津市在建設生態城市方面也卓有成效。“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2010年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率先建成生態城區,2015年把天津建設成為生態城市。2009年,大港區率先通過國家生態區建設技術評估展開生態城市建設:一是大力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下降2.1%、4%、3.03%,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3.77%、4.03%、1.9%,連續三年超額完成年度削減任務。二是改善城市空氣環境質量。2008年,天津市環境空氣質量達到和好于二級良好水平的天數為322天,占全年的88%。三是進行水環境的治理。2009年底,市區10條河道和大沽排污河已經提前完工,已建成污水處理廠32座,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四是著重進行生態保護和建設。加強了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監督管理,組織開展了礦產資源開發整治、自查摸底和查處工作,完成整頓和規范礦產資源開發秩序活動的監察驗收工作。五是安全處置固體廢物。建設了一批以靜海子牙環保產業園為代表的規模化固體廢物回收利用產業,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98%以上。六是初步治理了農村環境。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已有11個鄉鎮和810個村建成環境優美鄉鎮和文明生態村。七是深入推進循環經濟。編制完成《天津市循環經濟試點實施方案(2008—2012年)》,并先后公布了兩批共39個循環經濟示范試點單位[5]。
上海市在建設生態城市方面的具體措施有:調整升級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率,資源、能源的單位GDP消耗下降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合理分布人口數量質量及結構,提高環保投入,重點區域的環境進行綜合整治[6]。
三、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給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啟示
眾所周知,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論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公眾,人們早已認識到,影響空氣、水、土地、植物、動物及其他自然資源等一系列似乎獨立的問題,實際上都是環境問題。我們研究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對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啟示,旨在形成一種新的思路:用整體的、統一的眼光和思維進行生態城市的建設。盡管我們知道生態城市的建設不僅包括環境的改善,還包括經濟發展的生態和社會文化的生態。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只是環境生態化中控制污染方面的做法,但是,這種制度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可以應用到很多方面的。
首先,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碎片化現象嚴重。通過對大連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生態城市建設措施的介紹,不難看出,我國現階段生態城市建設仍然停留在英國初期的環境立法階段。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個別化處理模式,沒有形成一種整體統一的思維。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帶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就是用整體和統一的方式處理環境和生態問題。碎片化現象存在的弊端是很明顯的,它對污染的處理并不是真正的根除,只是“移地”保護了而已,即把污染物從A地移到了B地。因此,我國在進行生態城市建設的過程中,應當從各個方面杜絕碎片化現象:制度的制定要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本出發點,要有連貫性和持續性;環境保護方面行政機構的設置要進行整合,防止出現重疊,防止各部門都可以尋找到合理的借口來減輕自己的責任。總而言之,在生態城市建設的各個方面,都要貫穿一種整體和統一的理念,克服碎片化帶來的弊端。
其次,我國生態城市建設主要靠政策性號召,而缺乏技術性支持。英國整體污染控制制度中的三項核心規則是不至于產生過多成本的最佳可利用技術原則、最佳可行環境選擇和清潔技術。這三項規則很好地平衡了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且,當有多種污染源時,也采用這三種規則將污染降到最低程度的原則。而這三種規則是靠先進的技術做支撐的,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環境污染降到最低只能是空談。我國生態城市建設技術性成果少之又少,只是從表面上減少某個地區的環境污染,殊不知,對整個環境的保護是沒有效率的。將生態城市建設放到政策層面,體現了政府對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視。但是,缺少技術投入和技術研究的建設,只能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不能從根本上改善環境狀況。我們所做的,是暫時的保護,沒有從整體和長遠的角度,技術性地進行科學的建設。因此,我國在生態城市建設中,應當更多地投入科學技術,經過全面的衡量,達到持久和全面的生態建設。
最后,我國生態城市建設應當堅持風險預防的原則,正確處理好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城市化之間的關系。生態城市是“城市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居民滿意、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這個生態城市定義已經成為國內外生態城市理論界的共識[7]。英國在城市化早期,經歷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在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時候開始進行改革。英國的整體污染控制制度正是體現了預防優先的原則,謹慎地對待城市化過程中的環境問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現在正是發展經濟的關鍵時期。但是,中國既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體現了中國不會重蹈英國工業化初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因此,我國在建設生態城市的過程中一定要正確處理好城市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
[1]楊欽.英國的綜合環境污染控制制度[N].中國環境報,2001-05-26(3).
[2]孫法柏.英國環境保護行政機制:法律政策整合及管理一體化[C]//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法分會2011年年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1:47-51.
[3]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10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綠色發展與創新[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22.
[4]戴學章,姜卉.大連生態城市建設的回顧與思考[J].大連干部學刊,2009(7):11.
[5]謝華生,李紅柳,孫貽超,等.天津生態城市建設實施現狀及對策研究[J].天津經濟,2011(1):35.
[6]李秀娟.上海生態城市建設綜合評價及比較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07.
[7]李迎君.我國生態城市建設問題研究[J].改革與開放,2009(1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