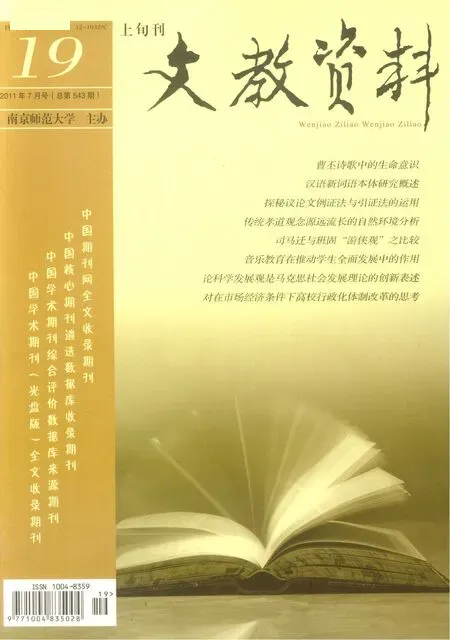《道連·格雷的畫像》與《驢皮記》的互文性初探
殷勤勤
(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道連·格雷的畫像》是十九世紀末唯美主義大師王爾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全書圍繞主人公神秘的畫像展開,描寫了一位純真美少年被罪惡引誘,一步步墮落乃至毀滅的傳奇故事。而這樣的寫作框架似乎和十九世紀法國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之一的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的一部長篇小說《驢皮記》中的整體布局有著某種程度上的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是對于西方古老的民間故事 《浮士德》的相關內容進行的改編,《浮士德》最初是關于一個德國巫師或星相家與魔鬼打賭,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以換取知識和權力的故事,這是關于浮士德故事的最初情節與框架。王爾德將其改寫成唯美主義的小說代表作《道連·格雷的畫像》,而巴爾扎克則在他的現實主義代表作《人間喜劇》的哲學研究篇中轉化為長篇小說《驢皮記》。
下面是兩部作品的整體框架列表:

可以說,這兩個文本是在同一世紀之中對于浮士德原篇的文本的遷移與重構,即對于同一題材、主題進行不同階段、歷史的闡發,通過一紙契約將主人公、誘導者和寶物三者相連,反映了一種時代歷史的需要與當時文化心態的轉變。
從上面的簡單列表中可以看出,這是兩部出現在同一個世紀之中的作品,出版相差了60年。回顧十九世紀初和十九世紀末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巴爾扎克在寫《驢皮記》的時候是處于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和發展的時期,當時的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這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形態巨變的時期,人的道德觀念和文化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時代的變遷所帶來在文學上的影響是對于現實的揭露與解剖。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其歐洲各國社會矛盾加劇,人心浮動,歐洲處于大變動的前夜,這是一個“世紀末”的騷動時期。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之中,作家都產生了一種幻滅感和危機感,萌發了一種苦悶、彷徨、悲觀、頹廢的心理,表現出藝術自衛的不安情緒。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的確立初期,還是處于“世紀末”的矛盾加劇時期,兩位作家都在反映這樣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在資本主義階段所不可避免的靈與肉的矛盾與沖突。區別于以往神話世界里的魔鬼,兩部作品都將其引入現實世界的殘酷之中,它是活生生的、存在的。兩位主人公都是矛盾沖突中的犧牲品,都是“墮落的浮士德”。浮士德的追求原本是被賦予了一種凈化、贖罪、得救的積極意義,而在本文所探討的兩部作品中,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被腐化、墮落和毀滅的形象。對于這樣一種完全相反的寓意轉變,所表現出來的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驢皮記》所描繪的是一個“被墮落的浮士德”,這樣所探討的重心就落到了“被墮落”之上,這是一個有因有果的陰謀與圈套。圍繞著作品的主人公,作者都選擇了一個類似于金三角的組合,即善良的主人公、不懷好意的誘導者、神秘的寶物。對于《驢皮記》中的主人公拉法埃爾來說,引領其道德墮落的初始即與拉斯蒂涅和福多拉的相識,自此,他沉湎于難以置信的放縱之中。而最終完成其墮落的關鍵在于那張神秘的驢皮,它能夠幫助拉法埃爾滿足他所有的一切欲望。然而,所有的欲望最終都會落空,因為以生命為代價的結果最終只能是毀滅。巴爾扎克在此所展現的是一種寄生關系,個人寄生在巨大財富之上,必然會對自己的生存加以限制,這是一個被迫選擇與放棄的過程。在此,作者所要揭露的是作為當時統治形式的資本主義本身,有著明顯的政治傾向性。而在《道連·格雷的畫像》中則是一個在“墮落中掙扎的浮士德”。同樣的處于金三角的構架之中,所不同的是在這里,王爾德所要凸顯的是主人公本身在不斷地選擇之中的掙扎、沖突與痛苦。為了留住青春的美麗,道連選擇了與魔鬼進行了靈與肉的交易,并且在亨利勛爵的蠱惑之下發展到把惡當作實現所謂美感享受的一種方式,殘忍地殺害了美的創造者畫家霍爾沃德。王爾德用藝術的手法把體現道連道德中惡的方面轉移到畫像之中,通過道連于掙扎之中結束其真實罪惡的肉體還原了原本美麗的畫像,從而達到了靈與肉之間的和諧統一。可以說,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圓夢式的結局,在藝術的象牙塔里與丑惡現實相抗衡,并持續掙扎與斗爭著。
同一個世紀,兩個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都選擇了同樣一個原型進行不同程度和寓意上的改編,同樣在這樣一個浮士德的難題上打轉,對于這一點而言,套入上文所說的互文性理論雙重焦點的第一個方面,說明前文本本身的重要性問題,即這是一個經得起歲月洗刷的原型經典,有著人類生存之中所共通的東西,你和現代之間都有著能夠引起共鳴的東西存在。“浮士德難題”所反映出來的是人性中共通的誘惑與被誘惑。總有能夠誘惑你的東西,也有著被誘惑的時候,不可避免。在早期浮士德形象的塑造上,就充分體現了這樣一個矛盾的統一。人類是一個靈與肉的結合體,在尋求精神的飛升的同時又受到了物質世界的牽引,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欲望的糾纏。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在現代社會之中,生活似乎變成了競技場,我們都在追逐著這樣一種認同,即“他人的承認,社會的承認”,這樣所帶來的只是一種必然的后果,導致個體自由的喪失和美好人性的迷失。誘惑與被誘惑的范圍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類不僅受著物質世界的吸引,而且人類本身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說,無論是原先的浮士德形象,還是十九世紀之中出現的“墮落的浮士德”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現實中的人性。與此同時,他們也給我們指出了一條精神之路,在問題與困境之中走向平衡。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在發現問題的同時,也隱藏著希望的狀況。無論是在小說之中的主人公本身最終體會到,還是在悲劇的結局之中讓讀者來深刻體會,其本質上是一致的,在人生悲劇的失敗之中悟出更高生命存在的意義,在欲望之中升華,其最終還是在肯定人的主觀改造能力。巴爾扎克與王爾德希望在墮落的形象之中提醒著現世的人們不斷改變不合適的生存環境,用實踐來證明更加美好的未來。
對于文章開篇所說的互文性中第二個焦點所指的問題,涉及文本與整個文化話語空間兩者之間的關系,即文本并不是單一的個體或群體,而是需要融合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去理解和探究的,這里所要強調的是文本所能共同表達出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的共同文化。可以說,《道》與《驢》兩部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共同傳達著資本主義時期的問題與矛盾。如果說巴爾扎克是一個在大量事實面前的一個外部揭露者,那么對于王爾德而言,則是一種身處于其中的資產階級內部的文化與精神危機的爆發。一個是客觀揭露事實的開端期,另一個則是經歷了一定的過渡與沉淀之后的反叛期。面對同樣欲望與道德的兩難處境,巴爾扎克選擇了赤裸裸地揭露,其實質是在鼓勵反抗;而王爾德所處的唯美主義實際上則是在逃避現實,躲進象牙塔之中。在兩者之間思想的變化流動之中所透露出來的是對于現實的一種無能為力。在過了大半個世紀的歲月之后,原本的激情與雄心早已沉淀,因為越真實地揭露出現實的丑惡,越感到無能為力,所以在唯美主義之中只能是表現出一種孤芳自賞的圍困與矛盾。無論怎么將藝術與現實和道德撇清關系,其結果都是撇不清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兩部作品其實質上都是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各種丑惡,但不難發現在十九世紀末的那種反抗與初期相比,在文本表達上要稍許軟弱很多。在《道連·格雷的畫像》的自序中,王爾德強調這是一部與道德無關的作品,他這樣說是一種消極對抗資產階級虛偽道德的一種自我保護手段。選擇回避藝術中的道德,更多的是因為擔心那些假仁假義的人們認為他的小說不符合當時資產階級的社會道德,從而指責他本人的不道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可以說這是一種妥協和退讓的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在事實上表明了資本主義仍處于相對強大的地位,遠遠超越于巴爾扎克時期,所以這一切的反抗只能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不能完結。但不可否認,在十九世紀這一整個世紀之中,資本主義所不斷暴露出來的問題與矛盾一直在困擾著作家們的內心,他們一直處于不斷地思考與探索之中,將傳統文化之中的某些內容重新提取出來并進行改編,用以闡釋、制約或針砭當代文化中的某些基本問題,這是引證往昔向今日發言。事實上,不僅僅是資本主義階段的問題,在人類生存過程之中,永恒地存在著類似于浮士德難題這樣的問題。貝爾將這些問題稱之為“原始問題”。他指出:“這些問題困擾著所有時代、所有地區和所有的人。提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人類處境的有限性,以及人不斷要達到彼岸的理想所產生的張力。……答案盡管千差萬別,但問題卻總是相同的。”[1]許多作家們從當代人文環境之中不斷地重復發現并敘述著這樣我們一直所處的困境,在這過程之中不斷塑造經典,重復著經典,并一直流傳下去,在經典的重構中重新鞏固其經典的地位。這樣,就將一個特定時期的共同文化傳達的空間擴大到一個更大的文化話語空間之中,這就是經典與經典作家所作出的貢獻所在。事實上,任何一個文本不可能完全獨創,但也不會是完全互文,沒有一點獨創性。作為經歷歷史沉淀保留下來的“一個文化所擁有的我們可以從中進行選擇的全部精神寶藏”,[2]總有它的獨特之處。在互文性視角之下來審視文學經典,可以說,經典是互文性的產物。互文性是一個開放和不斷變動的系統,不同的互文性系統會生成不同的文學經典。作者的寫作是互文性的,他以前讀過的文學文本勢必會對他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影響最深的莫過于文學經典。當經典形成記憶,在作者的互文性寫作和讀者的互文性閱讀之中,從而不斷塑造并加深經典,拓展經典的尺度和功能。
[1]南帆.沖突的文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12:122.
[2][荷]佛克馬,蟻布斯著.俞國強譯.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