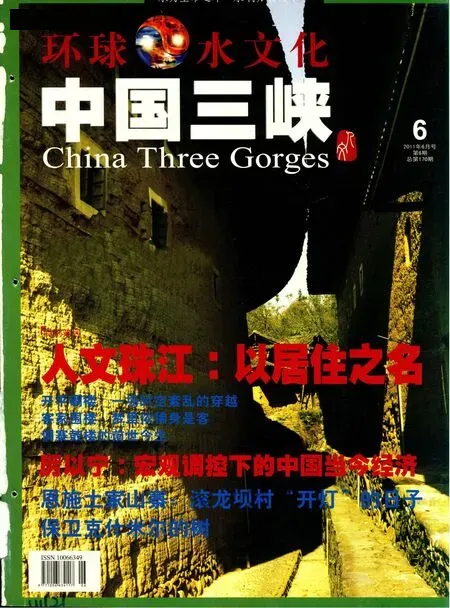西沱:云梯上的古鎮
文/孫榮剛 編輯/任 紅
我不止一次到過西沱古鎮。未到西沱之前,我曾經被徐悲鴻的名作油畫《西沱風景》所深深震撼。我想,坐落在長江南岸的西沱古鎮,肯定還有一條蜿蜒曲折的溪流環鎮而過。
《詩經·江有汜》說:“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說文》解∶沱,“江流別也。”《辭源》∶沱,“江水支流的通名。”但到了西沱古鎮一看,原是長江奔流到此,猛然折了一個Γ形的彎,據說,就因為這個彎內天然的回水沱,才有了現在西沱的名稱。
我在朋友那里翻了翻《石柱縣志》:“西沱,古名江家沱,又名石鼓峽,秦漢為施州西境,與臨江分界于江家沱,為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名‘西沱’。”
古鎮沿江彎而建,隨山勢而高,灰瓦白墻,點綴在一片古銅色的板壁背景下。環鎮是山,山后還是山,層巒疊嶂,一色翠碧,與天相接。
我最愛欣賞的還是云梯街,踏著青石板街拾級而上,一種激越就油然而生。顧名思義,云者,高也,梯者,級也。從江邊的石級往上數,一共是1124級,直達山頂。云梯街就像是一條從一座山頂掛下來的彩帶,串聯起古鎮的風景和故事。
三峽水庫未蓄水時,石級要斜斜地、陡陡地延伸到深深的峽江底。從下往上望,岸邊的人似乎渺小了很多。而今,三峽水庫蓄水到175米高程,坡畔的石級所剩不多了,在整塊的山石上開鑿出來的石級,不多幾步就到岸上。
于是,青石板街就曲曲折折地閃現在眼前。
問古鎮的老人:“這青石板是什么時候鋪上去的?”老人們會搖搖頭說:“我們也說不準。從我們小時就是這個樣子了!”有的青石板光滑滑的,照得出人影;有的青石板變了形,凹凸不平,那無疑是千百年來的腳板造成的,歲月的滄桑在那上面磨出悠遠的痕跡。
越往上走,地勢越高,一個平臺,就是一個高度。有的街面狹窄,因兩旁房屋的聳立,而顯得格外幽深,腳步踏下去,就會響起一種古老的回音;有的寬敞,豁然開朗,人又似乎回到了現在。回望來路,青石板街歷歷在目。還有眾多的小巷,曲曲折折的,寧靜安祥。
沿街是古色古香的木板樓,最高的不過兩層,底層板壁古舊,樓上小窗玲瓏剔透,隱隱透出唐詩宋詞的風韻。還有吊腳樓,偶或出現在哪個角落;還有張飛廟和關帝廟,倚山枕崖,幽靜在古鎮的一邊。老人們有的在街上閑走,有的或站或坐,三三兩兩,不緊不慢地講幾句《三國》,聊幾句閑話。女人們倚門而立,有的繡花,有的織衣,有的張羅著別的什么。一種“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的陶淵明境界,濃濃地包裹著古鎮。
但古鎮也有喧囂的時候。就在下街,你會看到一個敞房幾根柱子支撐起一個空落落的瓦頂,后面還有空大的院落。這里曾經是一座古鹽廠,是“下鹽店”遺址。

徐悲鴻的西沱風景,因古鎮而身價百倍,名聲鵲起。
下鹽店是清初西沱舉人楊氏所建,面積達一萬三千多平方米。木質結構的青瓦房,從布局到建筑,既巧妙,又精致,與云梯街的“上鹽店”風格迥然不同。
“上鹽店”是官鹽,“下鹽店”是私鹽。而本文所說的巴鹽古道就是從“下鹽店”開始的。自古以來,蜀地就盛產井鹽,每一朝代,都會有私鹽興盛的時候。相對官鹽而言,私鹽的形式要活躍得多,政府禁止不住,就開放一段時期。這座古鹽廠就是私鹽發達的一個見證。
院中,至今還有一口古井,而且嘗一嘗,咸味頗濃。這不禁會猛地勾動起人的遐思:當下鹽店興盛的時候,白花花的食鹽堆積滿屋,忙碌的人們,在汗味與熱氣中穿梭。而那些挑子二(挑夫)、背子客,或馭馬,在一片“嗨喲”聲中,將一袋袋食鹽從云梯街搬運出,借助江水,散往峽江兩岸,散往川江上下。
據說,這里一度商賈云集,市肆昌盛。史載: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川鹽銷楚,西沱成了鹽運的通道起點,貨物山積,碼頭繁忙;元代,川江水路在此設“梅沱小水站”,作為連接川鄂交通的水驛,是重慶出川的必經驛站。
清朝乾隆年間,西沱設有專門的朝廷巡檢司,總監川鄂兩省鹽務。不僅川鹽,還有百貨、絲綢、蜀繡等天府特產,都是經西沱上游的成都、重慶、涪陵等地運到西沱,再從西沱轉運到湖北恩施、利川、來鳳一帶。
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這條古鹽道又突然沉寂了,沉寂得如此過分。唯有古鎮上遺留下來的江西和福建會館,還在敘說著昔日的繁華。
我喜歡尋尋覓覓,總想著找出古鎮的另外一些秘密。果然,在云梯街的右側,一座別具一格的古建筑吸引住了我。這是兩樓一底的古居,門廊開闊,兩側風火墻高聳。走進去,是外間,再往內,是天井,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小院。有一塊石碑的碑文告訴我,這家已故的主人名叫熊福田,是一個中醫世家,曾是同盟會成員,秘密參加過辛亥革命。這座房子就是他臨近晚年,在奔走奮斗呼號一生之后,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家興建的懸壺濟世的所在。他的次子熊丸就曾經但任過蔣介石的專屬侍從醫官。熊家的后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熊雍盛,一見我,就指著墻壁上懸掛著的父親熊福田的照片,滔滔不絕地敘說起祖輩的一個個感人的故事,自豪感溢于言表。
還有一個地方,更值得一看。門前也立著一塊石碑,但沒有碑文,只鐫刻著:和成字號。看看四周,只有殘碑斷坦,荒草萋萋,和成字號的房子早已不知去向。石碑孤零零的,被鄰房的墻壁所擠壓。但就這個地方,曾是革命的前沿陣地。
那是1940年的冬天。在外人看來,這里不過是個普普通通商號,有柜臺,有貨物,有店員,人來人往,一如其他商號。但其實,這個商號就是峽江共產黨建立起來的地下交通站,當年中共地下黨和川東游擊隊,就經常出沒在這里。

熊福田最小的兒子熊雍盛敘說家史。 攝影/孫榮剛
在九年的時間里,和成字號就像一顆紅色的種子,一邊深深地扎進古鎮,一邊秘密地為革命籌集經費,日日演繹的是一部《紅巖》的一串又一串情節,直到“東方紅,太陽升”。

西沱古鎮,悠遠而樸素的韻律。 攝影/孫榮剛
云梯街快走盡了。一步一步爬上來,細數一下,有112個平臺。石級有的是用大青石塊鋪砌,年久磨損缺失,下腳得格外小心。到了山頂了,回頭一望,啊呀,好高好陡!我正站在離江邊起點1.9公里,海拔193米的高度。但見古鎮瓦脊鱗次櫛比,飛檐和風火墻偶或嶄露,錯落有致,一派明清的格調。
當地人告訴我,你要再來古鎮,最好是春節。外出打工的人回家了,滿街都是流行色。小伙子西裝革履,或迷彩配身,姑娘們發型時髦,短裙套靴,在古鎮調和出現代的潮流。鞭炮和鑼鼓聲時時響起,將古鎮的氣氛醞釀得更加活躍。有時,還會來一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的情調。
似乎是在忽然之間,滿街都是人,穿紅著綠的男女老少,挨挨擠擠。這里,小小的龍船劃出來了,一條龍燈舞起來了;那里,有人濃妝艷抹,土家裝束,一堆一堆跳起擺手舞、銅鈴舞。還有那邊,幾個山民古裝打扮,唱響了薅草鑼鼓和薅秧歌,還有川江號子,聲震峽江,響遏行云。而歌詞是新編的,冷不丁會嘣出“三峽大壩”、“北京奧運”,還有“奧巴馬”。
但我來的不是時候,看不到這種豐富的民俗場景,只是在心里向往。山風飄飄而來。再看云梯,迤邐而上,直到我的腳下。我驀然覺得,古鎮的人們日日行走的就是一架真正的云梯,一級一級,天天在上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產生一次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