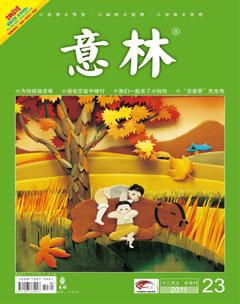我沒有撞人
嚴文華
“老師,我身體不舒服,不能來了。抱歉沒早點給你打電話。”學生筱歆約好了來找我談作業,卻遲遲不見蹤影。
但幾個小時后,筱歆出現在我的辦公室,她說:“老師,我想想還是來找你說一說,否則我真的是太難過了,心里很憋屈,我都快透不過氣來了。”
“發生了什么事?”
“我目睹了一起車禍。”“不,不,其實沒有車禍,只是可能的車禍。”筱歆又搖頭否定自己。
“能具體說一下嗎?”
“我今天騎車從外面回來,經過一個路口,很遠就看到一個老人斜側著身子、跛著腳過馬路。遠處來了一輛車,看到老人,車速慢了下來,但老人很慌,他開始跑,跑了幾步摔倒了……”筱歆的聲調低下來。接著,她又說:“我當時想停好自行車,去馬路中間把老人家的一只鞋子撿回來。正在猶豫時,我旁邊一個抱孩子的人對我說:‘你快走。”
“她讓你快走。為什么呢?”我沒反應過來。
“那個老人摔在我的面前,離我的自行車前輪很近。我說:‘不是我撞的!她說:‘我知道,所以我讓你快走。”
“你的反應?”
“我騎上車就走了,但我心里一直在說:‘我沒有撞人!”她的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可是我又問自己,沒有撞人為什么要逃走?我一路神情恍惚。”
“回到宿舍,我全身發抖、腳發軟。我想到了彭宇案,不就是因為好心扶了人就要賠那么多錢嗎?我可賠不出來。我也不敢出門,我覺得一下樓就會有人來抓我,說我撞了老人就逃逸了。”
“我有點惡心,想吐,但吐不出東西。還有點肚子疼。后來‘大姨媽來了……其實根本沒有到時間。”我驚訝了。這么強烈的生理反應,我有必要跟她再次確認:“你并沒有撞人是嗎?”
“我沒有。”她語氣堅定。
我們花了些時間討論——如果她留在現場最糟糕的結果是什么。她扶起老人,被老人誣為她撞了人。她想找目擊證人,迎面走來的人和抱孩子的那個人都看得清楚,但他們不愿卷入麻煩,都推說沒看見;這個街口本有交通錄像,偏偏那天壞了;現場交警也出警了,但交警根本沒有細細勘察老人身上是否有自行車的印記,只出具了“既不能排除騎車人沒有碰觸老人、也不能證明騎車人撞了老人”的證明材料,最后法院判她賠償10萬元。
“10萬元對我是個天文數字,我一個月勤工儉學不過1000元,畢業后也不過每個月3000元,我這一輩子不就完了嗎?”
我們又接著討論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證明自己,她這一輩子是否真的毀了。慢慢地,當恐懼的情緒表達出來后,理性和智慧慢慢回來。她提到可以通過主動報警、拍現場照片、發微博等方式證明自己,用到高薪企業就業、開網店或自主創業等形式掙錢還債,她甚至調侃:“說不定通過打官司,我會轉到法律方向去讀研究生,畢業論文就是《我沒有撞人的個案分析》。”
“所以,如果真的被賴上了,未必全是件壞事,你從此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勤奮的、能掙錢的人。”
筱歆輕松地離開了辦公室。看著她的背影,我在心里嘆息:筱歆沒有撞人,卻比撞了人還擔驚受怕。不是她hold不住了,而是整個社會hold不住了,因為人們連安心走路、安心開車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脅,讓一個大學生有如此巨大和強烈的情緒反應。
(康康摘自《大學生》2011年11月圖/志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