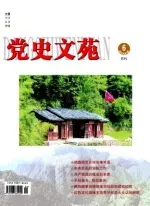戰友李白
■周 維
長征時,我在紅五軍團無線電分隊當隊長,我們隊的政委是李白同志。
電臺,是全軍團的耳目,是與總部聯絡的主要通信工具。沒有它,部隊的千軍萬馬就成了瞎子聾子,因此,那時我們都抱定一個信念: “電臺重于生命!”李白同志更是時常以此來鼓勵大家任勞任怨,克服困難,完成好通信聯絡任務。每次行軍,不論是高山大河,還是雪山草地,我在前面領隊,他則跑前跑后地照顧隊伍。有時他組織大家把發報機搬上懸崖,有時他和戰士們一起抬著發電機,邊走邊哼著湖南小調。長征路上,只要聽到他那快樂的湖南小調,我就知道電臺設備準沒問題。
到廣西的一天,部隊在山邊的村子里休息,我躺了一會兒,剛端起一碗苦菜湯,突然村子上空響起了“嗖、嗖、嗖”的槍聲。我出門一看,敵人正在山上用機槍向我們掃射。這時李白同志一身油污跑過來,一把抓住我: “隊長,你帶部隊趕快出村,我掩護你們!”
我當然不肯,讓他帶領部隊出村,可一把沒抓住他,他就飛一般地往山腳奔去,掏出手槍率領監護排向敵人開火。
電臺安全轉移到指定地點后,我焦急地等著李白。過了一陣,他們安全回來了,我一顆懸著的心終于放下來了,趕緊跑上去拉住他的手。他劈頭就問我: “怎么樣?電臺沒問題吧?”聽到我肯定的答復后,他樂呵呵地把袖子一卷,又跑去修發電機了。
在長征途中,任何艱難困苦我們都能忍受,可是電臺卻不像人,只要缺少或損壞了一個小零件它就不能正常工作。我們帶的備用器材很少,有些零件根本就沒有,這一路又大都渺無人煙,即使有個村子,也不可能找到電臺所需要的器材。為此,李白想盡了辦法。
過草地時,我們攜帶的汽油已經用光了。眼看電臺不能工作,李白同志就和我們大家一起商量辦法。一個電機工人出身的戰士告訴我們,酒精可以代替汽油。但酒精又從哪里來呢?又一個戰士說,他聽說酒精是用酒做的。于是李白同志到處去想辦法,終于找到了汽油代用品——白酒,使發電機開動了。不久,干電池又沒電了,他又找幾個內行的同志一起研究、試驗,在干電池上釘幾個眼,泡在鹽水里,這樣又可以使用一小時左右,后來找不到鹽,就用尿液來代替。有一次,發報機上有一只真空管失效了,剛巧有一封緊急電報亟待發出,幾個報務員急得團團轉,又是李白同志靈機一動,將收報機上的一只管子拔下,插在發報機上,使緊急電報得以及時發出。打那以后,這只管子兩邊合用,維持了很長時間。

李白烈士
就是這樣,長征途中一年多,困難一個個地被我們克服了,電臺工作從來沒耽誤過。
李白同志不僅愛護電臺,而且非常關心同志。長征途中的艱難困苦,是難以形容的,紅五軍團擔任全軍后衛掩護,走在全軍的最后邊,生活更苦一些,困難更多一些。在長征路上,就是行軍走路也不容易,而我們還要帶著電臺行軍,困難可想而知。有時前面一堵,走走停停,我們就邁不開大步;可有時卻為了趕上前面的總部,一口氣要小跑幾十里,如果摔了跤,拍拍土的工夫,隊伍就跑出里把地了。我們分隊帶的這部電臺,除了收發報機外,還有發電機、內燃機、汽油、蓄電瓶等,全隊100多人,就有七八十人抬機器。到了宿營地,別的部隊可以抓緊時間休息,我們卻要架線,整理機器,開始工作,有時電報還沒發完,部隊又準備行動,許多同志連眼皮都沒來得及合一合,又要抬起機器行軍了。李白同志為了減輕同志們的負擔,行軍時,他換下疲勞的戰士,自己參加抬機器;工作時,他和報務員一樣,輪流參加值班。戰士的鞋破了,他把自己的給戰士穿;戰士餓了,他把自己干糧袋里的炒青稞倒給戰士吃。過草地時,一把糧食就是一條生命啊!他常對別人說: “同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咯!”可他自己呢?饑餓、疲勞使他的圓臉瘦成尖下巴,還有兩圈深深凹下去的眼窩、布滿血絲的眼球……這些都是他徹夜不眠地工作的結果。同志們常勸他注意休息,有的戰士就用他說的話對他說: “政委,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咯!”他總是笑笑說: “我沒關系!”
部隊剛過彝族地區,就鉆進了深山老林。那一片原始森林大約有幾千年了,濃密的樹葉透不過一絲陽光,林子里陰森森、冷嗖嗖的,一層輕輕的霧從地面升起,霧里一股又濃又臭的潮濕、霉爛氣味,熏得我們頭昏腦脹。我那些天本來就有些不太舒服,被這瘴氣一逼,濁味一熏,只覺得渾身發麻,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把被單緊緊地裹住身子,咬著牙一步一步往上爬。雖然林子里冷得像冬天,我一身虛汗卻將衣服都濕透了。
部隊在半山宿營。走了一天崎嶇的山路,大家非常疲憊,一躺下就睡著了。我沒躺一會兒,感到燥熱得難受,支起身一看,機器旁邊點著一盞燈,李白同志坐在那里,用手支著頭。怎么又是他值班呢?我記得昨天夜里他剛值過班,準是他又讓報務員休息去了。想到這里,我翻身爬起來想去換換他,剛站起來,猛然覺得頭重腳輕,兩眼發黑,一下子栽倒在地。李白同志聽見響聲,跑過來扶我坐起: “怎么搞的,隊長?”
“沒啥,我換你值班,你休息一下吧!”我的聲音微弱得幾乎連我自己都聽不清楚。
他摸摸我滾燙的額頭說: “燒成這樣子,怎么不吭氣呢?”他倒了一杯開水給我。喝了水,我心里舒坦多了,掙扎著要起來。他按住我說: “同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咯!”說著,就把披在身上的毯子給我蓋上。他見我還想說什么,就指指周圍打著鼾聲熟睡的戰士們,把手指往嘴上一放, “噓”了一聲,便輕手輕腳地回到機器旁邊去了。

李白烈士紀念碑
天剛蒙蒙亮,部隊就出發了。今天要通過一個重要隘口,敵人正日夜兼程地往這里追。因此,我們必須搶先通過。
我發了一夜高燒,身子更虛了,勉強喝下半碗野菜糊糊,拄根樹棍就隨著隊伍出發了。李白同志讓指導員帶隊,自己卻又過來攙扶我上路了。沒走多遠,我突然篩糠似的渾身發抖,上牙直嗑下牙,手腳抽搐,不斷嘔吐。我心里清楚自己得了惡性瘧疾。
這時,前面一個勁往后傳口令: “跟上!跟上!”部隊不是在走而是在跑,我幾乎全身都壓在李白同志的身上,但還是跟不上隊,一個個戰士喘著粗氣流著大汗從身邊跑過去。“不能掉隊呀!不能掉隊!”我暗暗對自己說著。在這幾十里深山野林里,除了兇殘的敵人外,還暗藏著許多吃人的野獸。假設掉了隊,不被敵人捉住,也會被野獸吃掉。決不能掉隊!我狠勁擰自己的腿,想讓疼痛鎮住寒冷的感覺,并死死咬緊牙關不讓它們打架。
從身旁超過的戰士越來越多,我的力氣也越來越小,一次接一次的嘔吐,簡直把五臟六腑都要倒出來了。
我不能拖累老李呀!我的手從李白同志身上滑下來,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李,我……不……不行啦,你先……先走吧!”牙齒直打顫,費了好大勁,我才對他說完了這一句話。
“那怎么行!”他見我實在無法支持,就扶我躺下, “你等一等!”說完就跑開了。

作者周維將軍
我躺在地上,緩了口氣,聽見嚓嚓的腳步聲從身邊過去,我非常著急,掙扎著想爬起來,卻一次次都摔倒了。這時,許多戰士圍過來要爭著背我走。但我知道這根本不可能,幾百斤重的機器已經壓彎了他們的腰,磨破了他們的肩,在這樣一步一滑的高山峻嶺上,再背一個重病的人,怎么上得去呢?再說電臺比人重要啊,我決不能拖累他們。
正當我和幾個戰士爭辯時,李白同志老遠就喊著跑過來: “有辦法咯!有辦法咯!”只見他扛著一副擔架,是用兩根竹桿綁了幾根繩子做成的,他后面還跟著一個戰士。他把毯子往擔架上一鋪: “來,躺在上面!”原來,剛才他為我弄擔架去了。
“不行,老李!”我咬緊牙關掙脫了他的手,坐著不動, “我100多……多斤,這咋……行……行呢?你去照顧……電……電臺吧!”
“電臺重要,人同樣重要!”他叫兩個戰士把我抬到擔架上,他和另一個戰士抬起擔架就走。邊走邊說: “100多斤怕什么,幾百斤的機器不是照樣上山么。”
“老李……老李!”我不敢亂動,怕增加他們的負擔,只是有氣無力地叫著: “這樣……不……不行呀!”
“老周,好生躺著,擺子打過了就好了。”他們邁著大步走著,抬機器的戰士落在我們后面了。
昏昏沉沉不知過了多久,當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床上,軍團部的醫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邊,見我睜開眼睛,兩人一起急切地問我: “老周,好些了吧?”
我點了點頭,嘴里苦澀得十分難受。
“這30多里地跑得真快呀!李政委身體真棒,他沒讓別人換過一肩!”醫生告訴我。
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著他微笑的臉,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李白同志輕輕地替我揩掉不知是什么時候涌出來的淚珠。
長征勝利結束,我們來到了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后,李白同志奉黨的命令赴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卻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從此,我失去了一位可親可敬的好戰友。
責任編輯 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