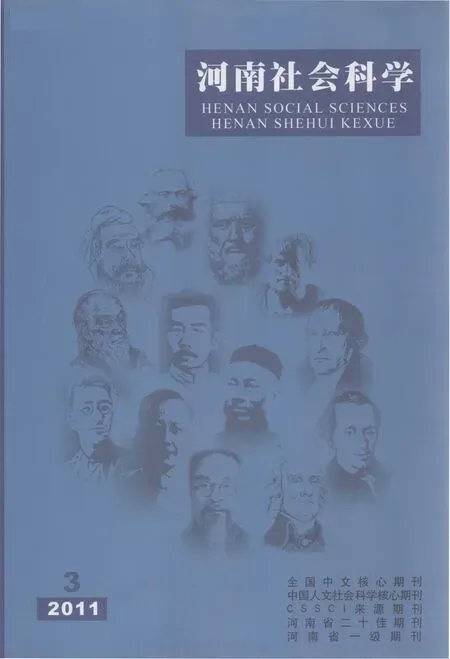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胥吏“群丑圖”
王保健
(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 鄭州 450002)
《聊齋志異》中的胥吏“群丑圖”
王保健
(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 鄭州 450002)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塑造了大量狐仙鬼怪等幻想中的形象,也塑造了現實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胥吏形象。這些胥吏貪贓枉法、欺上瞞下、魚肉百姓、挾持主官,其性格主要表現為貪、酷、猾等特征。蒲松齡塑造的胥吏形象反映了晚清胥吏腐敗的現實,是作者長期在實際生活中觀察的結果。蒲松齡關于胥吏的問題觸及了封建管理體制中的痼疾。
蒲松齡;胥吏;吏治;腐敗
一
所謂胥吏,是對在封建管理體制下服務于各級政府部門的辦事人員比較寬泛的稱呼,主要包括縣典吏、驛承、河泊所大使,府州縣的醫學、陰陽學、僧道官員以及各衙署的皂隸、馬快、步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仵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等。他們主要經辦各類文書、處理技術性工作以及從事各種雜務等。這類人社會地位不高,甚至為人鄙視。但他們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職能,掌管大量實際事務,是整個政府機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胥吏與普通百姓直接打交道,對百姓生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是支撐著整個封建官僚機器運行不可缺少的角色。
清代胥吏有其獨特性。晚清政治家郭嵩燾就曾說過:“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1]胥吏的作用由此可略見一斑。晚清政府全面腐敗,吏治腐敗尤為突出,胥吏腐敗也是普遍現象。《聊齋志異》中的胥吏形象就反映了晚清胥吏腐敗的社會現實。蒲松齡早年有過充當縣令幕賓的經歷,晚年又因苛捐等問題與蠹吏進行過堅決的斗爭,這都使他對胥吏群體有深入的了解。與《聊齋志異》中大量或善或惡、或美或丑的狐仙鬼怪等幻想中的人間妖魔不同,蒲松齡筆下的胥吏為非作歹、欺詐百姓、貪贓枉法、欺上瞞下,是一個個現實生活中的惡魔。
二
《聊齋志異》刻畫的胥吏形象鮮明。貪污是這些胥吏的首要特征。究其原因,與清代政治體制和吏胥來源有直接關系。一般而言,政府想要保證執政人員的廉潔,需要有外在(法律)和內在(道德)兩個約束機制,缺少了這兩個約束機制,則很難保證清廉。從外在(法律)角度看,清朝司法制度完備,官員們要受政府監察制度約束;從內在(道德)角度看,士人飽讀圣賢之書,具有道德自我約束力。唐代著名政治家劉宴曾經用一句非常精辟的話來說明士與吏品格上的差別:“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2]但清政府對“官”的這兩種約束在胥吏那里都不存在。他們既缺少法律的約束,又缺少道德自我防線。胥吏沒有品級,不受監察制度的約束,為“吏”的直接目的就是錢,所以貪污成為清代胥吏階層的普遍現象。因為貪,才顯得酷。同時,由于長期在政府部門混事,他們養成了敏銳的嗅覺,琢磨出了一套對付上司的“有效”辦法。于是,貪、酷、猾就成為胥吏的典型特征。蒲松齡正是抓住了他們這幾個主要特點進行深刻暴露的。
(一)貪
《聊齋志異》大約有20篇以上的文章寫到胥吏的貪婪。他們或者為了蠅頭小利而濫抓無辜,如《梅女》中的典史,為區區三百錢,竟誣梅女與盜通奸,還“將拘審驗”,以致“女聞自經”[3];或者借為政府辦事之機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如《促織》中的胥吏借為皇帝進促織的名義私加賦稅,以致“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3];或者為了錢財,執法犯法,害人性命,如《云蘿公主》中的安大業被鄰人誣告被捕,鄰人欲置其于死地,“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3]。這個受了賄的解差就在押解安大業的路上險些將其推墮深谷。面對這些血淋淋事實,蒲松齡在《冤獄》一篇中疾呼:“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只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3]
(二)酷
為了斂財,胥吏們使出了極端殘忍、骯臟和卑劣的手段。他們為勒索賄賂,殘酷地毆打百姓,視生命如草芥。如《席方平》中的獄吏因“悉受賕囑”,對席方平的父親“日夜掠,脛股摧殘甚矣”[3];又如《細柳》中的高長怙被抓到牢獄中,因“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被折騰得死去活來[3]。為了斂財,他們甚至泯滅人性,利用某些人的低俗心理,逼女犯表演一場又一場人犬交媾的丑劇。《犬奸》中的兩個差役,本應將“引犬與交”的賈婦和“嚙賈人竟死”的犬解往部院,但“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役乃牽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百人”,兩役竟“以此網利焉”[3]。酷吏不僅斂財,還大肆漁色。如《連瑣》中那個“赤帽青衣”的“齷齪隸”,就威逼民女連瑣為媵妾,以滿足淫欲。無辜的平民女子尚不能保持人格尊嚴,那些落在他們手上的女犯,更成了他們泄欲的對象。《伍秋月》一篇寫差役寡廉鮮恥地調戲女犯,“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為罪犯,尚守貞耶?’”[3]
(三)猾
奸猾也是蒲松齡筆下胥吏的重要特征。如果說貪、酷是胥吏對付百姓的手段的話,其奸猾主要是用來對付上級官員的。如前所述,由于胥吏經辦實際事務,熟悉民風民情,故而地方官員執政多依賴胥吏。胥吏則經常揣摩主官的愛好和心理,以挾制主官,從中漁利。在這些狡猾的胥吏面前,不要說一般官員容易被其蒙蔽,就是一些較為清明正直的主官也大上其當。《聊齋志異》曾塑造過多個欺瞞主官、徇私舞弊的猾吏形象。如《夢狼·附則》中名叫李匡九的官員原本“居官頗廉明”,卻免不了為猾吏愚弄:差役給一位富民羅織罪名后向其索賄銀一百兩,富民不肯,差役便帶富民去見李匡九。差役明知李已戒煙,卻故意到李跟前問“飲煙否”,李搖首,差役卻下堂告訴富民,說大人不同意。差役知道李愛喝茶,又上前去問“飲茶否”,李點頭,差役就告訴富民,說大人已同意。差役兩頭搗鬼,結果清官富民皆入其彀中[3]。《夢狼·附則》還講了主官楊公的故事。楊公“性剛鯁”、不徇私情、“尤惡隸皂”,他對隸皂要求嚴格,“小過不宥”。胥吏就針對他矯枉過正的心理加以利用。他知道楊公對“胥吏之屬”說情非常反感,喜歡“反而用之”,也反其道而行之。一個差役收受了一個重犯的賄賂,答應為其開脫。楊公審理此人時,猾吏在楊公開口之前故意說:“不速實供,大人械梏死矣。”[3]楊公果然很生氣,認為是猾吏沒收到賄賂故意使壞,就嚴厲斥責猾吏,放了邑人,結果正中差役下懷,真可謂“任你官清似水,難逃吏滑如油”[4]。
這一群貪、酷、猾的胥吏,既掌握著百姓生死,又欺瞞左右主官,常使封建法律形同虛設。《田七郎》一篇非常具有代表性:武承休的仆人林兒欲奸主婦未遂,逃至某御史家,武索要未果,訴至邑宰,竟然“勾牒雖出,隸不捕,官亦不問”。后御史訟武氏叔侄,邑宰二話不說,欲打承休的侄兒武叔恒,承休上前辯解,而“操杖隸皆紳家走狗”,反把武叔恒“垂斃”[3]。在《夢狼》一篇中,作者用一個白骨如山的場面來象征晚清的社會現實:白翁到兒子白甲的官衙,見衙中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后白甲化身“牙齒”的老虎。官衙人物要吃飯時,一巨狼銜一死人入內“聊充庖廚”,并可看見“墀下白骨如山”。蒲松齡不由得發出慨嘆:“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于虎者耶!”[3]
蒲松齡對胥吏階層痛恨至極,曾多次用“貪”、“蠹”、“虐”、“滑”、“狼”、“狨”等詞來形容胥吏,甚至建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也。故能誅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以為虐。”[3]
三
《聊齋志異》中關于胥吏的描寫,反映了晚清胥吏極端腐敗的社會現實。
晚清吏治腐敗眾所周知,胥吏腐敗尤為人注目。造成胥吏腐敗的原因大致有:首先,晚清社會矛盾重重,官員腐敗(貪污)現象嚴重,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對晚清官員腐敗的形象概括。上行下效,官員腐敗蔓延及胥吏腐敗。其次,清各級政府機構中的“官”主要出自不懂實務、唯知死讀書的“八股”科舉士子,他們承擔著管理國家行政重任,大多數人卻缺乏實際執政能力。再次,清代官僚體制中的任職回避和定期升轉制度(不得在原籍做官,三至五年一任等)使官員們無心或無力圓滿地處理政事。最后,清政府是滿族人的天下,那些實際統治權的把持者多是些不懂事務、能力低下的八旗子弟,他們與由科舉產生的官員相比更缺少執政能力。以上幾點是造成清政府行政管理特別是地方行政管理“一切操諸胥吏之手”局面的根本原因。
胥吏腐敗現象早引起了清代學者的注意。名儒顧炎武就痛陳胥吏腐敗危害:“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4]紀昀更是把“吏”作為害民之首來看待:“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5]對胥吏危害,清政府非常清楚,甚至皇帝也心知肚明。雍正曾指出:“各部之弊,多由于書吏之作奸。外省有事到部,必遣人與書吏講求。能飽其欲,則援例準行;不遂其欲,則借端駁詰。司官庸懦者,往往為其所愚;而不肖者,則不免從中染指。至于堂官,事務繁多,一時難以覺察目。縣既見駁稿,亦遂不復生疑。以致事之成否,悉操書吏之手,而若輩肆無忌憚矣。”[6]嘉慶亦言:“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諾成風,皆聽命于書吏。舉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從。”[7]政府為杜絕胥吏腐敗也曾作了一系列努力,如大量裁減吏額、削減待遇、取消轉官等多種措施。與以往朝代相比,清代統治者對胥吏的管理力度是最大的。但實際境況則是,清代胥吏危害社會、魚肉百姓的程度卻遠甚過以往任何朝代。
應該說,是晚清胥吏腐敗的客觀現實為蒲松齡在小說中塑造貪、酷、猾的胥吏形象提供了原型。
蒲松齡對胥吏形象塑造與他個人生活經歷也是分不開的。
作為在科舉考試中屢試不中的落魄文人,蒲松齡一生為貧困逼迫,有時幾乎到了衣食無著的境地。他的詩歌真實反映了這樣的生活境遇:“一甕容五斗,積此滿甕麥,兒女啼號未肯舂,留糶數百添官稅。”[3]“家無四壁婦愁貧。”[3]由于付不出租稅,受到蠹吏催逼的窘態和所受到的屈辱也經常通過詩歌流露出來:“吏到門,怒且呵,寧鬻子,免風波。縱不雨,死無他,勿訴公堂長官呵。”[3“]我方踟躕懷百憂,租吏登門如怒牛。縣牒丹書照紅眼,隳哭叫號聲嘍。”[3]由此可見,他對胥吏危害有切身的體驗。取壑之盛,誘官以酷,而后可以濟虎狼之勢。若加以詞色,則必內賣官法,外詐良民,倚勢作威,無所不至。往往官聲之損,半由于衙蠹,良可惜也。但其人近而易親,其言甘而易人;又善窺官長之喜怒,以為逢迎。若居官數年而無言聽計從之衙役,必神明之宰,廉斷之官也。……衙役一到,勢無虎狼,羅織鄉村,肆行貪虐,因之挨戶攢錢,迄無寧晷。”[3]
雖深知吏胥之害,但作為一個封建文人,蒲松齡并沒有認識到胥吏腐敗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所以他提出的治理措施雖有一定道理,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聊齋志異》中有不少貪酷的胥吏得到惡報的情節,顯示了蒲松齡想通過一些因果報應的故事來勸導胥吏棄惡從善的意圖。如《梅女》中的典史因受賄誣陷梅女致其死亡而受到冥報:妻子
蒲松齡曾做過江蘇寶應縣令孫蕙的幕賓,這使他對胥吏這個群體有更清晰、更準確、更深刻的了解。他曾在《公門修行錄贅言》中寫道:“君不見城邑廨舍中,一狨在上而群狨隨之呼?每一徭出,或一訟出,即有無數眈眈者,涎垂嗥叫,則志其頂,則揣其骨,則姑其肉。其懦耶少恐喝之;慷慨耶甘誘之;慳吝耶遍苦之。且大罪可使漏網,而小罪可使彌天。重刑可以無傷,而薄懲可以斃命。蚩蚩者氓,遂不敢不賣兒貼婦,以充無當之卮。”[3]他還在給孫蕙的信中說:“邑中人惟蠹役宜懲,下此則雖至賤之人,亦無所施吾系辱。”“每見蠹役貫盈,懼人覆算,遂如中山狼,借我囊以自庇,不惟眾怒難任,目恐豺狼之性,未能忘情于人肉也。”[3]
蒲松齡晚年也曾與蠹吏做過面對面的斗爭。經管淄川漕糧的蠹吏康利貞擅自增加稅收,加重百姓負擔。為了全縣百姓利益,蒲松齡不但到縣城找康利貞當面質詢,還寫信給縣官吳堂、王士禎、譚無兢等,揭露康利貞的行為:“小民有盡之血力,縱可取盈,蠹役無底之貪囊,何時填滿?”[3]“敝邑有積蠹康利貞,舊年為漕糧經承,欺官害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貧民,皮骨皆空。”[3]“康利貞為漕糧經承,妄造雜費名目,欺官虛民,每石派至二兩一錢零,此亙古所未有,而自彼創之,合縣皆為切齒!四月中,藩臺訪其蠹狀,行文到縣,使不得復入公門,大眾聞之,無不歡騰!今聞其厚賂顯者,薦使復其舊任,想一啖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購之也,聞者莫不失色。”[3]他不顧自己年老體弱,親自從淄川趕到省城濟南告狀,終于戰勝康利貞,維護了全縣百姓的利益。
針對胥吏制度的弊端,蒲松齡也提出過一些治理辦法。如他認為,杜絕胥吏危害,主官的責任非常重要。他建議主官要從自身做起,“擇事而行”、“擇言而聽”、“擇仆而役”,不給那些蠹役可乘之機;他還建議主官約束手下人,不要為他們的言語所惑,盡量約束他們,避免他們為非作歹。在《循良政要》中,他明確提出:“一,制衙役。凡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官害民之志。蓋必誘官以貪,而后可暴卒后在冥間為娼,以償其貪債,他本人亦暴斃。對這類故事產生的教育效果我們固然可以持懷疑態度,但它們卻無可置疑地反映了作者“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痛苦而無奈的心情和他“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的憤懣[3]。
蒲松齡塑造的胥吏形象,其意義并不在于為晚清無可救藥的社會提供一個治病的良方,而在于我們能夠透過這些形象描寫,更清楚地認識到了晚清胥吏腐敗的現實。
還需指出的是,蒲松齡塑造的胥吏形象還無意中觸及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個政治頑癥,一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中長期存在的痼疾。
胥吏腐敗并不為清政府所獨有,我們在明代也可以看到大量類似的現象。筆者認為,胥吏腐敗這一痼疾的產生,與封建政府體制本身有關。從宋代開始,科舉考試就成為封建政府選官的主要途徑,這種制度到明清時達到頂點。科舉取士制度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官,但這些奉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讀書人一向自命清高,不屑于也不擅長從事具體的事務管理,他們往往把一些具體政務交與胥吏處理。這樣,胥吏就成為封建機器上的螺絲釘,缺少他們,龐大的國家機器就不能順利運轉。但胥吏的正面作用卻一直沒有得到封建政府的重視。不僅如此,縱觀中國歷史,胥吏沒有品級,地位低下,明清士大夫甚至視他們為“奴隸”和“盜賊”。如清陸世儀說:“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并于世人君子者,吏也。”[8]錢大昕更說:“自明中葉以后,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9]清末馮桂芬還說:“后世流品,莫賤于吏,至于今日而等于奴隸矣。”[10]胥吏地位卑下,待遇也菲薄。《明(萬歷)會典》卷三九規定:“在京各衙門吏胥俸祿,多者每月米二石五斗,少者六斗。”“在外各衙門吏典(月)俸一石。”[11]這樣的俸祿僅能勉強過日。清代對胥吏一般只給予微薄的工食銀,根本無法糊口。經濟條件差,缺少入仕途徑,再加之文化道德素質低下,使胥吏成為封建統治結構中經常遭到詬病的群體。
[1][清]徐珂.清稗類鈔(第1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四九)[M].北京:中華書局,1989.
[3][清]蒲松齡.聊齋志異[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4][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M].黃汝成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
[5][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九八)[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7]清仁宗實錄(卷一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清]賀長齡.清經世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2.
[9][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
[10][清]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11][清]趙翼.廿二史札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
I206.2
A
1007-905X(2011)03-0151-03
2011-02-10
王保健(1956— ),男,河南虞城人,河南人民出版社副編審。
責任編輯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