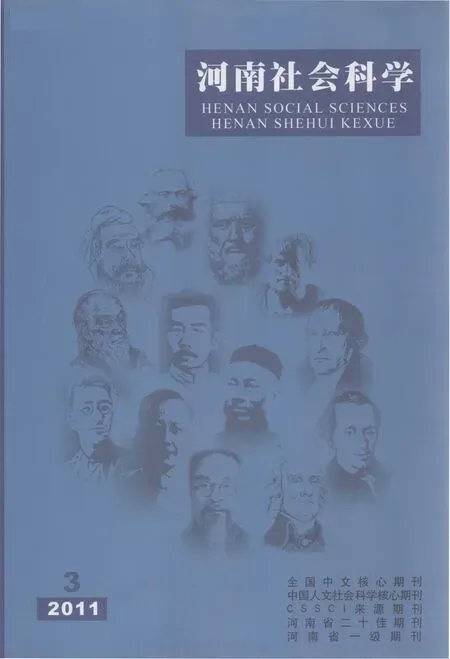瀆職罪主體司法認定中的疑難問題研究
魏穎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法學研究所,北京 100720)
瀆職罪主體司法認定中的疑難問題研究
魏穎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法學研究所,北京 100720)
瀆職罪主體的本質特征在于“從事公務”,即從事的工作性質是行使國家公權、執行國家公務。這一特征也是瀆職罪的前提條件,即要有“職”可“瀆”。公務職責是分析、判斷瀆職罪主體資格的邏輯起點。對瀆職罪主體資格的判斷應當是動態的、具體的,僅僅具有公職身份尚不足以認定,還要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涉案公務職責、是否利用涉案瀆職罪所對應之公職實施犯罪,以確定其所具有的公職與涉案公職是否具有對應性。
瀆職罪主體;公務職責;實質判斷;責任鏈;共犯
考察瀆職罪主體的法律演變歷程,從79刑法典的“國家工作人員”到97刑法典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再到相關立法及司法解釋的“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罪主體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寬到窄,再由窄向適度放寬的演變過程”①。法律更迭之果,緣于社會變遷之因。社會轉型時期,公權運作環境、決策環境面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多重影響②。國家基于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適時進行的機構改革、不同性質的社會職能部門分工的不斷調整、國家機關內部人員成分的多元化趨向等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使得具有公權的機構不再限于國家機關,公權的實際行使者也不再限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法律的授權、國家機關的委托使得不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事編制范圍的具有多樣社會身份的各種“編外”人員,在實際工作中同樣擔負并履行特定的公務職責。一系列反映社會職能分工等變化的立法及司法解釋使瀆職罪主體的表現形式隨著公權來源的日益多元化,也相應呈現出多樣性特征,形成刑法典、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組合而成的具有多重效力等級的規范體系,作為瀆職罪主體的司法認定依據。在司法實踐中,瀆職罪主體的認定不僅關系到罪與非罪、本罪與他罪的界限,而且,還涉及司法機關立案管轄范圍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1998年1月19日起施行)第二條:“人民檢察院管轄的‘瀆職犯罪’,是指刑法分則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罪。”因此,有學者提出,在訴訟程序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瀆職犯罪由檢察機關管轄,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公安機關管轄,但事實上,由于對瀆職犯罪主體本身缺乏認定的標準,其最終也導致了管轄上的混亂局面③。這在程序上凸現出準確界定主體的法律意義。
瀆職罪主體身份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公權運行過程中因覆蓋多個環節而形成涉及數個責任主體的責任鏈等現實問題所帶來的主體資格及責任范圍界定的復雜性,以及與瀆職罪主體資格密切相關的瀆職罪與關聯犯罪共犯的認定等一系列實務問題,構成瀆職罪主體司法認定中的難點。為了破解這些難點以探尋解決的現實方案,需要回歸到與該罪主體有關的基本問題上來進行研究。
一、瀆職罪主體司法認定中的不變因素:公務職責
在瀆職罪主體的司法認定中,與主體表現形式多樣性不同的是,“公務職責”是瀆職罪主體要素中恒定不變的核心和主線。首先,瀆職罪的主體在本質上是承擔某種公務職責的社會角色。97刑法典將該罪主體規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是為了限定主體應具有某種社會身份,而是因為具有這種社會身份的人員通常是國家事務的決策者、執行者。因此,認定瀆職罪主體的關鍵在于,主體是否具有涉案公務職責(而不在于其是否具有某種具體的社會身份)、是否利用涉案瀆職罪所對應之公職實施犯罪。“公務職責”是分析、判斷瀆職罪主體資格的邏輯起點。其次,根據97刑法典的規定,瀆職罪的主體為自然人,但與一般自然人犯罪不同的是,該罪主體在具備法定年齡和精神健康等刑事責任能力的基礎上,還必須具有“肩負公務職責”這一附加的內涵。因此,瀆職罪主體資格的判斷標準不單包括刑法條文所顯示的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人事身份,而且還要考察主體在具體案件中是否具有公務職責、危害行為是不是發生在代表國家行使該公職時的職務行為(包括濫為和應為而不為)。判斷過程是動態的、具體的,且行為人所具有的公職屬性的社會身份與涉案公職必須具有對應性。如果涉案公職與行為人擔負的職責無關,則行為人不構成瀆職罪。再次,瀆職罪與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等貪污賄賂類公職犯罪在客觀方面都具有“利用職務便利”的行為特征,不同的是,瀆職罪侵害的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貪污賄賂罪侵犯的客體則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不同的社會管理領域對應不同的公職,因此,瀆職罪的關鍵在于“職責”,不同的職責對應不同性質的瀆職犯罪。而貪污賄賂罪強調的則是“公權”這一事實本身,至于權力的具體內容并不影響行為的性質。這決定了在涉及瀆職罪主體的訴訟證明中,不僅要證明主體具有公職、從事公務,同時還要確認行為人具有的公職與該瀆職案對應的公職是否具有同一性,行為人利用的是否是該瀆職案涉及的公職。
二、瀆職罪主體資格的界定:客體立場上的實質判斷
司法實踐中,關于主體資格的界定,有如下兩個突出的現實問題。
(一)瀆職罪主體責任認定中,實質判斷與形式判斷的關系及對二者的運用
形式判斷是對相關法律解釋的文本注釋,是針對常規或典型情形的靜態的、形式意義的判斷標準,指主體具有“從事公務”的資格要素,以及圍繞這一要素延伸出的“從事公務的權力來源合法”和“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瀆職”等三項判斷標準。而實質判斷的核心同樣是“從事公務”,其依據的是瀆職罪的犯罪客體,即它是在實質上侵犯瀆職罪客體的前提下,對瀆職罪主體法律規定的適用解釋,是動態的、針對特定個案的判斷。歸納而言,形式判斷是從立法和解釋角度提出的,實質判斷則是從保護客體的角度提出的,是不同視角下的兩種判斷路徑。無論是形式判斷還是實質判斷,二者共同的基點在于,作為瀆職罪的兩類主體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它們的交集是“從事公務”,表明是否從事公務是核心的判斷標準,決定著基本的判斷方向。
這類似于瀆職罪主體法律規范體系所呈現的一般與特殊的特征,即“一般”為立法所規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同時,立法和司法解釋又根據不斷變化了的客觀事實,對瀆職罪主體做了擴大解釋,使現實中欠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形式要件但符合瀆職罪主體法律本質的人員也有可能成為瀆職罪的主體。因此,正如瀆職罪主體的立法規定和法律解釋的關系一樣,形式意義上的判斷標準與實質性判斷的審案思路并非矛盾而是互補的,兩者結合有助于嚴密刑事法網,在遵循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同時確保法律適用的彈性。
需要強調的是,立法中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瀆職罪主體的形式要件,作為“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判斷核心的“從事公務”是瀆職罪主體的實質要件。在較為復雜的案件中,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往往會相互結合、遞補適用。從法律效果和適用邏輯上講,由于形式要件并不必然能推理出實質符合性,因此,符合形式要件時仍需進一步證明實質要素。反之,欠缺形式要件但若可以確證實質要件符合性,則在現有立法及司法解釋的框架內,依然有主體資格成立的余地。
(二)具有多重身份的瀆職罪主體資格的界定
徇私類瀆職罪中,部門之間的分工有交叉甚至重疊,某項特定工作由多個部門共同負責時,主體資格的界定,尤其是兼具司法工作人員和行政執法人員雙重身份的公安人員的主體資格的界定問題較為突出。如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根據《刑法》第四百一十八條和2006年《立案標準》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該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招收公務員、省級以上教育行政部門組織招收學生的工作中徇私舞弊、情節嚴重的行為。該罪的犯罪主體是負責招收工作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符合該罪的主體身份,但是公安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幫助偽造考生戶籍的行為能否成為該罪的犯罪主體呢?據有關調研資料顯示,司法實踐中對此類案件主體資格的界定對該類同樣犯罪事實的案件,認識不一、定性不同:有的認為招收學生徇私舞弊罪的主體只限負責招生工作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公安民警利用職務便利幫助考生偽造戶籍的行為應認定為濫用職權罪;而有的則認為,公安民警可以成為該罪主體,因為公安民警在招生報名過程中負責戶籍審查這一特定招生環節的工作。又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根據《刑法》第四百零四條,該罪犯罪主體是履行征收稅款職責的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稅務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各級稅務局、稅務分局、稽查局、稅務所中代表國家依法負有向納稅人征收稅款義務并行使征收稅款職權的人員。那么其他征稅機關工作人員能否成為犯罪主體?實踐中,非稅務機關工作人員不征或者少征稅款的現象時有發生,如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稅、契稅由財政部門負責征收。盡管這些部門人員實施了與稅務人員相同的不征或者少征應征稅款行為,但由于其不具有稅務人員的特殊身份,因而他們不符合該罪的犯罪主體特征,以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同行為不同處罰、罪責不相適應的現象。
正如自然人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多重社會角色一樣,當我們在分析一個人在某一場合或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時,需要將之還原到該場合或事件中,做具體判斷,而不是泛泛地給他貼上所有可能的角色標簽。也即,不能脫離案件具體事實來判斷構成要件的具體要素的符合性。界定瀆職罪主體資格時,行為人具有涉案瀆職罪所要求的一般意義上的主體身份,但在具體案件中其并不負有構成涉案瀆職罪所對應的“公務職責”,此時,對判斷其主體資格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其是否具有涉案公務職責這一事實上的身份,而非形式意義上的檔案身份。因此,當行為人有雙重甚至多重身份時,引起刑法效果的是其在具體案件中涉嫌所違之“公職”對應的身份。同時,由于瀆職罪的前提是有“職”可瀆,因此,如果沒有相應的職責權限,則行為人作為該公職所對應之瀆職罪的主體的責任能力是有缺陷的,即便其行為對于該案危害結果的發生發揮了積極的助推作用,也不能構成以具有該公職為必要條件的特定瀆職罪。
三、瀆職罪責任主體的界限:責任鏈上的縱向考察
即縱向來看,涉案主體為多人時,如何確定一條責任鏈上刑事責任主體的范圍。
根據97刑法,瀆職罪是自然人犯罪,沒有單位犯罪。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決策錯誤型”瀆職犯罪往往是在單位領導主持下的集體決策所致。在這種情況下,刑事責任歸咎的范圍應當追究到哪一級?從實例判決分析,各法院處理明顯不一。有些案件已經明確顯示是整個單位的責任,但追究刑事責任時僅限于在這一職責鏈條末端的責任人(如主管局長—科長—副科長,則副科長被視為責任主體),這樣處理是否合理?還有一些案件,嚴重后果的出現是由于長期積累的問題所致。在這個過程中,主管人員經歷了人事上的調整,如趙某瀆職案件,2月10日發生嚴重事故,而被告人趙某是同年2月1日上任主管該項工作的。在這種情況下,對以往責任人既往不咎,僅依職責抓“現官”是否公正?而與上述情形相反的另一種情形是,責任追溯到結果出現之前、現已離開本崗位的責任人,如被告人耿某被指控在其擔任某市建設局主管質量監督的質監站站長期間有玩忽職守行為,導致某校教學樓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在使用8年后被拆除。耿某辯稱,其在該校教學樓工程竣工驗收前便被調離建設局質監站,沒有全程對教學樓的質量進行監督。因此,認定其構成玩忽職守罪的事實不清、證據尚不確實充分。上述兩種相對應的情形比較而言,后一種情形按罪處理是妥當的,注意到了權責對應,對責任人的追究公平合理。至于被告人的辯護理由,根據其行為在形成危害結果諸多成因中原因力的大小,在判決中可作為量刑因素,酌情處理。前述情況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和責任體制的復雜性在刑法適用中的具體體現。盡管這一問題是瀆職罪主體認定中的難點,但依然有一定的章法可循。在具體個案中,在一個責任鏈有多個責任人時,根據行為人在此鏈條上的位置及該崗位對應的職責范圍確定刑事責任能力的范圍,進而確定是否納入追究刑事責任的范圍。此外,還要從如何行使職責的角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來確定責任主體的范圍。
四、瀆職罪涉及的共犯問題:共犯視角下的橫向考察
即從橫向來看,如何解決瀆職罪相關的共犯問題。
(一)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能否成為瀆職罪的共犯
這個問題對應的相關理論是,無身份者能否與有身份者一起構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對此可分解為以下兩個小問題:
1.瀆職罪中,無身份者能否構成有身份者實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幫助犯或共同實行犯。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關于非司法工作人員是否可以構成徇私枉法共犯問題的答復[2003年4月16日(2003)高檢研發第11號]中明確規定:非司法工作人員與司法工作人員勾結,共同實施徇私枉法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以徇私枉法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但這里的“共犯”是否全部包括了教唆犯、幫助犯和共同實行犯?目前學界及司法界一致認為,無身份者可以構成有身份者實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幫助犯。但對無身份者能否與有身份者構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實行犯,則存在“肯定說”、“否定說”等不同見解。有學者在此基礎上分析認為,真正身份犯,只是具備該身份的人才能實施,而從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來看,并不完全排除無身份者實施部分實行行為,而成為某些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實行犯,如上述答復中明確規定“共同實施”。因此,得出結論: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能否構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實行犯,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凡無身份者能夠參與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實行行為的,可以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實行犯;凡無身份者根本不能參與真正身份犯的實行行為的,即不能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實行犯④。此外,依照我國97刑法對共同犯罪人的分類(主犯、從犯、脅從犯、教唆犯),結合司法實踐中的實際情況,無身份者根據其實際所起作用,在共同犯罪中可能是從犯,也可能是主犯。強調這一點是要引出下一個問題,即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確定該共同實施的犯罪的性質的依據是什么。
2.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實施瀆職犯罪,對該共同實施的犯罪的定性依據是什么。無論是單獨犯罪還是共同犯罪,定罪的基本原則必須是主客觀相統一,定罪的根據只能是法定的犯罪構成。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該規定代言了學界的“以誰是主犯為根據來定罪”的主張。這一主張在刑法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在司法實踐上也存在適用上的邏輯矛盾。理論上,主犯、從犯所表明的是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屬于量刑情節,而非定罪依據。定罪的依據是各共犯人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行為所對應的具體犯罪的犯罪構成,這就決定了定罪客觀依據的落腳點必須在“實行行為”上。實踐中,如果教唆犯和實行犯在共同犯罪中都是主犯,或被教唆人沒有實施所教唆的罪時,對教唆犯如何定罪將出現邏輯上的困難。因此,有學者總結認為:無身份者教唆、幫助有身份者實施或與之共同實施真正身份犯時,應依有身份者的實行犯的實行行為來定罪,即依有身份者所實施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來定罪,即使無身份者是主犯,也不影響上述定罪原則⑤。對此,有觀點認為,特殊身份論的觀點基于特殊身份所形成的便利條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主張一切以身份犯罪定性的觀點,存在罪刑均衡的問題,就職務侵占罪和詐騙罪而言,由于職務侵占罪的最高刑罰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詐騙罪的最高刑罰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因此,特殊身份論的觀點存在鼓勵無特殊身份者與具有公司、企業職員身份者勾結實施詐騙犯罪之嫌⑥。這種觀點是有針對性的,即適用于刑法分則基于某種特定行為,針對不同身份者規定了不同罪名的情形。而在瀆職罪的語境中,上述顧慮是不必要的。因為作為該罪客觀方面的“瀆職行為”所必需的“具有公職”的基本屬性,決定了無公職人員沒有實施瀆職行為的可能性,上述情形在瀆職罪中沒有存在的余地。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本文前述觀點,即在瀆職罪中,是否具有公務職責是認定主體身份的關鍵。在該罪中,“身份”意味著一種資格。身份的表現形式或概念稱呼隨著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公權運作機制、社會管理模式及其他領域社會變遷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但在不斷變化中,保持恒定不變的是,“身份”即是具有某種公務職責的事實,“公務職責”是確立瀆職罪主體身份的核心要素。
將上述兩個問題的分析歸納合并,可以得出結論: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可以成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罪的共犯,以所構成的相關瀆職犯罪定性。
(二)瀆職犯罪與關聯犯罪共犯的界限
在瀆職罪中涉及一些關聯犯罪⑦,例如,放縱走私罪與走私罪,私放在押人員罪與脫逃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與偷稅罪,放行偷越國(邊)境人員罪與偷越國(邊)境罪,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與犯罪分子所實施的犯罪等。這些關聯犯罪在理論上被描述為“前案”、“原案”、“原罪”、“本犯”、“前罪”、“前提罪”等。在這類犯罪中,瀆職者都明知其庇護對象是在實施犯罪行為,其特點可以概括為“內外勾結”。這就涉及對瀆職者的定性問題。
對此,理論和司法實務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認定為瀆職罪。理由是,刑法對瀆職犯罪的規定是一種特別規定。比如說,刑法規定的放縱走私罪,本身就排除了對放縱走私者以走私罪共犯定罪的可能性。也即,即使海關工作人員是與走私犯共同走私,由于刑法對海關工作人員專門規定了放縱走私罪,對其就不能再定走私罪了。類似的還有私放在押人員罪。在司法實踐中,私放在押人員案件大多都是在司法工作人員與在押人員的相互配合下發生的,如果將司法工作人員認定為脫逃罪的共犯,私放在押人員罪就形同虛設,在實踐中就幾乎沒有適用的可能性了⑧。二是對瀆職者原則上以瀆職罪定罪處罰,但當以相關共犯處理更重時,應以共犯對瀆職者定罪處罰。理由是,從共同犯罪和罪數理論角度進行分析,在這種情況下,瀆職者的瀆職行為實際上兼有瀆職犯罪構成要件和共犯構成要件的雙重性質,即他的同一個行為,在觀念上、形式上同時符合兩個犯罪構成,屬于想象競合犯形態,依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對行為人應當擇一重罪處斷⑨。三是瀆職者符合關聯犯罪的共犯時,直接按關聯犯罪定罪,不再認定瀆職。
筆者認為,前兩種觀點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認為在共生性瀆職罪中,瀆職者當然地構成關聯犯罪的共犯。而事實上,從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出發,成立共同犯罪,除了客觀上的共同行為之外,各共犯人還必須有主觀方面的共同故意。不少瀆職者對關聯犯罪者僅有客觀上的庇護行為,而無主觀上的通謀,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原則和共同犯罪的原理,瀆職者并不能成為關聯犯罪的共犯,而只能成立其自身主客觀要件所符合的相應的瀆職犯罪。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瀆職者的行為由于只觸犯了瀆職罪一個罪名,也就不涉及想象競合規則的適用了。因為,想象競合犯要求行為人的一行為必須觸犯數罪名。因此,上述前兩種觀點的理由并不周延。第三種觀點認為瀆職者在同時構成關聯犯罪共犯時,排除瀆職,僅認定關聯犯罪。這種觀點在實踐中也頗多分歧,實際上是以“關聯罪”過濾掉了“瀆職罪”。盡管就很多案件的處理結論而言,適用這種觀點和經過想象競合規則篩選過的結論是相同的,但不能因此便可此可彼,模糊二者的界限,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法律條文適用的完整性。在想象競合的情況下,涉及的數罪的條文在法律文書中都應引用,而不能僅引用適用從一重處斷原則后確定的罪名的條文。筆者認為,瀆職者在事前通謀型犯罪中,一方面,由于符合刑法總則規定的共犯主客觀要件而構成關聯犯罪的共同犯罪,另一方面,由于瀆職者是利用其職務、職權或者以公務履行職責為媒介而實施犯罪,決定了其行為同時必然侵犯了國家對行使公權力的基本要求和正常的管理活動,即侵害了瀆職罪所保護的客體。因此,不能因為關聯的共同犯罪的成立而省略成立共同犯罪過程中必然“攜帶”的“瀆職”。法律適用結論的相同不意味著法律適用過程的一致,而不同的法律適用過程關系到適用法律依據的完整性。
總結而言,對瀆職罪中的關聯犯罪現象在認定時應采用“兩段論”的判斷方法。首先,判斷瀆職者的行為是否分別構成相關的瀆職犯罪和關聯犯罪的共同犯罪。判斷的結果有兩種可能:一是只構成其中一罪。如濫用職權等瀆職行為沒有達到立案標準,而符合關聯犯罪的定罪標準,按關聯犯罪共犯定罪。又如,瀆職者的瀆職行為對關聯犯罪只有客觀上的庇護,主觀并無實施關聯犯罪的共同故意,則只構成相應的瀆職犯罪。二是構成瀆職罪和關聯犯罪的共同犯罪兩罪。其次,根據前述判斷結果分別做以下處理:在只構成一罪的情況下,直接適用對應的法律規定;在構成兩罪的情況下,適用想象競合犯的規則,從一重罪處斷。
五、主體視角下本罪與他罪的界定
除了判斷行為人是否符合主體資格外,瀆職罪主體特征付諸實務的典型實踐是甄別本罪與他罪。瀆職罪主體的本質特征在于“從事公務”,即從事的工作性質是行使國家公權、執行國家公務。這一特征也是瀆職罪的前提條件,即要有“職”可“瀆”。至于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以及是正式人員還是借用、聘用人員的身份形式并不影響主體身份的界定。此外,在刑法分則中,瀆職罪主體屬特殊主體,在瀆職罪內部體系中,又有一般瀆職罪和特殊瀆職罪之分,后者主體往往在一般瀆職罪規定的基礎上被進一步限定。因此,對于瀆職罪中的特殊主體,除具備瀆職罪一般主體資格外,還需要符合該罪主體的特別規定。
運用瀆職罪主體特征甄別行為性質需避免“唯主體論”傾向。這種情形在公訴實踐中較為典型。相比偵查機關追求實效、側重案件偵破的思維定式,公訴機關則偏向于構成要件符合性證明的思維模式。定罪的邏輯體系是犯罪構成。因此,區分此罪與彼罪的方法主要是比對構成要件。在客觀行為和主觀方面相同的情況下,不同主體身份成為定罪的關鍵。然而,對主體身份的應用如果走向極端就會形成“唯主體論”的定性傾向。這種傾向的錯誤在于,“就主體論主體”,缺乏構成要件整體觀,忽視其他構成要件對主體的限定作用。“唯主體論”在司法實務中進行定性判斷時,主要表現為兩個誤區:一是身份決定論。將身份視為定性的決定因素,忽視對主體行為是否屬于公職行為的考察。二是“多重身份”的情況下,先入為主,認同一種身份而后進行演繹式的論證,無視另一種特殊身份的存在。沒有比對行為人是以何種身份實施涉案行為的,屬于分析案件的論證方法錯誤,是在預先有傾向結論的前提下進行的先入為主的演繹論證。
注釋:
①李忠誠:《瀆職罪主體問題研究》,載《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第8頁。
②張國臣、黎志成:《群體決策支持系統在社會治安防范管理中的應用》,載《河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第72頁。
③武小鳳:《論瀆職罪主體構成的統一性要求》,載《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第89頁。
④⑤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82—583頁、第584頁。
⑥王志遠:《多元身份主體共同犯罪之定性難題及前提性批判》,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2期,第83頁。⑦⑧趙秉志、肖中華、左堅衛:《刑法問題對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03、504頁。
⑨楊祖偉:《略論偵查監督環節檢察機關的引導》,載《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第30頁。
D9
A
1007-905X(2011)03-0128-05
2011-01-25
魏穎華,女,河南鄭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 韓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