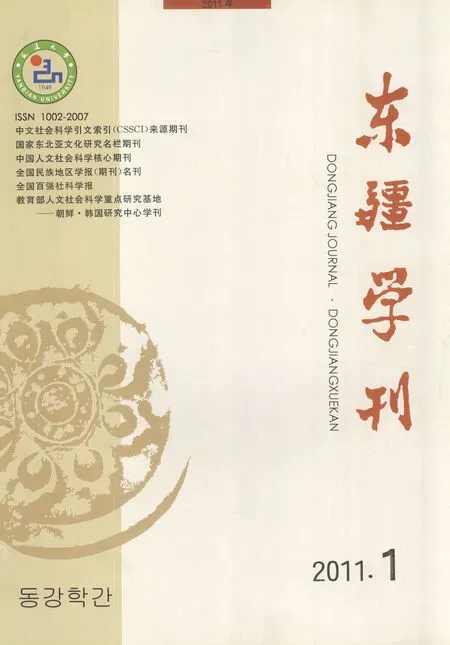試析朝鮮塔銘中的漢文化元素
李谷喬,李明非
試析朝鮮塔銘中的漢文化元素
李谷喬1,李明非2
朝鮮半島與中國(guó)的文化淵源甚深。特別是在唐代,中華文化向周邊國(guó)家都有傳播,其中以朝鮮半島所受到的浸潤(rùn)最為深厚。現(xiàn)以保存在《全唐文》和《唐文拾遺》中的16篇朝鮮塔銘為例,分別從佛教觀念、人物刻畫手法以及章法行文技巧方面來探討朝鮮半島所受漢文化、漢文學(xué)的深刻影響,并從半島塔銘文鮮明的漢文化印痕里,感受中朝文化交往的悠遠(yuǎn)和深厚。
朝鮮;塔銘;漢文化元素
興盛于唐代的禪宗,因其在心性理論上的獨(dú)到造詣,特別受中古時(shí)期朝鮮半島的歡迎。新羅朝(公元668—935)和高麗朝(公元935—1392)都曾輸入大量中文佛教典籍,也都派遣大批留學(xué)僧來華學(xué)習(xí)。伴隨著唐代禪學(xué)的東漸,朝鮮半島的佛家逐漸接受了中國(guó)僧侶的喪葬習(xí)俗,同時(shí),為高僧作蓋棺定論的特殊文體——塔銘,也在這時(shí)傳入了朝鮮半島。
所謂塔銘,指德高望重的僧人或居士亡化后,為傳揚(yáng)其一生功德而撰寫的銘文。因?yàn)槭强淘谑?并砌于僧人歸寂塔的正面,所以這類碑銘也被稱作“塔銘”。中國(guó)的塔銘在唐代達(dá)到了興盛期,涌現(xiàn)出大量經(jīng)典之作。從現(xiàn)存文獻(xiàn)看,朝鮮半島的塔銘正是以唐代塔銘為典范,其在佛教思想、人物刻畫手法、行文特色等方面,都呈現(xiàn)出大量的漢文化元素。
一、儒釋合流的佛教觀
朝鮮塔銘表現(xiàn)出鮮明的儒釋合流、援佛濟(jì)世的觀念,大文豪崔致遠(yuǎn)在《有唐新羅國(guó)故知異山雙寺教謚真鑒禪師碑銘并序》中寫道:
《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dāng)”。故廬峰慧遠(yuǎn)著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fā)致雖殊,所歸一揆。體極不兼應(yīng)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fā)其端,釋窮其致。”真可謂識(shí)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1](10864)
慧遠(yuǎn)、沈約,一為晉末高僧,一為齊梁顯宦,都是以儒學(xué)佛,深知儒家治世、佛家修心之道,認(rèn)同兩教相輔相成,同為濟(jì)世之良藥。崔致遠(yuǎn)在為新羅真鑒禪師正式寫銘文之前,舉慧遠(yuǎn)、沈約的例子,大談儒釋殊途同歸,實(shí)是在傳達(dá)當(dāng)時(shí)朝鮮半島的佛教觀。
半島高僧們也多持儒釋合流、以佛濟(jì)世的觀念。本來,僧人應(yīng)是避世而居,不愿與世俗接觸的,但朝鮮的高僧們卻愿意和皇親貴戚交往。翻檢《全唐文》和《唐文拾遺》中的16篇塔銘,可以確知,曾奉旨面圣的高僧多達(dá)11人,分別是:行寂、忠湛、無染、智詵、審希、利嚴(yán)、元暉、麗嚴(yán)、微、允多、慶猷。他們奉召來到京城,不僅僅是為國(guó)君講經(jīng)說法、祈福求祥,更有些人是來參議朝政的。
獻(xiàn)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孤幼遭閔兇,未能知政。致君奉佛,濟(jì)海人,與獨(dú)善其身,不同言也。幸大師無遠(yuǎn)適,所居唯所擇。”對(duì)曰:“……就有三言,庸可留獻(xiàn),曰:‘能官人’。”[1](10871)
無染(朗慧和尚)學(xué)成歸國(guó)后,經(jīng)歷了新羅文圣王、憲安王、景文王、獻(xiàn)康王、定康王、真圣王六朝,他與歷代帝王都有交往,頗得王室敬重,特別是獻(xiàn)康王給予無染極高的榮寵。前面引文就是獻(xiàn)康王大病初愈,向無染咨詢國(guó)政時(shí)的一段對(duì)話。無染這時(shí)也完全拋開了佛家不問世事的“清凈心”,從治國(guó)輔政的角度,簡(jiǎn)練地答復(fù)了國(guó)君當(dāng)下的政治最要?jiǎng)?wù)是“能官人”,即選拔合適人才,委以重任。可見,無染雖身在佛家,卻心存治道,有意消除儒家與佛家的差異,曾諭誡僧徒說:“道師(佛祖)、教父(孔子),寧有種乎?……或謂教、禪為無同,吾未見其宗……大較同弗與異弗,非!”[1](10871)可以說,無染是朝鮮儒釋合流、以佛輔政的典型代表。
此外,行寂、審希、利嚴(yán)、元暉等,也都是出入王庭、以佛法助王化的僧人,其贊同儒釋合流的言行都記載在他們的塔銘中:
(行寂)自欲安禪,終須助化。[1](10360)
——崔仁氵六兄《新羅國(guó)故兩朝國(guó)師教謚朗空大師白月棲云之塔碑銘》
(審希)大師高拂毳衣,直升繩榻。說理國(guó)安民之術(shù),敷歸僧依法之方。[1](11129)
總之,朝鮮半島的士大夫和高僧們,普遍傾向統(tǒng)合儒釋、援佛濟(jì)世的佛教觀,這其實(shí)與他們來唐訪學(xué),耳濡目染唐文化有著極大關(guān)系。據(jù)嚴(yán)耕望先生考證:“自太宗貞觀十四年新羅始派遣留學(xué)生起至五代中葉,三百年間,新羅所派遣之留唐學(xué)生,最保留之估計(jì)當(dāng)有兩千人……不但人數(shù)眾多,且留居甚久。”[2](441)塔銘的作者,如崔仁渷、崔致遠(yuǎn)、崔彥、金穎等,都是著名留唐學(xué)生,他們或科舉高中,或在唐為官,在漫長(zhǎng)的旅華歲月中,唐文化浸透了他們的靈魂,極大地影響著他們的認(rèn)知傾向。
我們?cè)龠M(jìn)一步考察唐代的宗教認(rèn)知思潮,可以發(fā)現(xiàn),社會(huì)上雖然儒釋道三家并行,但主流認(rèn)同的仍是儒家,絕大多數(shù)士大夫還是站在儒家的倫理和道德原則層面審視佛法旨義。柳宗元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儒以禮行,覺以律興。”[1](5936)白居易《策林·議釋教》說:“若欲以禪定復(fù)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xùn)在;若欲以報(bào)應(yīng)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1](6852)
恰恰是以儒學(xué)佛,從外部思考佛教的價(jià)值,讓士大夫們認(rèn)同了佛家的調(diào)養(yǎng)心性,進(jìn)而間接地也能協(xié)調(diào)宗法社會(huì)各方面關(guān)系的功效。如此一來,重主觀、避世的佛教便同強(qiáng)調(diào)客觀、積極入世的儒家一樣,都具有了拯物濟(jì)世的社會(huì)功能。這樣一來,表面上兩家變得沒什么大矛盾了,似乎還可以并行不悖。對(duì)此,劉禹錫曾在《袁州萍鄉(xiāng)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做過一段精彩評(píng)說:“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jié),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shì)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bǔ)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xí)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圣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至遠(yuǎn)也同功。”[1](6162)白居易講得更明白,他在《三教論衡》里說:“夫儒門釋教,雖名數(shù)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1](6162)
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這種泯滅儒佛差異、贊同兩教合流、共同為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服務(wù)的觀念,很有代表性,可以說基本上是唐代知識(shí)分子的主流認(rèn)知。朝鮮遣唐留學(xué)生、留學(xué)僧,所親歷感知的也正是這樣的佛教認(rèn)知潮流。作為朝鮮半島的知識(shí)精英,這些留學(xué)人員回國(guó)后,就把這種佛教觀帶回了本國(guó),從而出現(xiàn)了唐朝佛教觀在朝鮮半島的盛行。
二、使用細(xì)節(jié)刻畫人物
在寫人技巧上,朝鮮半島塔銘也承襲了唐代塔銘、墓志類文章的特點(diǎn)。
唐代的碑志名家,如張說,《舊唐書》稱其“尤長(zhǎng)于碑文、墓志,當(dāng)代無能及者”。[3](3057)我們考察張說碑銘墓志類文章,發(fā)現(xiàn)他特別注重使用細(xì)節(jié)突顯人物形象。在《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中,張說就通過細(xì)節(jié)描寫,表現(xiàn)了王室對(duì)神秀的極高優(yōu)待:
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qǐng)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guó)師。[1](2334)
神秀面圣時(shí),不僅不用起立致禮,還可以乘轎上殿,甚至能受到武后的屈尊禮拜,并被尊奉為“法主”、“帝師”。其中,“趺坐覲君”、“肩輿上殿”純屬細(xì)節(jié)描寫。張說用精簡(jiǎn)的筆法,形象地烘托出了神秀受皇室認(rèn)可的特殊的佛教地位。
其實(shí),這種通過細(xì)節(jié)刻畫人物形象的手法,在唐代塔銘、墓志類文章中極為常見,不僅僅是張說這樣的碑銘大家所獨(dú)有的寫作方法。正是受到了唐代同體裁文章的影響,朝鮮半島的塔銘也經(jīng)常使用細(xì)節(jié)描寫,而且在表現(xiàn)皇室禮敬高僧方面,半島作者的描寫甚至更為細(xì)致。例如:
(獻(xiàn)康大王)禮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手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緣,四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趨風(fēng)樹鳩列賀,六也;教國(guó)中磋磨六義者賦送歸之什,在家弟子王孫蘇判鎰榮首唱斂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樸邕為引而贈(zèng)行,七也;申命掌次,張凈室要敘別,八也。[1](10871)
這是崔致遠(yuǎn)在《有唐新羅國(guó)故兩朝國(guó)師教謚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中,敘述朗慧和尚面圣時(shí)所受到的極不尋常的禮遇。作者一連羅列了八項(xiàng)事例來突顯獻(xiàn)康大王對(duì)朗慧的優(yōu)禮:從國(guó)王親自為和尚供奉食物、傳香執(zhí)爐、締結(jié)世緣,到加贈(zèng)法號(hào)、命群臣慶賀,再到凈室送別、命文臣作賦送行等,都一一詳述出來,其筆觸之細(xì)膩,讓人驚嘆。在現(xiàn)存的16篇朝鮮塔銘中,我們幾乎都能找到詳盡描述國(guó)王禮敬高僧的細(xì)節(jié)。
當(dāng)然,細(xì)節(jié)描寫并不只限于高僧受到禮遇的情節(jié)中;在高僧學(xué)養(yǎng)方面,半島塔銘也傾向使用細(xì)節(jié)表現(xiàn)。例如:
(慧昭)謁神鑒大師,投體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頓受印契。[1](10865)
(云居道膺)大師謂曰:“曾別匪遙,再逢何早?”(利嚴(yán))對(duì)云:“未曾親侍,寧道復(fù)來?”大師默而許之,潛愜元契……謂曰:“道不遠(yuǎn)人,人能宏道。東山之旨,不在他人;法之中興,唯我與汝。吾道東矣,念茲在茲。”[1](11139)
(云居)謂曰:“戲別匪遙,相逢於此。運(yùn)斤之際,猶喜子來……所冀敷演真宗,以光吾道。保持法要,知在汝曹。”以此傳大覺之心,佩云居之印。[1](11146)
灌頂授記曰:“往欽哉。汝今歸本,曉悟迷津。激揚(yáng)覺海……”應(yīng)時(shí)豁爾,得未曾有。[1](7381)
——金獻(xiàn)貞《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并序》
以上都是師徒間的私下對(duì)話,如果不是塔銘作者在寫作前做了詳細(xì)了解,并且記述出來,后人則無從得知這么詳盡的對(duì)話細(xì)節(jié)。而這些詳實(shí)的談話記錄,無一例外地是在真切再現(xiàn)當(dāng)時(shí)的留唐學(xué)僧受中國(guó)老師高度認(rèn)可的場(chǎng)景。
三、前有“序”后有“銘”的章法行文特征
中國(guó)的塔銘,通常文體結(jié)構(gòu)是前有“序”,用以記敘高僧生平功德,可以說是一篇人物傳記;“序”后有“銘”,內(nèi)容是對(duì)高僧的褒揚(yáng),相當(dāng)于文末附上的頌詞。序文以駢體居多,銘文則一定是韻文。從現(xiàn)存文獻(xiàn)看,朝鮮半島塔銘也沿用了中國(guó)前序后銘的結(jié)構(gòu)方式,仿照唐文樣式,使用駢化的序文和韻體銘文。
我們先考察銘文。半島塔銘的銘文,常見的由四言、五言、七言古詩(shī)寫成,其中又以四言古體詩(shī)居多,如崔仁氵六兄的《新羅國(guó)故兩朝國(guó)師教謚朗空大師白月棲云之塔碑銘》:
至道無為,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粵惟正覺,誘彼群類。圣凡有殊,開悟無異。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水月澄心,煙霞匿曜。忽飛美譽(yù),頻降佳召。扶贊兩朝,闡揚(yáng)元教。瓶破燈明,云開月照。哲人去世,緇素傷心。門徒愿切,國(guó)主恩深。塔封巒頂,碑倚溪潯。芥城雖盡,永曜禪林。[1](10361)
這是一首古樸的四言古體詩(shī),概括了朗空大師一生的德業(yè)。類似的以四言詩(shī)為銘文的還有《高麗國(guó)原州靈鳳山興法寺忠湛大師塔銘》、《有唐新羅國(guó)故知異山雙寺教謚真鑒禪師碑銘并序》、《有晉高麗中原府故開天山凈土寺教謚法鏡大師慈鐙之塔碑銘并序》、《高麗國(guó)彌智山菩提寺故教謚大鏡大師無機(jī)之塔碑銘并序》、《高麗國(guó)溟州普賢山地藏禪院故國(guó)師朗圓大師悟真之塔碑銘》等。另外,《有唐新羅國(guó)故兩朝國(guó)師教謚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有晉高麗中原府故開天山凈土寺教謚法鏡大師慈鐙之塔碑銘并序》的銘詞是五言詩(shī),《大唐新羅國(guó)故鳳嚴(yán)山寺教謚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有唐新羅國(guó)故國(guó)師謚真鏡大師寶月凌空之塔碑銘并序》的銘詞是七言詩(shī)。值得一提的是,半島塔銘還有楚辭體和古體詩(shī)相結(jié)合樣式的銘文,如《新羅國(guó)武州迦智山寶林寺謚普照禪師靈碑銘》的銘辭:
禪心不定兮至理歸空,如活琉璃兮在有無中,神莫通照兮鬼其敢沖,守?zé)o不足兮施之無窮,劫盡恒沙兮妙用扉終。(其一)
有為世界,無數(shù)因緣。境來神動(dòng),風(fēng)起波翻。須調(diào)意馬,勤伏心猿。以斯為寶,施於后賢。(其四)
乘波若舟,涉愛河水。彼岸既登,惟佛是擬。牛車已到,火宅任毀。法相雖存,哲人其萎。(其五)
叢林無主,山門若空。錫放眾虎,缽遺群龍。惟余香火,追想音容。刊此真石,祀法將雄。(其六)[1](11135)
與銘文相比較,序文的史料和文學(xué)價(jià)值要更高一些。半島塔銘的序以駢文為主,間以散行單句。其駢體行文的特點(diǎn),最突出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
(一)四六句式,語言對(duì)偶
1.四四句式相對(duì):
命寄刳木,心懸寶洲。[1](10864)
焚葉為香,采花為供。[1](10865)
儀狀魁岸,語言雄亮。[1](10875)
2.六六句式相對(duì):
仍樓方便之門,果得摩尼之寶。[1](103594)
裨二主於兩朝,濟(jì)群生於三界。[1](10361)
灑法雨於昏衢,布慈云於覺路。[1](11133)
3.四四句與四四句相對(duì),組成兩個(gè)長(zhǎng)聯(lián):
今思前夢(mèng),宛若同符;始覺曩因,猶如合契。[1](11143)
雖云得月,指或坐忘;終類系風(fēng),影難行捕。[1](10864)
清眼界者,隔江遠(yuǎn)岳;爽耳根者,迸石飛湍。[1](10866)
4.四六句與四六句相對(duì),組成兩個(gè)長(zhǎng)聯(lián):
有學(xué)無學(xué),才嘗香缽之飯;二乘三乘,寧得藥樹之果。[1](7381)
甘泉忽竭,魚龍?bào)@躍其中;直木先摧,猿鳥悲鳴其下。[1](7382)
或聞異香,飛錫空而電奔;或觀瑞云,乘杯流而雨驟。[1](7382)
5.六四句與六四句相對(duì),組成兩個(gè)長(zhǎng)聯(lián):
先宴坐於松溪,學(xué)人雨聚;暫棲遲於雪岳,禪客風(fēng)馳。[1](11129)
遽裁熊耳之銘,焉慚梁武;追制天臺(tái)之偈,不愧隋皇。[1](11130)
以上是標(biāo)準(zhǔn)的駢偶句,屬對(duì)精切,韻律協(xié)和。此外,半島塔銘的駢偶句式還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等,這里不再舉例。
(二)使用典故
中國(guó)的駢體文在修辭上有用典的傳統(tǒng)。《文心雕龍·事類》中說:“事類者(即指用典),蓋文章之外,據(jù)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4](411)實(shí)際上,文章用典除了起到論據(jù)作用外,還能啟發(fā)人聯(lián)想,使文章語言簡(jiǎn)省,風(fēng)格典雅含蓄。朝鮮半島塔銘亦多使用典故,我們以下面數(shù)則為例,體會(huì)一下塔銘作者深厚的漢學(xué)功底:
西向陳倉(cāng),用顯霸王之道;今來寶地,將興法主之征。[1](11134)
不勞圯上之期,潛受法王之印。[1](11139)
爰切折梁之慟,亦增亡鏡之悲。[1](11141)
甘羅入仕之年,□窮儒典;子晉升仙之歲,才冠孔門。[1](11148)
“西向陳倉(cāng)”句,典故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5](2613)劉邦決意打回關(guān)中時(shí),使用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cāng)”之計(jì)。即在表面上命人搶修通往關(guān)中的棧道,以麻痹項(xiàng)羽的注意力,暗地里卻從陳倉(cāng)小路東進(jìn),劉邦與項(xiàng)羽爭(zhēng)霸天下的序幕由此開啟。“不勞圯上之期”句,典故出自《史記·留侯世家》。[5](2034)張良在下邳橋上遇一老者,老人故意將鞋丟落橋下,卻命張良取回。張良愕然,因見老人年邁,強(qiáng)忍怒氣取回鞋,并為其穿好。老人大笑,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與我會(huì)此!”后來老人果然授給張良一部書,上寫道:“讀此,則為王者師矣”。“亦增亡鏡之悲”句,典故出自《舊唐書·魏征傳》。[3](2561)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惋惜,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后世用“亡鏡之悲”比喻賢良逝世,國(guó)失棟梁。“甘羅入仕之年,□窮儒典”,典故出自《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5](2321)甘羅12歲就因功受封為上卿。“子晉升仙之歲,才冠孔門”,典故出自《列仙傳》。[6](65)子晉,為周靈王太子,因不滿靈王昏聵而出走。甘羅、子晉都是歷史上以才學(xué)見稱的著名人物。
從這些例句中使用典故的情況,我們可以感知到半島塔銘作者對(duì)于古代中國(guó)文史知識(shí)掌握之純熟。
四、結(jié)語
中國(guó)唐代文化的向外傳播,以朝鮮半島所受影響為最深。從大批派遣留唐學(xué)生,到大量輸入中華典章;從使用中國(guó)天文歷法,到采納唐朝的衣冠制度,半島接納唐文化可謂是不遺余力。半島塔銘的創(chuàng)作,就是中國(guó)佛家喪葬文化東傳的一個(gè)外在表現(xiàn),而其文章中所體現(xiàn)出的朝鮮佛教觀念、人物刻畫方法以及文體行文特征,更是帶有鮮明的中華文化影響的印痕。正是通過剖析半島塔銘的漢文化元素,我們才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古代中朝文化交流傳統(tǒng)之深遠(yuǎn)。
[1]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2]嚴(yán)耕望:《新羅留唐學(xué)生與僧徒》,《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
[3]劉晌,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4]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
[5]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6]王叔岷:《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責(zé)任編輯 梁浚]
K 312.877.45
A
1002-2007(2011)01-0013-05
2010-09-25
1.李谷喬,女,吉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講師,吉林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研究方向?yàn)榉鸲U與唐代文學(xué);(長(zhǎng)春 130117)2.李明非,男,東北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教授,研究方向?yàn)闁|北亞文學(xué)與文化。(長(zhǎng)春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