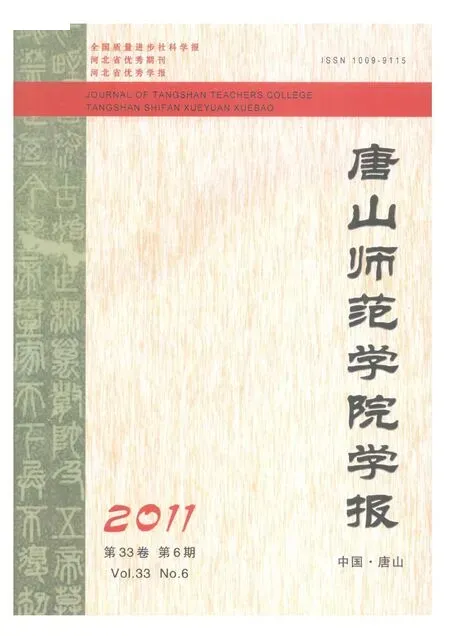關于《刑法修正案(八)》盜竊罪的幾個問題
仝其憲,李智利
(忻州師范學院 法律系,山西 忻州 034000)
關于《刑法修正案(八)》盜竊罪的幾個問題
仝其憲,李智利
(忻州師范學院 法律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將“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與“扒竊”從普通盜竊中分離出來,使之上升為行為犯,對其如何理解與認定,應窮盡已有的司法解釋,尋求其解釋的合理性與妥當性,并在此基點上探尋其立法精神與理由。
入戶盜竊;扒竊;攜帶兇器盜竊;解讀;立法精神與理由
《刑法修正案(八)》已頒行實施幾個月,此時對《刑法修正案(八)》的熱烈討論仍余音未盡。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是因為《刑法修正案(八)》的亮點頗多,值得一提的是對刑法第264條盜竊罪的修正:“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由此可以看出,對盜竊罪的修正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增設了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方式;其二,廢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其三,刪除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原有的兩種法定最高刑情節。特別關注的是“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作為行為犯首次上升為法律。對此如何理解與適用,其立法精神與理由是什么,諸如此類的問題是當前刑事理論界與司法實務部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擬展開較為深入細致的探究,冀希對我國的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一、“入戶盜竊”、“扒竊”與“攜帶兇器盜竊”之解讀應窮盡已有的司法解釋
對“入戶盜竊”、“扒竊”與“攜帶兇器盜竊”的準確理解,關乎到司法實踐中的正確定罪與量刑,甚至于影響到司法公正與社會秩序。新法剛剛頒行實施,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作為依據,有學者急切地期盼“兩高”作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兩高”的司法解釋本來已經洋洋灑灑千萬言之長了,解決新法帶來的實際問題,我們不能動輒就期望“兩高”的司法解釋給出答案,應根據已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釋尋求解決辦法,這種探尋問題的路徑無法實現時,才可冀希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實際上,“兩高”的司法解釋不可能也沒必要對刑法典的逐字逐條均作出較為明確的解釋。對此有學者不無深刻地指出,理論研究更應當關注如何增強刑法典條文的普適性,如何通過理論解釋來使刑法典保持持久、頑強、旺盛的生命力,而不能動輒求助于(或推責于)刑法典的修正或司法解釋。時代在發展,純粹理論推演中無法想象和難以預測的問題層出不窮。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全部等待和依賴刑法典的修正和司法解釋,更為可行的和負責任的方式是對刑法典進行與時俱進的擴張解釋[1]。因而我們應首先從已有的相關司法解釋尋求較為妥當的答案。
對“入戶盜竊”、“扒竊”與“攜帶兇器盜竊”的理解,筆者認為完全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搶劫罪”的司法解釋。擬歸納為以下理由作為支撐:(1)因為盜竊罪與搶劫罪均屬于侵犯財產罪的范疇,兩罪的犯罪目的均是非法取得他人的財物,侵犯的主要客體均是公私財物所有權。通常認為,搶劫罪是侵犯財產罪中最嚴重的一個罪,是以暴力、威脅等方法致被害人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無法反抗的程度,當場取得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盜竊罪一直是侵財類犯罪中發案率最高的犯罪,是采取“平和手段”秘密方法取得公私財物的行為。一般認為搶劫罪遠遠重于盜竊罪,在某些方面重罪可以統領輕罪,按照刑事法中通常的“就上不就下”原則,可以參考“搶劫罪”的司法解釋得出對“入戶盜竊”、“扒竊”與“攜帶兇器盜竊”的恰當解釋;(2)最高人民法院如果對類似情形再出臺司法解釋,明顯多余,同時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3)參照已有的司法解釋能夠達到合理的法律效果,沒有必要再出臺新的司法解釋,也不利于罪刑之間的協調性;(4)出臺過多的司法解釋,不利于公民的掌握與適用,更不利于公民的遵守,有礙于公民對法律的忠誠與信仰;(5)事無巨細、過分繁雜的司法解釋有違法律應具有的簡練性、抽象性、概括性與原則性品質;正如意大利刑法學家菲利所言:“法律總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疏和不足,因為它必須在基于過去的同時著眼于未來,否則就不能預見未來可能發生的全部情況。現代社會變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經常修改也趕不上它的速度。”[2]由此,從終極意義上說,在現代社會中,不可能存在完備而自足的法律;(6)過分明確細致的司法解釋意味著僵化,適用起來更為狹窄、更是漏洞百出,在粗疏與細密之間應尋求一個恰當的平衡點,力圖達到刑法的明確性、協調性與相對完備性[3],這才能解決實際問題;(7)汗牛充棟的司法解釋也無法窮盡紛繁多變的社會生活,期望司法解釋能夠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永遠都是一種奢望;(8)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有“對于入戶盜竊,因被發現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入戶搶劫’的司法解釋,由此可以看出,“入戶盜竊”參照“入戶搶劫”做相應的解釋有法律依據,也能夠保持法律概念之間的協調性。基于上述認識,筆者認為對“入戶盜竊”、“扒竊”與“攜帶兇器盜竊”的理解與認定,完全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搶劫罪”的司法解釋,無須再作出權威性的司法解釋,這樣也有利于罪與罪之間的協調性,有效地保護法益。
二、“入戶盜竊”之解讀
關于“入戶盜竊”的理解與認定,參照 2000年 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入戶搶劫”的解釋。以此可以推理出,所謂“入戶盜竊”是指為實施盜竊行為而進入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隔離的住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的漁船、以車為家的汽車、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進行盜竊的行為。
在認定“入戶盜竊”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戶”的范圍。“戶”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征,后者為場所特征。一般情況下,集體宿舍、旅店賓館、臨時搭建工棚等不應認定為“戶”,但在特定情況下,如果確實具有上述兩個特征的,也可以認定為“戶”。二是“入戶”目的的非法性。進入他人住所須以實施盜竊犯罪為目的。盜竊行為雖然發生在戶內,但行為人不以實施盜竊等犯罪為目的的進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戶內臨時起意實施盜竊的,不屬于“入戶盜竊”。三是盜竊行為必須發生在戶內。上述三個條件同時具備才能認定為“入戶盜竊”。由此可以判斷,進入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辦公場所以及公共娛樂場所盜竊的,因為它不符合上述“戶”的范圍,不屬于“入戶盜竊”。如果將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辦公場所以及公共娛樂場所等的一個部分作為家庭生活而居住并具有相對封閉性,而進入其內實施盜竊的,由于它契合了上述“戶”的功能特征與場所特征,筆者認為,應屬于“入戶盜竊”。
需要指出,“入戶盜竊”中行為人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復合行為,即入戶行為和盜竊行為是具有牽連關系的兩個行為,也就是說,入戶的目的就是為了實施盜竊,入戶是實施盜竊的必經階段。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非法入戶實施盜竊構成“入戶盜竊”的情形,在刑法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并無爭議與歧義。但有以下幾種情形值得注意:一是對于合法入戶時并無盜竊犯罪的動機,而是臨時起意實施盜竊是否構成“入戶盜竊”呢?筆者認為,根據上述的有關司法解釋與“入戶盜竊”的認定條件,不應構成“入戶盜竊”,因為“入戶”的目的不具有非法性,可以按普通盜竊處理;二是對于事先就有盜竊犯罪的動機,行為人憑借特殊身份或以合法理由入戶實施盜竊犯罪,筆者認為應認定為“入戶盜竊”,雖然行為人是以所謂的“合法”形式入戶的,但是他入戶的目的具有非法性;三是對于行為人事先具有搶劫的動機而入戶的,由于出現被害人熟睡或不在家等情形,轉而實施盜竊犯罪的,因為具有入戶目的的非法性,根據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認定為“入戶盜竊”;四是對于行為人基于盜竊犯罪的目的而入戶,之后卻實施了搶劫的,應構成“入戶搶劫”而不是“入戶盜竊”;五是對于行為人基于盜竊犯罪的目的而入戶實施盜竊犯罪,之后被發現,行為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內,這種情形下,應認定為“入戶搶劫”而不予認定為“入戶盜竊”。那么,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外,這種情形下,根據上述的司法解釋,只成立“入戶盜竊”,而不屬于“入戶搶劫”。
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將“入戶盜竊”作為行為犯,不以“數額較大”為構成要件,直接作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其立法精神與理由,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行刑法已將“入戶搶劫”規定為搶劫罪的加重情節,雖然“入戶盜竊”的嚴厲性和危害性不如“入戶搶劫”,但它比“入戶搶劫”發案率高,更為常見多發,嚴重危害了人們家庭生活的安寧,將“入戶盜竊”上升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旨在從嚴懲處那些膽大妄為、有恃無恐而嚴重危及公民生活、工作安全的犯罪分子[4];二是隨著人權保障的意識日益深入人心,人們更加注重個人的生活空間的安全感,人們往往將家庭生活作為享有自由權利和隱私權的“避風港”。“入戶盜竊”除了侵害他人的財產利益之外,還侵害了人們家庭生活的安寧,使人們喪失了生活的安全感,對此人們反響強烈;三是“入戶盜竊”實際上是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盜竊罪復合形態,根據刑法基本理論,應擇一重罪處罰,盜竊罪的法定刑高于非法侵入住宅罪,而較為輕緩的非法侵入住宅罪早已成為刑法上的一個獨立罪名,相比之下,“入戶盜竊”更具有可罰性,將它上升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有利于罪刑之間的協調性;四是“入戶盜竊”與普通盜竊相比,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一般來說,“戶”的特點具有封閉性、孤立性、自我保護性與外界關系疏遠性等,也契合了西方人所說的“風也可以進,雨也可以進,惟獨國王不可以進”的特質,因而,對于“戶”外界因素不能輕易介入。就“入戶盜竊”而言,行為人作案難度較大,其動機較為明確,對危害結果的追求較為熱烈,顯示出犯罪意識的堅定與執著,因而其人身危險性較大;五是“入戶盜竊”過程中,一旦被被害人發現,常常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脅,轉化為“入戶搶劫”,使被害人孤立無援、陷入十分危險境地,其后果不堪設想。為此,對“入戶盜竊”作為行為犯懲處,有利于減少此類犯罪的發生,相應的防止了更為嚴重的犯罪升級。
三、“扒竊”之解讀
關于“扒竊”的理解,根據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對于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參考現行刑法第291條對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規定。筆者認為,“扒竊”是指行為人在公共場所秘密竊取他人隨身財物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扒竊”,應注意把握以下幾個方面:(1)其作案地點是公共場所。對公共場所的理解為供人休息、活動、休閑、游玩等的場所,例如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以及旅客列車、船只、各種公共汽車、大中型出租車、飛機等正在營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其他公共場所,其主要特征是往來的不特定人較多;(2)其作案對象往往是不特定的人們隨身攜帶的現金或物品;(3)其行為方式是行為人一般徒手作案或借助刀片、小鑷子等小型工具作案。具備以上情形的,應認定為“扒竊”。
上述的司法解釋把“多次盜竊”與“扒竊”規定在同一個法條中即第四條中,兩個概念交織在一起,很明顯具有包容關系。而《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把“扒竊”作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那么,如何界定“多次盜竊”與“扒竊”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對此應從上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于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的司法解釋說起。對“多次盜竊”的理解,刑法理論與實務界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多次盜竊”因司法解釋的限定而又有了較為固定的含義,它所指的盜竊行為必須是入戶盜竊或在公共場所扒竊,如果盜竊不是在戶內或公共場所,則不能累計計算盜竊次數[4]。此觀點基于對司法解釋的嚴格解釋與文理解釋所得出的,為很多學者所贊同;另一觀點認為,“多次盜竊”中的“盜竊”,不應僅僅是指“入戶盜竊”和“在公共場所扒竊”兩種形式,其還應包括其他形式的盜竊在內。只是其他形式的盜竊,要達到成立犯罪的“多次盜竊”的程度,也應當比照上述《解釋》的第四條的規定,至少要達到“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的社會危害程度,否則就難以作為盜竊罪處理[5]。可以看出,此觀點是基于對司法解釋的論理解釋所得出的,近期有學者所倡導。筆者認為第二觀點較為可取,因為它能夠較為妥當的解決實際問題。《刑法修正案(八)》把盜竊罪的行為方式規定為盜竊財物數額較大、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與扒竊等五種行為方式,如果按照上述觀點一的主張,“多次盜竊”的行為方式僅指入戶盜竊和扒竊,而《刑法修正案(八)》卻把入戶盜竊和扒竊從“多次盜竊”中剝離出來,三者成為并列形式,按照上述觀點一的主張,“多次盜竊”就名存實亡了,這與《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模式不相符合。但按照第二種觀點的主張,上述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把入戶盜竊和在公共場所扒竊剝離出來,因為“多次盜竊”還包括其他形式,其仍然存在,這樣便與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模式相吻合。
對于“扒竊”的立法精神與理由,筆者認為,一方面,在公共場所扒竊的行為,針對的是不特定人的財產利益,同時嚴重地擾亂了社會秩序,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扒竊分子時常糾集他人、流竄多地、橫行鄉里,嚴重侵犯了人們的財產利益,也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秩序,擾亂了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由于這種滋擾群眾行為的個案難以達到“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的社會危害程度而不構成犯罪,而行政處罰因處罰力度不夠并不湊效,即使以“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成立犯罪追究刑事責任,也關不了多長時間,回歸社會后重新犯罪的幾率更高[6];另外,對于大多數扒竊分子由于作案持續時間長、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已經養成了好逸惡勞、好吃懶做與揮霍無度的習癖,其人身危險性較大。據此,增設“扒竊”作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有利于從嚴打擊此類犯罪,有效地保護法益。
四、“攜帶兇器盜竊”之解讀
關于“攜帶兇器盜竊”的理解與認定,筆者認為,同樣可以參照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和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補充規定對“攜帶兇器搶奪”的解釋。據此,所謂“攜帶兇器盜竊”是指行為人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盜竊或者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器械進行盜竊的行為。“攜帶兇器盜竊”的認定,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字義上來說,“攜帶”,《漢語大辭典》中解釋為“隨身帶著”;“兇器”,解釋為“行兇用的器具”,那么,“攜帶兇器”一詞可以解釋為“隨身帶著行兇用的器具”。根據相關司法解釋,這里的“兇器”是指槍支、匕首、刮刀等管制刀具,以及具有一定殺傷力的菜刀、斧頭等器具[7]。筆者認為,不應明確的框定“兇器”的范圍,上述殺傷力較強的器具當然應認定為“兇器”,但作為日常使用的菜刀、水果刀等物品,甚至一根普通的棍子、繩索、石塊等均可以視為“兇器”。那么,判斷這些器具是否屬于“兇器”,應從具體案件來考量,行為人是否將所攜帶的器具產生了兇器的用途,并用于所侵害的目標,是否對侵害目標構成現實的人身威脅;二是依據刑法上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在主觀上行為人必須對自己攜帶兇器盜竊有明確的認識,意識到自己是在攜帶兇器實施盜竊;在客觀上行為人攜帶兇器進行了盜竊,也就是說,攜帶兇器屬于盜竊行為的附隨情形。這樣,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夠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如果行為人在主觀上認識到自己是在攜帶兇器盜竊,但客觀上并沒有實施盜竊行為,就不能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否則,屬于主觀歸罪。相反,如果行為人在客觀上實施了盜竊行為,而主觀上并沒有認識到自己是攜帶兇器,也不能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否則,有客觀歸罪之嫌;三是根據上述司法解釋,行為人隨身攜帶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以外的其它器械盜竊,但有證據證明該器械確實不是為了實施犯罪準備的,不易以“攜帶兇器盜竊”定罪;四是行為人將隨身攜帶兇器有意明示或暗示,能為被害人察覺到并構成威脅的,直接適用刑法第263條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五是行為人攜帶兇器盜竊后,在逃跑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脅的,適用刑法第269條轉化型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對于“攜帶兇器盜竊”作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其立法精神與理由,筆者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行刑法中將“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本法263條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而“攜帶兇器盜竊”與“攜帶兇器搶奪”相比,一般來說,其嚴重性前者稍弱于后者或者幾乎相當。但依據現行刑法規定,對于“攜帶兇器搶奪的”轉化為最為嚴重的搶劫罪處罰,而“攜帶兇器盜竊”只有達到“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才能成立犯罪,否則,不以犯罪論處。由此可以看出,兩者處罰差別很大,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與各罪之間的協調性。《刑法修正案(八)》將“攜帶兇器盜竊”作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較好地解決了上述矛盾;二是在“攜帶兇器盜竊”中,一定程度上強化與堅定了行為人的作案心理,在此強烈的心理支配下促使其排除一切障礙,將犯罪進行到終點,因而其社會危害性較大;三是在“攜帶兇器盜竊”中,行為人在主觀上就有使用“兇器”的可能性,因而,當被被害人發現時,其行為往往轉化為搶劫,造成的危害后果更為嚴重。《刑法修正案(八)》將“攜帶兇器盜竊”作為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之一,將犯罪行為扼殺于初始階段,更有利于保護法益。
[1] 于志剛.危險駕駛行為的罪刑評價——以“醉酒駕駛”交通行為為視角[J].法學,2009,(5):23.
[2] 恩里科·菲利.犯罪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125.
[3] 張明楷.妥善處理粗疏與細密的關系,力求制定明確與協調的刑法[J].法商研究,1997,(1):15.
[4] 夏強.搶劫罪三題探微[J].當代法學,2001,(4):63.
[5] 董玉庭.盜竊罪客觀方面再探[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1,(3):52.
[6] 黎宏.論盜竊罪中的多次盜竊[J].人民檢察,2010,(1):24.
[7] 宋洋.《刑法修正案(八)》有關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立法完善之解讀[J].中國檢察官,2011,(3):41.
[8] 高銘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74.
(責任編輯、校對:王學增)
On Theft in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8)
TONG Qi-xian, LI Zhi-li
(Department of Law, Xinzhou Normal College, Xinzhou 034000, Chin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8) will separate indoor theft, a theft with lethal instruments and pickpockets from normal theft. And make them up for behavioral offence. How to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it, people should end the existing judicial explanation, seek the rationality of their explanation, and explore the legislative spirits and reasons on this basis.
intruding into another person residence to theft; a theft with lethal instruments; pickpockets; explanation; legislative spirits and reasons
2011-09-13
仝其憲(1974-),男,河南臺前人,碩士,忻州師范學院法律系講師,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犯罪學。
D924.36
A
1009-9115(2011)06-0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