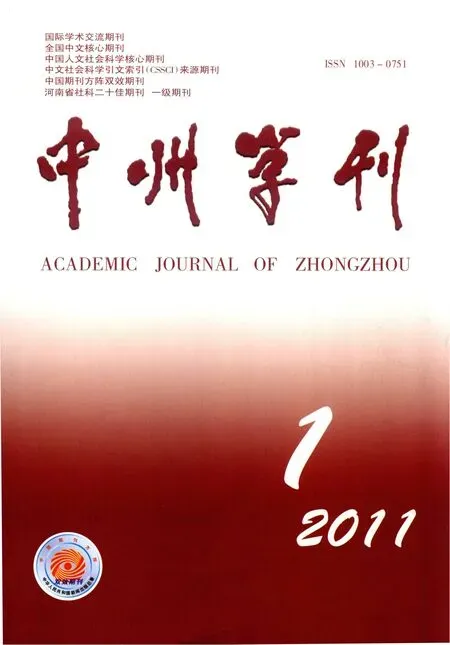《儒林外史》創作動因的思想史考察
王春陽
《儒林外史》創作動因的思想史考察
王春陽
清初興起的學術批判思潮是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的學術背景,在反理學的內在要求下,吳敬梓完成了《儒林外史》的創作。反理學作為一條明確的思想線索貫穿始終,統攝全篇。吳敬梓反理學思想的形成明顯受到顧炎武、黃宗羲和北方顏李學派的影響,從其交游情況來看,對他影響最大的當屬程廷祚。
《儒林外史》;創作動因;反理學
關于《儒林外史》的創作動機,除了“名利”、“泄憤”、“勸懲”、“炫才”、“醒世”、“救世”這幾種說法外,亦有論者將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的動機作為一個動態過程進行分析,認為“在《儒林外史》的整個創作過程中,不存在一個固定不變、一以貫之的動機,相反,吳敬梓的創作動機是處于不斷變化發展之中的”①。作為一部獨立創作的藝術性極強、內容豐富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存在多個創作動機不足為怪,但是認為吳敬梓創作中“不存在一個固定不變、一以貫之的動機”則值得商榷。如果我們結合吳敬梓的人生經歷和其所處時代,從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不難看出,清初的學術思潮,特別是反理學思潮對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有著深刻的影響。
一、清初的反理學思潮與《儒林外史》的創作
理學是從北宋時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學術體系,是宋明學術的核心。它以開放的姿態融合了佛、道的積極因素,成為符合當時時代要求的理論形態,是中國儒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從南宋末年開始,理學體系中的程朱理學逐漸受到統治者的青睞。后來,元、明兩代也都多方表彰程朱理學,并將朱熹學說定為科舉取士的依據,程朱理學在政治上取得了獨尊的地位。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被統治階級所提倡,充分說明了其在理論思維方面所達到的高度,體現了學術對社會變化的深刻反映,但是學術與政治合流,學術就不可避免地淪落為政治的工具。為了政治的需要,學術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經常遭到支解,程朱理學的命運也不例外。自從程朱理學被統治階級定為官方哲學以后,其政治依附性逐漸增強,而其學術獨立性卻日漸式微,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為人們思想發展的桎梏。到了明朝中后期,嚴重的社會危機此起彼伏,僵化的程朱理學因為沒有隨時代發展而發展,所以很難承擔起解決這些危機的重任。王陽明從挽救明王朝政治危機的意愿出發,起而發揚陸九淵的“心即理”思想,主張“圣人之學心學也”②,并與佛教禪學相結合,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學說。王陽明的學說大大發展了程朱的理學思想,為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明朝思想界的活躍和發展。雖然心學是濟理學之窮的一個更為開放的理論系統,為當時的思想解放潮流打開了閘門,但心學無限夸大人的主觀精神的作用,將人們的注意力進一步引向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助長了明代后期不務實際學風的盛行。
明清易代后,滿族入主中原,在人口數量和文化上占據優勢地位的漢民族處于被滿族統治的尷尬地位。特別是清政權入主中原之初采取的一系列比較激進的措施,給漢族知識分子心靈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在痛定思痛中,他們試圖尋找明代滅亡的原因。清初的知識分子多是從文化的原因來闡釋社會政治問題,認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③,把宋明理學清談空疏學風看做使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批判在清初學術界成為一股思潮,這是清初知識分子整體思考結果的反映。對此,杜國庠評價說:“在中國學術史上,明清之交……這個時代之所以重要,是它總結了五百年的所謂理學,而完成這一任務的,則為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人。經過他們的批判,理學是決定的終結了,絕沒有死灰復燃的可能。”④理學在清初受到學術界的清算和批判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理學是否終結卻值得商榷。從歷史的邏輯看,在清初,由于諸多原因,理學的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在形式上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說明。
第一,理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一方面,理學在幾百年的發展中已經成為社會法則,在社會生活和宗法倫理中占有指導地位,作為一種習慣勢力,理學在當時的社會中仍有強大的影響力。朱彝尊說:“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顏李學派的開創者李塨亦發出了“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的感慨。另一方面,理學作為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是中國古代理論思維的一個高峰,任何要取代它的學術體系都面臨著超越它的理論困難。如果不能超越程朱理學所達到的思維高度,就很難真正得到知識分子的青睞。即使批判理學最為用力的顏元也承認:“談學論史輒抑宋之迂儒腐相,而力闡唐、虞之府事修和,周、孔三物習行,一啟口而謗詈遂成。以王法乾、張仲誠之賢,動成交壘,路驤皇抱王佐大略,亦煩辨商。”⑤
第二,統治者大力提倡理學。清初經過近40年的發展,在形式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滿漢民族矛盾,并完成了在清朝中央政權控制下的祖國統一。隨著政治的逐步穩定,清政權文化控制力不斷增強,明清更迭時期那種極端自由的學術氛圍已經不存在了。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康熙帝最終選擇了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康熙五十一年(1712),他把朱熹在孔廟從祀的地位大大升格,由東廡的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的“十哲”之一。他詔令當時的理學名臣李光地、熊賜履等編定《性理精義》,還刊刻了《性理大全》、《御纂朱子全書》等書籍。他把程朱理學抬到了超越孔孟的地位,在為《朱子全書》所作的序中說朱子“集大成而紹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之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學,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開天下,白明德而止于至善,無不開發后人而教來者也……非圣人復起,必不能逾此”。在最高統治者的推崇下,學術風氣大為改觀,出現“宗朱子為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⑥的局面,以至于“世儒習氣,敢于誣孔孟,必不敢非程朱”⑦。因此有學者認為:“康、雍、乾三代完成了有明一代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即真正確立程朱理學的一尊地位,把皇帝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推向極端。”⑧
因此,理學雖然在清初遭到一大批學者的批判,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批判理學的任務并沒有完成。但在統治者尊崇理學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下,學界對理學的批判形式不得不發生變化。清初那種對理學明目張膽、大張旗鼓的批判形式是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隱性的、曲折的批判形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和政府的文化政策發生正面的激烈沖突,既能達到批判的目的,又能保證學者自身的安全。
作為經學家的吳敬梓,正是在反理學的內在要求下,借助文學創作這一方式來完成批判理學的重任的。因此,“《外史》的取境與立意不再跟著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或民間市井心理走了。它的出現是士人覺醒這個歷史進程孕育出來的”⑨。所以,“曹雪芹更屬于藝術家的氣質;而吳敬梓,相對說來,更帶有思想家的氣質”⑩。這也是吳敬梓的好友程晉芳對其為何創作《儒林外史》十分不解的原因:“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11]
二、《儒林外史》的反理學內蘊
《儒林外史》中具有強烈的的反理學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質疑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神圣性、權威性。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備受清朝統治者的推崇,儼然成為理學的代表和化身,在當時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吳敬梓卻通過人物對答的形式,質疑朱熹的權威性、神圣性。如:
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后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后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12]
吳敬梓在此僅將朱熹歸結為諸儒中的一家,將其放在了和其他儒家學派同等的地位,這在當時是需要極大勇氣的。
2.揭露在政治控制下理學的殺人本質。在政治的干涉下,理學逐步變成了統治者維護其利益的文化工具,成為禁錮人們思想行為的利器。這一代表人物是徽州府秀才王玉輝。作為一介寒士,他連自己女兒也養活不來,一生卻偏只有一個志向,就是要“纂《禮書》、《鄉約書》來嘉惠來學,勸醒愚民”。當女兒要自殺殉夫,其他人都力勸存活要緊之時,只有他在理學倫理思想的支配下極力支持說:“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這樣做罷。”[13]但女兒自殺以后,受到政府表旌,建祠立坊,為封建“倫紀”生色時,王玉輝卻倍感心傷,熱淚直滾。王玉輝言行的矛盾、內心的掙扎,表達了吳敬梓對理學殺人本質的控訴。
3.揭露政治控制下程朱理學的虛偽性。在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倫中,“信”由朱熹大力提倡并作為理學的重要倫理基礎。但是,理學的具體承載者,卻大多是言行矛盾的偽君子。嚴貢生就是明證,他一邊吹噓自己“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一邊橫行鄉間,欺壓百姓,即便是自家兄弟的財產也要占為己有。出身貧苦的匡超人是另一個典型,父親在臨死之前還諄諄教導他說:“僥幸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14]這樣一個本性質樸的人,最后亦蛻變為一個言而無信、坑蒙拐騙的無恥之徒。而翰林院侍讀高老先生對杜少卿父親的一段評價更說明了當時士人群體的集體虛偽:
與新時期長江流域監督形勢相對應的是,質量監督工作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等問題凸顯,長江流域監督管理存在幾個方面的突出問題,監督工作亟待進一步發展:一是體制機制要進一步完善,新時期的監督工作對人員數量、素質的要求更高,急需新增一批具備綜合性、專業性的人才隊伍投入長江流域監督崗位上來,同時制度也需要進一步優化以適應新時期監督工作的需要。二是工作方式要逐步創新,對不同類型的工程項目,采取有側重的方式監管,實行質量分類和差別化管理,做到因地制宜。三是監管方式要與時俱進,對線性工程要采取信息化手段開展監控式管理,實行遠程監督。
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呆子: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里的辭藻,他竟拿著當了真。[15]
這種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充分揭示了依附于政治的理學的虛偽性。
4.批評理學的空虛無用。明初靖難之變中的方孝孺以死殉節,即便現在也被視為忠于國家、忠于氣節的殉道者,具有正面的積極意義,傳統價值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譽方孝孺為“忠節奇儒”。方孝孺在封建社會具有很高的道德意義,但吳敬梓卻顛覆了這種價值評判。他借杜慎卿之口說:“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皋門雉門怎么!這人服斬于市,不為冤枉的。”而對斬殺方孝孺的朱棣卻大加褒獎:“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著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16]吳敬梓這種驚世駭俗之論,正是對理學空虛無用的批判,也是其渴望學術負有經世之責的具體體現。
5.批判科舉制度的弊端。科舉制度作為一種人才選拔方式,本身有其合理性,吳敬梓之所以批判科舉制度,是由于在明清科舉考試中,將考試內容局限于程朱注疏的狹小范圍,由于內容的禁錮,使科舉制度逐步失去了活力,其結果不是選拔人才而是摧殘人性。范進、周進二人,因為科場屢屢失利,精神上受到了折磨,處于非正常的瘋癲狀態。而深在閨閣的大家閨秀魯小姐,由于夫君不熱衷科舉而郁郁寡歡,長吁短嘆:“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17]魯小姐的父親也因為此女婿的“不務正業”而差一點丟掉性命。
三、吳敬梓反理學思想的形成過程
吳敬梓出身于一個“家聲科第從來美”的科舉世家,本人也是八股制藝的高手,程朱理學的尊奉者,至少在其移家南京之前,他還是沉浸在理學之中,極力走科舉仕途之路,甚至為了博取功名,不惜演出一幕“匍伏乞收”的丑劇。所以,在吳敬梓移家南京之前,他并沒有明確的反理學思想。吳敬梓反理學思想的形成是一個過程,主要緣于自身生活的變化。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使吳敬梓對社會人生進行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家庭的敗落和科舉仕途的失意,使吳敬梓具有了一些挫敗感,再加上鄉人對其敗家的歧視和指責,吳敬梓舉家遷到南京。南京是當時南方的學術中心,思想極其活躍,又遠離北京政治中心,文化環境相對輕松,反理學思想相對濃厚。在這里,吳敬梓接受到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經世致用思想,并逐漸受其影響。新舊思想的碰撞,使吳敬梓對自己以往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個反思的參照。他對科舉制度和程朱理學進行了深入思考并有了新的認識,自己的思想也逐漸改變,最后脫離了程朱理學的桎梏,走上了政治批判的道路。
可見,吳敬梓移家南京后,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交游范圍的擴大,特別是通過和程廷祚的交往,使他了解并接受了顏李學派的思想,繼承了顏李學派的反理學精神。吳敬梓和當時許多學者一樣,自覺扛起了反理學的大旗。在這種歷史使命感的驅使之下,除了以“治經”這種方式批判理學以外,吳敬梓還開始了《儒林外史》的創作,試圖通過文學創作形式,以傳統的文以載道形式來表述自己的反理學思想。因此,他借助于自己所熟悉的素材,用反理學這一條明確的思想線索統攝全篇,構成了《儒林外史》那種嚴謹、獨特而又和諧統一的連環短篇結構,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描下了濃重的一筆。
注釋
①謝艷麗:《〈儒林外史〉創作動機新探》,《文教資料》2008年第3期。②王陽明:《陸象山全集序》,《四庫備要》,中華書局校刊本。③陸隴其:《陸稼書文集》,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1頁。④杜國庠:《杜國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7頁。⑤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541頁。⑥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卷一,《四庫備要》,中華書局校刊本。⑦陳確:《陳確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432頁。⑧⑨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0、5頁。⑩何滿子:《吳敬梓是對時代和對他自己的戰勝者》,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270頁。[11][20]朱一玄、劉毓忱:《〈儒林外史〉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29、191頁。[12][13][14][15][16][17]吳敬梓著,張慧劍校注:《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57、497、185、356、310、124頁。[18][19]戴望:《顏氏學記》(二),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97頁。
責任編輯:一鳴
I206.2
A
1003—0751(2011)01—0212—03
2010—10—18
王春陽,男,南陽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南陽47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