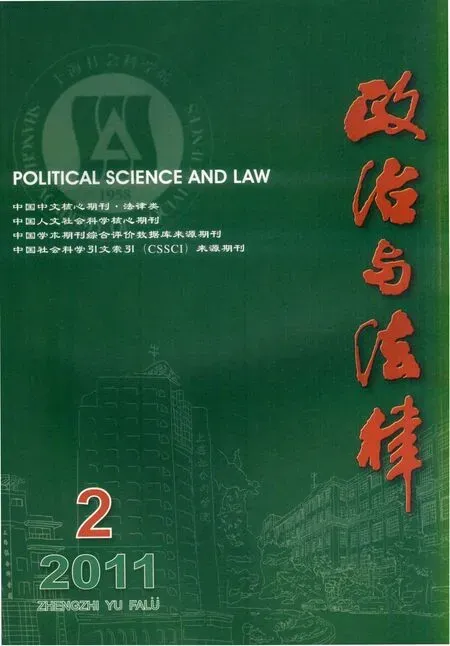英國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的構(gòu)造與借鑒
周新
(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北武漢430072)
嚴(yán)格責(zé)任是英美刑法中的一種獨特責(zé)任形式。據(jù)英國學(xué)者統(tǒng)計,英國刑法中總共存在8000多種犯罪,其中一半多的犯罪為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從組成上看,在這8000多種犯罪中,大約540種犯罪為嚴(yán)重犯罪;在嚴(yán)重犯罪中,123種犯罪涉及到嚴(yán)格責(zé)任因素,許多犯罪可以判處監(jiān)禁刑。1可見,嚴(yán)格責(zé)任在英國刑法刑事責(zé)任中具有重要地位。實際上,各個英美法系國家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地位和具體內(nèi)容并不完全一致,然而我國刑法學(xué)界卻普遍對此認(rèn)識不足。本文擬以英國判例法為基點,考察嚴(yán)格責(zé)任的本體構(gòu)造,并在此基礎(chǔ)上對我國刑法中有關(guān)的爭議問題進(jìn)行分析,為進(jìn)一步深化比較研究拋磚引玉。
一、對英國刑法有關(guān)嚴(yán)格責(zé)任重要判例的解讀與分析
眾所周知,英國刑法屬于判例法,要弄清楚英國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的構(gòu)造,脫離具體判例無疑會在方法論上存在缺陷。在英國刑法中,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從類型上可以分成普通法犯罪和制定法犯罪。無論普通法犯罪還是制定法犯罪,都是通過判例來發(fā)展刑法有關(guān)規(guī)則的。
(一)1979年的Lemon and Whitehouse V.Gay News案
該案是普通法犯罪(瀆神罪)在嚴(yán)格責(zé)任方面的現(xiàn)代判例。本案中,一本名為“Gay News”的雜志刊載了一首關(guān)于耶穌生前所謂的同性戀行為和死后與其尸體發(fā)生同性戀行為的詩,該雜志的編輯和出版者受到了指控,指控理由是他們觸犯了普通法上的瀆神罪(blasphemy),最終,兩人被認(rèn)定為有罪,兩被告提起上訴,上議院駁回了該上訴。上議院認(rèn)為,無論被告是否意在瀆神,危害后果已經(jīng)由故意出版發(fā)行的行為而產(chǎn)生了。2當(dāng)該作品具有使基督教徒震驚并憤怒的傾向時,該寫作就是瀆神行為。至于編輯和出版商,只要出版了該作品,就構(gòu)成了犯罪,這正如屠夫在不知道肉是變質(zhì)的情況下賣出了不適合人類食用的肉一樣,同樣構(gòu)成了犯罪。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該犯罪是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
事實上,除了瀆神罪之外,普通法上的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還包括公共滋擾罪(publ ic nuisance)、蔑視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 t)、各種刑事誹謗罪(criminal l ibel)和觸怒公共道德罪(out raging public decency)。4普通法上的現(xiàn)代判例,在公共滋擾罪方面有1993年的Shor rock案,在蔑視法庭罪方面有1954年的Evening Standard Co.Ltd案,在觸怒公共道德罪方面則有1990年的Gibson案。盡管在現(xiàn)代英國刑法中,控方已經(jīng)很少根據(jù)上述普通法罪名而提起指控,但是它們客觀上仍然存在。5
(二)1846年的Woodrow案
該案是制定法犯罪中適用嚴(yán)格責(zé)任的第一起案件,確立了否定犯意的事實錯誤不能成為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辯護(hù)理由的規(guī)則。本案中,被告被指控出售變質(zhì)的牛奶,但被告辯稱,自己以為牛奶是沒有問題的;法院認(rèn)為,在犯罪成立方面,被告這種否定犯意的事實錯誤在認(rèn)定是否構(gòu)成該罪上是無關(guān)的,控方只要證明被告出售了牛奶并且該牛奶是變質(zhì)的就可以了。
此后,在英國刑法的現(xiàn)代判例中,根據(jù)1972年的Alphacel l V.Woodward案,被告被認(rèn)定成立了1951年的《防止污染法》所規(guī)定的犯罪。在該案中,被告造成了河水的污染,法院認(rèn)為,被告不知道污染正在發(fā)生并且錯誤地相信其過濾系統(tǒng)仍在有效運轉(zhuǎn)的認(rèn)識,不能成為免責(zé)理由。在1984年的Wrothwel l Ltd V.Yorkshire Water Authority案中,被告錯誤地認(rèn)為其工廠的排水管是與公共排污管相通的,實際上,該排水管與附近的一條河流相通,法院認(rèn)為,這種認(rèn)識不足以對抗控方,因為該罪是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6
(三)1875年的Prince案
該案是有關(guān)被害人年齡判斷上適用嚴(yán)格責(zé)任的典型判例。本案中,被告誘拐了一名幼女,該幼女告訴被告她已18歲,她同意與被告一起離家出走。被告相信了她的話,并帶走了她。被告被認(rèn)定有罪,法院認(rèn)為,被告不知道幼女的年齡在16歲以下的事實與犯罪成立無關(guān),因為該罪在這方面不要求犯意。
在1998年的B V.DPP案中,一個15歲少年坐在一個13歲女孩旁邊,并要求她為其口交,該男孩被認(rèn)定犯有嚴(yán)重猥褻不滿14歲兒童罪(gross indecency on chi ld under the age of 14),根據(jù)一審法院和上訴法院所作的法律指導(dǎo),這是一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被告人相信女孩的年齡超過了14歲不是本罪的辯護(hù)理由。7被告提出上訴,2000年,上議院一致接受了被告的上訴,并指出,當(dāng)議會沒有指明要求主觀要素時,并不一定意味著犯罪是嚴(yán)格責(zé)任的以及真實的相信不能成為辯護(hù)理由。Hut ton勛爵指出,Prince案是一個“已經(jīng)消失且不一去不復(fù)返時代的遺跡”,在以后可以被“忽視”。上議院認(rèn)為控方必須證明被告知道或者對被害人不滿14歲持輕率態(tài)度。這一判決在嚴(yán)格責(zé)任方面具有深遠(yuǎn)意義。8它意味著在真正犯罪(real crime)領(lǐng)域,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要求犯意。這一規(guī)則也為2003年新的《性犯罪法》所采納,在該法中,盡可能寫明罪過方面的要求,如果沒有寫明的話,則表明是有意而為,該犯罪是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9
根據(jù)英國刑法最新的判例和立法,在誘拐罪方面和猥褻罪方面,被害人年齡方面的判斷已經(jīng)不再是嚴(yán)格責(zé)任了。如果行為人的確發(fā)生了被害人年齡方面的認(rèn)識錯誤,則可以免責(zé),因為這些犯罪是要求犯意的犯罪。但是,強(qiáng)奸罪仍然是一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無論被害人是否同意,行為人與不滿16歲的幼女發(fā)生性關(guān)系即構(gòu)成犯罪,對于被害人年齡判斷上的錯誤不能成為辯護(hù)理由(因為這是一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不過,如果被害人的年齡在13歲到15歲之間,那么,根據(jù)1956年的《性犯罪法》,24歲以下的被告擁有一項辯護(hù)理由,即,所謂的“年輕人的辯護(hù)理由”(young man’s defence)——他以前從沒有受到過類似起訴,并且相信被害人已有16歲且這種相信具有合理基礎(chǔ)。10
(四)1970年Sweet V.Parsley案
該案是關(guān)于如何在制定法中確定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重要判例。本案的被告是一名教師,她將自己在農(nóng)場的房子出租給了一些學(xué)生,她自己只是偶爾在此過夜。她除了收取租金外很少對學(xué)生們進(jìn)行管理,只是在自己偶爾住在那里時若學(xué)生在深夜太吵鬧會要求他們安靜。她被指控犯有1965年《危險麻醉品法》第5條規(guī)定的以吸食大麻為目的管理不動產(chǎn)罪,因為警察在那里找到了大麻。11她最初被認(rèn)定有罪,但上議院撤銷了有罪認(rèn)定。Reid勛爵指出:“如果(犯罪定義)的一部分在犯意方面沒有寫明,那么,將存在如下推定:為了有效執(zhí)行議會的意志,我們必須將有關(guān)詞句理解為要求犯意。”他還區(qū)分了真正犯罪與假犯罪(quasi-criminal of fence),在假犯罪中,這種要求犯意的推定會更容易被推翻。12
在1985年的Gammon(Hong Kong)Ltd V.A-G of Hong Kong一案中,Scarman勛爵代表樞密院進(jìn)一步對此進(jìn)行了說明:(1)在一個人被認(rèn)定犯某罪之前,法律上存在要求犯意的推定;(2)當(dāng)該犯罪在性質(zhì)上屬于“真正的”犯罪時,這種推定尤其強(qiáng)烈;(3)該推定適用于所有的制定法犯罪,只有在制定法清楚地規(guī)定或者為了該制定法有效執(zhí)行而必要的暗指之外,該規(guī)定才能被取代;(4)可以取消該推定的惟一情況是制定法關(guān)系到社會焦點問題,例如公共安全;(5)即便與制定法和社會焦點問題有關(guān),該推定仍然是成立的,除非情況表明嚴(yán)格責(zé)任的創(chuàng)制能夠通過促成更多的注意以避免禁止行為的發(fā)生從而達(dá)到有效執(zhí)行該制定法的目的。在前述上議院2000年對于B V.DPP的判決中,上議院的勛爵們強(qiáng)調(diào)了這種立場,并將其提升到憲法性原則的地位,這樣一來,要推翻要求犯意的推定就更加困難了。13
從判例法實踐看,法院在將制定法解釋為嚴(yán)格責(zé)任方面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法官們在一些關(guān)鍵性的制定法用語上的解釋基本是一致的,這些用語有“允許、容許”(permit ting or al lowing)、“造成”(cause)、“持有”(possession)、“明知”(knowingly)、“惡意地”(wi l lful ly and mal iciously)。
當(dāng)制定法中存在“允許、容許”時,這通常表明控方應(yīng)證明被告意識到使行為非法的情況,或者他有意避免核實該行為非法。例如,制定法規(guī)定允許或容許他人駕駛制動系統(tǒng)有缺陷的車輛為犯罪,那么,因為只有在知道其制動系統(tǒng)有問題的情況下才能談得上進(jìn)一步地允許或容許,因此,這是一個要求犯意的犯罪,反之,如果制定法規(guī)定使用或駕駛制動系統(tǒng)有缺陷的車輛構(gòu)成犯罪,那么,控方則無需證明被告知道車輛的制動系統(tǒng)有瑕疵。當(dāng)制定法中存在“造成”時,如果理性人會認(rèn)為結(jié)果是由被告所造成的,那么,就無需考慮被告是否知道他在做什么,即不要求犯意(為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反之,如果不能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該犯罪應(yīng)要求犯意。這方面的典型判例是前述1972年的Alphacel l V.Woodward案。在該案中,理性人都會認(rèn)為河水污染的結(jié)果是被告造成的,因此,該罪為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當(dāng)制定法中存在“持有”時,這些犯罪通常被解釋為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但是當(dāng)制定法中存在“明知”時,則通常表明該犯罪是要求犯意的犯罪。“惡意地”一語則通常暗含該罪要求一定的主觀意識,因此屬于要求犯意的犯罪。但是,在這方面也有例外,例如,在1936年的Cotteri l l V.Penn案中,被告錯誤地認(rèn)為他射擊的是一野鳥,實際上該鳥是一只家鴿,他被指控非法且惡意地殺害家鴿。在這里,控方只需證明被告朝鳥射擊就行了,無需證明被告知道該鳥是家鴿。14
二、對英國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之嚴(yán)格程度的分析
(一)嚴(yán)格責(zé)任的“嚴(yán)格性”及與絕對責(zé)任的關(guān)系
從以上判例可以看出,嚴(yán)格責(zé)任是與犯罪成立與否有關(guān)的責(zé)任。因此,要認(rèn)識嚴(yán)格責(zé)任的“嚴(yán)格”性,就必須了解英國刑法是如何分析犯罪定義中犯罪成立要素的。在犯罪定義中,犯意和犯行是犯罪成立方面的兩大要素,其中,犯意(廣義)種類有故意、輕率、過失,犯行要素包括行為、結(jié)果、周圍情況(sur rounding circumstance),有時候,僅僅只是一種“狀態(tài)”(state of af fair)也可以組成犯行。15就這些犯行要素而言,它們可以與故意、輕率、過失相對應(yīng),從而組成各種各樣的犯罪。在分析犯罪定義時,也必須將其分解為犯行和犯意這兩大類要素。兩者是同時發(fā)生的(coincidence),只不過一個是犯罪的外部要素,一個是犯罪的內(nèi)部要素。
盡管我國學(xué)者對于什么是嚴(yán)格責(zé)任存在各種各樣的理解,但是,對于嚴(yán)格責(zé)任的定義,在英國刑法中卻不具有如此的“多元性”。可能在具體措詞上稍有不同,但具體內(nèi)容則基本一致。簡單地講,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是對犯行的一個要素或數(shù)個要素不要求證明犯意的犯罪。16而犯行要素,則由行為、結(jié)果和情況(circumstance)組成。因此,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是相對于犯罪成立而言的,它不需要控方在犯意方面進(jìn)行舉證;然而,在犯行方面,控方仍然需要加以證明。因此,將嚴(yán)格責(zé)任理解為純粹的結(jié)果責(zé)任是不正確的(結(jié)果責(zé)任在犯行方面也沒有自愿性之類的要求)。特別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于某種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而言,其嚴(yán)格責(zé)任性并非一定適用于該罪犯行方面所有的要素,它也可能是適用于犯行方面的一個要素。典型的例子,如上文中與不滿16歲的幼女發(fā)生性關(guān)系的強(qiáng)奸罪。在這里,在犯行方面,只有被害人的年齡(屬于“周圍情況”)是“嚴(yán)格”的,不需要與此對應(yīng)的犯意,但是,犯行的其他方面,如性交行為則仍然是有對應(yīng)犯意的,必須由控方舉證。
至于嚴(yán)格責(zé)任與絕對責(zé)任的關(guān)系,英國學(xué)者杰斐遜對此有清楚地說明,他說:“在過去,嚴(yán)格責(zé)任常常被稱為絕對責(zé)任,這種叫法現(xiàn)在也存在。但是,我們常常說嚴(yán)格責(zé)任并不是絕對責(zé)任,絕對責(zé)任意味著被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主觀要素并且在普通法上和制定法上不存在任何辯護(hù)理由,而嚴(yán)格責(zé)任則是需要某些內(nèi)心要素,也存在辯護(hù)理由。”17實際上,判例中有些法官在談到嚴(yán)格責(zé)任時仍然習(xí)慣地使用絕對責(zé)任的措詞,這無疑是一種誤導(dǎo)。
現(xiàn)代英國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謂的“絕對責(zé)任”,這一點也獲得了權(quán)威學(xué)者的支持。史密斯教授和霍根教授指出:即便是像1933年的Larsonneur案和1983年的Winzar V. Chief Constable of Kent這樣的“情況犯”(situational of fence)也不是“絕對責(zé)任”。在Larsonneur案,被告因護(hù)照過期而離開了英國去了愛爾蘭,卻被愛爾蘭警方遣返給了英國警方,她立即遭到了逮捕,法院認(rèn)定她因在已被拒絕入境的情況下“被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在英國而構(gòu)成犯罪。在Winzar案中,被告被發(fā)現(xiàn)醉倒在醫(yī)院的長凳上,警察到來后,他仍然沒有離去,警察遂將其用車帶到高速公路上,他被指控在醉酒狀態(tài)下“發(fā)現(xiàn)”于高速公路上而被認(rèn)定有罪。在這種合法強(qiáng)制不能成立辯護(hù)理由的情況下(這一點相比于其他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而言要更為極端),至少也是存在脅迫(duress)這樣的辯護(hù)理由的。18可見,在嚴(yán)格責(zé)任中,責(zé)任雖然是嚴(yán)格的,但不是絕對的。
(二)嚴(yán)格責(zé)任的辯護(hù)理由
事實上,在英國,責(zé)任不是絕對的,通常都會存在辯護(hù)理由。這些辯護(hù)理由有的來自于普通法,有的則直接來源于制定法。普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一般性地適用于所有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制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則通常只適用于該特定的犯罪。
1.普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
在英國刑法中,并非只要具備了犯意和犯行,就成立了犯罪。辯護(hù)理由的存在,將否定被告人的刑事責(zé)任。英國刑法中的辯護(hù)理由主要有未成年、自動行為、精神病、脅迫、緊急避險、錯誤等。當(dāng)然,在嚴(yán)格責(zé)任中,事實錯誤并不能成立免責(zé)理由,不過,一般說來,其他辯護(hù)理由仍然是成立的。例如,根據(jù)1952年的Leicester V.Pearson案以及同年發(fā)生的編號為“2 Al l ER 71,DC”的案件,非自愿行為(involuntary conduct)和脅迫就可以成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中的辯護(hù)理由。1989年的Martin(Col in)案的法律規(guī)則是,受脅迫而產(chǎn)生的特定情況也可以成為辯護(hù)理由,1999年的Eden District Counci l V.Braid案的法律規(guī)則是,因受威脅的脅迫可以成為辯護(hù)理由。不過,根據(jù)1997年的DPP V.H案,精神病的辯護(hù)理由不能適用于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理由是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是不要求犯意的犯罪,而精神病則是直接否定犯意的辯護(hù)理由,但是,該判決也遭到了學(xué)者的批評,認(rèn)為這是不合理的和“荒謬”的。19
可見,在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中,辯護(hù)理由能否成立,是與犯意直接相關(guān)的。事實上的錯誤,因為其功能是否定犯意,所以不能成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中的辯護(hù)理由。這樣看來,嚴(yán)格責(zé)任的實質(zhì)在于控方不需要證明犯意,辯護(hù)方也不能以缺乏犯意為由否定犯罪,但是除了事實錯誤這種否定犯意的辯護(hù)理由外,其他的一般辯護(hù)理由仍然適用于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不過,這里的舉證責(zé)任由被告承擔(dān)。
2.制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
嚴(yán)格責(zé)任,由于不要求犯意,因此可能會產(chǎn)生極端化的后果。對此,制定法在制定的過程中常常也會根據(jù)具體情況而設(shè)計一些制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以弱化可能出現(xiàn)的極端結(jié)果。這種辯護(hù)理由只能適用于該特定犯罪,并不具有普遍性。
例如,在1990年的《食品安全法》中存在大量的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該法第21條第1款規(guī)定,如果行為人能夠證明他已經(jīng)采取了合理的預(yù)防措施并且行使了一切適當(dāng)?shù)闹?jǐn)慎(al l due di ligence)以避免自己和自己控制下的他人實施該法所規(guī)定的犯罪,則不構(gòu)成相應(yīng)犯罪。20又如,1971年《濫用麻醉品法》第28條規(guī)定,對于持有毒品和與毒品有關(guān)的犯罪,如果被告能夠證明他既不相信也不應(yīng)懷疑或者沒有理由懷疑有關(guān)的物質(zhì)是管制的麻醉品,則不構(gòu)成犯罪。此外,在1968年《商標(biāo)說明法》第24條第1款規(guī)定,被告如果能夠證明犯罪的實施是因為信賴他人提供的信息、他人的行為和默認(rèn),或者系因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而產(chǎn)生,并且他行使了適當(dāng)?shù)闹?jǐn)慎以避免實施該犯罪行為,同樣不會構(gòu)成犯罪。1985年《計量法》第34條規(guī)定,如果被告能證明他采取了合理的預(yù)防措施并且行使了適當(dāng)?shù)闹?jǐn)慎以避免實施該犯罪行為,則不構(gòu)成該法第6部分所規(guī)定的犯罪。21
這些制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和普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一樣,是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成立與否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只看到在起訴時不要求證明犯意的一面,而看不到事實上存在的辯護(hù)理由的一面,是難以對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有準(zhǔn)確認(rèn)識的。
三、我國刑法學(xué)界關(guān)于嚴(yán)格責(zé)任的有關(guān)爭議問題的分析與思考
(一)我國刑法學(xué)界對嚴(yán)格責(zé)任的理解分歧
刑法學(xué)界對于英美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的研究,經(jīng)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由淺到深的過程。在嚴(yán)格責(zé)任方面,有關(guān)研究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景象”,然而對于嚴(yán)格責(zé)任“是什么”的前提性問題,學(xué)者們的理解也是“百花齊放”的。目前,有關(guān)嚴(yán)格責(zé)任的認(rèn)識,存在如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第一種觀點為“無罪過說”。這種觀點認(rèn)為,嚴(yán)格責(zé)任,也叫絕對責(zé)任、無過錯責(zé)任,是指法律允許對某些缺乏犯意的行為追究刑事責(zé)任,22它不要求行為人對其損害和后果具有道義上的過錯責(zé)任,在排除犯意的條件下,行為人仍可定為有罪。23
第二種觀點為“主觀罪過不明說”。這種觀點認(rèn)為,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是指行為人主觀罪過形式不明確時,仍然對其危害社會并觸犯刑律的行為追究刑事責(zé)任的制度。24
第三種觀點為“無主觀罪過或主觀罪過不明說”。這種觀點認(rèn)為,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制度,是指對于缺乏主觀罪過或者主觀罪過不明確的特殊侵害行為追究刑事責(zé)任的刑法制度。25
第四種觀點為“過錯推定責(zé)任說”。這種觀點認(rèn)為,嚴(yán)格責(zé)任區(qū)別于絕對責(zé)任、無過錯責(zé)任,是舉證責(zé)任倒置的過錯推定責(zé)任。它既有實體價值,又有程序價值,法官有自由裁量權(quán)。26
以上觀點的分歧集中于以下幾點:(1)嚴(yán)格責(zé)任與絕對責(zé)任、無過錯責(zé)任究竟有無區(qū)別,抑或等同;(2)在實行嚴(yán)格責(zé)任的情形下,行為人究竟有無罪過,抑或是罪過不明;(3)嚴(yán)格責(zé)任究竟是不是一種過錯推定責(zé)任。這些關(guān)于嚴(yán)格責(zé)任本體論的不同解讀,無疑嚴(yán)重制約了嚴(yán)格責(zé)任比較研究領(lǐng)域的進(jìn)一步深化和拓展。
(二)對學(xué)界在嚴(yán)格責(zé)任問題上理解分歧的評析
對應(yīng)于上文對英國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追本溯源的考察分析,不難看出,目前學(xué)界在嚴(yán)格責(zé)任問題的認(rèn)識失之偏頗。至少,在上述爭論焦點問題上,以英國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為基點,可以得出如下結(jié)論。
第一,在現(xiàn)代英國刑法中,只有“嚴(yán)格責(zé)任”沒有“絕對責(zé)任”。“絕對責(zé)任”只是“嚴(yán)格責(zé)任”的一種稱謂,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學(xué)術(shù)稱謂上并不嚴(yán)謹(jǐn)。我國學(xué)者要么認(rèn)為絕對責(zé)任有別于嚴(yán)格責(zé)任,27要么認(rèn)為嚴(yán)格責(zé)任等同于絕對責(zé)任,從英國刑法的實際內(nèi)容看,這兩種觀點都不能成立。因為,正如上文所述,責(zé)任并不是絕對的,無論是英國刑法學(xué)者公認(rèn)的極端的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如1933年的Larsonneur案和1983年的Winzar)還是制定法上的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都是存在辯護(hù)理由的。準(zhǔn)確地講,“絕對責(zé)任”只是對于“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一種不準(zhǔn)確的別稱。
第二,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并不是罪過不明的犯罪,也不是沒有罪過的犯罪。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是罪過形式(故意或者過失)不明確的犯罪。這種理解已經(jīng)脫離了英國刑法判例法有關(guān)的司法實踐——嚴(yán)格責(zé)任不要求控方在犯意上(故意、輕率、過失)舉證,不要求舉證并不是因為罪過不明,而是基于有效執(zhí)行法律等其他考慮。28同時,不要求舉證,不一定表明被告實際上是無過錯的(但理論上也可能存在無辜者被定罪的情況),它只是不要求控方證明有關(guān)犯行的犯意要素。
第三,嚴(yán)格責(zé)任并不等同于過錯推定責(zé)任。首先,在嚴(yán)格責(zé)任中,控方不需要就犯行的某一個要素或某些要素的犯意舉證,不需要舉證并不是推定它們存在。其次,從實質(zhì)上看,在嚴(yán)格責(zé)任中,合理的事實錯誤,也將會導(dǎo)致犯罪,這表明行為人可能會因為沒有過錯而被定罪(而不是推定其有過錯)。再次,從嚴(yán)格責(zé)任的地位看,更不能將嚴(yán)格責(zé)任理解為過錯推定,因為它相對于要求犯意原則來說是一種例外,29這說明不能將其放在犯意原則下統(tǒng)一理解。此外,法官在辯護(hù)理由的問題上,并沒有自由裁量權(quán),只能在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和制定法的規(guī)定中按照遵循先例原則進(jìn)行解釋。
(三)對英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現(xiàn)實反思
從上述解讀可以看出,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中,就嚴(yán)格責(zé)任的犯罪要素而言,在證據(jù)方面存在著舉證責(zé)任的轉(zhuǎn)換現(xiàn)象。即被告如果要否認(rèn)犯罪,他必須就普通法上和制定法中存在的相關(guān)辯護(hù)理由舉證。從嚴(yán)格責(zé)任所存在的辯護(hù)理由看,它們的功能就在于緩解嚴(yán)格責(zé)任所可能帶來的極端后果,因此,是兼顧公平和正義的具體體現(xiàn)。如果只看到嚴(yán)格責(zé)任理解為強(qiáng)調(diào)效率之功利性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公平性的一面,這是不妥當(dāng)?shù)摹嶋H上,嚴(yán)格責(zé)任在強(qiáng)調(diào)效率的同時,在制度上也有一定的辯護(hù)理由作為公正的保證。
從英國刑法來看,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數(shù)量多、分布廣,盡管面臨理論界的批評,但這并未撼動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基本地位。現(xiàn)代英國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在具有“嚴(yán)格性”的同時,也具有各種普通法和制定法上的辯護(hù)理由來緩解該嚴(yán)厲性;在筆者看來,這種先“嚴(yán)”后“松”,體現(xiàn)的正是立法者與被告方在舉證責(zé)任上的一種“博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刑法完全可以“棄其糟帕”而“取其精華”,在控方難以證明而被告方容易證明的犯罪要素的問題上,廣泛實行嚴(yán)格責(zé)任(前提是允許被告提出合理的抗辯)。當(dāng)然,如何結(jié)合我國刑法犯罪構(gòu)成的特點,構(gòu)建我國的嚴(yán)格責(zé)任制度,這正是比較刑法領(lǐng)域亟待理論界進(jìn)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筆者認(rèn)為,英國樞密院在1985年對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適用的嚴(yán)格限制性解釋點明了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的用意與要旨,即所規(guī)定犯罪涉及諸如公共安全這樣的社會公眾所共同關(guān)注的焦點問題。這一解釋為我們借鑒其合理內(nèi)核指明了方向。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些涉及社會公眾根本利益的問題上,規(guī)定類似于英美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那樣的制度。例如食品安全問題、環(huán)境污染問題、醉酒駕車致人重傷死亡問題等。至于哪些問題屬于涉及社會公眾根本利益的焦點問題,立法機(jī)構(gòu)既可以主動關(guān)注,也可以通過民意調(diào)查和民意測驗收集整理。必要時,可以進(jìn)行聽證,廣泛征求社會公眾的意見。總之,對有關(guān)問題的入罪必須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和社會基礎(chǔ)。
考慮到我國刑法犯罪構(gòu)成服從于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基本原則,在這些犯罪中,在犯罪要件中不宜缺少主觀方面要件,否則,將構(gòu)成刑法體制內(nèi)不可調(diào)和的根本沖突。借鑒英國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的做法,制度設(shè)計的重點應(yīng)當(dāng)放在主觀方面的證明上,應(yīng)當(dāng)明確規(guī)定一定情況下犯罪嫌疑人的舉證責(zé)任。在犯罪嫌疑人容易證明而控方難以證明的情況下,將舉證責(zé)任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在此種情況下,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證明存在相應(yīng)的事實和情況(在英國刑法中表現(xiàn)為辯護(hù)理由),則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上的不利后果。具體而言,在具體犯罪的犯罪構(gòu)成設(shè)置上,要在實體法領(lǐng)域適當(dāng)引入可反駁的推定條款。被告對于此類推定的否定,負(fù)有舉證責(zé)任(這并不違反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刑法基本原則)。事實上,我國刑法中已經(jīng)存在類似的可反駁推定。例如刑法對于攜帶兇器搶奪轉(zhuǎn)化型搶劫罪的規(guī)定,在刑法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對于攜帶兇器搶奪的,也并非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認(rèn)定為搶劫。審慎確定廣大人民群眾所關(guān)心的涉及公眾根本利益的焦點問題,并采用可反駁的推定的立法技術(shù),在犯罪要素的證明上,賦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舉證責(zé)任,并在刑法中明確規(guī)定下來,不乏為借鑒英美刑法嚴(yán)格責(zé)任合理內(nèi)核的一條可行而有效的途徑。這樣,既可以提高對于此類社會焦點問題涉罪行為的打擊效率,又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和主客觀相統(tǒng)一原則,可以按照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
注:
1 Ashwor th and Blake,The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Criminal Law Review 1996,P306.
2 Nicola Padfield,Criminal Law(second editon),Butterwor ths,2000,P58.
3 Smith&Hogan,Criminal Law(Ten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wor ths,2004,P118.
4、17[英]邁克爾·杰斐遜:《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頁,第165-166頁。
5 Nicola Padfield,Criminal Law(second editon),Butterwor ths,2000,P58.
6 Clarkson&Kenting,Crimnal Law Text and Materials(f i f th edition),Sweet&Maxel l 2003,P222.
7 Catherine El liot t and Frances Quinn,Criminal Law(third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0,P28.
8 Nicola Padfield,Criminal Law(second editon),Butterwor ths,2000,P60.
9 Russel l Heaton,Criminal Law Text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359-360.
10 Alec Samuels,Opinion—Sexual Of fences And Criminal Intent:What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Journal Of Criminal Law,Apri l 2002,PP66-97.
11 Clarkson&Kenting,Crimnal Law Text and Materials(fi f th edition),Sweet&Maxel l 2003,P222.
12 Nicola Padf ield,Criminal Law(second editon),Butterwor ths,2000,P60.
13 Richard Card,Criminal Law(16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sorths,2004,PP167-168.
14 Alan Reed&Peter Seago,Criminal Law,Sweet&Maxel l Limited,1999,PP99-105.
15 Smith&Hogan,Criminal Law(Ten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wor ths,2004,PP36-111.
16 Nicola Padf ield,Criminal Law(second editon),Butterwor ths,2000,P58.
18 Smith&Hogan,Criminal Law(Ten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wor ths,2004,P132.
19 Richard Card,Criminal Law(16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sorths,2004,P179.
20 Smith&Hogan,Criminal Law(Ten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wor ths,2004,P137.
21 Richard Card,Criminal Law(16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sorths,2004,P181.
22儲槐植:《美國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
23鄭耀華:《英美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刑法問題與爭鳴》(第4輯),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24李文燕、鄧子濱:《論我國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中國法學(xué)》1999年第5期。
25劉生榮:《論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法學(xué)研究》1991年第1期。
26付霞:《論刑法中的嚴(yán)格責(zé)任》,中國政法大學(xué)2004年碩士論文,第9頁。
27駱梅芬:《英美法系刑事法律中嚴(yán)格責(zé)任與絕對責(zé)任之辨析》,《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9年第5期。
28嚴(yán)格責(zé)任犯罪利弊共存,其“利”表現(xiàn)在:促進(jìn)謹(jǐn)慎、威懾力強(qiáng)、便利執(zhí)法、減輕犯意證明的困難等,參見Catherine El l iot t and Frances Quinn,Criminal Law(third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PP32-33. 29 Richard Card,Criminal Law(16th edition),LexisNexis But tersorths,2004,P157.
- 政治與法律的其它文章
- 我國不動產(chǎn)登記簿制度研究**本文是湖南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不動產(chǎn)登記疑難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8YBB112)的階段性成果。
- 論證據(jù)意義上的事實
- 論14世紀(jì)至19世紀(jì)英國上議院司法權(quán)的變遷
- 酒后駕車可否投保商業(yè)型保險——臺灣酒后駕車險的經(jīng)驗借鑒
- 論我國行政訴訟中法定判決理由既判力**本文系武漢大學(xué)博士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101060102000010)的成果之一。——以撤銷訴訟為視角
- 律師毀滅證據(jù)、偽造證據(jù)、妨害作證罪的憲法學(xu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