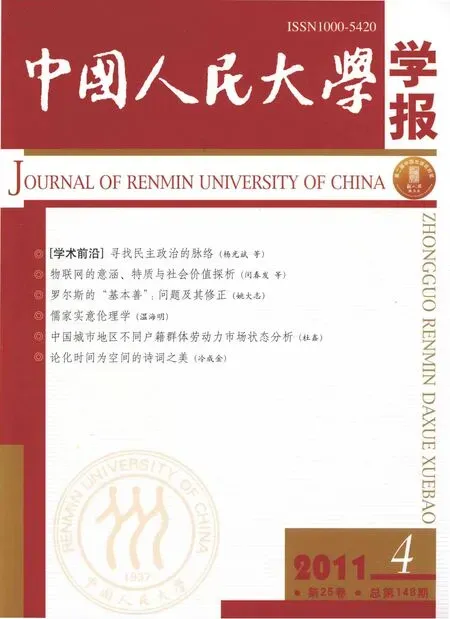《史記》、《漢書》所載易學傳授體系與漢初的易學傳承考辨
白效詠
一、疑古信古:學界關于孔子與易學傳授的兩種觀點
關于易學與孔子的關系,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易學傳自孔子;一種則以為易學和孔子沒有關系。傳統觀點認為,孔子傳過易學,《周易》的“十翼”即為孔子所作。自宋代歐陽修即開始懷疑這一看法,歐陽修作《易童子問》,開否認“十翼”為孔子所作之先聲。近代疑古思潮興起后,不少學者對傳統的說法持否定態度,認定“十翼”非孔子所作,易學與孔子沒有關系。持這一觀點的學者頗多,本文不擬一一列舉,其中馮友蘭、錢穆和“古史辨派”的顧頡剛、李鏡池堪稱代表,而又以李鏡池的論述最為詳盡。李氏引《魯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來否定今本及古本《論語》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以此來否定孔子研究過易學。李氏還將孔子所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當做諺語來看,又把《史記·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定為京房(宣帝時之京房)所插入,這樣,就徹底否定了《周易》與孔子有關的證據。[1](P184-214)主“十翼”為孔子所作者,這一派的學者有范文瀾、任繼愈、李學勤和金景芳及其弟子呂紹綱、李衡眉等人。這一派大都承認《易傳》與孔子有關,孔子是傳過《周易》的。其中金景芳及其弟子的觀點較有代表性,他們認為“十翼”也即《易傳》可分為四部分:一部分為孔子繼承前人的舊說,一部分為后人竄入的與孔子無關的東西,一部分為孔門弟子所記孔子講《易》言論,而大部分為孔子所作。李衡眉先生的《孔子作易傳之明證、補證與新證》一文頗能說明這一派的觀點立場。李學勤也從音韻學的角度指出“亦”、“易”二字在上古音中屬于不同的韻部,不可能傳訛,從而有力地駁斥了李鏡池的“孔子與易學無關”說。此外,李學勤又引《帛書周易》之《要》篇、《繆和》篇、《昭力》篇等,證明孔子晚年是研究過易學并傳授過易學的。[2](P13-15)
二、《史記》、《漢書》所載易學傳授體系為司馬談追記自家淵源
否定孔子傳易學者,必然要否定《史記》、《漢書》所載的易學傳授體系,臺灣學者何澤恒的《孔子與〈易傳〉相關問題覆議》及《孔子與〈易傳〉相關問題覆議續》可以說是否定《史記》、《漢書》所載易學傳授體系的代表作。①何澤恒:《孔子與〈易傳〉相關問題覆議》、《孔子與〈易傳〉相關問題覆議續》,載《周易研究》,2001(1)、(2)。何澤恒的質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1)《史記》、《漢書》記諸《易》師的姓名、里居頗不同,傳授先后亦互異。(2)何氏引日本學者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②該文收入《周易研究論文集·易傳探源》(第一輯)。一文的研究成果,指出“這些傳《易》者,多是楚、江東、燕等在邊鄙的人物,最后在齊尤盛行”。而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子貢、子夏、子游都不獲孔子傳《易》,孔子獨傳一籍籍無名的商瞿,不合情理;“而商瞿再傳,卻又多為人所罕知的邊鄙人物”,此事值得懷疑。(3)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所載《易》之傳授線索,自商瞿至田何都是六傳。何氏引崔適在《史記探源》中的質疑,以為六傳之間,“計三百二十六年,是師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逾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余歲而受業,乃能幾及,其可信耶”。[3](P217)據此,何氏贊同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一文中“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受《易》于楊何,孔子晚年喜《易》而作《十翼》之說,以至其前傳《易》系統,或即源出于楊何”的觀點,并得出“這一傳《易》系統,漢初以下的,自應可信;至于先秦一段,便靠不住了”的結論。
筆者以為,要研究漢代易學的有關問題,有必要對《史記》、《漢書》所載的易學傳授系統的真實性加以討論,而何澤恒據以上論據并不足以否認易學傳承系統的真實性。在無新的證據出現的情況下,不可輕易斷言這一傳承系統不可信。
《史記·儒林列傳》記載易學傳承線索曰: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4](P3127)又曰:
言《易》自菑川田生。[5](P3118)《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
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6](P2211)《漢書·儒林傳》載易學傳授次第更為詳細,且記載了司馬遷之后易學的傳授情況: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征為太中大夫。齊即墨城,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7](P3597)
考兩書所載,雖然于漢代之前易學之傳授略有不同:《史記》所記為“矯子庸疵”,則此人蓋姓矯名疵字子庸;《漢書》則以為是“橋庇子庸”,則此人似姓橋名庇字子庸。《史記》以為“馯臂子弘”受易于商瞿,然后傳矯子庸疵;《漢書》則以為橋庇子庸受易于商瞿,然后傳馯臂子弓。另外,周子家到底是名“豎”還是名“丑”,其傳人到底是“光子乘羽”還是“孫虞子乘”,兩書所載也不同。但二者俱明言易學傳自孔子,且傳授路線清晰。
對于司馬遷所記《易》傳授系統源出于楊何說,筆者十分贊同。其實,這一問題蒙文通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他在《經學導言》一文中說:“史公學《易》于楊何,學《道論》于黃子,《史記》一書,只有《周易》和《老子》的傳授才可考,因為這兩家是太史公的本師。”[8](P26)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9](P3288),他所稱引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見于今本《周易》,他所謂“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也源于今本《周易》“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之說。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載其父稱引、論述的《易傳》內容看,司馬遷對其父親的易學是十分了解的,《史記·儒林列傳》所記易學傳授系統為田何傳王同子仲,王同子仲傳楊何,而不記田何還傳易于他人,足以說明這一系統是司馬談所追記的自己的易學淵源,故而不及《漢書·儒林傳》所載的周王孫、梁項生、丁寬、服生等人。因而,關于楊何之前的傳授系統,司馬談當是得自楊何。當然,司馬談所記的這一傳承系統未必精確。班固在《儒林傳》的贊中追憶西漢官學初立時的情況說:“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10](P3620-3621)楊何本是田何的再傳弟子,所傳即田何之易學。當時傳自田何的易學為唯一的官方易學,所以掌管官方記錄的太史公司馬談追記易學淵源,也只能是沿著他的老師楊何上溯田何的易學來源。但這并不表明傳自孔子的易學只有田何及其后學這一支。
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將其父追記的自己的易學淵源當做自孔子以來易學傳授的唯一系統收入《儒林列傳》。但丁寬、周王孫、服生等的易學并未中絕,尤其是丁氏易學,經田王孫、施仇、孟喜、梁丘賀等后學的弘揚,至漢宣帝時已大顯于世,施、孟、梁丘各自成家,成為易學中影響最大的一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易學還是頗重師承淵源的。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此事被其同門梁丘賀揭破,謂:“田生絕于施仇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11](P3599)梁丘賀不惜開罪同門孟喜,力證孟喜之象數易學并非出自師門,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學者們維護師門易學純潔性的決心。孟喜也因為不能堅守師法而為漢宣帝所輕:“博士缺,眾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12](P3599)梁丘賀本從楊何弟子京房學易,之所以被漢宣帝征召為郎官,正是因為他京房弟子的身份。所以,在當時如此看重易學師承的情況下,學者們重視記錄自己的易學淵源,明己之易學所出,也是很正常的事。因而記錄這一易學傳承體系的,當不只是楊何、司馬談,丁寬及其弟子亦應對這一傳授體系有記錄。班固作《漢書》時,史料較司馬遷時代更為詳備,《史記》所不載的,《漢書》作了補充,《史記》所載有誤的,班固據其他史料予以訂正,這樣的推測應是合理的。班固據劉向《七略》所作的《藝文志》,對丁寬、服生、周王孫及其弟子蔡公等人的易學著作都有收錄,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班固看到了許多由丁寬及其后學、服生、周王孫及其弟子蔡公等人所保留下來的易學資料,其中就包括易學的傳承體系,并據之對司馬遷所記的得自其父的易學傳承系統加以修訂,這就是《史記》、《漢書》所載易學傳承系統有所不同的原因。
三、孔門易學流傳并非只有商瞿一家
《漢書·藝文志》敘述孔子卒后儒家經典傳習的情況時云: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肴亂。[13](P1701)
據此,在孔子之后,本來“《易》有數家之傳”,并非僅《史記·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所載的只有一條單線傳承。
所以,司馬遷和班固所記載的商瞿至田何的傳承,只是數家中的一家,甚至更有可能是一家中若干支派中的一派而已。而“這些傳《易》者,多是楚、江東、燕等在邊鄙的人物,最后在齊尤盛行”及“師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逾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余歲而受業,乃能幾及”,這兩種情況雖然看起來不太符合一般學術的傳承情況,但并非絕無可能存在,只是幾率較小而已。如果是數家中有這么一家甚至一家若干支派中有這么一派,其實不足深怪。幸運的是,這一派經田何在漢初的傳播得以發揚光大,逐漸成為儒門易學主流,至楊何時被立為官學,成為官方認可的經典。為鞏固自己的官方地位,得以立為官學的流派往往視其他流派為競爭對手,不遺余力地打壓,這在漢代的學術界是普遍現象。《詩》學內部江翁對王式的排擠則堪稱典型:
(式)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逿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14](P3610)
王式精于《詩》學,受到博士們的擁戴,“世為《魯詩》宗”的江翁生怕王式威脅到自己的地位,進而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在王式指出自己的錯誤之后,竟當眾辱罵,終致王式終老于家。于此可見當時學派斗爭之激烈,一派一旦得勢,往往有極強的排他性,千方百計地壟斷學術。田何易學一派獨大,不可能不排擠其他學派。其他學派則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日益式微,鮮有知名學者,所以《史記》、《漢書》之《儒林傳》在易學方面以收錄田何后學為主,田何易學傳承淵源遂得大白于世。
何澤恒所謂顏淵、子貢、子夏、子游等得意門生都不獲孔子傳《易》,偏偏籍籍無名的商瞿獨得垂青,仍是把《史記》、《漢書》所記的田何一系當做儒門易學唯一的傳承。若果真如此,則田何之前每代只傳一人,自田何始傳授多人,也讓人難以理解。在田何一系外,顯然還有別的易學流傳。孔子傳《易》也絕非獨傳商瞿一人,從出土的《帛書周易》來看,不少孔門弟子都曾向孔子請教過《易》,其中子貢赫然在列。而現存文獻中也保留了子夏傳易的蛛絲馬跡。
《帛書周易》之《二三子》篇的內容,即為二三子向孔子請教易學問題。雖未明云二三子為何人,但從討論問題之廣博來看,并非萍水相逢偶然為之,其人當是孔子弟子。而《要》篇則保存了子貢與孔子討論《易》的寶貴資料:
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夫子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福。《尚書》多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樂(其辭也。予何)尤于此乎!”①本文所引《帛書周易》內容,均以廖名春的《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為主并參考其他校釋。廖名春:《帛書周易論集》,359~40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類似的子貢問、孔子答共三則,足征孔子之易學固已傳子貢矣。此外,《昭力》、《繆和》兩篇也是關于傳易的內容,學易者為昭力、繆和等人,傳易者雖未明言為孔子,但據“子曰”而言,似亦為孔子,因為就現存資料而言,“子曰”還找不出不是“孔子曰”的例證。
《子夏易傳》今本雖為偽書,但卻透露出子夏也存在傳易的可能。清人姚振宗所輯《七略佚文·六藝略佚文》謂“《子夏易傳》,漢興,韓嬰傳”,其下又有“西河、燕、趙之間”之語。[15](P110)韓嬰代表著漢代儒家之另一易學重鎮。《漢書·儒林傳》云: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后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16](P3613-3614)
孟喜本從丁寬弟子田王孫受易學,其易學的主要淵源還是來自丁寬,屬于田何一派。從“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來看,傳自韓嬰的易學與傳自田何的易學并不一樣。韓嬰的著作今存《韓詩外傳》10卷,其中保留了一些韓嬰的易學學說,從中也可推斷出易學在韓嬰學說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漢書》也未記韓嬰易學所從受,但從其傳《子夏易傳》來看,很有可能是子夏易學的傳人。
據《漢書·藝文志》,系于韓嬰名下的易學著作為《韓氏》二篇,至于劉向《七略》所著錄的《子夏易傳》則不見于《漢書·藝文志》,這一現象引起了后世學者的種種猜測。余嘉錫等以為《漢書·藝文志》所收易傳《韓氏》二篇,即劉向《七略》所著錄之《子夏易傳》,只是被班固改了名字,這一猜測無疑最為合理。因為班固《漢書·藝文志》本是損益劉向《七略》而成,其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17](P1781)《子夏易傳》不在所省之列,必然保存在《藝文志》中,而《七略》又明言《子夏易傳》乃韓嬰所傳。但接下來余嘉錫認同前人《子夏易傳》之“子夏”與孔子弟子子夏無關說,并認為“子夏”為韓嬰或韓嬰之孫韓商之字。[18](P205-209)這一觀點其實不能成立,原因如下:據《七略佚文》,劉向《七略》所著錄韓嬰詩學著作甚多,均作《韓故》、《韓內傳》、《韓外傳》、《韓說》等,不以字命名,亦無“韓嬰傳”三字。而著錄其他易傳,具以“易傳某氏”為名,不合于韓嬰所作之易傳以字命名。且就今之所見《七略佚文》來說,其著錄漢人著作,或以姓氏(如《歐陽章句》)或以姓名(如《許商五行傳記》),同姓氏者則以大、小作區別(如《大夏侯章句》、《小夏侯章句》),從未見以字命名者。《子夏易傳》果為韓嬰或韓商所作,以例應作《易傳韓氏》或《易傳小韓氏》。所以,從命名來看,《子夏易傳》不應為韓嬰或韓商所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19](P2203)作為孔門文學科佼佼者的子夏,又曾經從事過講學,有學說或著作傳世,也符合邏輯。而韓嬰傳學之地西河、燕、趙之地與子夏講學之地有重合處,他繼承子夏的學術是極有可能的。綜上所述,則韓嬰所傳易學極有可能源自子夏,而韓嬰所傳的易學更是田何一系外別有易學流傳的鐵證。
此外,荀子也多次論述過《易》,荀子之易學亦不在商瞿—田何一系的傳承體系中,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商瞿—田何的傳授系統只是漢代經師追記他本人的易學來源,所記的并非從孔子開始的整個易學傳授史。
四、漢初其他易學的流傳
其實,在漢初易學的傳承中,田何弟子周王孫所傳的“古義”也是有別于田何易學的一種。在田何的五個傳人中,丁寬在漢初易學傳授中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僅從田何受《易》,還從田何弟子周王孫受易學“古義”,即《周氏傳》。丁寬從田何受易,“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20](P3579)可見丁寬盡得田何易學。丁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21](P3579)關于周王孫的“古義”易學,劉大鈞曾經作出這樣的推斷:“帛本《易》當屬周王孫《周易》‘古義’,號《周氏傳》者的可能性較大,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各家。”劉氏還將周王孫的“古義”定為田何所傳:“當時田何傳《易》,除有今本卦序的‘今義’外,尚有傳于周王孫的‘古義’。估計為了避免‘后世之士疑丘’,故‘古義’只秘傳給個別弟子,并不公開傳授。周王孫傳丁寬,丁寬傳田王孫,田王孫傳孟喜。”他將此“古義”的傳承定為:“田何——周王孫——丁寬——田王孫——孟喜——焦延壽——京氏。”[22](P112-114)這樣,把《帛書周易》推定為周王孫之“古義”,并以為得自田何,且此“古義”為后來京氏易學之祖。筆者很難認同劉氏的推斷。劉氏作出此論斷的依據是“西漢《易》本由田何一人傳之”,因而斷定無論是周王孫的“古義”還是后來的“焦延壽獨的隱士之說”,都應出自田何。事實上,前已言之,漢初易學的傳授要復雜得多,傳《易》者也絕非田何一人。周王孫“古義”易學不太可能也傳自田何,理由如下:其一,如果丁寬未能盡得田何之易學,則田何不應該主動謝絕丁寬的繼續學習,并于丁寬東歸之際說出“易已東矣”的話來。所謂“易已東矣”,當是田何傾囊相授之后的話。其二,如果像劉大鈞先生所說的那樣,田何只把“古義”秘傳周王孫一人,而不傳丁寬,則田何也一定會叮囑周王孫謹慎選擇傳人。田何只傳周王孫而不傳“讀《易》精敏”的丁寬,說明丁寬非其人。周王孫在丁寬東歸途中即將田何秘傳的“古義”傳于丁寬,豈不違背師教?于情于理均不太可能。其三,如“古義”為田何所傳,如劉大鈞先生所做推斷,“田何曾授《易》給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等四人(筆者按:其實還有梁項生)。……故田何所授四家之《易》當有不同”,則是田何本身兼通兩種易學,一為傳于丁寬等的易學,一為傳于周王孫的“古義”。田何這兩種易學又從何而來呢?田何易學傳自孫虞子乘,以此上推,以至孔子,則是孔子所傳的易學本身即是兩種,即自孔子傳《易》以至田何,皆為兼傳“古義”及漢初通行之易學。何以自孔子至田何之師孫虞子乘兩種易學皆可同傳一人,而到了田何則分開傳授?甚不合情理。所以周王孫之“古義”,必非受自田何,乃是另有傳人。西漢被稱為“王孫”者并非尋常百姓,都是周天子或諸侯王的后代。周王孫為洛陽人,而洛陽是東周王朝之故都,所以周王孫極有可能是東周王室的后裔。周王朝在“學在官府”的時代曾經是文化壟斷者,衰落后也是最主要的文化保存者。《周易》成型于周文王手,本是周王室傳家之學,所以周王孫保留易學之“古義”是極合情理的事情。周王孫的《周氏傳》,也即所謂“古義”,正是易學別有流傳的另一佐證。
《漢書·藝文志》載:“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23](P1704)班固本于劉向《七略》而作的《藝文志》,只是說田何傳易,并不是說傳易者唯田何。所謂“傳者不絕”,當是指傳易學者較多,易學廣為流傳,與“《易》有數家之傳”所言一致,并非指易學傳授一線不斷絕。另外,就先秦易學發展來看,易學也并非為儒家所壟斷。如蔡澤曾引《周易》乾卦爻辭“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來闡述“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圣人之常道也”這一道理。[24](P2422)而蔡澤本人并非儒者。民間費氏易學、高氏易學顯然不屬于田何易學一系,實為易學在民間流傳的明證。《漢書》謂費氏易學“長于卦筮,無章句”,又說高氏易學“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25](P3602)而卦筮和陰陽災異正是正宗的孔門易學所排斥的東西。
《漢書·儒林傳》還提到“齊即墨城,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26](P3597),《史記·儒林列傳》也謂“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27](P3127),俱未言其易學之所從受,如果其易學來自田何一系,則應該明言其師承,因為漢之后田何一系易學傳授記載的相當清晰。由此可知,他們的易學很可能并非來自田何一系,其學術淵源已經不可考知。“言《易》者本之田何”,只能說明他們的易學受到過田何的重大影響。因為最初(建元五年)立為官學的就是田何的再傳弟子楊何,若欲求官干祿,就不能不向官學靠近。《史記·儒林列傳》于此稱“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更能揭示這一現象的本質。一種極為可能的情況是,由于其他的易學未被立為官學,故其學術淵源也未被記錄下來。他們以易學得高官,又被列入《儒林傳》,再次證明了漢初傳易者絕非田何一人,在儒家內部也別有易學流傳。
在詩學的著名傳人轅固生的思想學說中,也可明顯地看出易學的影響。《漢書·儒林傳》記載了他與黃生在景帝面前的一場學術爭論: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28](P3612)
轅固生關于湯武革命的觀點,顯然是受到了《周易》“革卦”《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影響,承認湯放桀、武王伐紂的合法性、合理性。我們不能肯定轅固生也是易學的傳習、研究者,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也受到了易學的影響。《漢書·兒寬傳》又載:“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29](P2633)兒寬曾從之學習,則褚大之《易經》受自何人,亦不載,似亦非田何一系。
綜上所述,漢初儒家的易學流傳并非只有田何一系。《史記》、《漢書》所載的易學傳承淵源很可能是田何或其后學的追記。但田何在漢初以專門傳易而知名,他的后學楊何被立為易學博士,成為最早被官方認可的易學,田何易學也就成為官方易學的主流。田何易學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斷吸取、融合別的易學,其后學也逐漸分流,各自成家。周王孫的易學“古義”在這一融合的過程中與田何易學融合,是為丁寬一支易學流派。韓嬰之易學在漢初也有傳授,但并未得到官方的認可。
五、余論:孔子與易學傳授
厘清《史記》、《漢書》所載易學傳授系統的真實面目及易學各派的流傳,我們不難發現,“孔子傳易說”很難被駁倒,雖然“十翼”未必完全出自孔子之手。《論語》中孔子多次這樣評價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30](P431),“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1](P480),“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32](P578)據《左傳》記載,《周易》在孔子所處的時代廣泛流行,《左傳·昭公十二年》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33](P2063)
當時,人們不僅以《周易》的象數占筮吉兇,還運用義理,結合人事來判斷,對事情的當否作出預測。而以周文化的繼承者自任的孔子,“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34](P160),偏偏對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周易》不加學習、研究,則不合情理。否定孔子傳《易》者,多同時否定孔子刪《詩》、《書》,如此則孔子不僅不作,而且不述,與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不符。另外,《呂氏春秋》卷二十二《慎行·壹行》載:“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35](P207)《韓詩外傳》卷八載:“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在戰國秦漢時期,孔子曾經研究過《周易》是得到學者們認可的。《呂氏春秋》的成書去孔子不過二百三十多年,所記應該有較高的可信度。
此外,《帛書周易·要》所載孔子的話“吾好學而才聞要,安得益吾年乎”與《論語》中“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思相近,可以相互印證,足征所謂《魯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為無稽。“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與《史記·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相符。孔子“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觀其德義耳”的言論與《論語》中他“不占而已矣”的話也若合符契。而《繆和》篇所記孔子對“恒卦”的解說,也說明《論語》記載的孔子所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就是“恒卦”卦辭,并非諺語。以上說明,孔子傳易信而可征。
[1]李鏡池:《易傳探源》,載《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2]《孔子與〈周易〉》,載李學勤:《綴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崔適:《史記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86。
[4][5][6][9][19][24][27]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7][10][11][12][13][14][16][17][20][21][23][25][26][28][29]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8]蒙文通:《經學導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5]姚振宗:《七略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8]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2]《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0][31][32][34]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33]《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2003。
[35]《呂氏春秋》,長沙,岳麓書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