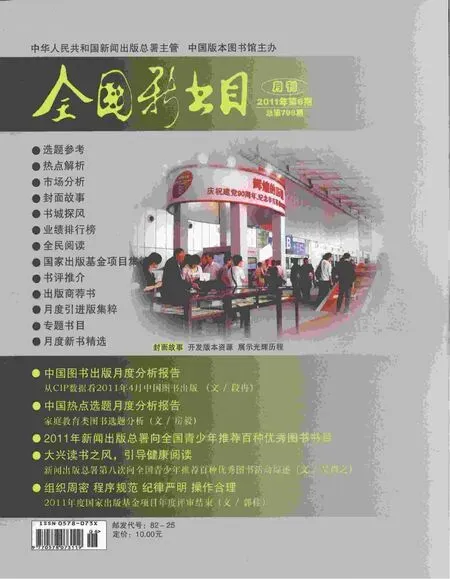大時代的“小生活”——評《莉莉姨媽的細(xì)小南方》(作家出版社出版)
■吳義勤
朱文穎的長篇新作《莉莉姨媽的細(xì)小南方》呈現(xiàn)了另外一種全新的處理模式,它讓我們看到了文學(xué)在處理歷史/時代與人的關(guān)系時的一種更文學(xué)化、更人性化的可能性,在朱文穎的筆下,歷史/時代不僅不是支配性的、絕對性的主體,甚至已經(jīng)不是影響人物命運的“背景”,它當(dāng)然仍然在人物的命運轉(zhuǎn)折中發(fā)揮著作用,但對比于人物本身的那種強烈的主體性,對比于人物那種強大的內(nèi)心生活和精神生活,對比于人物那種情感與精神的超越性,歷史/時代確實已經(jīng)成了一種“第二性”的可有可無的存在。
《莉莉姨媽的細(xì)小南方》表現(xiàn)的是大時代的“小生活”,在大時代的布幕上,作家注視的恰恰是生活和時代的“小細(xì)節(jié)”,這種注視使得歷史/時代完全內(nèi)心化與精神化了。小說的時間跨度其實是很大的,它涵蓋了從上個世紀(jì)50年代到21世紀(jì)頭十年的中國社會生活,從激情而狂熱的紅色生活經(jīng)驗到商品經(jīng)濟大潮中的人生百態(tài),小說多有涉及。但是小說的重心并不在于這種歷史/時代的變遷所帶來的戲劇性的展示,而是努力要呈現(xiàn)的是歷史/時代之外的另處一種“生活”與“人生”。可以說,小說敘述的是“生活”之外的“生活”,“時代”之外的“時代”,“人生”之外的“人生”,而這種“生活”與“人生”在絕對性的歷史/時代敘事中常常是被遮蔽和忽略的。因此,小說的敘事動力不是來自于歷史/時代的戲劇性變遷,而是來自于被壓抑在歷史/時代邊緣處的情感觀、價值觀、世界觀與那種宏大的歷史/時代的沖突。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圍繞童家和潘家兩個家庭而展開,這兩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既有著現(xiàn)實的故事,又有著傳奇性的“前史”。而其中有兩個敘事元素特別引人注目,它們一是愛情,一是孤獨。

《莉莉姨媽的細(xì)小南方》就這樣以柔軟的、女性化的敘事方式“重述”著歷史,并通過對“愛情”與“孤獨”兩個主題詞匯的詮釋,讓我們看到了一群大時代的“另類”生存者。他們作為堅硬的、枯燥的歷史/時代一道異樣的風(fēng)景,使歷史/時代變得飽滿、豐富而有趣,使歷史/時代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文學(xué)性和精神意味。莉莉姨媽無疑是一個具有特殊美感的典型文學(xué)形象,是朱文穎式的審美觀和歷史觀的象征,“我經(jīng)常會在雨天的時候想起親愛的莉莉姨媽,我外公外婆的長女。她就站在青石板路那棵最老的梧桐樹下,背對著我們,腰肢處有著細(xì)微柔軟的弧度。我的莉莉姨媽直到真正的老年降臨時還有著少女般的動作和姿態(tài)。她的少女和老年時代沒有真正的界線。她內(nèi)心有一種奇怪的東西,談不上好壞,難以論雅俗。正是它們,最終打敗了她的年齡以及她臉上垂褶累累的皺紋。”“她那細(xì)高跟的鞋子發(fā)出的聲音。清脆的,激越的,仿佛仍然在和什么東西賭著氣。仿佛也在和自己賭著氣。和自己以前沒有堅持賭氣下去的那一部分賭著氣。這次再也不握手言和了。這次一定要再賭氣下去。真的,她就是這樣的。她搖搖晃晃走路、對著鏡子美美地描摹口紅的時候就是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她的形象撕破了歷史/時代的堅固帷幕,證明了在任何時代都有可能存在另外的“生活”,證明了個體生命自我選擇的可能性與合法性,證明了忠于心靈和愛本身的價值觀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