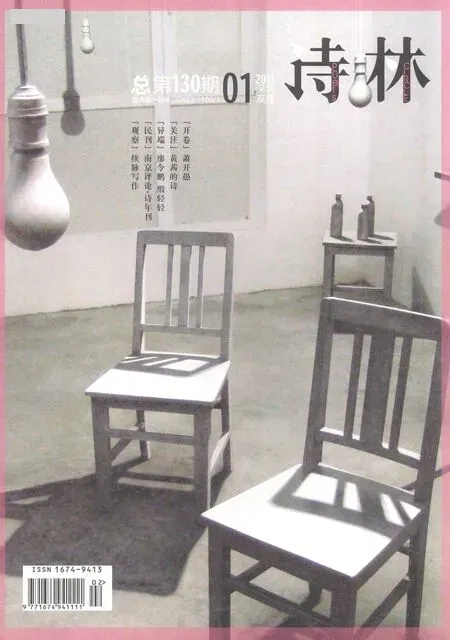胡桑詩選
胡桑詩選
胡桑檔案
簡介:胡桑,1981年生于浙北湖州。先后求學于西安、上海。2007年至2008年,任教于泰國普吉島宋卡王子大學。現居上海。
詩觀:詩歌是一個自律的語言世界,它通過詞語,盡可能地向世界開放,并以自己的方式糾正世界。詩歌需要最大限度地開掘人類精神,在時間與超時間的雙向運動中萃取生命的本質。

惶然書
我迫不及待地完成。從地平線返回,
背負著夜的寂靜,那令人渴望的形式,
學習如何再一次進入生活。白晝永不消失,
就這樣存在著,像自己一樣盲目。
回到這張活下來的床,回到
食物的體內,一只鐘在拒絕時間,
我看見日子裂開。但你和我的
痛楚之間,一場風暴被目光熄滅。
各自的寧靜在風暴的中心完成。
我入住恐懼,敲開它的缺席,
喪失之風吹開了另一個建筑。
那些記憶裸露在一個空洞的下午,
它們在用另一個聲音說話,
走向野蠻,用借來的步子。
我逐漸變輕,但一個諾言回到我身上,
只要有一條縫隙,時間就不會自行消失。
在語法之外,搜尋一個句子。
語言坐在語言的臉上,它是藏于
自身的殺手,事物在四周懶散地走動,
那些秘密,無異于桌上的杯子和空氣。
“世界比我想象的還要突然。”
還要惶惑。它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變得短暫而遲緩,破碎在人群中,
使我更加惶惑。但我看見無數個未來。
與小跳跳漫步沙家浜
那么多風,吹散了革命。
事物緩緩展開,風一整塊掠過。
氣候在蘆葦中結巢,
竹橋架在歲月上,獨自風化。
它來自湖水和魚,那么深。
在人少的石路上,我扔掉上海,
找到了落葉一般的存在。
樹不說話,你的話很多,
但話語就像寧靜的雪。
“巨大的事物是對世界的一次沖擊。”
雪落下,重新安排我內心的秩序。
我們坐在石橋上,像兩只很瘦的風箏,
幾個女人快樂地走過,巨大的風車
由圖1(工藝流程簡圖)可知,主要增加的機泵有吸收塔塔底泵(4臺),尾氣增壓機(2臺),大約共增加了159.5kWh用電消耗,電耗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能耗消耗。
停在湖邊。語言慢慢凝聚。
善良就像天空,干凈起來。
就這樣,時間停了片刻。
世界大了許多。我感到無比羞愧。
幸福就像那些睡蓮,
你叫不出名字,但它們一直在生長。
褶皺書
一
收藏起聲音。這些名字
和一個空洞的下午,來自沉默的影子,
它們逐漸稀薄,無法聚集在窗口。
窗子上,一小片孤獨被生產,
時光在它身上打結,然后從咖啡中起飛,
棲止于女人的胸口,這是十年前
不再生長的歲月,魚網里溜走的一條銀魚
患上謊言癥,懂得了權力的藝術,
在女人的腹部優雅地行動。憂傷遲遲不來。
出租車司機緊握著生活的手掌,與游客閑聊,
那是一片腫大的林蔭,和密封的記憶,
半夜的欲望從霓虹燈中溢出,
沒有人被拯救,懶散的星期天已經死于節日。
一個肥皂的節日,在家庭的摩擦中萎縮,
憂傷早已到來。我們已經長大,順應了時鐘,
學會了濫用語言:溫柔猶如夜晚,粗暴猶如白晝。
“寂寞不可避免”,僅有的秘密丟失在競爭的途中,
事物日益笨拙,塵世的反諷充滿了門口。
二
鋪開一張紙,細微的褶皺里,歷史漏出來,
角落里保存過去的目光,憐憫和憤怒的雨。
表達提前到來,甚至不能感知,但它必須
被刺破。沒有疼痛,就沒有閃現的過去。
尚未破碎時,完整是一張色情的臉。
故鄉在霧中迷失了自己,永遠是異鄉。
“世界以恐怖玷污了我們的日子。”耳垂上的聲音
滴落,塵世一點也不危險,只有心靈警惕純潔。
但有兩個人超越了空間,和細若游絲的羞澀,
虛無并未吞沒兩個身體,和房間里的橘子。
事物在夾縫中到來,宇宙偏離了中心,
命運掛在眼淚上,燃燒得諱莫如深。
筆直的天空,在瞳仁上彎曲,悖謬才是
真正的命運,而最終的悖謬是沒有悖謬。
萬物終有結局,卻必須有所挽留,
它們消失的時刻踅入一小片燈光,初生的樹冠。
“我們都不是那么樂觀的人。”夜晚不喜歡
強制,它高傲、懶散,在露水中蜷起了自己。
三
但是,窗口的陽光并不平靜,掙扎著
像一種古老的瘋狂,舔著桌子上一只夢幻的水果。
來往的過客搶占了語言的客廳。一個簡單的穿衣過程
被一再回放,真理會從腋下墜落,變成觀眾的智慧。
一顆稚嫩的行星在樹葉間閃爍,敲打行人的脊背。
我們都是有限的人,在傍晚的弄堂里乘涼、隱秘接吻。
時代被謊言擊碎。“那么多幽閉時代的幸存者”
涌上街頭,秩序很不干凈,攜帶了太多受傷的灰燼。
每個人用自己的唾沫,煮一種私人的快樂,
整個人間,要一遍遍刪改,去除憂愁。
“從夢境中清醒過來,瘋狂占據了世界。”
眼瞼在哆嗦,夢的痕跡如此清晰,一張起皺的紙。
古老的預言占據了生命。有人會不再存在,
恐懼猶如邪惡的醫術,躲進藥方。我們尚未完
成自己。
如何完成自己?時間,一條堵住的下水道,
生活的局限在暗處回流,靈魂的漏洞或許更加麻煩。
紙張打開了,身體也打開了,痛苦在所難免,
迫不得已地折疊一下,這些獨一無二的痕跡,必須接受。
十一月五日午后,狂風大作
風,如一場暴雨掉在地上
打開了事物不同的心臟
這生長在安達曼海的透明孩子
清洗了城市,如同革命
知識分子們被吹散,撒落在路邊
夜色在眼里渾濁,那就是虛無
窗外是星期四,樹葉響動
窗口,電腦在謀殺世界
一個詞試圖回到家中
時間漂流在外,風襲來
剝去樂觀的惡,事物如同妻子
躺在床上,逐漸減壓
夜讀黃仲則
臨睡前,我找到一種語法,
它像八月的水果,裸露在月光里。
月光夜泊于翻譯之外,安慰一條江。
我希望像你一樣取悅于漢語,
再用詩句驚絕四座,治療疾病,
撫平創傷,哄著大陸入睡。
可你在一首詩的題目里病了,
且困頓于經濟,糾纏于倫理。
歡愉總是那么短暫,猶如重聚。
游歷大江南北時,你知道,
毀滅歷史的人輕易走在你前面,
正如病患先于早晨侵入你的病榻。
幽燕的沙塵如何開拓胸懷?
這是你的內疾,你珍惜中國
給你的一切,哪怕是絕望。
你答應語言,給她一個良好的歸宿。
你要把她嫁給日益貧瘠的北方,
給她一條古典的河,以及甜蜜的晚霞。
但被毀掉的歷史越來越沉重,蒼白,
就像陰暗的天氣,壓倒一個人的內心。
一個缺少漫游精神的民族孕育了多少游子。
在糧食上跋涉是最痛苦的。
透過昏黃的八月,你看到一塊大陸
正在下沉。沒有一段史詩能拉它一把。
格律詩滋養起來的心靈,脆弱就像西瓜,
一本短詩集放在臺燈下,我不忍心望見窗外密集的小區,
黃仲則,你用詩建造的房子,早就隨著你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