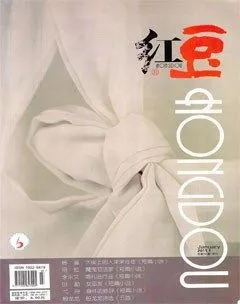身體的修辭(短篇小說)
弋舟,本名鄒弋舟,1972年生,祖籍江蘇無錫。2000開始小說創作,有長中短篇小說100余萬字刊于各類文學刊物,部分作品輯入若干選本。并被選刊轉載,著有長篇小說《蝌蚪》、《巴格達斜陽》、《跛足之年》。中國作協會員,甘肅省作協理事,甘肅省文學院為其成立“弋舟工作室”。獲第二屆“黃河文學獎”中短篇小說一等獎、第三屆“黃河文學獎”中短篇小說一等獎、敦煌文藝獎、金城文藝獎;中短篇小說集《我們的底牌》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就讀于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
我感到了骨頭的牙 咬住另一些陰天
緊緊地 不松口
從去年咬到今年
——沙戈《一年》
除了一雙眼睛,他的臉基本上被白色遮蓋住。無影燈下的白色非常耀眼,有種趾高氣揚的光芒。躺在那張古怪椅子上的她,很難把這個男人和昨夜聯系在一起,因此,她意識到,這個男人終究還是一個陌生人。他們認識一年了。當時,她恰好剛剛離異一年。同事把這個牙醫介紹給她,他們用了一年的時間,走到了昨夜。她知道自己并不年輕了,但依舊難以做到坦然。昨夜并不順利,起碼,在她是有種隱含的抵御。牙醫不能理解她的態度,也許還覺得那些額外的摩擦有點多余。牙醫吮吸她,她突然咝咝地吸起涼氣來。她無可遏制,那一瞬間,牙醫的舌頭糾纏而來時,有尖銳的痛,牽扯了她的某根神經。整個過程伴隨著她的吸氣聲。平靜下來后的牙醫發現了她的異樣。她沖進衛生間,拼命地漱口。牙醫免不了產生誤解,赤裸著趴在衛生間的門框上,禁不住責問她:“有必要嗎?”而她,顯然也明白了牙醫的不快,嘴里含著一口水,用手指盲目地示意。她在艱難地表達,仿佛急于澄清事實。而她要澄清的事實,無非是——她的某顆牙齒痛。可這有必要嗎?當眼前的男人終于露出恍然大悟的樣子時,她覺得有股無以復加的委屈淹沒了自己。看著她的眼眶涌出淚水,牙醫笑了。他果斷地決定:第二天就給她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此刻她躺在了這張古怪的椅子上。
來之前她有些猶豫。那個疼痛的根源,似乎已經模棱兩可了。其實,昨夜的痛是否真的來自—顆牙齒,她自己都不能完全確定。她指認著某顆牙齒,無非是需要把虛無的疼痛安放在一個合理的位置上。是牙醫,最終敲定了這個位置。昨夜,他打開了衛生間的浴霸,熾熱的光照耀著她大張著的口腔。“張大些,再大些。”牙醫用手卡住她的下頜。暴露的口腔,令她倍感羞辱。她覺得自己的疼痛迅速轉移了,流竄到某個永遠無法確認的部位。頜骨在隱隱作痛,發出細碎的咔嚓咔嚓聲。“就是它了,一顆齲齒。”牙醫卡著她悲傷的臉說。她怒不可遏地掙脫了自己的臉,長發掩蓋了她瞬間的憤怒。牙醫沒有察覺出她情緒的變化。在這個女人的口腔里,他發現了一顆齲齒,這讓他萌生出職業的優越感。這個女人一年來在他心目中所有的矜持于是都瓦解了。因此,牙醫以高高在上的口氣向她指出了一顆齲齒所能造成的危害:牙髓炎,關節炎,心骨膜炎乃至慢性腎炎以及全身的其他疾病。“這種細菌性疾病……”牙醫用近乎傲慢的口吻說。這種細菌性疾病——這樣的句子令她難堪,仿佛一語中的地定義了她的生活。同時,那最終波及全身的后果,也令她不寒而栗。那時她的心理幾乎崩潰了,不明白自己為何這樣,赤身裸體,待在一個陌生男人的家里,被檢測,并且被詆毀,生活中所有糾結著的哀傷,都凝聚在那顆糟糕的齲齒上。
今天早晨,他們在牙醫家門前分手。她鉆進出租車里,牙醫趴在車窗外,敲打著車窗玻璃,叮嚀她準時來醫院就診。她茫然地點了頭。然后她趕到了學校,她是一名小學教師。在校門口,她遇到了送兒子來上學的前夫。前夫匆匆向她打了聲招呼,一瞬間,那種無以復加的委屈又淹沒了她。這種細菌性疾病——她想起了牙醫的這句術語。目送著前夫躊躇滿志的背影,她怨懟地認為,這個人就是“這種細菌性疾病”的病灶,雖然如今已離她而去,卻給她的生活留下了一顆巨大的齲齒。
兒子由前夫撫養,上三年級,正是頑皮的時候,中午和她一同在學校吃飯,該午睡的時候,卻吵著要出去買雪糕。她神經質地煩躁起來。“雪糕會弄壞你的牙齒!”她惡狠狠地說,并且伸手卡住兒子的胖臉,把兒子的嘴掰開,檢查起兒子的牙齒。兒子粉嫩的口腔令她茫然,她分辨不出那些牙齒的優劣,只是感到失措的慌亂。直到兒子大吼著哭起來,她才落寞地釋放了兒子。
懷著這樣的情緒,她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一共是四節課,卻讓她有筋疲力盡之感。放學的時候,前夫并沒有來接兒子,他的母親,她曾經的婆婆,一臉冷漠地從她的手里接走了孫子。兒子向她告別,走出很遠了,突然回過頭朝她齜牙咧嘴地做了個鬼臉——他在炫耀自己的牙。她也想回敬兒子一下,但嘴角牽動了一下,終究只是露出了一絲苦笑。這時她已經忘記了和牙醫的約定。她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昨夜的效應此刻顯露出來。她感到了身體的異樣,畢竟,她是個離異了一年的女人。她在路邊的櫥窗里看到了自己,發現自己的衣服折皺很多。這讓她一陣不安,仿佛暴露了巨大的破綻。她隱約記起了昨夜那個牙醫兇猛的進攻以及自己本能的抵抗。她覺得自己的呼吸有些短促,并且有些輕微的耳鳴。她凝視櫥窗里的自己,依稀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閃而過。她回頭張望,看到前夫正捧著一束明媚的黃玫瑰站在馬路邊倉皇四顧。恰在這時手機響起來。起初她并沒有聽出對方的聲音,直到那個人理直氣壯地要求她,她才恍然大悟。“來治牙!”牙醫斬釘截鐵地說。
身下的這張椅子令她不安,她很容易就把它和記憶中的損害聯系在一起。她曾經躺在這樣的椅子上,張開雙腿,根除掉自己的第一個孩子。那時,她剛結婚不久,懷上了第一個孩子,但卻被診斷出了心臟病。醫生說她并不適宜生育,那樣很危險。于是只有打掉。她躺在婦科診室,和現在一樣,同樣需要暴露自己隱秘的洞穴,擴張,照射,將身體無望地呈現著。她身下的那張椅子,高大,冰冷,可以升降,唯一不同的是,有兩根支架,用來惡毒地舉起她的雙腿,這唯一的不同并不能把它和眼下的這張椅子區別開。它們的本質是相同的,強硬,不由分說,充滿了機械與醫學的暴力,能夠迅速剝奪人的尊嚴。她覺得自己被這張椅子綁架了,被無形地勒索著。
被白色包裹的牙醫與昨夜判若兩人,甚至他的聲音也在口罩后面發生了改變:“張嘴,別緊張。”——有股椅子的味兒。可是她反而更緊張了,雙手不由自主地攥緊了椅子的扶手。她的手指蒼白、修長,指甲里殘留著白色的粉筆末,右手中指的關節上還有一團批改作業時遺留下的紅色墨水。牙醫觀察到了她的緊張,有些正中下懷的愉快,隨即做出了令她吃驚的舉動。他捧起了她的手,放在掌心,溫柔地拍了拍。她感到突兀,心臟一陣抽搐。她似乎厭惡牙醫的這個舉動,但卻用力地握住了對方的手。牙醫在口罩后滿意地笑了,發出被遮蔽的咯咯聲。仿佛得到了許可,他終于肆無忌憚地探究起她來。她覺得,牙醫的腦袋幾乎完全扎進了自己的口腔。“很糟糕,嗯,很糟糕……”牙醫的聲音甕聲甕氣地回響在她的口腔里。他開始使用工具了,口鏡,探針。一陣難以言傳的酸痛被這些工具激活,猖獗地蹦跳在她的神經上,然后直抵心臟。她不禁發出了呻吟般的嗚咽。牙醫卻因此變得興味盎然,饒有興致地越發鼓搗起來。她的口腔里有一個焦點,仿佛是她神經中樞的神秘按鈕,一經碰觸,就能令她徹底崩潰。牙醫持續地敲打這致命的地方,淺嘗輒止,鍥而不舍。他似乎是在考驗著她能忍受多久,也似乎是在檢驗著自己能堅持多久。
她流淚了,完全是生理性的。每一下敲打都令她痙攣,大張著的嘴呼嚕出含糊不清的聲音。她突然有了某種不可名狀的興奮,有種惡毒的摒棄一切的亢奮情緒風暴般地席卷了全身。她痛恨,同時也渴望這種施虐般的折磨。她認為生活對于她,就是一個反復施虐的過程。起初是心臟病,莫名其妙地選中了她,她因此被扔在了婦科診室的椅子上,不得不掏空自己的子宮;她并不甘心,吃了三年的藥,把自己弄成了一個渾身散發著苦澀的女人,然后,冒著生命危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兒子。她精心將兒子喂養到小學三年級,卻被前夫帶離了身邊,為此她和前夫經歷了艱苦的訴訟,但最終的判決依然是——剝奪。她并不是—個前衛的女人,除了前夫,她在昨夜之前沒有和任何男人共宿過,她的道德觀排斥婚姻之外的床笫之歡,但是她終究被生活強硬地改造了……一切都仿佛喪失殆盡,活著的態度,與生俱來的榮辱觀,都呈現出一片狼藉。現在又是齲齒!“這種細菌性疾病”再一次將她扔到了毫無尊嚴的境地,被窺視,被玩味,被不由分說地侵犯。
牙醫終于放棄了他游戲般的診斷。現在,他決定填充那顆牙齒上的齲洞,仿佛是要給她身體的漏洞打上一個補丁。但她卻斷然拒絕了,粗暴地說:“拔掉!”她是脫口而出的,不假思索。“拔掉?”牙醫再一次捉住了她的手。但是她的手揮起來,堅決地說:“拔掉!”“嗯,沒有炎癥,可以拔——也好,一勞永逸。”牙醫執著地捕捉著她揚在空中的手,抓住,握緊,迎合著她。不錯,一勞永逸,這正是她此刻的想法。
她被注射了麻藥。注射前,牙醫詢問了她的病史,她隱瞞了自己的心臟病。她并不是有意要隱瞞,她只是感到厭倦,她不愿把自己想象得千瘡百孔。麻藥讓她的知覺空曠。她感到口腔沉重,像是塞進了一顆鉛球,仿佛有一個粗魯的大漢,在她的嘴里伐木。她隱約覺得自己的骨頭被撼動了,身體的一部分被連根拔起。
那顆齲齒終于出現在她眼前,帶著一縷血絲,當啷一聲,掉在一只金屬托盤里。看著這顆脫離了自己的牙齒,咬著一團紗布的她,心情在剎那間抑郁起來。“要嗎?”牙醫的聲音仿佛無限遙遠。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費力地表示出了她要。于是,拔掉的齲齒連同進入過她口腔的那些器械,被裝進了一次性的盒子里。“這只盒子你帶走,下次復診時帶上。”牙醫突然變得有些冷漠了,恰如一個男人房事后慣常的那樣不耐煩,也許是拔牙的過程讓他回到了自己的職業角色中。他機械地叮囑了她一些注意事項:不要做激烈的運動,勿高聲談笑,不要用舌頭舐創口,兩小時后方可進食等,總之,一切都需要暫時地改變,一切都亂了。她依舊躺在那張古怪的椅子里,發現自己已經被汗水浸透,身體像經歷了一場骯臟的戰爭那樣無力自拔,所有的洞穴都麻木并且凌亂。牙醫還說了一些話,但她完全聽不清楚了,耳朵里一片蜂鳴。她的臉色灰白,表情渙散,眼角的細紋在無影燈下浮現出來,似乎還在蛇游著蔓延,這令她的臉看起來仿佛正在不可逆轉地龜裂。她可是真的并不年輕啦!牙醫在內心感嘆著。兩人之間特殊的關系,使牙醫忽略了眼前這個女病人的異樣。
后來,她捧著那只一次性盒子離開了診室。牙醫追出來,塞給她一樣東西。那樣東西藏在一只裝藥片的袋子里,因此她很自然地將它當做了藥片。她很疲憊,有些遲鈍,連禮貌性的告別都沒有,就迅速走出了醫院。她是走得有些急了,仿佛要立刻擺脫什么。但是她全身一點力氣也沒有,一陣決步后,她只得在醫院門前蹲了下來。
此刻已經是黃昏了,天邊有一團烏云遮住了夕陽。
她蹲在路邊,頭垂在懷里,覺得自己像一塊被壓縮在罐頭里的肉。她知道自己的姿勢很不雅觀,平時她非常討厭蹲姿,但現在她心力交瘁,心臟的壓力迫使她放棄掉內心的好惡。她蹲在那里,很委頓,很哀傷。稍微緩過些勁兒,她就頑固地站了起來。一陣頭暈目眩,她覺得世界有一瞬間是顛倒著的。此刻她愣了一下,以為自己產生了幻覺,因為她在窒息中又一次看到了前夫的背影。那個熟悉的背影和全世界一同倒立著,在她眼里旋轉了一圈,才腳踏實地了,但是依然在左右晃動,世界宛如波濤蕩漾的海面。
果然是前夫。她略感驚訝,今天實在是蹊蹺,他們居然第二次不期而遇。正當她恍惚的時候,前夫恰好回頭了,一眼就看到她。他們距離并不遠。也就十來步的樣子,但彼此的眼神卻仿佛是無盡的眺望。很顯然,前夫有些尷尬,他在猶豫,是不是該過來打個招呼。她卻異常平靜,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夫胸前的那捧玫瑰上了,那一團很大的黃色,完全充斥在她的視覺里。她想,他就這樣捧著這些花在街上亂轉嗎?他不是這樣的人啊,以前鮮花是會令他害羞的,他是一個恥于把自己和華麗聯系在一起的男人。她嘴里緊咬著的那團紗布,已經被唾液浸透了,藥水的氣味混合著血腥,辛辣無比,嗆得她咳嗽起來。前夫終于走了過來,不過搶先到達的還是那捧黃玫瑰。他說:“很巧啊?”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該告訴他自己剛剛拔了一顆牙齒,她有這樣的愿望,甚至還很迫切。但是她欲言又止。
這時一個年輕女人從她身后沖了上來,幾乎是蠻橫地插在了他們之間。于是,前夫胸前的那捧花轉移到了這個女人的懷里。她立刻就明白了眼前的局面,手捧鮮花的前夫,是在等這個女人。女人對前夫熱烈地說著話,不經意地一回頭,就讓她感到了自卑。她覺得這個女人真年輕啊,完全還是個孩子,你看看,她還穿著那種有卡通圖案的褲子!可是這和自己又有什么關系呢?但是她卻沒來由地火了,隔著年輕女人,突然厲聲向前夫吼道:“你還有一點責任心沒有?你就是這樣帶兒子的嗎?你把他一個人扔在家里,你也做得出……”她的情緒不可自控,麻木的口腔讓她發出的每一個字都顯得像石頭一樣渾濁有力,她覺得快要上不來氣了,只能一邊吼一邊用力呼吸。結果,那團浸著血的紗布從嘴里飛了出來,居然飛過年輕女人的肩頭,跌落在那捧玫瑰花里。年輕女人驚叫了一聲,這令她無地自容,同時也加劇了她的沖動。她繼續激烈地斥責:“你知道兒子的功課已經有多糟糕了嗎?你現在應當待在他身邊,那才是你正確的地方!你不愿為他負責,為什么當初要搶走他?”前夫的臉憋出了紫色,他不能理解她此刻的態度,他從未見到過她如此暴怒的樣子,即使在他們關系最惡劣的時候,她也沒有這樣威風凜凜過。
手捧鮮花的女人嚇壞了,試圖拉著前夫離開,但剛一抬腳,就被她兇狠地阻擋住。她攔在他們面前,咄咄逼人地迫近年輕女人的臉。當她們近距離對視的一瞬間,她被年輕女人眼里那種不易察覺的輕蔑給激怒了——她輕蔑什么?她懂什么?一個穿著卡通圖案褲子的小孩!她將自己所有的憤恨都歸咎于這個年輕的女人。雖然殘存的理智告訴她,自己并沒有任何權利,但是這又如何?即使對方真的無辜,此刻她也需要將自己的憤怒有所針對地傾瀉出來。有那么一刻,她似乎平靜了下來。其實她是在醞釀。她醞釀著的,是一口含著血的唾沫。她覺得自己的口腔里有一個源泉,那是她身體里的洞,所有的一切都從那里汩汩流出。當她覺得這口唾沫已足夠充沛的時候,她對準年輕女人的臉吐了出去。但她沒有勇氣去看自己這口唾沫達到的效果。她在一瞬間吐空了自己,明白自己做了不可思議的野蠻的事情。她拔腳欲走,剛剛轉身,卻癱軟在地。她覺得自己的胸腔有種緊縮感,隨即一種壓榨性的疼痛貫穿了她的肺腑。她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心臟病突發了。雖然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診斷出了這種疾病,但從來都沒有發作過,疾病始終只是張著隱形的翅膀威脅和恐嚇著她,讓她活在陰影里,時隔多年,今天,它終于降臨了。她甚至有種千回百轉的感慨,禁不住淚流滿面。
她發現自己的四周迅速聚攏了一群人。最早貼近她的,是一個老年男人,年紀很大,幾乎可以做她的父親了,還穿著那種豎格條紋的病號服,看來是醫院的病人。老頭將她的身體扳成側臥的姿勢,用自己的腿靠在她的脖子上,以與實際年齡不符的洪亮嗓門大聲對圍觀的人宣布:“我要給她急救。”然后,居然伸手去松她的腰帶。她的意識正在逐漸喪失,那只扯在自己腰帶上的手卻令她驟然復蘇了。她神奇地坐直了身子,令她欣慰的是,此刻前夫向她伸出了援手。他從身后抱住了她,雙手插在她的腋下,協助她站了起來。那個老頭立刻大聲疾呼道:“你這樣做會要她命的!她必須就地躺著!”老頭是在警告前夫。盡管她知道老頭言之有理,指出的是一個重要的常識,但卻非常反感老頭的態度。因為當前夫的手插在她腋下的一剎那,她感到了洶涌的傷心,可是她多么渴望這樣的有所依托的傷心。所以她反感老頭的干涉,仿佛對方是要驅散自己的希望。她配合著前夫,努力站穩身子,懷著一種優勝者的近乎炫耀的情緒,向圍觀者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她要表達的立場是——他們,她,還有前夫,他們是一個共同體。
一切宛如奇跡。在前夫的攙扶下,她居然緩步向醫院里走去。好事者尾隨著他們;那個老頭興奮地大張著嘴,喋喋不休地說:“看著吧看著吧,她就要死了!她走不了幾步啦……”他甚至大聲數著她的步子;還有,那個年輕女人,收拾起所有委屈,臉上掛著殘留的血沫,手捧著黃色的玫瑰,順從地跟在身后——她都有些憐惜起這個年輕女人了。以她為中心,一支隊伍形成了。在她的意識里,這支隊伍有種隱隱的莊重之感,仿佛浩浩蕩蕩,如同一場肅穆的儀式。她被自己感動了。她覺得自己是用生命為代價進行著一場跋涉,好像童話里的人魚,每一步,都走在刀刃上。她已經感覺不到心臟的壓力,某種玄秘的力量替代了心臟,支撐著她的肉體。她動情地將頭依靠在前夫的肩上,那一刻,她覺得原諒了生命中的一切,非常甜蜜。
眼前出現了醫生。她有片刻的迷惘,任由醫生們把她放在了一張推車上。但是她很快驚醒,急迫地去尋找前夫,當她終于發覺自己已經無法支配自己的身體時,那種巨大的無可轉圜的殘酷的無能為力,鋪天蓋地而來。
四周都是忙碌的白影,有人在往她的舌下塞藥片。她依稀看到了前夫,很模糊,像是映在櫥窗里的影子,她看到,有一團朦朧的黃色偎依在前夫的懷里,前夫在撫慰著那團黃色,她都能想象出前夫的神態了,一定是一臉的小心,低聲下氣。想到這兒,她甚至想笑了,恍惚著在心里嘀咕:“這下,你可是有了大麻煩了……”
依然是除了一雙眼睛,他的臉基本上被白色遮蓋住。無影燈下的白色非常耀眼,有種趾高氣揚的光芒。
看到她蘇醒過來,牙醫如釋重負地捂住自己的臉。
事實是,她連那張古怪的椅子都沒有下來,就直接昏厥了過去。心臟病發作得令人措手不及,幾乎沒有任何先兆,而且,當時牙醫完全沉溺在某種違背醫學原則的興致勃勃中,根本沒有注意到她的變化。當那顆齲齒剛剛脫離她的牙槽,她就不省人事了。
牙醫被嚇壞了,對于自己的輕率追悔莫及,他明白一場置入死亡的事故意味著什么。她被送進了搶救室。整個搶救過程牙醫都守在旁邊,因此,牙醫在忐忑地祈禱之余,也目睹了一個最奇怪的昏迷者所表現出的癥狀。她面色蒼白,嘴唇發紫,仿佛化了濃艷、奇異的戲妝,而且,喪失了意識的她,居然有著豐富多彩的夸張表情,時而哀傷,時而喜悅,有那么一刻,她還綻露出和煦的微笑,這一切,都令她宛如一個正在表演的演員,而她頭頂的無影燈,也恰如舞臺上孤獨的燈光。其他醫生無暇他顧,只有袖手旁觀的牙醫捕捉到了她的每一個表情。牙醫不能理解她的表現,他的醫學知識不足以為他解釋這其中的奧秘。牙醫把這一切當做自己的幻覺了,他想自己一定是被恐懼搞暈頭了。
她蘇醒過來,仿佛穿越了一條無盡的隧道。這是一條環形的隧道,光滑,緊迫,卻又布滿粗糲的阻礙,如同母親的產道,從生到死,周而復始,終點即是起點。她的意識順暢地與昏迷之前的記憶對接起來,她明白自己經歷和臆造了什么,她的心臟一度停止了跳動,在那條死亡的通道上她洞見了自己內心所有的秘密。她的確是被掏空了,就像在譫妄中奮力吐出那口血水、向整個世界唾棄一樣,此刻,她變得空空如也。
她繼續留在醫院里治療。第二天,她的同事來看她。這個同事正是她和牙醫的介紹人。她一眼就看出了這里面的原因,她知道,牙醫把同事叫來,是基于一種怎樣的邏輯——喏,看看你給我介紹的人吧!這也正是牙醫的想法。牙醫很憤懣,他不能原諒,自己結識的這個女人居然有嚴重的心臟病,他本來是很認真的!他覺得自己被欺騙了,有種蒙受損失后的追究心理。同事帶來了一束花,令她吃驚的是,那居然是一束黃玫瑰。由于受到了牙醫的埋怨,同事的情緒有些低落,只是簡單地慰問了她幾句,就匆匆告辭了。臨走前,同事對她說起了她的兒子:“你兒子今天沒來上學,你通知他們了嗎?”她知道,同事所說的“他們”,是包含著她的前夫的。在這座城市,除了“他們”,她再也沒有其他的親人了,如今她出了事情,在所有人看來,最應當被通知的,就是——他們。一念及此,她本來空空如也的心立刻灌滿了悲傷。她始終一言不發,像一個真正的病人那樣虛弱。
同事走后,牙醫來到了她的身邊。他依然把自己包裹在白色后面,他這樣的裝扮,令她根本想不起他真實的面貌了。他很專業地翻了翻她的眼皮,又將手指搭在她脖子的動脈上測了測,儼然一副主治醫生的派頭,盡管,他只是一名牙醫。接著牙醫又看了看液體瓶上貼著的配方,然后,他將一只藥片袋子塞在她枕邊。那里面放著的,是一件禮物吧,也許是一枚寶石戒指。牙醫決定用這枚戒指結束他們一年來的交往。結果是,這只袋子和她昏迷中經歷的某個細節重疊了,她不由得一陣心悸,有種夢魘走進現實的驚懼。同時,這也令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呢?”她說出了蘇醒后的第一句話。“什么?”牙醫疑惑不解,而且,他也沒有足夠的耐心去搞明白。“我的牙,我的——齲齒。”她嚴肅地說。“牙?”牙醫愣了片刻才回過神來,他有些惱火,仿佛聽到的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問題,所以他沒好氣地質問道:“你還要它干什么?不過是一顆齲齒!”她深深地吸了口氣,這一刻,她才充分感覺到了自己口腔里缺失了某樣東西,當她開口的時候,那個豁口仿佛刮過了一陣風。她在這陣風的伴隨下,空空蕩蕩地說:
“它是我的牙,是我身體的一部分,盡管,它是一顆齲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