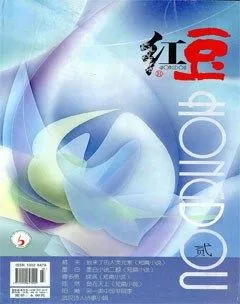山里山外(外兩篇)
李杰玲,女,漢族,現就讀于上海師大。在《古典文學知識》、《文史知識》和《貴州社會科學》等核心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并有文學作品和譯文發表于《譯林》、《寫作》、《廣西文學》、《廣西日報》等刊物,有作品被《讀者》轉載。
外公/今天陽光這么暖/你冷不冷?/今天/你送給我的眼睛/許許多多流星/又大又亮
外公/今天陽光這么暖/你冷不冷?/風一次次摸遍藤椅/她記得你的溫度/讓我順著風向找你/你一定要一定要/坐在門口等我
外公/今天陽光這么暖/你冷不冷?/讓我順著山路/再找你一次/你千萬不要把門關了/你可以把目光/綠綠地伸出冬天的土地/你總擔心我們迷路/找不到你
外公/今天陽光這么暖/你冷不冷?/我知道你就站在墻角/靜悄悄地等/你數著山的鳥聲/你數著人的腳步
外公/讓我順著山路/再找你一次
——題記
我所生活的城市不遠處有山,站在六樓以上隱約可見它們起伏的線條。我沾滿了二十多年城市的灰塵,那些山的翠綠欲滴是遙遠的風景。以前的我,不大關心它們,它們不會說話,不會吵吵嚷嚷地引起我的注意,它們也不會走到我面前,要我欣賞它們。所以我和山,是生活中的兩條平行線。
但我習慣了它們的存在,它們遠遠地、淡淡地存在,正如我習慣了生活中有外公的存在。他總是沉默地坐在大樓門口旁的藤椅上,看書、抽煙;抽煙、看書。我們都極力反對他抽煙。面對我們一次次的反對,他每次都是略帶笨拙地笑笑,然后仍然緩緩地抽出一根煙,小心地點上。在煙霧里,他略帶歉意地看著我們。多年后我才明白,煙,是外公的語言;煙,是外公的歷史。沉重如山的他,如何能離開煙?
但是當時的我不懂,我忙得像一個小小的加速的鬧鐘,每天都要在書本、試卷里熱熱鬧鬧地“響”上許多許多次。
外公卻一直很安靜,安靜得像遠處的山。跑來跑去的我只在喘會兒氣兒的時候才抬起頭,看一眼遠處的翠綠,一如我只會在假期里,才回到遠處的鄉村看望他。
外公是一根瘦削的古藤,固執地纏在鄉村這棵無語的大樹上,哪怕他的枝葉都已延伸到燈紅酒綠的城市,并已扎下各自的根。我們費盡口舌,他仍然不肯挪一挪,城市的繁華于他,遠不如無聲的田地。他的固執就像他門前不遠處的山一樣,移不動。
外公的生活簡淡如山,除了吃飯和散步的時間他會離開那把藤椅、書和煙之外,其他的時候,他總是沉默地坐著,看書、抽煙、咳嗽;咳嗽、抽煙、看書。偶爾地,他會抬起頭,看山。他和山的對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長。后來他明顯地老了,視力下降,無法看書了,他就看山。他只能看山了,山很大,山很綠啊,誰的眼睛會忽略它們呢?但是我的外公啊,他一天天瘦了,一天天小了,小得那么輕易地就會被忙碌的子女們不經意地忽略,一個是大學教授、一個是公務員、一個是上班族……都很忙。
“我很好的。”他在電話里用力地大聲喊,“我很好啊,你們忙,不用回來啊。我還能吃很多,牛奶、半碗米飯……”
山還青著,山還綠著……
我原以為,外公會和大山一樣,只要我張開眼睛往門口的方向一看,他總會在那里……
許久許久之后我仍然沒有完全接受這個事實:山還在,外公卻不在了。他說了,第二天他要親自去耕種過的水田,看看別人把那塊地耕得怎樣了。但是,他沒有走到水田里,他,走到了山里。
按照鄉村的習俗,他和他的煙,都默默地躺在了山上。
山沒有走,他走了。他離開了我們,跳到了山的懷里,靜靜地。
他仿佛在說:“山不過來,而我,總要過去……”
他真的就這樣過去了。他就這樣,猛地從我們的生活中抽身離去,讓我猝不及防;他就這樣,猛地在我的心上,移來了一座悲傷的大山。外公走后的日子有時會變得很粗糲,像棱角尖銳的石子,“呼啦”地擦過我的肌膚。
從此之后的山,多了一個外公。山不再遙遠,不再是簡單的粗線條。我至今不會抽煙,但是外公的煙啊,生活的舌尖終于慢慢地把它的味道告訴了我。外公的煙,將永遠繚繞我的生活、我的青山。
母親的孩子
母親彎下腰的時候,黃昏就低下來了。
母親坐在草坪的石埂上,把粗糙的食指伸進鳥籠逗小鳥兒玩——這是她們幾乎每天都要做的游戲。每當這時,籠中的兩只小鸚鵡就格外高興地叫起來、跳起來,用尖尖的小嘴兒搶著啄母親的手指,母親就輕輕地喚它們的小名,像哄小時候的我一樣,哄著它們,逗得它們很開心,“吱吱呀呀”地回應,仿佛能聽懂母親發出的每一個音節。
每當這時,母親的目光就會像六月的湖水,悄悄地漫過整個黃昏。
我有時候會陪母親在黃昏里坐坐。如果我在,母親總會把鳥籠推到我跟前,靜靜地看著我和小鳥兒玩,從不跟我爭。她安靜地坐在我身邊,臉上的每一跟橫線豎線都溢出笑意。但是這樣的時候很少。家離圖書館很近,騎車只要十來分鐘,除了上課,我基本都待在圖書館里,忙著自己的事情——考試、論文、作業,總是做不完。于是許多個黃昏,就只有小鳥兒陪著母親,陪著她,等我回家。
我從圖書館回來時,母親的耳朵遠遠的就能捕捉到我的車鈴聲。我還沒走近,她就會站起來,轉過身,面向我,笑著,迎接我,留下兩只小鳥兒在籠子里“吱吱”亂叫,尋找那突然失去蹤影的粗糙手指。
然后,母親小跑上來,拉下我肩上重重的書包。她就這樣,一手提著書包,一手提著鳥籠,等我把自行車放好,一起進門。
做晚飯時,母親就像小鳥兒一樣,高興地不停地說話,說她的工作,說她接觸的各種各樣的學生,說生活……母親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呢,一邊看看電視,一邊看看母親,有時插上一兩句話。然而大部分時間是她在說,我就笑著,耐心地聽她說。
除此之外,黃昏很安靜。
后來,我到了另一座城市求學,家鄉的黃昏,就只有母親和小鳥了。父親在電話里說,母親還是準時坐在門外的草坪上,每每都要坐到天黑,聽到車鈴聲,她就習慣性地站起來,往小路上看。我知道,坐在黃昏里的母親依然會把自己的手指伸進籠子里給小鳥兒啄,把思念也遞給了小鳥兒一可是,小鳥兒們又怎能啄得動她的思念?
我背著母親的牽掛來到了另一座遙遠的城市另一所高校。這所學校里也有一個大草坪,每次黃昏經過,看到小鳥兒蹦跳,我就忍不住靜靜地站上一會兒,看它們覓食、蹦跳和歡叫。它們,多么熟悉,像我的親人。
媽媽啊,我想,我要給家里的兩只小鸚鵡重新取名了,一個叫姐姐,一個叫妹妹……
愛·護
每個人成長的路上都會有難忘的人、難忘的事。二舅媽是我永難忘記的一個。我們相處的時間其實不多,因為兩家離得很遠。說話也不很多,她總是忙前忙后。但是她,卻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默默地給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課。
二舅媽是護士,在醫院里是,在家里,也是。
外婆病重的那年,就住在她家里。我有三個舅舅,三個舅舅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工作,工作都很忙。二舅媽很干脆,一挽袖子,說:“我是護士,就讓媽住我們家,方便照顧。”
其實二舅媽也很忙,那時孩子也還小,也需要照顧,二舅舅公務繁忙,家里的事兒,基本都由二舅媽操勞。那時外婆已住了很長時間的院,院里冷清,夜里沒人說話,外婆有些孤單,但她忍住沒有說,怕增加家里人的負擔。但是細心的二舅媽察覺到了,她二話沒說,和院里的主治醫生談了一下,就把外婆接回家照顧了。
二舅媽家住小區六樓,那時沒有電梯,外婆體質虛弱,爬上六樓是很吃力的。二舅媽向來做事干脆利落,她蹲下來,不顧外婆再三推讓反對,就背上了她,慢慢挪上了六樓的家門口。
老人在家里開心多了,然而時間長了,也悶。白天二舅要上班,舅媽就盡量調休,和同事換班,白天待在家里,晚上上班。孩子白天在幼兒園,她就專心照顧外婆。聽診器、體溫計、注射器、各種藥片……家里一應俱全。每天,她都要準時給外婆量血壓、測體溫,或者打針,病情一有變化,就馬上通知醫生。為了讓外婆經常呼吸到新鮮空氣,解解悶,二舅媽還時不時主動要求背外婆下樓走走、散散步。
如此日復一日,她成了院里、小區里的榜樣,知道的,都夸她。可是二舅媽忙啊,忙得甚至沒有時間和鄰里、同事好好聊聊天,面對別人的夸贊,她只是淡淡地笑笑,轉身又忙去了。
生活本是不可測量的,但是二舅媽,卻用她的體溫計,在每一個平常的日子里,不僅給醫院里陌生的病人,也給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心,量了一個溫度,讓我們知道,我們的心,可以有多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