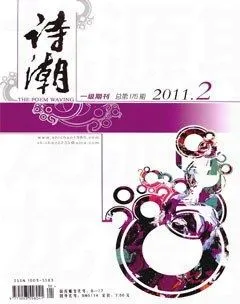第三只眼睛
“但在我眼里春天可見的臉龐/悲傷如遺忘之夢”。
——[俄羅斯]瓦列里·勃留索夫
詩名是顧彬的觀點,“沒有英雄的詩”了。
顧彬作為德國漢學(xué)家密切關(guān)注中國的文學(xué),他以一句“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是垃圾”的棒殺聞名于世,但也成了在一次次采訪中他無法回避的話題,不得不一次次負(fù)累地解釋(他只是指個別作家)。但他說,這些年中國詩歌還有一些可以和世界上最好詩人的作品相比。
他又說“沒有英雄的詩”了。
第一節(jié)首句“魚受到了警告”,令人深思回味。接下去寫了與一撥詩人同游慕田峪長城,王家新同往否,不得而知;但他顯然讀過王家新一首寫魚的詩——中國畫中的一尾魚,帶來了河流,給詩人帶來了滋潤(指文化藝術(shù));在《沒有英雄的詩(節(jié)選)》中的“魚”,當(dāng)喻指為“詩”。
顧彬替中國當(dāng)代詩歌把脈。他說一些詩人已沒有“釣具”和“故鄉(xiāng)”了——直接挑戰(zhàn)中國當(dāng)代一些詩人:詩的語言、技巧不行,詩的精神品質(zhì)也不行,接著舉例論證:其一,詩人作詩的任意性“在長城上他們?nèi)我?拋出詩行,/隨后抱怨/此處也無人上鉤。”沒人接茬,又能怪誰?一個“也”字特別搶眼;其二,詩寫得沒有刺激人的新意,徒然是“烤熟的鱒魚”。他寫詩人只會耍嘴皮,不會干“抹灰漿”等實事,即使做也只是搞一些沒有新鮮感的“鱒魚五重奏”,不過是自娛自樂的活動。之后,顧彬?qū)懰南M娙藗兒尾挥懻撘幌略姼柽吘壔膯栴},保留它“渴望永久的居留權(quán)?”末節(jié),顧彬替中國當(dāng)代詩歌開藥方。“詩行不是英雄”的原因是,“它尋覓輕巧的形式/猶如魚尋求柔和的火”這怎么行呢?他意思是“如果它們?nèi)淌芨呱胶烷L城,來承受眼的饑渴和胃的貪欲”,如何?承受高寒惡劣生存環(huán)境的煎熬,吸納歷史滄桑感和虛無的痛苦,以提煉出人類終極的詩學(xué)意義。也許不無出路,亦如他所說:“究竟泰初有言/還是太初有鰭?”他期望魚“鰭”能生翼,中國當(dāng)代詩歌或成為堅忍的魚、奮飛的魚,“怒而飛,其翼者若垂天之云”,且“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6a1fb2de607e130223f5697309d00059c0d1b639ae6694348d1f2957cbf3faac里”,抑或成為莊子《逍遙游》中的鯤鵬?而“泰初有言”之“有”:無名無有;一之所起,此“一”即“道”也(《莊子·天地》)。顧彬希望詩人要對“道”的堅守,使之“性修反(返)德”,德至同于泰初,然后才有飛翔的“鰭”。倘不如此,會不會成為嚴(yán)力一首令人絕望的《釣魚》的“魚”:“經(jīng)過了許多年的等待/我的魚鉤啊/終于在沒有魚的池塘里/自己游起來/但在更多年的游動之后/它滿臉無奈地/一口吞下自己。”當(dāng)然,詩人們不想成為這樣的“魚鉤”。
顧彬在中國“耍大牌”,不妨看看他寫詩的手腕如何?
他的一首《于道觀中》寫在樂山見道姑接手機,頗為現(xiàn)代:“她纖細(xì)的左手中,輕握一部白色乖巧的手機”“她在與誰作答?遠(yuǎn)方的神”,是不是離道遠(yuǎn)矣?倘若你先讀到顧彬等一行人,進道觀是先穿過后門,又“本該左行,卻誤入右門”時被道姑喝住:“讓我們回轉(zhuǎn)過去,重新邁出生命的步伐……”;“我們在太一打聽太一/是神還是榜樣”時,她說,“只是榜樣。”你就不會這樣想,因為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正道直行且又道行極深的道姑,你還可見到“她的手指可通過220伏電壓,掌控高峰的道觀,/她愿意為我們這樣的人醫(yī)治,用她的左手和右手。”柏樺在《顧彬詩選》序二里說這首詩,顧彬“先由德文寫就,旋即又被他親手譯成中文……可見其用漢語寫詩的駭人魅力”。
我們不妨看看他其他的詩。
他的《耶魯》寫一種絕望:“他只跟別人分享灰燼/在陌生的壇子里。”
《鴉樹》中他質(zhì)言:“烏鴉實存,為何烏鴉,諱言烏鴉?”烏鴉這不吉祥之鳥,它們生存之道令人類敬畏:不怕大雪、狂風(fēng),以波恩和萊比錫之間的每棵樹為家;“飛過風(fēng)和雨……不怕黑暗和空虛。它們稠密的羽毛屬于鄰近的大地”,這使人想起了西川《夕光中蝙蝠》的結(jié)尾:“夕光在胡同里布下陰影/也為那些蝙蝠鍍上金衣/它們翻飛在那油漆剝落的街門外/對于命運卻沉默不語”,一樣令人驚異!
《滅火騎士——致翟永明》,他記錄一次郊游、拍照,或一次演講,未了寫道:“從此我們懸在世界的上方/輾轉(zhuǎn)不眠,/夜里在寒光中/尋找住房。”顧彬的詩給人一種精神的震懾和警醒,這是國內(nèi)詩人所匱乏的。
即便是寫他私密性的《雙人床》,寫一個老男人愛的隱秘:“我樂意在你手中,/而不聽窗外的貓叫,/我愿看見你,看你來臨,/身穿玫瑰/走進一個夜里”之歡愉;“最后的荊棘冬天折斷”之絕望,亦絕不低俗,很美。
德國是一個為世界貢獻出歌德、托馬斯·曼、卡夫卡的國度,德國漢學(xué)家、詩人顧彬?qū)ξ膶W(xué)的判斷自然比國內(nèi)的批評家要苛刻得多,不管是作為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和詩歌的第三只眼睛,還是作為人性的第三只眼睛,他仿佛是個異數(shù),讓人警醒、反思……
這是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我想起了北島一首《無題》的開頭:他睜開第三只眼睛/那顆頭上的星辰/來自東西方相向的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