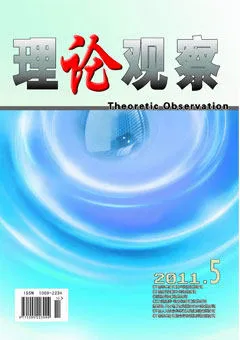韓國古代詩學的中國情結(jié)
[摘要]國古代詩學在其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批評對象、詩學理念及審美追求等諸多方面,與中國古代詩學有著與生俱來的親緣紐結(jié),因此整個韓國古代詩學中流溢著無法抹卻的中國情結(jié)。雖然二者存在著眾多相似、相類之處,但韓國古代詩學絕非中國古代詩學的簡單移植與翻版。韓國古代詩學接受中國古代詩學的過程,實質(zhì)上就是對中國古代詩學進行“主體間性”批評的過程。二者之間是一種共同參與,一種主體的分有、共享或一種共同創(chuàng)造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韓國古代詩學;中國古代詩學;中國情結(jié);主體間性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1)05 — 0065 — 04
朝鮮朝中期的詩學家洪萬宗在其《旬五志》中,概觀韓國古代文學的文脈歷程時曾經(jīng)說到:
我國自殷太師歌《麥秀》以來,世幕華風。文學之士前后相望······北學中原,得師友淵源之學;既東還,延引諸生,獎?wù)摮删汀ぁぁぁぁぁぶ廖页恼氯照瘢燃缃游洌暳_、麗而尤盛,亦不可一、二計也······近世東溟鄭公立幟詞擅,振耀一代,西漢之文,盛唐之詩,于斯復見。〔1〕
《麥秀》是韓國古代最早發(fā)生的文學文本之一,從那時起,韓國古代詩人就“世慕華風”。自高句麗、新羅至高麗的數(shù)百年間,“文學之士前后相望”,皆“北學中原,得師友淵源之學”,并傳之于后輩。到了朝鮮朝時期,文學之士更是“比肩接武”,與中國文學的互動,尤勝前朝。即便是在其“近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仍可欣賞到“西漢之文”與“盛唐之詩”的風采神韻。這足以說明韓國古代文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親緣關(guān)系。
韓國古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在創(chuàng)作上的“形似”,其根源在于二者深層的文學理念上的“神似”。換言之,韓國古代文學之所以“形似”于中國古代文學,是由于韓國古代詩學“神似”于中國古代詩學。因此,我們可以說韓國古代詩學有著濃濃的中國情結(jié)。
一、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的中國化
韓國古代詩學的形式與體制深受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召喚”,同時這種“召喚”也深深地契合了韓國古代詩學的審美“期待視野”,進而造成韓國古代詩學在感性直觀上始終彰顯出一抹靚麗的中國色彩。
其一,詩學話語。韓國古代詩學自其發(fā)生之日起,闡釋與倡揚其詩學思想的話語就一直使用漢語,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15世紀中葉韓國本民族語言文字創(chuàng)生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漢語言文字始終是韓國古代社會共同的書面語,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韓國古代詩學主導的話語形式。因此,韓國當代著名漢學家李炳漢曾言:“從很早以前,我們的祖先就使用漢語言文字來寫文章和作詩,并且欣賞和評論用漢字創(chuàng)作的詩文,建立了真正的韓國漢文學史的傳統(tǒng)。”〔2〕
其二,詩學體制。韓國當代著名詩學家趙鐘業(yè)曾言:“韓國之詩話起于高麗中葉,實蒙宋詩話之影響者也。”〔3〕縱觀整個韓國古代詩學的演進歷程,韓國古代詩論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深受宋代詩話的啟蒙,特別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六一詩話》的體制結(jié)構(gòu)是語錄體式的,即由一條條在內(nèi)容上互不相涉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每一則論詩條目,往往只論一人一事,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長短隨宜,應(yīng)變而制,富有彈性,優(yōu)游自在。如其第10則云: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弦。”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4〕
韓國古代詩家對這種論詩體制頗為青睞,從高麗時期李仁老《破閑集》、崔滋《補閑集》、李奎報《白云小說》與李齊賢《櫟翁稗說》,到朝鮮朝時期徐居正《東人詩話》、成伣《慵齋詩話》、李濟臣《清江詩話》、梁慶遇《霽湖詩話》、洪萬宗《小華詩評》、南龍翼《壺谷詩話》、洪重寅《東國詩話匯成》、金昌協(xié)《農(nóng)巖雜識》等等,都沿襲了中國古代詩話(特別是《六一詩話》)的論詩體制與方法,幾乎沒有什么新的變化與發(fā)展。如李仁老《破閑集》中有一則曰:
還康先生日用欲賦鷺鷥,每冒雨至天壽寺南溪上觀之,忽得一句云:“飛割碧山腰。”乃謂人曰:“今日始得古人所不到處,后當有奇才能續(xù)之。”仆以為此句誠未能卓越前輩而云爾者,蓋由苦吟得就耳。仆為之補云:“占巢喬木頂,飛割碧山腰。”夫如是一句置全篇中,其余粗備可也。正如珠草不枯,玉川自美。〔5〕
高麗詩家對歐陽修論詩體制的仿效,即便到了朝鮮李朝時期也沒有多大的改觀,徐居正《東人詩話》言:
文章所尚隨時不同。古今詩人推李、杜為首,然宋初楊大年以杜為“村夫子”,酷愛李長吉詩,時人效之。自歐、蘇、梅、黃一出,盡變其體。然學黃者尤多,江西宗派是已。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6〕
中國學者蔡鎮(zhèn)楚先生在論及中韓詩話的關(guān)聯(lián)時指出:“中國詩話論詩條目的組合方式,大致有并列式、承返式、復合交叉式、總分式等四種類型,而朝鮮詩話論詩條目的組合方式,則比較趨于單一化,大致采用并列式的條目組合。如徐居正的《東人詩話》,凡143則,大致按時間順序編排論詩條目,無須起、承、轉(zhuǎn)、合,隨手述錄,與宋人初期詩話一脈相承。”〔7〕這說明《六一詩話》所開創(chuàng)的“以資閑談”的隨筆式的論詩傳統(tǒng),作為一種“召喚結(jié)構(gòu)”,暗暗契合了韓國古代詩學的審美期待,并使之在韓國古代詩學的文化語境中相續(xù)相禪,生生不息,遂成為一種歷史文化的積淀。
其三,以詩論詩的習尚。“以詩論詩”是東方詩學獨有的文學批評形式,古代的中、日、韓等國均有此風習時尚。韓國古代詩學如李奎報《論詩》、金時習《學詩》與《感興詩》、洪良浩《詩解》、申緯《東人論詩絕句》與金正喜《論詩》等等,無不承襲了杜甫《戲為六絕句》與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之以詩論詩的批評樣式。
二、詩學內(nèi)容的中國元素
韓國古代詩學不僅在形式上有著濃烈的中國情結(jié),而且其詩學內(nèi)容的闡釋與衍展,同樣有中國元素的大量存在。
其一,專論中國古代詩家。韓國古代詩家在闡釋其詩學思想時,往往把中國古代的詩人詩作作為他們的論詩對象。如李仁老《破閑集》在研討“琢句之法”時云:
啄句之法,唯少陵獨盡其妙。如“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之類是已······及至蘇、黃,則使事亦精,逸氣橫出,啄句之妙,可以與少陵并駕。〔8〕
在此,李仁老認為在漢詩創(chuàng)作上,雕琢詩句的功夫當首推唐代大詩人杜甫,能“獨盡其妙”。惟有宋代的蘇軾與黃庭堅可與之比肩。
朝鮮朝李瀷《星湖僿說》論李白、杜甫、韓愈等中國詩人的條目,水準頗高,多有自得之見。其“李、杜、韓詩”條云:
屈原之作《離騷》,其志潔,故其稱物也芳,蘭蕙、菌蓀、揭車、杜蘅之屬,爛然于齒頰之間,其芬馥便覺襲人,所以為清迥孤絕,能瀉注胸臆之十怨九思也。后惟李白得其意,就萬匯間取其清明華彩馨香奇高陶鑄為詩料,一見可知為胸里水鏡,世外金骨也。茍非其物,雖原、白異材,亦何緣做此口氣乎?凡詩之能事,多在五字。〔9〕
李瀷對屈原《離騷》“其志潔,故其稱物也芳”的認知,其實就是承襲了中國古代詩學所強調(diào)的“文如其人”、“詩品出于人品”的倫理批評取向。為論證和強化這一理念,李瀷列舉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杰出詩人并結(jié)合其詩作來加以闡明。如此的論詩方式,在韓國古代詩學批評中,不勝枚舉。
其二,論韓國古代詩家時兼及中國詩人詩作。韓國古代詩論雖時常可見中國的“影子”,但其論詩的對象大多還是以本國、本民族的詩人詩作為主。由于中韓兩國文化上的淵源,許多著名的韓國古代詩家不僅曾到中國游歷,而且有的還師從中國詩人與學者,耳濡目染,師承遞傳,因而使得中國的詩學傳統(tǒng)漸染于韓國古代詩壇。故此,韓國古代詩家在評論韓國漢詩時,常常與中國古典詩歌進行比較,這樣既標示了韓國古代漢詩與中國的淵源,同時又試圖指出二者的異同。“李奎報《白云小說》、成伣《慵齋叢話》、金安老《龍泉談寂記》、李濟臣《清江詩話》、申欽《晴窗軟談》、樸永輔《綠帆詩話》等,每論朝鮮‘漢詩’,便涉于中國詩人、詩歌、詩風,論述精到。”〔10〕這在韓國古代詩學中是極為普遍的。高麗時期的崔滋非常推崇李奎報的詩歌,甚至認為李奎報的詩與唐代大詩人李白不相上下:
今世之為警句者,殆未免辛苦之病也。然庸才欲率意立成,則其語俚雜。俚雜之捷,不如善琢之為遲也。善琢茍至于極慮,恐見崔融借髓而死。文順公(李奎報)《北山親題》云:“山人不出山,古徑荒苔沒。應(yīng)恐紅塵人,欺我綠蘿月。”此詩置李白集中,未知孰是。〔11〕
又如徐居正在《東人詩話》中,把朝鮮詩人崔恒《詠黑豆》與蘇軾《詠海棠》及黃庭堅《詠茶蘼》相較:
古之詩人,托物取況,語多精切。如東坡《詠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以婦人譬花也。山谷《詠荼蘼》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以丈夫譬花也。崔文靖恒《詠黑豆》云:“白眼似嫌憎俗意,漆身還有報仇心。”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殆不讓二老。〔12〕
其三,使用與中國古代詩學相類的范疇。任何一詩學思想的成熟與詩學體系的完善,其最為鮮明的標志,就是用以闡發(fā)詩學理念的范疇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認同。韓國古代詩學所使用的范疇,幾乎與中國傳統(tǒng)的詩學范疇沒有多大差別。如崔滋《補閑集》言:
新警。如文順公《萬日寺樓》云:“渡了幾人舟自泛,噪殘孤虎鳥猶鳴。”
含蓄。如芮學士樂全《閑居》云:“萬里行裝春已暮,百年計活夜何長。”
精彩。如文順公《甘露寺》云:“霜花照日添秋露,海氣干云散夕霏。”
飄逸。如陳補闕《江上》云:“風吹釣叟帆邊雨,山染沙鷗影外秋。”
清遠。如皇祖《北山圣居寺》云:“別洞白云欹枕送,到山明月卷簾迎。”
感懷。如文順公《病中》云:“病憶故人空有淚,老思明主若為情。”〔13〕
以上品評文學風格的詩學范疇,在中國古代詩學批評中是極為常見的,韓國古代詩家借以品鑒本民族的詩人詩作,這既體現(xiàn)了中、韓古代詩學的親緣關(guān)系,同時也是中國傳統(tǒng)詩學范疇的生命力在韓國古代詩學語境中的綿延,體現(xiàn)了中韓傳統(tǒng)詩學的互動。這也從另一層面說明,中國古代詩學范疇在融入韓國古代詩學語境后,它不可避免地被植入了韓國本民族的文化色彩。
其四,“使事”、“用事”的中國元素。“使事”與“用事”是指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援引前人的典故,以增強文學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一種創(chuàng)作技巧與手法。此法在中國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由來已久,至唐宋達于頂峰,如唐之李商隱、宋之蘇軾、黃庭堅等可謂代表。韓國古代詩家在創(chuàng)作中也十分講究“用典”,徐居正《東人詩話》言:
古人作詩,無一句無來處。李政丞混《浮碧樓》詩:“永明寺中僧不見,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際,人斷小舟橫渡頭。長天去鳥欲何向,大野東風吹不休。往事微茫問無處,淡煙斜月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四句本韋蘇州“野渡無人舟自橫”,五、六句本陳后山“度鳥欲何向,奔云亦自閑”,七、八句又本李白“總為浮云蔽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句皆有來處,妝點自妙,格律自然森嚴。〔14〕
由此可見,韓國古代詩家作詩講究“句句皆有來處”,但其所來之處往往源于中國典故。對此,崔滋言:“凡為國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則六經(jīng)、三史;詩則《文選》、李、杜、韓、柳。此外諸家文集,不宜據(jù)引為用。”〔15〕這在韓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幾成共識。詩人作詩要“使事”或“用事”,而所使、所用之“事”,以中國典故為準的。
三、詩學理念的中國趨向
古代的中、韓兩國同處于東亞文化圈,也都深受儒、道、釋哲學的影響。由于都以儒、道、釋精神為其文化哲學的主干,所以中、韓兩國的古代文化在思維習慣以及文化價值取向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韓國古代詩學是在接受了中國古代詩學影響的前提下發(fā)生和發(fā)展的,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就完全抹殺韓國古代詩學的客觀存在及其應(yīng)有的民族品格。
法國當代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言:“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chǎn)生的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6〕雅斯貝爾斯認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臘、印度、中國及以色列等地幾乎同時出現(xiàn)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對人類最為關(guān)切的根本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例如古希臘有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與孔子,以色列有猶太的先知們,以他們?yōu)橹行男纬闪烁髯圆煌奈幕瘋鹘y(tǒng)。這些文化傳統(tǒng)經(jīng)歷兩千多年的發(fā)展已成為各自文化圈內(nèi)人類文化的主要精神財富。
基于此,我們認為韓國古代詩學在理念及方式上雖與中國古代詩學有諸多交叉之處,但絕不能簡單將韓國古代詩學看成是中國古代詩學的復制與翻版。韓國古代詩學與中國古代詩學理念上的趨同,恰好說明了韓國古代詩學與中國古代詩學有著無法抹卻的親緣關(guān)系,這種親緣關(guān)系就是韓國古代詩學理念所呈示出的中國趨向。
其一,儒化的詩學觀。古代韓國自古就有尚儒尊孔的傳統(tǒng),故此,韓國古代詩學往往強調(diào)文學的“美刺”功能,注重詩品與人品,追求文學的人性美。這與中國古代儒家的詩學理念一脈相承。徐居正言:
吾東方之文,始于?三國,盛于高麗,極于盛朝。其關(guān)于天地氣運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況文者,貫道之器。六經(jīng)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純乎道。今之學者,誠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經(jīng),不規(guī)于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則?其所以羽翼圣經(jīng)者,必有其道矣。〔17〕
韓國古代詩學的儒化詩教觀,體現(xiàn)于韓國古代漢文學的方方面面,對韓國古代漢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繁榮產(chǎn)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其二,抒情言志的文學本質(zhì)觀。中國的詩學傳統(tǒng)強調(diào)詩歌的藝術(shù)本質(zhì)與審美特性在于“言志”與“緣情”,韓國古代詩學對此也極為認同。
詩者言志,雖辭語造其工,而茍失意義所歸,則知詩者不取也。〔18〕
夫詩言志也,如善辯者,悠揚反覆,融解無難······〔19〕
詩者,志之發(fā)也,有語有意,意深而語淺,故語可了而意不可窮。〔20〕
吁!詩者,出自情性虛靈之府,先識夭賤,油然而發(fā),不期然而然。非詩能窮,人窮也,故詩自如斯哉。但有才者,天亦猜之,于世人又何尤焉,惜哉!〔21〕
夫詩發(fā)于情也。古人云有聲畫,信哉言乎!蓋詩與畫何異哉?有畫其性情者、畫其身世者、畫其形容者、畫其者焉。〔22〕
由此可見,韓國古代詩學所主張的抒情言志的思想與中國傳統(tǒng)詩學如出一轍,體現(xiàn)出韓國古代詩學在關(guān)于文學本質(zhì)問題的認識上與中國詩學傳統(tǒng)的趨同。
其三,詩宗唐、宋的風尚。詩分唐、宋是中國文學史上持久的論爭話題,同樣,它也常常影響著韓國古代詩學的審美與理論取向。自新羅后期至高麗初,韓國詩壇崇尚唐詩,推崇的詩人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如李仁老極力盛贊杜詩,曾言:“啄句之法,唯少陵獨盡其妙。”“自雅缺風亡,詩人皆推杜子美為獨步。”高麗中后期,韓國詩壇則轉(zhuǎn)而大興宗宋之風。尊崇的詩人主要有蘇軾、歐陽修、梅圣俞及黃庭堅等。特別是蘇軾聲望最重。崔滋云:
近世尚東坡,蓋愛其氣焰豪邁,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幾効得其體也。今之后進,讀《東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風骨,但欲證據(jù)以為用事之具,剽竊不足道也。
可見,蘇詩的氣韻與風骨甚至被高麗詩壇尊奉為詩的典范。徐居正《東人詩話》云:“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尚蘇之風在韓國刮了數(shù)百年,聲勢之浩蕩,一直蔓延至李氏朝鮮。由南龍翼《壺谷詩話》言李朝“文體專尚東坡”、金萬重《西浦漫談》亦云“國初承勝國之緒,純學東坡”,可見一斑。
時至近世,韓國詩壇由于受明代七子“詩必盛唐”復古思潮的影響,崔慶昌、白光勛與李達攜“三唐詩人”的盛譽乘勢而起,柳夢寅言:“近來學唐詩者皆稱崔慶昌、李達。”當時的韓國詩壇日益表現(xiàn)出尊唐黜宋的審美取向,如所謂“似唐”、“法唐”、“逼唐”、“不減唐人”、“可肩盛唐”、“盛唐風格”等批評話語不絕于耳。與此同時,鄙視宋詩的聲音亦此起彼伏。“詩至于宋,可謂亡矣。所謂亡者,非其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23〕至李朝英祖、正祖年間,韓國詩壇又流露出青睞清代乾嘉詩風的傾向,于是又掀起了“唐宋兼宗”的熱潮。
關(guān)于唐詩與宋詩的不同,韓國古代詩家亦有自己獨到的認知,如申欽在《晴窗軟談》中指出,唐詩與宋詩各有千秋,理應(yīng)分別視之:
唐詩如南宗,一頓即本來面目;宋詩如北宗,由漸而進,尚持聲聞辟支爾。此唐、宋之別也。〔24〕
同時,申欽也嚴正地批駁了詩分唐、宋(尊唐抑宋或尊宋貶唐)思
想的偏執(zhí):
世之言唐者斥宋,治宋者亦不必尊唐,茲皆偏矣。唐之衰也,豈無俚譜?宋之盛也,豈無雅音?此正鉤金與薪之類也。〔25〕
對唐詩、宋詩如此公允的品評,即便在中國詩學批評史上也頗具價值。
四、韓國古代詩學對中國古代詩學的“主體間性”批評
韓國古代詩學雖然在諸多方面都流露出血親似的中國情結(jié),但韓國古代詩學絕不是中國古代詩學的照相式的復制,相反,韓國古代詩家在汲取中國古代詩學精華時常常秉持著清醒的民族自我意識,從眾多韓國古代詩家著述的書名,如《東人詩話》、《海東詩話》、《東國詩話》、《東人論詩絕句》、《東詩話》、《東國詩話匯成》、《東詩叢話》、《海東諸家詩話》、《朝鮮古今詩話》、《小華詩評》等等,即可見一斑。至于詩學話語中所宣稱的“吾東”、“我東”、“我東人”、“吾東方”、“吾東國”、“東詩”等等稱謂,更是隨處可見。由此,我們可以斷言,韓國古代詩學對中國古代詩學的接受絕非簡單、機械地受容,而是一種“主體間性”的批評。
主體間性的主要理念是研究或規(guī)范一個主體是怎樣與完整的作為主體運作的另一個主體互相作用的。認為文學實踐主要表現(xiàn)為人與人之間所進行的社會交往活動。這種“主體—主體”關(guān)系所體現(xiàn)的是互為主體的雙方間的“對立、對峙——對話、交流”。這種主體之間的交流首先是一種共同參與,一種主體的分有、共享或一種共同創(chuàng)造。它強調(diào)相互間的投射、籌劃,相互溶浸,同時它又秉有一種相互批評,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調(diào)節(jié)的批判功能。在此基礎(chǔ)上展開了主體間本位的廣闊天地,不斷達成主體間的意義生成。〔26〕我們所謂韓國古代詩學的中國情結(jié),實質(zhì)上就是韓國古代詩學對中國古代詩學的主體間性批評,這種情形不是只體現(xiàn)于韓國古代詩學與中國關(guān)聯(lián)的某一方面,而是體現(xiàn)在二者關(guān)聯(lián)的所有層面。
前蘇聯(lián)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巴赫金認為,碰撞后的不同文化必定會保有其各自的文化主體性,即文化自我首先必須是一個“我”,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文化。所以,他更強調(diào)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性、對話性,認為交流與對話是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同時,文化之間的交往本質(zhì)上不是獨白,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灌輸與強制接受,而是在平等、民主的對話交流中進行卓有成效的理解,進而造成意義的增殖與再生。〔27〕對于韓國古代詩學的中國情結(jié),我們亦應(yīng)作如是觀。
〔參考文獻〕
〔1〕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4卷)〔M〕.首爾:太學社,1996:640-641.
〔2〕鄭判龍.韓國詩話研究〔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7:22.
〔3〕趙鐘業(yè).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M〕.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227.
〔4〕歐陽修著,鄭文校點.六一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9.
〔5〕趙鐘業(yè)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49.
〔6〕趙鐘業(yè)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444.
〔7〕蔡鎮(zhèn)楚.比較詩話學〔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272.
〔8〕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49.
〔9〕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6卷〔M〕.首爾:太學社,1996:715.
〔10〕蔡鎮(zhèn)楚.比較詩話學〔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274.
〔11〕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102.
〔12〕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500.
〔13〕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108.
〔14〕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416.
〔15〕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1卷〔M〕.首爾:太學社,1996:107.
〔16〕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4.
〔17〕徐居正,等.東文選:卷一〔M〕.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1982.3.
〔18〕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卷)〔M〕.首爾:太學社,1996:525.
〔19〕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卷)〔M〕.首爾:太學社,1996:604.
〔20〕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6卷)〔M〕.首爾:太學社,1996:668.
〔21〕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2卷)〔M〕.首爾:太學社,1996:534.
〔22〕趙鐘業(y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卷)〔M〕.首爾:太學社,1996:596.
〔23〕許筠.覆瓿集·卷四·宋五家詩序〔M〕.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0:251.
〔24〕蔡鎮(zhèn)楚.比較詩話學〔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289.
〔25〕鄺健行,等.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M〕.北京:中華書局,2002:107.
〔26〕金元浦.文學解釋學〔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254.
〔2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第4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0.
〔責任編輯:李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