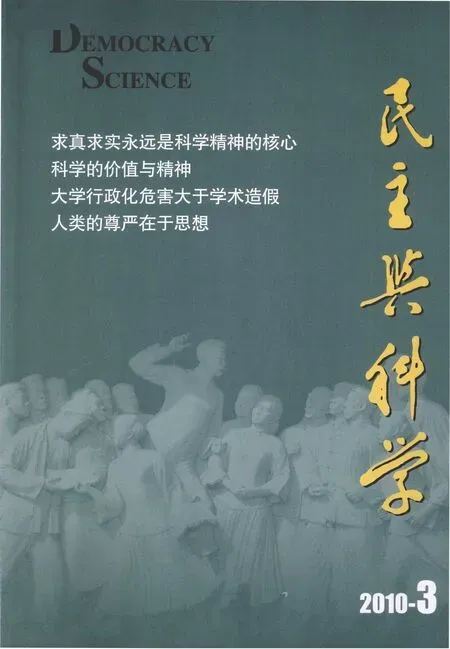值得一過的人生
■諶洪果
值得一過的人生
■諶洪果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論語·學而》
貧富與樂道好禮
孔子與子貢的這段對話,是《論語》中的精彩之筆,華彩斷章。整個對話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探討了一個人面對貧富當如何處之泰然的問題;后半部分則形象表達了孔子贊賞并踐行的“溫故而知新”、“學而時習之”的學問觀。一問一答、啟發聯想的兩個回合對話,不僅再次闡發了孔子的快樂原則,也表明了其對禮和道的終極追求;更重要的是,借助《詩經》話語的神來之筆,這段對話為我們樹立了一種充滿直覺意境、審美情趣的君子風采:他如玉石般高潔,又如玉樹般臨風,還如玉器般能經受切磋琢磨的磨練而依然風姿綽約,瀟灑翩翩。孔老夫子作為教育家的獨特教學方式,栩栩如生地躍然紙面。
在孔子的開導中,“貧而樂”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因為貧窮,了無牽掛、一身輕松而樂,還是指因為在貧窮之中有所求索,而不在乎窮困的外在生活狀態,甚至因有所樂而忘記貧寒呢?這里的關鍵在于“所樂者何”。《論語》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開篇,提綱挈領,已經點出了在孔子心目中,快樂的根源在于學習并實踐的過程,這是一個值得一生去求索和修行的過程。所以,這里的樂,一定不是自娛自樂的出世神秘主義態度,毋寧是一種滿載入世價值取向的修身過程。在皇侃本的注疏中,“樂”下面多了個“道”字。鄭玄《注》云:“樂謂志于道,不以貧為憂苦。”這是對“貧而樂”的恰當把握,即所謂的“安貧樂道”,注重的是后面的“道”的追求,這就使得“樂”有了實際的指向,這種指向超越了物質經濟條件的限制,體現出一種超凡脫俗的人生境界。
其實,有關樂道而忘貧的精神狀態,在《論語》中還出現過數次,比如《述而》篇:“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里的“樂亦在其中矣”是緊接著“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的描述,表面上似乎是一種逍遙自在的道家之樂,但實際上全句當做轉折的解釋———即便粗茶淡飯、起居簡陋,仍然可以找到快樂的方式,而不能做因果的解釋———因為粗茶淡飯、起居簡陋,所以自得其樂。從該句下面的那句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孔子心目中的“義”和“道”等,才是真正超越貧富的。富貴之所以于我如浮云,不是因為富貴本身真的不好,而是因為我沒有固守道義,所以再多的富貴都是無價值的。又比如《雍也》篇記載了孔子對顏回的夸贊:“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里顏回之“不改其樂”,乃是指其不受貧困的束縛而孜孜于道的追求,所以貧窮本身并不構成憂慮的根源,而不是說貧窮本身有多么好。孔子在此反復申說了顏回的“賢”,即一種積極入世的道德典范。
不僅如此,《論語》中還從否定的角度論述了“樂道”的難能可貴。在《憲問》篇,孔子直截了當地承認:“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表明他并不認為貧困簡樸的生活狀態本身是善好的,值得耽于其中的,相反,要想安于貧困,到達無怨的境界,真的要付出“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代價,但“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樣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
子貢是生意人,孔子最闊的學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儒商”,既會做買賣,還有文道的修為。所以,這段對話具有充分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孔子因材施教,恰逢其時地引導子貢認識到,對待貧富的態度無論如何“無諂”和“不驕”,都不如從貧富本身的視野抽離開來,將眼光投向“樂道”和“好禮”,這是人生更重要的事情。貧而無諂富而不驕,僅僅是一種消極自善的人生立場,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才是積極精進的人生取向。《論語》中的樂,總是聯系著積極修身的道德實踐的,這種修身實踐重在改造世道人心,而不受外在環境和際遇的影響,所以《衛靈公》篇中孔子教導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小人是耐不住窮困寂寞的,一窮就胡作非為了。所以《大戴禮記》中云:“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哪怕負耜凍餓,仍然不能忘記行道守仁;所以孟子能旗幟鮮明地號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見,這一人格資源已經成為儒家的一個重要精神傳統。孔子秉持的是經世濟民的人生觀,而不是消極無為的避世觀,貧而樂,是堅守道統,是為將來的入世做充分的積累和預備;富而好禮,是做好表率,是通過自我督責的示范來影響和教化社會。
切磋琢磨的問學精神
子貢在受教之后,對老師的道行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真的是個非常聰敏的學生,馬上就想到只有《詩經》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可以表達此刻的感受。切、磋、琢、磨分別指向對骨、牙、玉、石的四種不同的加工過程,大多數人因此將其理解為精益求精的問學態度,但其中的含義遠比這要豐富得多。關鍵的問題在于:這句詩與前面的對話,尤其是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的論斷之間,具有怎樣的關聯性?
該詩語出《詩經·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大致譯為:“望那淇河水灣,綠竹豐茂婀娜;一位斐然君子,如被精雕細琢的象牙玉石:嚴正勇武,威儀顯赫;這樣文采飛揚的君子,令人永遠不能忘懷。”在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講君子修行之難。而且,切磋琢磨所針對的骨、牙、玉、石等,在當時要加工是非常困難的,必須由專業化的匠人完成。所以,求學不僅過程艱難,還需要仁者之手才能有所成。一個安貧樂道、喜歡禮法的人,在常人眼中或許是一個潦倒寒士,但在子路眼中竟然如同詩中君子那樣威儀煊赫,怪不得孔子要贊嘆了。更重要的是,骨牙玉石在當時主要指兩種物件,一種是宗教祭祀的器具,一種是生產日用工具。作為宗教器具,幫助人們崇拜和提供價值準則;作為日用工具,則幫助改造世界。所以應該引導流俗,而不被流俗引導。所以整句話的意思是君子要通過修身來引導天下。
由此可以看出,子貢所聯想到的詩句與前面對話的相關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孔子對于他的貧富觀的回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如朱熹和錢穆所言,老師參透了學生無法了悟的境界,讓人噓唏義理之無窮。也正是因為義理無窮,所以“不可廢學問”,因此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另一方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身指向了君子之風的禮義仁道,是貧而樂、富而好禮的人生風度的最好闡發。無論是貧而樂道還是富而好禮,都說明了君子如璞玉,需要修身打磨,光靠天性是不行的,切磋琢磨是一生的事業,這個過程并不是讓人生畏的痛苦,而是本身就蘊含著巨大的幸福。
如果說,子貢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與前面的對話之間所確定的關聯性,主要建立在某種類比的基礎之上,那么,孔子進一步的發揮,即他對子貢“告諸往而知來者”的嘉許,同樣是一種類比的思維。《詩經》凝聚了孔子所向往的三代之風,言詩和言禮一樣,都需要某種心有靈犀的神會,需要充分的想象力。孔子贊賞的就是這種想象力以及在這種想象力驅動之下的道德實踐。李澤厚看到后世注疏者對于切磋琢磨的解讀(意指精益求精的修煉過程),當然不大符合原意,但問題在于,孔子和子貢都并沒有也不需要對這句詩給予具體的解釋。雙方都知道對方意指的是什么。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子貢和孔子運用的類比思維,和西方以英美法為代表的那種類比思維,是有本質的差別的。我把子貢和孔子的類比稱為“聯想式類比”,而把建立在先例制度基礎上的類比稱為“推理式類比”。在聯想式類比這里,發揮就是運用,比如“告諸往而知來者”中的“往”和“來”分別指過去、未來,但可泛指事物的兩個方面,所以《公冶長》篇說:“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這種類比,嚴格來說仍然是粗糙的、直覺的、詩化的、審美的、人生的。推理式類比則注重理性的區別技術和程序裝置,以特殊化的方式推進普遍化的進程,是一種法的發現的過程,所以是知性的、邏輯的、分類的。子貢的引詩和孔子的夸贊,說明聯想式類比重在“舉一反三”,目的在于將已有知識領悟貫通,適用于生活實踐的各個層面;而推理式類比則蘊含著從已知推知未知的求知取向,是一種鍥而不舍的超驗探索,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
值得一過的人生
孔子和子貢的這段對話充滿了立體感、豐富感、層次感、景深感和歷史感。它促使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到底什么樣的人生才是值得我們過的?蘇格拉底說,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維特根斯坦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奧斯特洛夫斯基說,當我們回憶往事,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從值得過的人生來衡量,憂傷喜樂、貧窮富貴、失敗成功等等,都將附屬于某種更有價值的人生取向。保羅在他的“獄中書信”中寫道:“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孔子一生的“守信好學,守死善道”,也是這種值得過的人生的生動寫照。
當然,在孔子這番貌似平和達觀的話語中,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某種失落和不甘。貧富的劇烈起伏和落差,畢竟會在弘揚道統的孔子心靈投下陰影。兩千年之后,那位致力于反抗孔子反抗絕望的魯迅,則更加痛徹骨髓地體驗到了由富到貧的困頓:“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可以看見人生的真面目。”而在另一片土地,則有人在《箴言》中對上帝懇切禱告:“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不貧窮也不富足。”貧會怎樣,富會怎樣,都不是最重要的,原來生命并不需要刻意尋求某種極致的體驗,但我們卻可以從平凡的日常生活管理中學會某種自主的人格、開明的精神(enlight-ened)、進取的心態、堅韌的意志,以應對可能面對的各種貧富巨變、災難富足、大悲大喜。一種樂觀、豁達、淡定的生命姿態或許不是單靠修行和外在的事功就能獲得的,而要靠某種“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的內在豐盈,以及這種豐盈表達出來的對人生的激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來成就。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