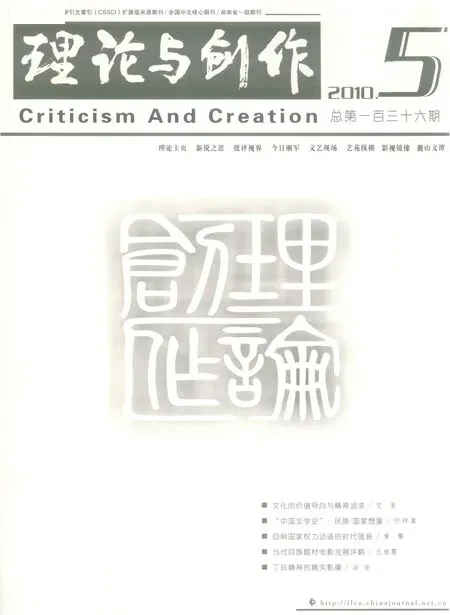《空城》的奧秘:都市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意識(shí)
■向榮 王寧
《空城》是成都作家春綠子發(fā)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春綠子以一顆對(duì)女性的悲憫之心,用文字直抵城市女性的內(nèi)心深處,探討了在消費(fèi)主義文化語境中都市各階層女性真實(shí)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困境。在對(duì)當(dāng)代男權(quán)文化進(jìn)行解構(gòu)的同時(shí)踐行一種不無痛楚的女性探索。盡管對(duì)女性的想象不無浪漫主義的成分,但作者卻能在對(duì)生活世界的情感體驗(yàn)和內(nèi)心經(jīng)驗(yàn)中,從敘事上守護(hù)著對(duì)于女性的道德認(rèn)同和命運(yùn)關(guān)懷。
傳統(tǒng)的文學(xué)作品,由于深受男性邏各斯中心思想的束縛,在描述女性時(shí),總是從男女兩性的關(guān)系著手,從男性的角度來寫女性,兩性之間的關(guān)系通常呈現(xiàn)為二元等級(jí)的對(duì)立狀態(tài),使男女在社會(huì)生活中分屬兩大不同的陣營:社會(huì)性的男人和家庭性的女人,并由此導(dǎo)致了兩極分化的男女情感對(duì)立,表現(xiàn)為一系列的子等級(jí)的二元關(guān)系:比如智力和美貌、邏輯和直覺、現(xiàn)實(shí)和幻想、文化和自然等等,突出強(qiáng)調(diào)其兩性之間的等級(jí)差別,前者通常要優(yōu)越于后者。而《空城》則是站在反男權(quán)文化的倫理角度,通過兩性之間在道德上的二元關(guān)系,來突出男女兩性在道德上的等級(jí)差異,也就是讓城市女性獲得一種人格上的道德優(yōu)勢(shì),而那些擁有各類社會(huì)權(quán)力的男人,總是有或大或小的道德瑕疵,這些道德瑕疵又總是同社會(huì)權(quán)力的腐化現(xiàn)象有內(nèi)在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性。如此一來,《空城》的審美意識(shí)里便蘊(yùn)含著對(duì)男權(quán)文化等級(jí)關(guān)系的顛覆意識(shí)。
作者在小說的封面寫到:“《空城》是一部關(guān)注女性生態(tài)的小說,一部透視社會(huì)心態(tài)的小說。”小說中充斥著男男女女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而這些人物之間或多或少都有些關(guān)系。比如尹老三與嚴(yán)芳、畢慧,嚴(yán)芳與張楚云,謝芹與曾憲、李南,蘇明與李馬華,楊玉瓊與袁少輝等等。他們每個(gè)人都處于不同的社會(huì)階層,扮演著不同的社會(huì)角色。盡管如此,小說中所有的男女兩性關(guān)系,實(shí)際上都被暗置在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之中。男人自始至終都是掌握權(quán)力的一方,他們的社會(huì)職務(wù)或文化身份表明他們是社會(huì)的“權(quán)力者”,而女人無論是中產(chǎn)女人或是底層女性,在權(quán)力場(chǎng)域中,她們都是弱勢(shì)者,她們沒有什么權(quán)力。如果說有,那也只有依附或屈從于“權(quán)力者”的惟一“權(quán)力”。這就說明,小說對(duì)當(dāng)下城市女性命運(yùn)的觀照和描述依然是放置在一個(gè)男權(quán)社會(huì)的歷史語境中,是從“社會(huì)心態(tài)”(即男權(quán)文化)的后面去關(guān)注“女性生態(tài)”的。這樣的敘事方式和文化語境的設(shè)置,從而也使小說講述的女性故事更多了一些普遍性的意義。
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她們多多少少帶有我們這個(gè)消費(fèi)時(shí)代的文化特征。如女主人公蘇明,有著茅盾筆下的梅女士、慧女士那類都市知識(shí)女性的影子,不僅擁有美麗的外表,還有聰明、智慧和良好的學(xué)識(shí),對(duì)于周遭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感到壓抑和不滿,最后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提升自己,使自己超越情感困惑和世俗利益的糾纏。也有處于都市社會(huì)底層的普通市民,如謝芹、畢慧、楊玉瓊等,她們擁有的是作為傳統(tǒng)女性所具備的道德與品質(zhì),善良而又軟弱,但在面臨人生或情感抉擇的時(shí)候,她們用行動(dòng)證實(shí)了自身的社會(huì)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了精神上、人格上的超越和提升。當(dāng)然,茅盾筆下的進(jìn)步女性除了情感生活外更關(guān)注革命運(yùn)動(dòng),而春綠子筆下的女性生存在日常化的世界中,作者就主要是在感情領(lǐng)域中通過男女關(guān)系透視這類女性的精神世界和內(nèi)心經(jīng)驗(yàn)。在這些女性形象塑造中,作者肯定了女性把握自我命運(yùn)的現(xiàn)代品格,表達(dá)了對(duì)女性主體性的尊重。不但賦予她們自強(qiáng)勤勞的女性品質(zhì),而且最后還賦予她們獨(dú)立于男性意志之外的女性主體性。在兩性互相審視時(shí),他也總讓這類女性獨(dú)占道德優(yōu)勢(shì)和人格強(qiáng)勢(shì),她們雖然是現(xiàn)實(shí)中的弱勢(shì)群體,但她們總以柔弱的堅(jiān)強(qiáng)和溫軟的情懷成為那些強(qiáng)勢(shì)男人心中的依托對(duì)象。作者以贊賞的態(tài)度塑造這些女性,讓她們?cè)跀⑹轮姓紦?jù)中心位置,這不僅體現(xiàn)了作家對(duì)男性意識(shí)的超越和對(duì)男性中心思維的突破,還表達(dá)了作者關(guān)注女性的理想主義情懷。
作家對(duì)蘇明、謝芹這類都市女性主體性的高揚(yáng),是在小說所描寫的男女不平等的社會(huì)地位上對(duì)女性的細(xì)心體察和理解,但同時(shí)也寄寓他自身多重的心理需求。這些心理需求,既有男性對(duì)女性的欲望,也有男性把自我人格的一個(gè)側(cè)面轉(zhuǎn)化成女性形象之后進(jìn)行書寫的藝術(shù)沖動(dòng)。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實(shí)則是作家內(nèi)心女性視角與男性視角相疊加的藝術(shù)結(jié)果。
《空城》中的女主人公蘇明是一位年輕的富商,既是市園林局處長李馬華的情婦,又是市宗教局處長鄭云生的女友。她相貌美、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是青山綠水園林公司的經(jīng)理。男人的眼睛到她那都成了掃描儀,在她身上做著全方位的掃描。每到一處,她就立即成了中心,所有的人對(duì)她的贊美中都會(huì)帶有曲意逢迎的意味。然而,也正是因?yàn)檫@樣的“尤物”優(yōu)勢(shì),在這個(gè)物欲縱流、權(quán)力至上的消費(fèi)主義社會(huì),蘇明作為一女年輕開發(fā)商為了得到城北公園那項(xiàng)工程,為了商場(chǎng)上的利害得失,卻始終受處在權(quán)力之上的園林局處長李馬華的制約,成為他泄欲的對(duì)象,成了他的情婦。在如此屈辱不甘的情形下,為了找尋心靈上的解脫,她只能每天晚上在虛擬的網(wǎng)絡(luò)世界里書寫自己的心情,反復(fù)咀嚼自己寫下的文字,只有這樣她才覺得自己已經(jīng)遠(yuǎn)離了市井,遠(yuǎn)離了一切骯臟。她習(xí)慣了在每一個(gè)夜晚,在與那個(gè)網(wǎng)名叫“流水天涯”的一次次交流中,感受另一個(gè)真實(shí)的自我。每晚在虛空里相會(huì),象一束淌在黑夜里的清泉,永遠(yuǎn)沒有目的,沒有方向,甚至沒有邏輯。就像小說中所提到的“她把這小屋當(dāng)作是自己最后的領(lǐng)地,她不會(huì)讓任何人踏進(jìn)半步。走出這套小屋,她就是另一個(gè)人,一個(gè)在市井里應(yīng)接交際的女人,一個(gè)渾身裹滿紅塵的女人”。蘇明試圖在《莊子》中找到自我,當(dāng)坐在梳妝臺(tái)前,面對(duì)鏡子中的自己,感覺恰是莊周化蝶的意味。她想跨出小屋里的那道門,那就是另一個(gè)女人了。“她早就覺得,這世上有兩個(gè)我,一個(gè)是永遠(yuǎn)封閉在這房里的我,一個(gè)是在市井里苦苦廝混、游刃于紅塵中的我。只是不知道哪個(gè)我更接近真實(shí)。”
或許是命運(yùn)使然,蘇明遇到了重江湖義氣的況二哥。在這里,況二哥從最初的欲望對(duì)象,到對(duì)她人格的敬佩,最終把她當(dāng)親妹妹一樣對(duì)待。也正是因?yàn)闆r二哥,才使得蘇明終于擺脫了李馬華的束縛。這個(gè)腐敗官員在后來被況二哥開車一直追,結(jié)果栽進(jìn)了魚塘。生命的最后時(shí)刻,竟是跟一個(gè)摔爛了的壞鴨蛋在一起。也許這也正應(yīng)了那句話,“善有善報(bào)惡有惡報(bào)”。但如此惡報(bào),竟打上了黑道的烙印。一種深刻的現(xiàn)實(shí)反諷就有些意味深長了。好在況二哥黑色的行俠仗義最終也受到蘇明的道德感召,去公安局自首。而蘇明得知李馬華出事后,她的困惑包圍了她,她只得走出了那套小屋,駕車出城。當(dāng)看到“高木寺”三個(gè)字時(shí),眼前的一切景象似都與夢(mèng)中相合。蘇明心里一片空茫,似乎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更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另一場(chǎng)夢(mèng)里。就在這里他遇到了鄭云生,鄭云生對(duì)宗教倫理的認(rèn)識(shí)與對(duì)現(xiàn)世的領(lǐng)悟,又逐漸成了蘇明感情上的寄托。且看下面鄭云生所述:“一種必須超越精神文化和宗教倫理的力量,必須突破上帝和佛所到達(dá)的高度。我們知道,佛主張向內(nèi)看,因?yàn)橄騼?nèi)看會(huì)使我們開悟,但是我們卻長了一雙始終向外看的眼睛。這雙永遠(yuǎn)向外看的眼睛,使我們看到的總是物質(zhì),我們便會(huì)產(chǎn)生求取的沖動(dòng)。佛在這里遇到的難題是無法破解的。除非有一種力量能徹底還原物的本質(zhì),而不是佛所說的一切皆是幻象,我們可能會(huì)放棄追逐物質(zhì)的沖動(dòng)。或者改變我們的生理形態(tài),讓這雙始終向外的眼睛反轉(zhuǎn)過來。所以,那種力量必須是超時(shí)空的,或者超自然的。”
是的,或許還要借助鄭云生所說的“需要一種必須超越精神文化和宗教倫理的力量,必須突破上帝和佛所到達(dá)的高度的力量”。蘇明才能從空蒙的細(xì)雨中走出迷津,找到真正的自我。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彰顯女性獨(dú)立個(gè)性、肯定女性主體性的同時(shí),也在他的創(chuàng)造物身上投射了男性主體對(duì)女性的愿望。鄭云生的超越性宏論,看上去總像是作者在為他偏愛和同情的蘇明指點(diǎn)人生迷津,描繪人生愿望。這些愿望可能會(huì)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邏輯,體現(xiàn)了他在平等意義上對(duì)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為人的生命邏輯,僅僅承載著他對(duì)異性的心理需求。如果后一類愿望過分強(qiáng)大,就可能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的女性生命形成心理壓抑,尤其在男性話語處于強(qiáng)勢(shì)地位的時(shí)候。中國現(xiàn)代男性敘事在女性外貌氣質(zhì)的描述上,就充分表露了男性對(duì)女性外表形象的期待,這些期待或關(guān)涉男性的精神需求,或關(guān)涉男性的本能欲望。像茅盾筆下一系列性感魅力的進(jìn)步女性,它們代表著作家男性立場(chǎng)對(duì)女性人物世界的制約。在現(xiàn)代男性敘事文本中,進(jìn)步女性仍需在外貌上獲得男性心理需求的美感。這種美感即使溢出了某一男性人物的心理需求之外,也不能溢出男性作者對(duì)女性的心理需求。當(dāng)女人們身處精神困境甚至走投無路時(shí),關(guān)鍵時(shí)刻,總是有一個(gè)飄然似仙的男人站出來,為她們引領(lǐng)方向,指點(diǎn)迷津。《青春之歌》中的盧嘉川對(duì)于林道靜來說,正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引領(lǐng)者”。《空城》的敘事仍不例外。由此可見,男權(quán)文化的慣習(xí)是多么的強(qiáng)大。它好象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shí)”在《空城》中的審美表征。所以反男權(quán)的《空城》,最終也還是在男權(quán)的岸邊沾濕了褲腳。
《空城》中的其他女主人公,如謝芹、畢慧、楊玉瓊等,他們雖沒有像蘇明那樣處于社會(huì)的上層,但作為社會(huì)中下層中的普通百姓,他們身上展示的卻是傳統(tǒng)女性所具有的品質(zhì)。然而,她們每個(gè)人在面對(duì)情欲時(shí),終究也是男性欲望的對(duì)象物,只不過她們各自又有區(qū)別。如謝芹與市教育局處長曾憲。曾憲早就被她的的身材與美貌所吸引。謝芹是茶室女招待員,憑借曾憲的關(guān)系,她完全可以換個(gè)環(huán)境換個(gè)工作,但她并沒有。尤其是在曾憲出事后,謝芹把他留給她的全部財(cái)產(chǎn)捐給了災(zāi)區(qū)。在物質(zhì)、金錢利益面前,她把握住了自我。她對(duì)曾憲的感情可以說,完全是來自于自己的房客李南。李南作為男人,這個(gè)無權(quán)的打工者是《空城》中惟一的“好男人”,是整章小說中作者預(yù)設(shè)的最完整的男性形象。在小說的敘述上,作者卻把他設(shè)置成了缺席的不在場(chǎng)。這不啻又是一個(gè)反諷,抑或是作者精妙的修辭策略——好男人即便有,他也只不過是一種理想的“影子”,他總是以缺席的方式存在。而謝芹對(duì)李南一往情深,說到底也就是對(duì)一個(gè)“影子”的虛幻感情,于是她就把對(duì)李南的感情就無奈地放在了曾憲身上。這個(gè)缺席的不在場(chǎng)與小說中的其他男性人物,不僅僅是曾憲,還有尹老三、李馬華等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尤其是在道德品質(zhì)上。從這一點(diǎn)上看,作者雖站在男性立場(chǎng)上書寫男性罪惡、腐敗、陰險(xiǎn)的形象,但還是對(duì)男性形象的批判有所保留,對(duì)理想的男人有所期待。
畢慧、楊玉瓊一個(gè)是茶室女招待員、茶室老板尹老三的情婦,一個(gè)是肥腸店老板的情婦,這兩個(gè)人可以說也是男性欲望的對(duì)象物。她們吸引男性之處在于其外貌、老實(shí)、穩(wěn)重的個(gè)性,這兩個(gè)女性在這里就成了他們情欲上、心理上的需求品。這些都是自己的現(xiàn)任妻子所不具備的:茶室老板的妻子能做到的只是兩人不停的吵架,打罵。但在小說里作者也并不完全否定這個(gè)形象,茶室老板的妻子是個(gè)好母親,尤其是在兒子被綁架時(shí),她的那種著急,是母親對(duì)兒子愛的母性力量的展現(xiàn)。肥腸店老板的妻子張燕,每天從早到晚要做的只是一再的輸錢贏錢打麻將,在面對(duì)楊玉瓊時(shí),她說話、做事是那么的干脆利落,展現(xiàn)出的是一幅毫不在乎的樣子,楊玉瓊直接就成了“老板娘”。然而,作為別人的情婦也只是暫時(shí)的。當(dāng)大地震來臨時(shí),似乎所有的人在被世俗、陰暗遮蔽之后終于清醒了,終于意識(shí)到生命的價(jià)值、道德感隨之萌發(fā)。作者塑造的這些底層女性形象,其情感結(jié)局是與處在中層的蘇明相一致的,她們最后都尋找到了真正的、屬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寄托。
按照女性主義理論,男性作家在女性人物的美貌與性感上并不僅僅投射了男性對(duì)異性的欲望。其實(shí),女性人物明艷的軀體、旺盛的生命力中所流溢出的生命活力,亦熔鑄著男性對(duì)自我生命的期待。其實(shí),何止是男性敘事對(duì)女性身體美的描述,即便是男性敘事對(duì)女性性格的描述,也同樣傾注著男作家自我的人格傾向、心理需求。男性敘事中自主型女性的陽剛氣度和生命激情,顯然凝聚了男性作家對(duì)這種氣度的渴望和呼喚。把男性自我人格的某一側(cè)面易身為女性面目,使之超越現(xiàn)實(shí)限制而得到淋漓盡致的抒寫,是男性敘事中常見的現(xiàn)象,也是男性作家借助女性人物形象來表達(dá)自己的人格傾向、心理需求的結(jié)果。
作者春綠子十分強(qiáng)調(diào)都市女性身上的道德感和生命強(qiáng)力,這也是他一直贊揚(yáng)的底層群體身上的閃光點(diǎn),同時(shí)也是都市世界和都市男子所缺乏的。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他對(duì)種種都市病象開出的治療藥方:為都市注入市井之氣、民俗之風(fēng)和淳樸的自然氣息,以對(duì)抗都市人生命的衰竭和生存的虛偽矯飾。那些都市女性的向往和期冀,隱藏著作者對(duì)都市男子強(qiáng)健生命力、對(duì)道德感的召喚。與其說是在盛贊她們,不如說是為了主題的需要而造了一面鏡子,用女性的“道德強(qiáng)勢(shì)”來襯托都市男性的精神衰竭。
綜上所述,春綠子筆下的女性形象各有千秋,其形象的審美價(jià)值和思想意義也能給予人們積極的啟示。“她們”以自己在男人眼中不尋常的操行塑造著靈魂,揭示著人生的真諦。馬克思曾說過:“每一個(gè)了解一點(diǎn)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會(huì)有偉大的社會(huì)變革,社會(huì)的進(jìn)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huì)地位來精確地衡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3卷,第571頁)可以說,作家春綠子認(rèn)識(shí)到了這一點(diǎn),所以,他在艱難的創(chuàng)作道路上嚴(yán)肅、公正、客觀地反映了這個(gè)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并努力探索著以較高的藝術(shù)水準(zhǔn)去表現(xiàn)女性身上那種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