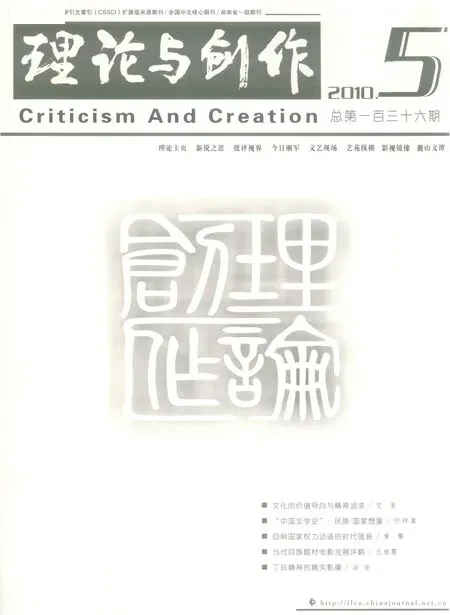1940年代知識分子的“建國”想象——以西南聯大詩人群為中心
■ 趙麗苗
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改革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以文學喚醒民眾,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一直以來都是現代文學的一個內在的目標。近代中國的處境使得作家們不管怎樣追求藝術上的完美,也始終擺脫不了家國身世的感懷,以致有評論家用“感時憂憤”或“民族寓言”來描述整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
文學史上的1940年代通常是指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間。那是一個溢出常軌的時代,較之此前,中國的民族危機更為嚴重,國破家亡、流離失所,成為那時大部分人的普遍境遇。秉承入世傳統的作家們有棄筆從戎,直接投身前線的,也有以文字為宣傳工具,為抗戰搖旗吶喊的。文學無可避免地滲入了戰爭的因素:“戰爭直接影響到作家的寫作心理、姿態、方式以及題材、風格。即使是某些遠離戰爭現實的創作,也會不自覺地打上戰時的烙印。”①具有學院派背景的聯大師生們雖然在政治氣候變化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注重學術的研究和學習”,不像后來的“整天談政治、談時事”②,但他們并沒有躲在大后方的書齋里,有意隔絕于時代政治,而是立足于學理層面,對文學與抗戰的關系做出了長遠性的思考;在力圖與世界文學同步發展、進行新詩“現代化”探索的同時,也通過詩歌寄予了他們的國家想象。
一、體驗祖國的“山山水水”
“抗戰的烽火,迫使著作家在這一新的形勢下,接近了現實:突進了嶄新的戰斗生活,望見了比過去一切更為廣闊的,真切的遠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狹小的天地里,不再從窗子里窺望藍天和白云,而是從他們的書房,亭子間,沙龍,咖啡店中解放出來,走向了戰斗的原野,走向了人民所在的場所;而是從他們生活習慣的都市,走向了農村城鎮;而是從租界,走向了內地……”③
“戰爭給了許多人一種有關生活的教育,走了許多路,過了許多橋,睡了許多床,此外還必然吃了許多想象不到的苦頭。然而真正具有教育意義的,說不定倒是明白許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氣,天氣不同還多少影響到一點人事。”④
這兩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戰爭對作家們生活的影響。盡管身份不同,知識結構各異,羅蓀和沈從文卻不約而同道出了自己在戰爭中的兩點最重要的體驗:一是走過了很多以前沒有到過的地方,接觸了更為廣闊的現實;二是與普通民眾有了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接觸,懂得了更多的人事。這大概是戰爭中很多知識分子的共同體驗,西南聯大的師生也不例外。
雖然處于相對平靜的校園環境中,但在“警報的笛子到處叫起”、硝煙味彌漫不散、生命時時受到威脅的嚴酷環境下,書桌再也不能如往常一般平靜。原本單純的書齋生活,無可避免地會被戰爭的相關經驗,如動蕩、奔波、殘酷等所侵蝕。在敵人戰火的逼迫下,聯大師生們的生活中起碼增添了三項平時難以體驗到的內容:長途遷徙、跑警報和參軍。作為整體的聯大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遷校:一次是從北方遷往長沙,一次是從長沙遷往昆明。此后還有文學院的在蒙自與昆明之間的搬遷,以及后期往貴州敘永分校的繼續撤退。
正如羅蓀所述,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讓詩人們走出了校園,走出了書房,走出了亭子間;生活范圍從北京、上海等幾個主要城市延展到廣大的內陸地區;他們因此得以近距離觸摸到祖國遼闊的土地和風俗各異的山山水水。周定一在《贈林蒲》中是這樣描述詩人的生活的:“告別岳麓山,/告別多情的湘水,/詩人撐起一把傘,/堅實的步伐,/開始踏上三千里。//過萬重山,/過千條水,/過神秘的桃花源。……/你旅店的情思,/飄渺于故國山河;/北地的風塵,/還遙遙在背后追趕。/你終于來到這蠻荒小城,/脫下風塵剝蝕的行裝,/伴一湖清水,一園好花,/用你飽蘸感奮的筆,/寫出這一路神奇。//今天你又卷起行裝,/揮手向湖水,/揮手向小城,/向湖邊的友人指點星星。/這滿天的星斗下,/到處都是詩人的家。”經過了“萬重山”“千條水”的詩人們,正是用“飽蘸感奮的筆”寫出了自己對祖國的新認識。馮至將自己在此期間出版的散文集命名為《山水》,著意于呈現那些在大后方意外發現的“還沒有被人類的歷史所點染過的自然”:那是礁石嶙峋、風緊浪急的贛江;是昆明郊外經過民族廝殺后消隱于自然中的一個無名的村落;是像“插入晴空的高塔”一樣“在我的面前高高聳起”的有加利樹;也是“躲避著一切名稱”卻“不辜負高貴和潔白”的鼠曲草。在馮至沉潛于自然山水的同時,卞之琳也在構思著他的《山山水水》。他無意于像傳統小說那樣營構曲折的情節,而是以詩人的筆墨饒有趣味地講述著他所體驗到的地理、風物、典故。只不過與馮至有意忽略那些人跡的所在,在靜默中尋找著人與自然、歷史與現實的關聯,思考著人類的運命不同,經歷延安之行后的卞之琳將筆觸伸向了正在進行的大后方的建設。于是我們看到在詩人關于山水的講述中出現了展示知識分子寧綸年開荒經歷的《海與泡沫:一個象征》。而那部紀念延安之行的《慰勞信集》更是詳盡地呈現了解放區的畫面:正在修建的把各地“一塊一塊拼起來”的飛機場、“熱和力的來源——煤窯”、“拿著鋤頭、鐵鍬、槍桿、針線”,男女老少共同開荒的場景……
在歷覽祖國的山水之外,聯大師生還有了同普通民眾進行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聯大遷徙中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在一路行進中,也十分留意進行民間采風。走在內陸貧瘠的土地上,他們不僅切身體驗了民間的疾苦與艱難,也發現了潛藏于其中的活力和民族的希望。這使他們再下筆寫作時,就增添了比以往更多的現實感和厚重感。穆旦的《出發》、《原野上走路》就是寫聯大師生三千里步行南遷的見聞感受的,但這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游山玩水,而是在用“他們的血液和原野的心胸交談”,用他們的熱情感受那“祖先走過的道路”,通過把脈來思考民族的命運:軍山鋪“坐在陰暗的高門檻上的孩子”、太子廟“枯瘦的黃牛翻起泥土和糞香”、蝴蝶飛過的“開花的菜田”、那“自由闊大的原野”把詩人從城市的絕望中撈起,進而激起了詩人的“野力”和對這個民族的期望。
而在戰時的特殊環境中,這些山水土地上又不可避免地上演了戰爭的場景。大后方戰時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跑警報”。據當事者回憶,昆明的警報之頻繁,“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⑤每當警報響起,大家就往郊外跑,俗稱“跑警報”。穆旦將這一過程形象地記錄在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詩》里:瘋狂的人們往防空洞里跑——在防空洞里的談話和感受——警報解除后往回走——發現了被炸毀的樓和僵死的我。如果這還算常態的戰時生活的話,那么親身參加抗日遠征軍則為穆旦、杜運燮等提供了直接的戰爭經驗,在他們筆下出現了描寫那場艱苦戰爭的《給永遠留在野人山的戰士》、《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作品。但仔細分析這些描寫戰爭的作品可以發現,詩人們很少正面描寫戰爭的場面,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活動在這些場景里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發現西南聯大的很多詩歌是直接以人來命名的。卞之琳的《慰勞信集》簡直就是一部延安各色人物的剪影集,集中每首詩的題目都是一位或一群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如《前方的神槍手》、《建筑飛機場的工人》、《地方武裝的新戰士》、《放哨的兒童》等。杜運燮筆下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士兵:《號兵》、《狙擊兵》、《被遺棄在路旁的死老總》、《一個有名字的兵》……在這些詩中,詩人或從戰士(人)的感受來體驗戰爭:“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沖擊,/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穆旦《森林之魅》),或關注戰爭中人的處境和精神面貌。在《一個有名字的兵》里,杜運燮以調侃的筆調寫出了張必勝在別人眼中冒著傻氣的一生:張必勝“做過兩次人:一次在家里種田,另一次是當兵”,他是個麻子,卻“老實得出名”。種田的張必勝勤勤懇懇,“犁田割稻樣樣都行,/樣樣都比人家多一倍”;當了兵的張必勝挑水、砍柴、打草鞋、上火線送飯,“震醒了全連”。詩歌題為《一個有名字的兵》,但張必勝作為抗日戰爭中默默奉獻的無數士兵中的一員,他的名字其實又往往是為人忽略的,他的生與死并沒有太多的人關注。在此,詩人看似輕松和毫不在意的筆調與張必勝對“生”的認真和執著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而結尾處,詩人筆鋒一轉,讓張必勝在慶祝抗戰勝利游行后死在路旁,悲劇意蘊陡增。這種輕松與嚴肅、喜劇與悲劇的對比,形成一種反諷的戲劇張力,引發了讀者對戰爭中人的境遇的思考。從人的處境和體驗出發,詩歌中的戰爭描寫就不僅是呈現一種客觀的苦難畫面,而是滲入了詩人的主體思考。
這種主體的密切參與,使得詩人們在了解了祖國的山水、接觸了民間的現實之后,能更深入地體察分析國家的痼疾,并進而以強烈的擔當意識尋找解決這痼疾的出路。
二、承擔我們時代的使命
如果說1930年代的現代派還能沉浸在“深閉的園子”里做一個唯美的“尋夢者”,那么經歷國破家亡的1940年代詩人,卻必須面對這樣的《我們的時代》:“一座偏僻的小城”,因接納了大城市遷徙的人流而變得繁榮,也因此成為敵人襲擊的目標。于是這里出現了死亡,出現了憂患,也出現了“丑惡的面目”,但我們不愿意“坐在方舟里”,不會“讓什么阻住了我們的視線”,而是要“向著過去的艱苦”、“向著遠遠的崇高的山峰”迎上去。我們渴望著將來有一天擁抱著我們的朋友說,“我們曾經共同分擔了/一個共同的人類的命運”,卻“不愿聽見幾個/坐在方舟里的人們在說:/‘我們延續了人類的文明。’”正因為處于這樣一個艱苦的時代,西南聯大的詩人們不可能像他們所推崇的艾略特等西方前輩那樣,沉浸在藝術反叛的滿足中,以“非個人化”的冷漠姿態對資本主義文明提出質疑。他們更強調要表現“本土”的情緒,表現“茁生于我們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爭和希望”。⑥他們以直視苦難、平庸和黑暗的勇氣,通過詩歌創作肩負起了屬于那個時代的使命。
基于這種直視的勇氣,詩人們首先在詩歌中大膽呈現了“病態中國”的真實形象。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是晚清時期隨著西學東漸而傳入中國的。形成伊始,作家們就迫不及待地通過他們的作品展開了各種國家想象。不管是《老殘游記》里的“危船”意象,還是《新中國未來記》中的未來展望,都是這種想象的表現。而近代中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局面,又使得作家們往往將國家想象與“病”聯系在一起,“治病”幾乎成為了改變中國落后局面的不二隱喻。魯迅在《吶喊·自序》里那段有關“病”的著名表述更是廣為流傳:“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⑦西南聯大的詩人們,沿襲了這種“探病”的傳統,以敏銳的洞察力,診斷著中國的病灶所在。于是我們看到,他們的詩歌中呈現的中國是饑餓的:“昨天已經過去了,昨天是田園的牧歌,/是和春水一樣流暢的日子,就要流入/意義重大的明天:然而今天是饑餓。”(穆旦《饑餓的中國》)這個中國正面臨著干旱的死寂:“所有的溝渠呈露/出干裂的泥床,像枯了的海露出水手的骨骸/落葉的樹木露出干枝。”(鄭敏《旱》)這個中國已成為一片“潰敗”的荒村:“荒草,頹墻,空洞的茅屋,/無言倒下的樹,凌亂的死寂……”(穆旦《荒村》)這個中國正處于嚴酷而漫長的寒冬:在中國的冬夜里,“北風強勁地掃過流血的戰場”,“城市遍布著凌亂的感傷”,“饑餓死亡的交響透過凍裂的時間緩緩奏鳴”,而“當雪花悄悄蓋遍城市與鄉村,/這寒冷的國度已埋葬好被絞死的人性。/只有黑暗的冬夜在積聚、凝縮、起霧,/那里面危險而沉重,是我們全在的痛苦。”(羅寄一《在中國的冬夜里》)在此之前,現代詩歌中很少出現如此慘烈的意象:流血、凌亂、饑餓、死亡。但這并不是冷靜、客觀地展示苦難,而在字里行間滲透著詩人的體驗:凄苦、戰栗、哭泣,最后凝結為“全在的痛苦”。這種經由體驗而凝結的意象,正是穆旦所提倡的“新的抒情”的表現,它讓我們在遠離那個時代的今天,讀來仍能感受到那種痛惜和沉重。
與苦難的國家形象相對應的,是有承擔的詩人主體的出現。深受西方現代派詩風影響的西南聯大詩人們,雖也在努力表現現代的、“殘缺”的自我,但并不局限于個人經驗的小范圍內,而體現了向“集體”尋求力量的強烈意愿。在討論到“我”的發展歷程時,蘇格蘭詩人彭斯曾對現代的“我”與伏爾泰式的“我”作了這樣的區分:后者“與它所欲影響的世界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理性主義和相信‘進步’的政治觀”,批評諷刺的目的是為了影響和反對現有的力量;而前者受外在的影響,透過消極態度,“來漸變他面對的世界”。⑧梁秉鈞認為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詩》等詩歌中變幻的、不確定的、毫無英雄色彩的“我”,已經表現出現代的“我”的傾向。但其實穆旦等詩人詩中雖然不再高揚“我”的主體意志,卻并沒有放棄相信“進步”的政治觀。詩人們一方面在詩中直面著現代的、不完整的自我,一方面又展示了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生活著的民眾,包括古老中國貧困的農民、抗戰的士兵、積極投身建設的群眾等,他們勇敢而堅韌,分別承載著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們”成為“我”的后盾。正因為有了千萬人民作為背景,詩人可以勇敢地宣稱:“我們看見,這樣現實的態度/強過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不毀于戰爭。服從,喝采,受苦,/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責任——”(穆旦《控訴》);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我敢于同古老的中華民族一起,靜靜地“承接著雪花的飄落”。但現代對于主體的“我”的自覺意識,又使他們不可能完全消融于大眾之中,而保持著自我的獨立思考。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詩》中,“我”雖然自由地轉換于你、我、他的身份中,是人民中的一員,卻又處處呈現為具有差異的個體。在詩的結尾,“我”走出人群,獨自體味了死亡:“當人們回到家里,彈去青草和泥土,/從他們頭上所編織的大網里,/我是獨自走上了被炸毀的樓,/而發見我自己死在那兒/僵硬的,滿臉上是歡笑,眼淚,和嘆息。”這里既有直面死亡的承擔,又分明帶著現代人獨有的失落感。但這種現代情緒并沒有轉化為世紀末的頹廢和徹底的虛無與絕望,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期待激勵著詩人們,雖身處寒冬卻仍要向春天歌唱。
三、面向“現代化”的“建國”展望
詩人們之所以敢于袒露和直面這個古老民族的累累瘢痕,是因為他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和對祖國新生的期待。在西南聯大的校園里,存在著兩種對抗戰的看法:一部分人鑒于中國當時武器裝備與日本的相差懸殊,對抗戰持較為悲觀的態度,其代表有吳宓、陳寅恪、馮友蘭等。陳寅恪曾賦《蒙自南湖》一首:“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生平;橋邊鬢影猶明滅,樓上歌聲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關山幾萬程”⑨,頗為形象地表達了“悲觀派”人士當時的心態。這些熟讀傳統詩書、深諳歷史舊事的學者們,將西南聯大的南遷與晉宋南渡聯系起來,既然短期內對“王師北定”不抱多大希望,那么他們希望通過保存傳統文化來延續民族命脈。而另一部分親身參與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或在新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師生們則秉持啟蒙的理想,從戰爭中看到了民族發展的新契機。他們“由于對于人類歷史的一種真知灼見”,“在自己的痛苦中點起一把地下火,吹燃他,擴大他,想燒毀一切,也好重建一切”。⑩首先,他們對抗戰的前景是樂觀的。聞一多對飯桌上充斥的亡國論調深惡痛絕;穆旦極力推崇艾青那“充滿著遼闊的陽光和溫暖,和生命的誘惑”的詩歌,贊頌他在詩歌中“歌頌新生的中國”,提倡詩歌“對于生命的光明面的贊美”;朱自清更將目光擴展到建國,“我們在抗戰,同時我們在建國”,并因此認為詩人作為“時代的前驅”,“有義務先創造一個新中國在他的詩里”?。其次,他們從抗戰中看到了民族新生的可能。“五四”退潮后,復古主義的興起、思想界的沉滯、文學中的灰色情調都使新文學家們感到不滿。抗戰爆發固然使中華民族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強大的破壞力也預示了打破沉滯黑暗、重新振興的可能。沈從文這位致力于“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的作家,也從耳聞目見中發現了“湘西在戰爭發展中的種種變遷,以及地方問題如何由混亂中除舊布新,漸上軌道”?,因此寄希望于通過戰爭凈化墮落的中國。朱自清則感到“抗戰以來,第一次我們獲得了真正的統一;第一次我們每個國民都感到有一個國家——第一次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中國是自己的”?。穆旦也認為抗戰“使整個中國跳出了一個沉滯的泥沼,一洼‘死水’”?,喚起了中國人的斗志和覺醒的意識。鳳凰涅槃固然要經受煉獄般的痛楚,但也正因為其敢于拋棄陳舊的過去,才能獲得新生。對冬天的直視,是因為看到了春天的來臨。
于是我們看到詩人們在不憚于展露丑陋和黑暗的同時,內心又充滿著戰勝困難的強大信心和對光明的堅定向往。穆旦的詩作《贊美》,可謂是他自己所呼吁這類作品的典型代表。在這首詩里,詩人懷著強烈的對未來的期待,贊美那堅韌的歷史締造者——人民。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因“有無數埋藏的年代”,而蘊積了“說不盡的故事”、“說不盡的災難”,這些漫長歲月里的主角是“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傴僂的人民”,他們經歷了無數朝代的變遷、經歷了希望和失望的輪回,卻“永遠無言地跟在犁后旋轉”,延續著“受難的形象凝固在路旁”。然而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刻,他們“放下了古代的鋤頭”,“溶進了大眾的愛”,雖然意識到自己死亡的命運,意識到等待新生的路“是無限的悠長的”,但“他沒有流淚,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盡管在句句詩行中,我們可以體驗到那“夾雜著纖細的血絲”的痛楚,但詩人以堅定的信心宣告:“我們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著,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對抗戰勝利和民族新生的展望,讓詩人們不僅將目光投向當下的抗戰,也開始關注未來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朱自清在《詩與建國》一文中,從理論上明確提出應在詩歌中表現國家現代化的要求。他認為現在的詩人大部分在“集中力量歌詠抗戰”,他們雖然也相信“建國必成”,但較少地在詩中表現現代化建設的成績。而這是抗戰以后的目標。只有出現了“歌詠現代化的詩”,才能“表示我們一般生活也在現代化”,因此他呼吁“建國的歌手”的出現。?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這里所說的“現代化”,已不同于1930年代現代派詩歌中出現的都市現代化。他所指的不是跑馬場、電影院、舞廳等現代消費場所,而是大后方經過戰爭破壞后的重建,包括新的公路鐵路的開通、城市市容的整修和防空洞的挖建等。
在這種理論觀照下,杜運燮的《滇緬公路》就被朱自清稱贊為是朝著“現代史詩”方向努力的作品。在詩人筆下,滇緬公路已不僅是一條實體的交通線,同時還承載了整個民族的等待。它不僅連接著原始的過去、無情的現在,也會通向光明的未來。這條“不平凡的路”的“不平凡”的建設者也許在承受著饑餓、辛勞、陰謀的剝削,但從來不缺乏勇敢與堅韌,也不會喪失對自由和勝利的期待。這些“每天不讓太陽占先,從匆促搭蓋的/土穴草窠里出來,揮動起原始的/鍬鎬,不惜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為民族爭取平坦,爭取自由的呼吸”的勞動者,同英勇的戰士一樣,成為促進民族發展的群體英雄。正如朱自清所稱贊的,這首詩“不缺少‘詩素’,不缺少‘溫暖’,不缺少愛國心”,它表現出“忍耐的勇敢,真切的歡樂,表現我們‘全民族’”,是對整個民族前途的展望。?這種表現現代化建設的詩歌,同樣出現在卞之琳的筆下。只不過卞之琳無意于史詩式的長篇書寫,詩中也很少有那種沉雄磅礴的氣勢,而是充滿了獨特的“卞式”機智和幽默,但其中同樣表達了對“建設者”的贊美:“所以你們辛苦了,不歇一口氣,/為了保衛的飛機、聯絡的飛機。/凡是會抬起頭來向上看的眼睛/都感謝你們翻動的一鏟土一鏟泥”(《修筑飛機場的工人》);他還看到了群體的創造力:“如今你們把一條支線/扭轉了方向,斷斷又連連,/十里,十里,又九里十九盤,/轉上去,轉上去,轉進了太行山,/回想起來我還是驚奇:/時間抹不掉這條痕跡!”(《抬鋼軌的群眾》)
在《想像中國的方法》一書中,王德威先生提出了“小說中國”的概念,指出小說流變與中國命運的關聯。他認為“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小說記錄了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象,而小說本身的質變,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表征之一。……談到國魂的召喚、國體的凝聚、國格的塑造,乃至國史的編纂,我們不能不說敘述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小說(虛構!)之必要。”?這一論述一方面肯定了小說這種文體的地位,另一方面則強調了在正統的歷史敘述之外,文學想象的重要性。比較小說而言,中國的現代詩歌固然不以虛構見長,然而其參與中國現代化進程,記錄這進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象”的作用卻應是一致的。西南聯大詩人們1940年代的詩歌創作,為我們呈現了大一統的建國神話之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認識和展望。在詩歌“現代化”的探索之外,為我們思考文學與國家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從這個層面上或許可以說,“詩歌中國”與“小說中國”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注 釋
①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頁。
②聞一多:《八年的回憶與感謝》,《聞一多全集》第3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549頁。
③羅蓀:《抗戰文藝運動鳥瞰》,《文學月報》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
④沈從文:《云南看云》,《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頁。
⑤汪曾祺:《跑警報》,《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頁。
⑥穆旦:《他死在第二次》,《穆旦精選集》,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
⑦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⑧轉引自梁秉鈞:《穆旦與“現代”的我》,《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頁。
⑨王云:《訪蒙自隨筆二則》,《笳吹弦誦在春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頁。
⑩李廣田:《詩人的聲音》,《李廣田文集》第3卷,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頁。
??朱自清:《愛國詩》,《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9頁、第359頁。
?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第 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
?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全集》第 10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穆旦:《〈慰勞信集〉——從〈魚目集〉說起》,《穆旦精選集》,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頁。
??朱自清:《詩與建國》,《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頁、第353頁。
?王德威:《小說中國》,《想像中國的方法》,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