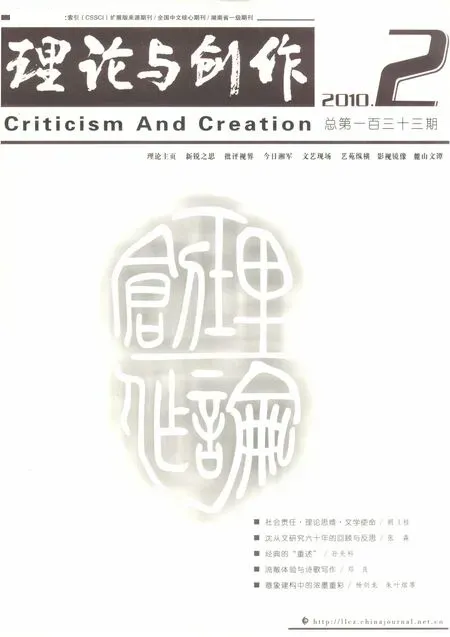流散體驗與詩歌寫作——海外華文詩人洛夫訪談
■鄧艮
一、兩度“流放”的被迫與自我選擇
問:洛老您好,這是一次等待很久了的詩歌對話。我將您一生在物理時空中所經歷的身體上的不斷位移和流動,以及隨這種流動帶來的心靈上的侘傺猶疑狀態,難以名之,就叫流散體驗吧。
您曾將自己1996年的移民溫哥華稱為“二度流放”,自然是相較于1949年離家到臺灣這“一度流放”而言。但對于這兩次位移的歷史情境和原因,我注意到,不同論者與您的表述之間都有些出入。龍彼德在《洛夫評傳》和《一代詩魔洛夫》兩書中都曾詳細記載了您1949年到臺的始末。按他的說法,您當時是報名參加“陸軍司令部在衡陽招考青年學生到臺灣受訓,成績優良的可保送到陸軍軍官學校”,您當時21歲,正想趁青春年華到外面闖一闖,何況還有繼續求學的機會,結果報名后被錄取。這雖說有偶然的機遇因素,但這畢竟是您自己的主動選擇。我注意到,您在更多的場合卻說當時是“被一股時代之風刮到了臺灣”,“為時勢所迫”。請問您當時到臺的最初動因是什么?能否談談當時的一些詳細情況?
答:1949年我從湖南衡陽出走臺灣,跨出了獨行天涯的第一步,到今天已經60個年頭了。對當年所謂的“第一度流放”,事隔半個世紀,其詳細經過我已記不太清楚,但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在心理上,當年的確是被迫出走的;第二,想到外面去闖天下,這乃出于年輕人對一個新世界的憧憬,對自創前途的向往。對我來說,這兩點其實并不矛盾,“被迫出走”與“自我選擇”,兩者都是決定這次去臺灣的重要因素。
先說“被迫出走”。1949年前后,我年方20,還是一個不諳世事而又極為敏感和熱情的大孩子,喜愛文學,好交朋友。當時正值國共交鋒最嚴峻的時期,中共隨時可能渡過長江攻入湖南。在這種大氣候下,市面蕭條,謠言四起,社會動蕩,政治氣壓十分低沉,弄得人心惶惶,大家不知何去何從。朋友中有的慫恿出走,有的誘勸留下,勸我留下的,還會在還我的借書中夾一張紙條,警告我不要亂動,語帶威脅。當他們得知我有意去臺灣時,更是恐嚇我:如去臺灣,你將面對難以預測的后果云云。在這種強大的心理壓力下,我咋辦?最后還是第二個因素“自我選擇”決定了我人生第一次急轉彎的意向,即我不甘于待在家鄉接受一個未知的命運,我得出去看看新的世界,打造自己的前途。所以我的“第一度流放”,最初起因于“時代之風”的吹送,再加上一個可以轉移命運的個人意志。時隔40年后,我于1988年首次回歸家鄉衡陽探親,與一群同學故舊相聚時,其中就有一位對我直言,他就是那位當年奉命寫字條的人。這時兩岸已經和解,對臺胞采懷柔寬容政策。
問:后來您移民溫哥華,自稱“二度流放”。您說自己“二度流放”是因為當時兩岸關系的緊張,“以及臺灣內部政治惡斗與社會環境日趨惡化”,因而“一半出于政治與環境因素,一半出于自我選擇”。也有論者說您移民海外的“客觀因素”是“臺灣政治、社會、自然環境的惡化”,而“主觀因素,與六十年代后隨著臺灣社會的全面開放而大批進軍第一世界的留學生、移民們一樣,是潛在的對西方文化的欣賞、向往——至少是部分的、一定程度的欣賞、向往”。您如何看待這種評價?
答:我于1996年移居加拿大,自稱“二度流放”。有人并不贊同我用“流放”二字,我現不妨把“放逐”、“流亡”、“流放”三個意義接近而實質上是有所不同的名詞加以厘清。“放逐”是專制帝王或獨裁者對異議分子的一種懲罰方式,像屈原被楚懷王放逐湖南,韓愈貶于海南,蘇東坡貶于黃州。“流亡”通常指因戰亂或在改朝換代的政治斗爭中被迫逃亡他鄉異國,如德國作家托瑪斯·曼,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以我的情形而論,這兩次大遷移都是出于“被迫出走”和“自我選擇”兩大因素,只不過比較而言,我的“二度流放”中的“自我選擇”的成分比“被迫出走”要大些。我來加拿大,時年68歲,算是晚年了,居然還有如此膽識與決心,干出這番令兩岸詩友大為詫異的事來,其客觀因素就如你說的那樣,但你指出這位論者所說的主觀因素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要知道,即便在六十年代的白色統治時代,臺灣對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學藝術)的開放一直都較為寬松。對西方文化的欣賞向往,完全不必“進軍第一世界”,跑到外國去取經,文學刊物的譯作和坊間翻譯的外國文學專著隨時可以看到。在六十年代,我主編《創世紀》詩刊時,就曾經有系統地把西方有代表性的最優質也最前衛的現代主義詩歌理論與作品介紹給臺灣讀者。我于晚年移居海外的主觀因素無它,就是為了尋找一個寧靜安適、少世俗干擾的地方,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多寫點令自己滿意的作品,現在證明我這個意愿并沒有令我失望,《漂木》與《背向大海》的問世還算是差強人意的成績。
問:其實無論形勢所迫還是主動選擇,并無多大意義。最重要的是,因這兩次位移而造成的生命的懸置狀態和流散體驗,才生長起了您的詩。可以說,沒有這種體驗,就不會有您詩的現有形態和質素。您同意我這樣的看法嗎?不知您如何看待這兩次位移對自己的生命和詩歌創作的影響?
答:你說因這兩次位移而造成的生命的懸置狀態和流散體驗,才生長起了我的詩,這話很對,但不全對。藝術創造的因素很復雜。作為一個詩人,我一直在培養與擴大我的胸襟,開拓我的多元創作領域。由早期的個人抒情書寫,轉入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探索與實驗,到中期再轉換軌道,開始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對古典詩歌意象永恒之美的發掘,以及在融合現代與傳統,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互參照和熔接等問題上所做的努力,都證明我并不想只走一條路。經過各種理念的轉換和對語言形式的不斷實驗,我不停地尋找新的創作突破口,我努力盡可能做到每一首詩都是一個新的出發。亦如我經常說的:不斷撤退,又不斷占領。不錯,這兩次流放經驗對我詩歌的創作、風格的養成都很有影響,但并不能涵蓋我詩歌美學養成的全部過程。我的多變性、復雜性(或豐富性)、叛逆性,造就了這個不為正人君子之類的人所喜的綽號——詩魔。其實所謂“生命懸置狀態與流散體驗”,除了受到流放經驗的影響外,還有一項重大因素,那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初抵臺灣的顛沛流離、迷失方向的日子里,正好碰上鋪天蓋地而來的存在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浪潮,這些觸及現代人的荒謬與存在的焦慮等終極問題的思想,剛好可以配合我當時那失落與孤獨的低沉情緒,而把這些新思潮視為一種精神的救贖。正由于這兩種影響相互擰扭,才擰出了《石室之死亡》和四十年后的《漂木》這兩部詩集。
二、修正的超現實主義與臺灣現代詩
問:說到《石室之死亡》,那是您的成名作,也是您詩歌創作史上一塊耀眼的界碑,但對它的評價,也可謂泥沙俱下。無論毀譽,論者往往都涉及“超現實主義”的話題,您自己也有這方面的專文論述。比如簡政珍在談到《創世紀》詩刊時曾說,由于當時“現實是詩人難以碰觸的禁忌”,“超現實變成詩人保存自我的方式”,“是當時詩人的放逐地”。還有論者從當時政治、經濟、教育、傳媒乃至國際形勢等方面討論了西方現代主義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盛行的原因。我想問的是,選擇超現實主義,盡管您說你們實踐的是“修正過的超現實主義”,在你們當時是出于藝術的自覺還是一種策略的考慮?您如何評價西方現代主義潮流在臺灣的盛行對臺灣現代詩發展的影響?
答:關于臺灣詩人采用超現實主義手法寫詩,是不是當時詩人的放逐地,是不是為了不敢碰觸政治禁忌而采取的一種權宜之策,這個問題,坦白說,對我個人而言,當年我以超現實主義手法寫《石室之死亡》時,并沒有這種策略考慮。我從來不曾公開聲明,說選擇超現實手法是為了掩護自己不致因觸及政治現實而犯禁。在今天看來,我想這個問題一半可能是實情,而另一半多少是一種托辭,怕因詩意隱晦避免評論界的攻訐而作為借口。我個人的選擇絕對是出于藝術的自覺。當年,在那個嚴厲的白色統治時代,以超現實主義或其它現代主義的手法作為煙幕來保護自己,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我相信這類詩人不是真正了解和信奉超現實主義的人,而只是玩票、趕時髦。
六十年代臺灣現代詩的崛起,是以紀弦為盟主的現代派之成立為發軔的。紀弦祭出了“現代派六大信條”,主要強調現代詩是“橫的移植”,是波特萊爾以降西方現代主義各個流派在中國的發揚,而不是中國傳統詩歌的繼承。這一觀點的確有點偏頗,不但不為保守人士所容,也不完全為詩人所接受。但是,紀弦的主張確是一次石破天驚的提醒,讓詩人突然發現“五四”以來的白話詩,不僅膚淺、庸俗、稀松、粗糙,警覺到胡適所謂作詩如作文的觀念對日后的新詩人為害不淺。那種淺白直陳的白話完全不能作為表現現代思想與現代生活節奏的媒介,當然更談不上詩的原創性的追求,因此不得不扭過頭來向西方最具前衛性與創造性的現代主義學習,從美學觀念到表達技巧,照單全收。其中超現實主義是一個最神秘最詭奇的藝術流派,一個令保守派害怕而嚴加抗拒的流派。
當時在臺灣我雖不是第一位接觸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卻是第一個透過翻譯與評介有系統地把它介紹給臺灣詩壇。我自己更是不顧詩壇輿論的喧囂,運用超現實那種非理性的手法從事詩歌的創作實驗。于是大家都說我是西方超現實主義在臺灣的代言人(日后大陸詩評家則說我是臺灣超現實主義的掌門人),以至所有攻擊超現實主義的矛頭都對準了我。若干年后我已自覺到超現實主義的某些限制與缺陷,尤其懷疑所謂“自動語言”的可行性。自動寫作完全擺脫知性的控制,任韁馳馬,結果寫出來的東西就如夢囈,不知所云,以至造成詩歌藝術的全然無效。
問:所以,您一直很重視對詩歌語言的經營。
答:我不是一個信奉“詩歌止于語言”的唯語言論者,我的基本詩觀是:詩是一種有意義的美,而這種美必須透過富于創造性的意象語言才能出現。既重視語言本身的無限魅力,同時也追求詩的意義,一種境界,一種實質的內涵,一種對生命的體驗與感悟。這個意義絕不是說理的、訓誡的或勵志的、顯示社會責任感的那種意義,而只是詩性的,純粹的藝術本質上的意義。基于此,我便有了修正超現實主義,或是超現實主義中國化的意圖。如何修正?又如何中國化?首先我想到的是,從中國古典詩歌中尋找參照系,從李白、李商隱、孟浩然、李賀等詩中去搜尋超現實的影子。我為什么要找這幾位老前輩?因為我從他們的作品中發現了與超現實主義同質的內在因子,那就是“非理性”。中國古典詩歌具有一種非常玄妙的神奇的、直探藝術本質的東西,那就是“無理而妙”。“無理”是超現實主義與中國古典詩歌二者十分巧合的共同素質,可是僅僅說“無理”,恐怕很難達到一個作品在藝術上的完整性和有機性,讀來不免滿目煙云,一頭霧水,而中國詩歌高明之處就在那個“妙”字。換言之,詩,絕不止于“無理”,最終還要能獲至絕妙的藝術效果。在這一觀念的啟發下,我的修正的中國化的超現實主義便有了譜,于是我便開始做著各種實驗,試著透過可解與不可解的語言形式的經營、虛與實的表現手法的相互搭配、知性與感性(近乎非理性)的有機調和,以期獲至“無理而妙”的驚喜效果。
在臺灣,除我之外,另外還有兩位超現實主義詩人:痖弦與商禽。而采用現代主義表現技巧,如暗喻、象征、歧義、聯想、切斷等類似超現實手法來寫詩的人,那就不勝枚舉了。可以說,臺灣老中青三代詩人很少不受這種修正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幾十年發展下來,這種熔古典與現代于一爐、從非理性中表現玄妙詩意、既反常又合道的詩路,已成為今天臺灣現代詩的主要風格。
問:但是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臺灣不斷涌現的新興詩社,力撥西化潮流,矛頭多指向《創世紀》“詩風晦澀”、“孤絕虛無”。您在《一顆不死的麥子》(1972)和《我們的信念與期許》(1974)兩文中曾談及“創世紀”詩人在創作觀和風格上將“有所修正”、“有所演變”;“以往的晦澀實有其不得不爾的理由,而今日之健朗則全然出于詩人的自覺”。客觀地說,您覺得這一反西化的潮流對你們是否有所觸動?盡管雙方對于“晦澀”、“虛無”等的理解并不一致。
答:現在回頭來看六十年代的現代詩,的確覺得有些過于激進,紀弦即號稱他領導的現代派是詩的另一次革命,凡革命自不免矯枉過正。那時的現代詩晦澀已成風氣,為追求創新,詩人出盡各種招式,進行各種實驗。幾十年后再來檢討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兩個很有意義的信息:其一,在那個群雄并起、寫詩像跑百米的狂飚時代,難免魚目混珠;但在有見識的讀者面前,魚目與珍珠,畢竟還是分得清的。直到今日,原創性強、結構完美的作品都未被時間淘汰,現仍廣為傳誦,杰出詩人的名字都一一走進了歷史。其二,晦澀得完全不可懂,甚至不可意會,或者過于明朗淺白,淡化為散文的假現代詩已銷聲匿跡。這固然是由于詩人的自覺,但外界的批評也多少起了些警惕作用。至于所謂“孤絕虛無”,那是詩人個別的傾向與精神狀態,指責它只能證明批評者的淺陋無知。事實上那時(七十年代末期)對現代詩的反抗,主要來自“鄉土派”、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本土詩社,表面是反現代主義的晦澀、脫離現實,而實際上是為了向外省人爭奪詩壇主導權和話語權,骨子里更是族群意識在作祟。開始他們的政治語言中把我們劃為“外來政權”,繼而激化為“去中國化”,因而倡導現代化最力、也最有影響力的《創世紀》詩刊便成了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
問:那么鄉土文學運動是否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產生的?到1978、1979年的鄉土論戰,已經變成了一味的政治之爭。有論者說,“本土化”并不必然導致臺獨。我讀到的這方面的資料非常有限,您能否談談這方面的一些情況,包括臺灣的省籍矛盾之類的。
答:有人說“本土化”并不必然導致臺獨,但臺獨卻是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所謂“深綠”的本土派分子在興風作浪,他們為了奪取政權,以仇恨國民黨為名,以仇恨外省人、去中國化為實。鄉土文學論戰,本質上是政治之爭。不過,不論是當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或以后的任何政治運動,我與《創世紀》的詩人從不介入,我們爭論的不是政治,而是藝術,是詩歌本身。我主編《創世紀》時只組織過一次抗日專集,我自己也發表過一首反日的詩:《武士刀小志》,以后再也沒有寫過政治詩。那些本土派詩人對我們凡與詩歌無關的批評,我們一概不予理會。我們堅持一個觀點:要打政治筆戰,請到別的刊物上去打,絕不可在詩刊上打,維護詩刊的純潔性是主編的責任。
問:您的《魔歌》、《時間之傷》一變《石室之死亡》時期的無限內轉和“混亂”(我說的混亂,包含“豐富”之意),而呈現一種簡靜的風格,于是有人乃簡單地說你是從西化到回歸傳統。對此謬論我想不值一駁,因為那實在是對您詩歌的“隔”。您曾說,我們就生活在傳統之中,無所謂回歸。事實正是如此,傳統根本就是無法斷裂的。還有人說您是從“橫的移植”發展到“縱的繼承”,“在東西方文化相會相激的橫坐標,與一個偉大的民族從遠古走向現代的縱坐標的交叉點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是“回歸傳統的轉變”。其實,這些表述背后我感到都有一種我們習慣的現代/傳統、西化/回歸的二元對立思維在作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您的創作不斷“進步”,后期作品繼承了前期的“優點”而又克服了“缺點”,您怎么看待這種創作中的進化論觀點?
答:在我早期的創作經歷中,大家熟知我確實是受過西方現代主義的洗禮,在新的滾滾藝術思潮中,年輕詩人無一能免于這個影響。我的《石室之死亡》、《外外集》、《西貢詩抄》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1960-1970),但到了《魔歌》時期,我主動地自覺地逐漸在語言風格和意象處理上都開始做了些調整,而在思想上開始撞入了莊子與禪宗的領域,且進一步體認了“天人合一”的哲理,并發展為結合莊禪與儒家思想的“物我同一”論(這可見我的《魔歌》自序)。如果從我前后期整體的創作路線來看,我的擁抱西方現代主義與回眸傳統、反思古典并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產生了相輔相成的作用。我的創作歷程絕不像有人所說我是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似乎是對立的。
想必你也知道,在我現有的作品中,誰能分辨出哪是西方的?哪是傳統的?正如詩人莊曉明所說,“洛夫的詩藝既有深厚的傳統功底,又經歷了西方超現實主義等詩歌各種流派的洗禮,精純地掌握了聯想、暗示、通感等現代技巧,這使得他的詩境既熟悉,又陌生,既來徑依稀可尋,又去向茫然無辨”。至于現代化,可以說是我終生不變的追求,在這一追求中,我從不曾去想這是西方的現代化,或是中國的現代化,對我來說,現代化只有一個含義,那就是創新。
所謂“進步”,這是某些評論家較簡單的泛論,當然,任何一位詩人都有他早年的“青澀”期,中年以后的日趨成熟乃是很自然的發展過程,無所謂“進步不進步”。至于有人說“后期繼承了前期的優點,而又克服了缺點”,我不太了解指何而言,也許是說我前期的作品看不太懂,后期作品比較好懂。就詩的欣賞而言,你不覺得這種邏輯思維是否過于簡單?誠然,這確是我美學觀念與藝術風格的蛻變過程,卻不是什么優點與缺點的更替。何謂優點?何謂缺點?對藝術的欣賞往往會受到主觀感受的左右,你認為是缺點,也許正是別人眼中的優點。曾有人說我受害于超現實主義,這是無稽之談,因為剛好相反,我這一生得益于超現實主義(并不一定指法國布洛東的超現實主義,而是指一種世界性的藝術思潮)遠遠大于西方的任何其它派系。我中晚期的作品仍大多采用超現實手法,卻又不那么明顯地看得出來,這一套表現手法已成為“洛夫獨門”手法,我的注冊商標了。
三、還鄉錯位與詩歌天涯美學
問:1988年您終于回到隔絕40年的故鄉,隨后又歷覽祖國名山大河,但是比較您此前此后的鄉愁題材詩歌,我認為還是返鄉前的鄉愁詩更耐人體味,而且,返鄉后您反而在這方面寫得也較少了。這當然可以從“距離產生美”的角度加以解釋,但是否還有其它原因呢?回鄉后由于親歷的負重面與記憶的美好面發生錯位,我感覺您這時期的詩因此多了批判的色彩而趨于沉潛?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自己這一時期的詩美風格?
答:我與故鄉隔絕了40年之后,于1988年首次返鄉探親這一事件,的確是我鄉愁詩系列的一個分水嶺。你說我回鄉前的鄉愁詩比回鄉后的鄉愁詩更耐人品味,也不無道理,但回鄉后的鄉愁作品在數量上并不少,只是在情感的內容與濃度上有了變化。正確地說,應稱之為旅游詩,例如《杜甫草堂》、《杭州紙扇》、《紹興訪魯迅故居》、《出三峽記》、《登黃鶴樓》、《夜宿寒山寺》、《登峨嵋尋李白不遇》等等,這些詩雖未明寫鄉愁,卻間接抒發了另一種大鄉愁——文化鄉愁。回鄉前的鄉愁詩是情的感動,而以后的文化鄉愁詩則增加了知性的深度和人文的內涵,除了美的感動外,也可引起讀者省思而有所啟發。
鄉愁詩之所以吸引人,甚至動人心魄,一方面由于如你所說的距離美,另一方面是由于想象空間大,這種想象空間卻需以記憶中的事實為根據,想象可以把現實美化。我的《湖南大雪》現實感很強,是我在1988年回湖南故鄉之前一年寫的。詩中的情景都是出自想象,有人讀到詩中有關文革的描述時,還以為我是大陸詩人哩!這就是想象的真實,詩歌創作的一項最重要的因素。想象最怕現實的對撞,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剛一進入現實,原來的想象便像泡沫似的戳破了,幻滅了。親友故舊面目全非,出生老屋前面的池塘枯了,屋里住了陌生人,滿山的樹林都在大煉鋼時期被砍伐殆盡,中山路變成了解放路,我就讀的小學已改為黨校。我含淚靠在老屋的土墻上,極目向屋內搜尋童年時的情景,久久無言,最后我恍然大悟:原來的故鄉是回不去了,鄉愁是一種永遠治不好的病。我還有一種體驗:回鄉之前內心有很大的壓力,壓力可引發創作的沖動,回鄉后壓力沒有了,也無所期待了,令人失望的現實取代了美好的回憶和浪漫情緒。我第一次回鄉后雖然也寫過一些鄉愁詩,如《與衡陽賓館的蟋蟀對話》、《衡陽車站》,但總覺得缺少點張力和想象空間,不過后來我寫的旅游詩,可讀性還是很高的。
問:回鄉探親雖然是兩岸隔絕政治的初步解凍,但我認為它對您后來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尤其對您之后思想觀念的改變所起的作用。這次回鄉的結果,用您的詩句來說,是您意識到:“我曾是/一尾涸轍的魚/一度變成作繭的蠶/于今又化作一只老蜘蛛/懸在一根殘絲上/注定在風中擺蕩一生”。或許這正是您選擇“二度流放”的一個內在理路?《漂木》對“心中的原鄉”的尋找是否就是緣于此而拒絕了把大陸、臺灣甚至溫哥華及任何一個具體的地理位置作為泊地?
答:不錯,我承認你的看法。我選擇“二度流放”,漂泊異鄉,正是為了尋找一個寄托心靈、安頓疲憊的靈魂的所在,也就是你所謂的“心中的原鄉”。其實這種尋找從1949年獨自告別了有形的家園之后就已開始。想必你還記得,2007年我在湘西鳳凰縣舉辦的“《漂木》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典禮上講過的話,我說“《漂木》這首長詩,主要是寫我尋找精神家園而終不可得的悲哀,它是一種絕望的想象觀照”,“《漂木》寫的不只是悲劇,而是對悲劇的超越”。我自己認為,第二句話更能詮釋這首詩的關鍵涵義,道出了這首詩的真正精神。《漂木》的悲劇是生命的悲劇,每個字、每一個意象,都是為了說出這么一句話而存在:生命的無常,宿命的無奈。我有一個終生遵循的創作座右銘:以有限暗示無限,以小我暗示大我。這就是說,我寫我個人的悲劇,同時也暗示了整個人類的悲劇。事實上我詩中很少出現“悲劇”二字,卻通過各種意象,仰首對空默默地訴說對于“無常”與“無奈”的浩嘆。
問: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漂木》透露著您對任何一種虛妄保持警惕與拒絕。但同時,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苦痛的參與者和承擔者,您以詩堅持對“心靈的原鄉”和“遠方的夢”的搜尋,以一種悲憫情懷張揚起人之尊嚴的旗幟,而唱響了“一首失聲天涯的歌”。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您“天涯美學”的內涵,不知對否?我很喜歡“失聲天涯的歌”這個詩句,失聲天涯與我們所處的喧嘩騷動的時代構成了對立,它不僅展示了您悲情的一面,也展示了您悲情中的執著,即堅持以詩歌唱,盡管那唱出來的旋律往往不是流行色。
答:謝謝你對“天涯美學”做了如此完美的闡述與補充,你的詮釋已給《漂木》提供了一個新的解讀角度,尤其欣賞你所說的“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苦痛的參與者和承擔者,您以詩堅持對‘心靈的原鄉’和‘遠方的夢’的搜尋,以一種悲憫情懷張揚起人之尊嚴的旗幟,而唱響了‘一首失聲天涯的歌’”。我在上一個提問的回答中已有過尋找“精神家園”或“心靈原鄉”的說法,而所謂“遠方的夢”,也可在第一個提問的回答中找到投影,那就是當年我離家出走的原因之一:即年輕人對于一個新世界的憧憬和自創前途的向往。不過,你把“一首失聲天涯的歌”僅僅解讀為“詩歌”,我認為稍有點著相,似乎不應坐實在某一具體的事物上。這首歌實際上是生命之歌,漂泊者感悟到生命的荒誕與虛幻而唱出的哀歌。
問:有個現象,現在一談海外華文文學,論者往往一上來就是什么“身份認同”、“失根焦慮”、“文化危機”等等,似乎任何一個海外作家只要用這些理論一裝,就完成了評論。我倒是很懷疑是否這些作家都會產生“異化”的“他者”感。我并不是說這些理論沒有意義,而是反對那種集裝箱式的評論模式。請問洛老,您有失根焦慮、身份危機的體驗嗎?請結合您的經歷談談這種現象。
答:從我的許多作品中,尤其是《漂木》,的確可以看出一種“失根的焦慮”和“身份危機”的體驗,不過說是“身份危機”不如說是“心靈失去座標”的彷徨感,缺乏“文化認同”的失落感。初來溫哥華時,由陌生環境衍生的孤寂感自是難免。我曾寬慰自己說:由臺北移居異國,只不過是換了一間書房,每天照樣讀書寫字,可謂樂在其中,活得瀟灑。我覺得愈接近晚年,社會圈子愈來愈小,書房的天地則愈來愈大,這種現實世界的萎縮、心靈空間的擴充,也算是一種超越。這正像魯迅的詩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和秋冬。”然而,每當面對現實和獨處時,就瀟灑不起來了。有時黃昏外出散步,獨立于北美遼闊而蒼茫的天空下,我會驟然感到眼前一片茫然,發現我在人世間的定位竟是如此的曖昧和虛浮。但另一方面,我又隱隱覺得人在最孤獨的時候,反而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自我已和萬物融為一體,變成了身旁的樹、石頭、溪流、飛鳥、游魚等等,這就是為什么我詩中常出現這種“神與物游”的奇妙意象。
據說革命者如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先生少小離家之后便再也沒有回去,他們或為革命大業奔走海外,或征戰沙場,飄忽不定,我想當不至于引起什么“失根的焦慮”和“身份危機”的問題,這也許因為他們是以國為家,沒有離散感,也沒有時間去體驗漂泊的滋味。革命者與詩人都是精神上的漂泊者,只不過詩人更提升一個層次,他雖已失去了原鄉,甚至沒有了國,但他可以世界為家,宇宙為家。
四、從生命詩學到禪思詩學
問:我有一個感覺,您的詩歌似乎總是處于一種“歸”與“歸不得”的張力結構中,歸的渴欲和歸不得的彷徨構成了您詩的一種基本情態。我所謂的歸,并不僅僅指地理上的海峽勾通,而是您詩中展露出來的物質、精神、身體、心靈以及文化諸多方面的歸與不得歸的撞擊。這或許就是您所謂的“天涯”。也正因為這樣一種豐富的矛盾,我才視您的禪詩是您對自己緊張的生命情態的一種平衡,而不是一種故作姿態的所謂“超越”與逍遙。這樣,對您將古典詩的現代改寫和與古代詩人的對話,我認為就可以避免將古典詩歌美學與現代詩美學進行某種優劣評判。不知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現代禪詩與古典禪詩的根本區別在哪里?
答: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水平,足證你對我以及我的作品的觀察既犀利而又深刻,我也佩服你的眼光與解讀詩歌的能力。你說我的詩歌似乎總是處于一種“歸”與“歸不得”的張力結構中,歸的渴望與歸不得的彷徨構成了我詩的一種基本情態,這應是闡析“天涯美學”的一個重要提示,同時也是我在前面講的有關《漂木》的思想內核之一,即“尋找精神家園而終不可得的悲哀”。你還提到,我寫禪詩是為了對自己緊張的生命情態的一種平衡,這也沒錯。依我自己的解釋,禪本是一種生命的覺醒,它除了可以紓解緊張的生命情態之外,也可以松弛人生負面經驗所累積的壓力。我一向以極輕松的態度來看禪詩,它是一種隨興而至、遇機而生的產物,它不是什么“真言”,也沒有什么“大義”,它是不需思考而可獲得的東西,也不是須經長久醞釀才能構成的篇章。禪詩是墻角突然長出的一勺小花,樹上無意中掉在頭上的一片葉子,也像清晨打開大門一片雪花飄進脖子里一路冰冰地溜下去。禪詩完全不在我們的預計之中,一首好的禪詩可使你眼睛一亮:啊,生命原來是如此的富饒溫馨,但又發現生命也是如此的虛無,就像那片溜進脖子里的雪花,它使我們清醒地感覺到人生的荒寒。
我認為宋人嚴羽說得好:“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妙悟正是開啟禪詩之門的一把鑰匙。什么叫做妙悟?以現代心理學來說,妙悟即是一種直覺式的心靈感應。嚴羽繼而又說:“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由此可知,參禪也好,作詩也罷,學問幫不上什么忙,得靠妙悟。妙悟不是一種知性的辨識能力,而是一種超理性的心靈體悟,所以真正的禪詩是無言的,禪就隱藏在那沉默的語言空間里。我的禪詩也都是信手拈來,偶然得之的。著名詩評家沈奇教授在談到我的禪詩時曾說:“由生命詩學而禪思詩學,從一代詩魔到靈動蕭散的書法家,在洛夫而言,這不是美麗的遁逸,而是換一種方式觀照人生,審視世界。”他畫龍點睛地先提到“生命詩學”,而后轉入“禪思詩學”,這說明我創作生涯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還有,這個順序也很重要,禪詩乃是以生命的深刻體驗為基礎的。一個像徐志摩這樣的抒情詩人,要想進入禪詩的境界是很難的,甚至胡適也不能,因為他雖博學,卻既不悟禪,也不懂詩,而魯迅可以寫禪詩,因為他具有深厚的生命哲學的底蘊。
關于古典禪詩與現代禪詩的異同問題,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很難說出個所以然,我只能以淺薄的知識說出我個人的體認。古代最早的禪詩是有文學修養的高僧,以詩的形式來傳達禪悟或禪意,是宣揚佛道的一種媒介,所以這種寺院禪詩往往禪意勝過詩意,甚至有禪無詩。在當時不叫詩,而叫偈,如神秀最有名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后來到了中唐,僧人寒山與拾得悟性較高,他們的禪詩也較富詩趣,但真正禪詩的高峰期是在盛唐時期,不僅王昌齡、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等,即使好道的李白、尊儒的杜甫,也都寫過禪詩。我總覺得,像王維的詩,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孟浩然的詩:“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等,都是詩中有禪意,禪中有詩趣,詩禪交融,渾然一體,這才是嚴格意義下的禪詩。古典禪詩大多是山水詩,表現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系,禪意詩趣卻藏在大自然的景物中。而現代禪詩的題材較為廣泛,通常取材于生活,把人生的感悟寄托在日常生活情趣中,因此禪詩有時乃以抒情詩的風格出現,現代禪詩甚至會以現代主義的象征與暗示手法來表現,我就曾經試過以超現實手法來寫禪詩,例如《金龍禪寺》。有人說,現代禪詩脫胎于日本的俳句,非也。我所讀到的俳句有禪意的不多,詩味也不夠,總覺得缺少那么一點禪的妙悟和詩的境界。
五、政治、偶然性與詩歌
問:可以說,您一生大都處在政治的漩渦中,但您的作品很少直接寫政治,這當然是一個優秀作家的表現。自然,我們也總會在您文本的某些空白、斷裂處發現政治,甚至您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或許這就是詹姆遜所講的政治無意識?
答:我不懂你所謂的“政治漩渦”是什么?政治,如依廣義的解釋為“眾人之事”,那么我們人人都在政治漩渦之中,如依狹義的解釋為政治實務或政黨政治,我自認為未曾沾到一點政治污水。我承認,在六、七十年代的軍旅生涯中,確曾奉命寫過一些所謂“軍中戰斗文藝”之類的東西,但這些作品從未收入出版的詩集中。其實詩人要想遠離政治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說總會在某些空白、斷裂之處發現政治,這是無法避免的。但作為一個詩人,我的狷介與不合時宜的性格,是不可能讓我介入任何政治事件或政治運動的。我認為一個現代詩人應當關心政治,但不必參與政治。一則由于我孤傲的個性,再則也是受到美國總統甘乃迪一句話的啟發,他說:“政治使人腐化,詩歌使人凈化。”不過話得說回來,自古至今,許多詩人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李賀、蘇東坡、龔自珍、聞一多、馮至、艾青等哪一位不曾涉及政治而未遭迫害?但有趣的是,他們聞名于世、流傳千古的優秀作品卻又看不出有任何政治污染的痕跡,尤其是古典詩歌。
問:再問最后一個問題。近年來,關于您詩歌創作的研討會比較頻繁,規模較大的比如2007年10月12-14日在湘西鳳凰舉行了您的三千行長詩“《漂木》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0月23-26日,又在湖南衡陽舉辦了“洛夫國際詩歌節”,可見詩學界對您的認可。恰如首都師范大學吳思敬教授在鳳凰會議上總結時說的,至少有三項成果值得肯定:您打破了詩只屬于青年的認識,在晚年仍然詩思敏捷;打破了以往長詩多為敘事詩的慣例,而以意象的流轉,經營出《漂木》這樣的杰作;第三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您還只是一個影響限于臺灣的“臺灣詩人”,現在,您已經是一個著名的中國詩人。2007年7月,您又在八十高齡出版了最新的詩集《背向大海》。2009年4月,臺灣普音文化出版了四卷本的《洛夫詩歌全集》,是對您詩歌創作六十年的一次集中展示,請問這個全集是否意味著您決定封筆?或者您今后在創作上還有什么設想嗎?
答:許多人都曾問到我今后的寫作計劃,我一聽到這樣的提問便會大感欣慰,因為我雖屬高齡,但大家對我尚有所期待,認為我寶刀未老,鋒芒猶在,只是我一向沒有寫作計劃。詩歌的創作絕不是一項設計工程,它唯一依恃的是一顆敏感而明慧的心靈。以我來說,除了三千行的《漂木》有過一個粗略的大綱外,就連《石室之死亡》的寫作也都是風起水生、水到渠成之事。我是相信靈感的,有時靈感驟發,筆下有如神助,絕妙的詩句,詭奇的意象,會臨空而降。可能這些只是尚未成篇的吉光片羽,便隨手往抽屜一扔,一兩個月后偶然翻出一看,竟會驚呼:這是誰寫的好詩句?我常說:壞詩是腦子想出來的,好詩是心靈撞出來的。這種偶然性(happening)才是藝術創作一項最重要的因素,寫詩尤其如此。當然,沒有計劃并不等于沒有方向、沒有自我的期許,只是這種方向和期許只有自己知道,卻無法具體地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