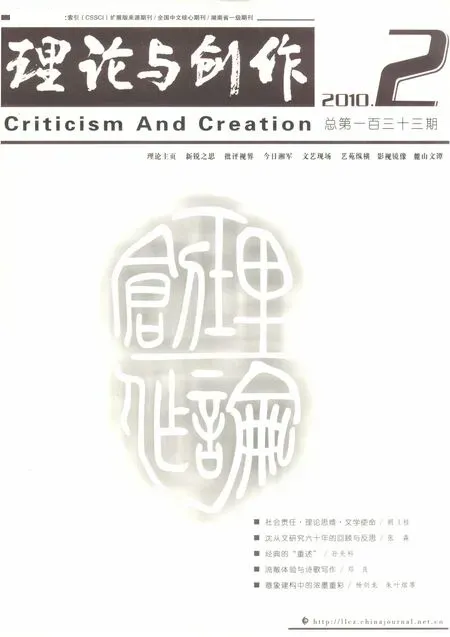政治與思想革命的不平衡關系的表現——“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一種基本關系的還原研究
■ 張喜田
“十七年”的農村題材小說,由于作家的深入扎根生活、事件的親歷性、社會擔當精神,以及現實主義的創作追求,使他們的作品較大程度地實現了“形象大于思維”,讓人可以不停地闡釋,每次均有新發現。接受者的解讀參與了作品的建構,膨脹了作品的內涵,雖然時有誤讀誤判、自說自話的一廂情愿。
一、兩種革命:一個被忽略的常識存在
“十七年”的農民經歷著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全面轉變,那就是擺脫個體勞動走向集體勞動,這是一場未曾有過的政治革命。伴隨著這場政治革命,他們的思想也將發生一場革命,即所謂思想革命。政治與思想之間有交叉重合之處,因為,政治由行動和思想所組成。但由于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農民的特點,農民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呈現出很大的不平衡性。我們所說的政治與思想的不平衡性著重表現在,一是農民的思想并不一定隨其政治行動的轉變而轉變,即歷時意義上的不同步性;二是政治行為的進步并不預示著思想的先進,即共時意義上的不同質性。“十七年”的農民的政治革命著重有合作化運動和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集體經濟,其實政治革命就是集體化的實現與鞏固。農民的思想與農民的文化并不一致,此處的“思想”著重指在傳統與現代碰撞與交融中形成的對集體與個人的關系、財富與權利的追求、社會發展、家庭處境、自己命運的思考、理解、持守等。在現實中,農民們的政治行動雖已符合社會主義政治精神的要求,如加入集體、參加階級斗爭等,但他們的思想卻常常沒有同步跟上來。或者說,他們的思想雖然不合于當時的政治標準,但是卻仍有歷史的進步性。……思想與行動的節拍常常不合拍,正是在這種合拍中產生了張力,既影響了農民前進的步伐、歷史命運,也影響了作家對農民的表達。
不管“十七年”的政治革命功過是非如何,但這的確發生了,千千萬萬中國人親歷了,幾代人、多個階層的人都受其影響,尤其是農民的思想。政治革命可以帶動思想革命卻不能代替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是長期的、連續的、遠比政治革命艱難和復雜。思想具有構成性作用,政治若不被思想認同,政治也將困難重重、失誤連連。因此,欲使政治革命取得成功,政治革命一要正確,二要時刻注意思想革命。這個問題當時的工作者、作家也注意到了,即常說的“關鍵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就是說要想讓農民政治上進步、跟上黨的步伐必須關注他們思想上的問題。這是“十七年”農村工作、農村敘述的一個基本問題,具有本體性的地位,但在近幾年的“重評”、“回歸”的文學浪潮中卻常被忽略或避而不談。
政治革命與思想革命乍一看是一個比較清晰的關系,但細究起來卻又不太容易說得清。我們通過重返經典,細讀文本,還原一個文本的乃至歷史的現實,去看一看農民、農村工作者、作家在這兩種革命中的處境與行為,從而實現農民的處境與表達、身份與建構、訴求與誤讀的歷史還原。此處的“還原”是在中國人的常識意義上的運用,不同于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即恢復原狀,盡量貼近、符合對象的歷史真實性。
二、文學表達的“顯”與“隱”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基本主題是如何讓農民走上集體和發展集體,而后期所進行的階級斗爭也是圍繞集體而展開的。
(一)思想進步的滯后性(欺騙性與反動性)
合作化運動變個體私有為集體公有、變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為集體生產。生產方式的改變,必然同農民的歷史文化積淀、同農民的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道德準則發生激烈的矛盾與沖突。
作家表現了農村的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斗爭,斗爭的起因是由對互助合作的不同看法造成的,斗爭的內容是走不走合作化道路。合作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們對此不理解,心理上覺得參加合作化是失去財產。“窮人”(貧下中農的大部分)因為貧窮無什么可失,也就無什么可顧慮,參加互助合作還可以獲得一些東西;而且他們沒有個人發家的條件和資本。對個人發家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他們就積極參加合作化運動。中農稍有資產,參加互助合作資產有可能失去,但個人發家條件又顯然不夠,抵抗不過富裕中農。黨的宣傳使他們對互助合作抱有幻想,但又怕合作化搞糟了不但得不到東西反而連老本也會賠了,因此他們就動搖徘徊。富裕中農是農村資產較多的人,他們有個人發家的條件,他們入社明顯地是把財產“歸公”,而且合作社的美好藍圖畢竟還沒有兌現,農民務實的心理使他們不相信沒見過的東西,因此,他們就強硬地抵制合作化運動。由于現實處境不同,農民各階層對合作化的態度也就不同,可見,這種不同是農民們的財產欲造成的,而不是政治覺悟。“窮人”愿意得到財產,“富人”不愿失去財產,正如同《暴風驟雨》中“趙光腚”之所以革命是因為他“光腚”一樣,他們的思想根源相同。然而,作家在表現時卻因為前者合于合作化的需要而進行歌頌,后者因不符合而進行批判。這種思想判斷是簡單的,只看到了表面的與合作化的對應,而未看到深層次的與合作化的對立。這幾類人的思想可以發生對立,也可以發生斗爭,但這種對立、斗爭很微弱,因為二者沒有質的區別,沒有調和不了的矛盾,而且他們之間可以互相轉換。任老四沒有錢時積極跟梁生寶走,一旦有了錢就不愿意。這說明“窮人”“富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并且很容易轉化。
作家受狹隘的政治視角的限制,片面夸大政治革命同思想革命的同一性,而無視其不平衡性,小說中出現了壁壘分明的局面。農村中各個階層、各式各樣的人物政治與思想上均分為左、中、右。合作化的帶頭人和積極分子是農村這場政治革命中的左派,其思想也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身上或者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私有觀念和農民的精神負擔。合作化的反對派是這場政治革命中的右翼,滿腦子是自發的資本主義思想,他們是私有觀念和農民精神負擔的體現者。這樣,農村的政治革命就成了梁生寶們“革”別人的命,郭世富們只有被別人革命的資格,而農民的思想革命就成了梁生寶們教育、改造梁三老漢、郭世富們。
作家雖然因政治視角的限制,使他們簡單地看待農民的行為與思想的關系,但是他們在不經意或不自覺之間暴露兩種革命的不平衡關系,這也許是現在流行的顯性主題與隱性主題的表現之一吧。兩種革命的不平衡表現和顯隱性表現的典型代表莫過于梁三老漢了。
梁三老漢的思想和行動是傳統的農民發家思想、與梁生寶的繼父子關系以及現實處境綜合作用的結果。長期統治著農民的自發意識使他對合作化運動不理解、不支持乃至消極抵觸。他的經濟狀況是富而不裕。他有發家的可能,并不是一無所有,因此對集體化、共同富裕不滿、對兒子不滿。他又不太富裕,經濟地位低下,在現實生活中不被人尊重,有著卑微屈辱感。一方面逆來順受,一方面對富人有著本能反感。與富人不站在一條線上,與黨在精神上相通。(不過,這種“相通”是用黨的階級路線壓別人、抬自己,實現新的不平等,而不像作家理解的那樣是思想覺悟的體現。)個人發家人力不足(兒子異心)、財力不足(生產基礎差)、政治又不允許,這些堵死了他個人發家的路。這種境況迫使他不得不與黨、與互助合作保持一致,這種“一致”不是心悅誠服,而是形勢所迫。但是因為有梁生寶的關系,他的轉變又有很大的“自愿”成分,這種“自愿”也很難說是思想覺悟的提高,更多是農民心理的一種調劑。他認識到自己對生寶的對抗只是發牢騷而已,不能左右他的行動,也只有多關心兒子的事業。他把自己的發家夢轉移到兒子身上,讓兒子成功,從而“光宗耀祖”,從而使自己因不能發家而造成的心靈空虛用兒子的成功來填補。他把互助組的成功歸于兒子,把互助合作事業當成兒子的個人事業。由于兒子使互助成功他才對互助組滿意,他也因為兒子的成功才覺得臉上有光。可見,他的轉變并不是有了思想認識,并不是政治覺悟的提高,只是農民思想、心理的自我調節,某種程度上也帶有阿Q的“精神勝利”的特點。
同樣,梁生寶的政治行動與思想基礎也有很大的不同質性。他身上有很重的農民的落后性。在處理素芳的問題上,表現了梁生寶身上農民文化對素芳的合理追求的壓抑和摧殘,但作家卻以此體現梁生寶的品德純正、人格高尚,這無疑是對梁生寶身上丑陋的東西加以美化。在與改霞的關系上,也顯示出了梁生寶身上的農民文化對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的壓抑和批評。梁生寶有著濃厚的故土難遷的戀土情緒,而改霞則是在現代工業的沖擊下,具有新的追求、新的意識的現代女性,但梁生寶卻貶低、責斥改霞,這是農民文化對現代文化的排斥和壓抑。作家對梁生寶這種思想和行為進行肯定,這是因為梁是合作化運動的積極分子,是合作化有用人才,他的思想和行為便都是正確的。
作家表現了一些領導人的“青天意識”,也把他們做為“青天”來表現,并對這種“青天”意識進行歌頌。劉雨生堅信“吃飯的一屋,主事的一人”,把合作社的“一籃子”工作全歸自己管,成功與失敗全由自己負責,他不啟發大家對社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只靠個人包打天下。柳青雖然反對郭振山的“青天”意識和“恩賜”觀點,但又把梁生寶做為救世主來塑造。活躍借貸時,人們依靠郭振山失敗了,靠梁生寶得救了,度過春荒。他儼然成了救世主。在任老四退組時,梁生寶與任老四的一段對話已點明了他具有“青天”意識。蕭長春也成了偶像,人人崇拜。如果對他們的一些思想不加警醒與改造,這些合作化的領導者,發展到后來不知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郭振山、范登高們真實地體現了農民革命的動機和發展過程,他們革命的動機是為了獲得利益。一旦革命違背他們自己的利益時,他們便不革命了,甚至反對和阻礙革命。他們的革命合于歷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歷史上農民起義往往如此,“打皇帝”是為了“做皇帝”。郭振山們的革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是作家們卻把他們孤立地看待,不能與其他階層如梁生寶們聯系起來看,也不能發展看。
郭振山們大多是老革命者,“老”革命落后,說明了農民革命的規律性,有一種可怕的歷史循環。農民革命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做保證,其結果很可能走向革命的反面,這也揭示了梁生寶之輩的發展前景:郭振山們的昨天就是梁生寶們的今天,郭振山們的今天也就是梁生寶們的明天。但是作家塑造郭振山們是為了給梁生寶們建立對比物。這種對比不是互相見證,互相聯系,互相參照,從而尋找兩者的相似性和臨界點,而是簡單對照,片面地肯定和否定,兩者一優一劣,肯定一方,否定一方。對比之后不是出現聯系的全面的觀點,對農民的革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是把兩者孤立分裂,由“壞的”映照了“好的”可貴與強大,從而產生了樂觀的情緒。他們的對比不是從文化的、歷史的角度去進行,而是單一地從當時的政治、階級的角度入手。作家只批判郭振山們思想落后不積極參加合作化運動,一心搞個人發家,而對他們如此革命的歷史根源、文化積淀注意不夠,也就陷于就事論事,而忽視了他們的典型性、代表性,也就對整個農民階級革命的復雜性注意不夠。其實他們與阿Q們的革命何其相似!
(二)思想的劣質化(惡化、丑陋化)
在行為上合于時代需求的人,其思想作家不無溢美,相反,不合于時代要求的,則極盡“集丑”與惡化。
落后人物身上薈萃了農民的“惡”,作家很少表現他們身上“善”的因素。農民身上的二重性到他們身上只剩下了“惡”的一重性。他們自私、狹隘、頑固,甚至剝削他人,瘋狂抵制和破壞合作化運動。“糊涂涂”一家里里外外,男女老幼均無一是處。作家對他們全是批判,缺少贊揚,這種狀況越來越突出。郭世富、王菊生只是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而被批判,到了《艷陽天》中的“彎彎繞”、“馬大炮”則是要破壞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道路,由階級斗爭轉化為兩條道路的斗爭。他們不僅受批判,而且也要消滅。
農民身上的確有很多不利于社會主義的因素,農民思想是相通乃至相似的,差別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別,但是由于政治行為的不同,就把優劣截然分開,顯然不合適。同時,這種“不利于”只是放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方可看出,一旦離開,也可能有其他的歷史價值,他們身上的一些因素也值得借鑒。如把郭世富們的勤勞致富、勞動創業的行為全作為資本主義的自發行為加以批判,把個體生產中的計劃謀略、經營管理水平看作是奸詐、陰險而極盡嘲笑。正是這些層次間的張力和不連貫性,露出了隙縫,使后人能夠不停的解讀。敘事是最高的調和機構,具有構成與再生作用。正是由于作家的如實敘述,使我們感覺到了這些落后農民身上的可貴之處。當然,作家有時也意識到了這些價值,如《山鄉巨變》對王菊生夫婦、張桂秋夫婦的勤勞、儉樸、愛惜農具加以贊揚,比較忠實于生活、忠實于農民,盡管作家也在批判他們的政治落后。
從當時農村的中心工作出發表現一切裁決一切,這具有很強的政治意識形態性,它提供了未來社會秩序的藍圖,卻忘記了背后的歷史動力,所以有時對農民的落后性的批判又具有很強的歷史反動性。如對范登高跑買賣、郭振山窯場入股、郭世富囤糧的批判就值得商榷。他們之所以受批判,一方面因為他們這是個人發家的行為,與當時共同富裕的政策不合,另一方面,這也是長期的小農經濟產生的“重農輕商”的農本思想的流露。“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著作家,自然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談話的,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它的最后結論”,是“農業中的宗法經濟”。①商品經濟是封建社會后期新生的經濟形式,比農業經濟先進,它受到封建經濟的排斥。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在農村是通過打倒封建經濟建立起來的,超越了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因此僅僅以反對個人發家的資本主義思想為借口反對個人的商品經濟,實際是從農業經濟出發反對商品經濟。如此批判的作家,與馬克思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著作家”一樣是反對歷史潮流的。
三、底層的無語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留下了一系列農民形象,身份雖然被后人不停地評說,但給后人留下的印象還是基本固定的。
“十七年”的生活與文學中,政治處于至上地位,具有很強的統攝性,而對政治的闡釋、貫徹掌握在權力者手中,即掌握在政治權力(執政者)與知識權力(作家)手中。農民的處境、命運、思想,農民自己無法表達,即使有所表達也常被人誤解,他們總是“被表達”。在被表達的過程中,他們的“真實”往往是被改寫的,他們的合理訴求得不到表達與尊重,更不可能實現。比如農民們發家致富的思想被丑惡化反動化,郭世富、王菊筋,甚至姚士杰的渴望富裕和經營策略被作為自私、奸詐消滅掉。《風雷》中因羊秀英賣狗肉就把她從生活到人品全盤否定,孰不知這不就是另一個胡玉音(《芙蓉鎮》)嗎?
身份創建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權力問題。身份形成以對“他者”的看法為前提。對自我的界定包含著對“他者”的價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區分。作家在與敘述對象的權力關系中處于統治地位,利用自己的話語霸權對農民進行了改寫與重塑。政治權力為突出自己的正確性,強化農民的落后性與反動性。知識權力為了突出自己的文明與現代,強化農民的愚昧與野蠻。總之,政治的統攝性,遮蔽、過濾、改寫、弒奪了農民思想的復雜性與合理的歷史訴求。
尤其在對女性的描寫中,顯示出了比較典型的特征。在趙樹理的創作中,大家一直公認,趙樹理的婦女觀比較落后。在作家的落后人物譜系中,婦女占比重大,并且婦女形象中,落后形象比重大。如此描寫,是因為婦女們在政治上比較滯后,其原因不做過多分析。但是,婦女除了政治特色之外,還應有其他的權力訴求,不應因政治的落后而否定其他的訴求。如素芳雖然是被誘奸,但是卻獲得了性的快感,但這被作家當作政治背叛道德墮落進行了非常厭惡的描寫。劉雨生的前妻離婚也有自己的原因,劉只是盡到一個領導的責任,而沒有盡到丈夫的責任,所謂“大公無私”其實正是把家人(妻子、兒女)當作了男人的私有財產。
問題最大的當屬知青的表述,如對知青的城鄉選擇的表達就顯示了極大的權力在場。“十七年”作家大量涉及這個問題,如《春種秋收》、《創業史》、《韓梅梅》等。作家處理時往往采用一邊倒的傾向:知青回鄉務農是熱愛勞動、熱愛家鄉,而向往城市、奔赴城市是好逸惡勞、忘本叛家的表現。這種模式是農本思想的體現,也是“十七年”簡單的意識形態劃分造成的,更是一種城市權力的在場。作家、政策制定者都是在城里,并且大多是由農村到城市里的定居者,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農村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美好之處,但對于接受過教育的知識青年來說,農村畢竟是閉塞、狹小的,外面的世界好大、好有誘惑力。城鄉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如何,城市是人類進步的標志”②,所以,走出農村,奔向城市是一種莫可名狀的沖動。這些城市利益的既得者,卻往往以政治、農村建設、合作化運動的需要而阻止甚至詛咒農村知青進城。
在農民身份敘述與構建的過程中,構建者的身份也顯現出來。知識就是權力。鄉村敘述中知識者時時在場,即權力總在場。政治權力、知識權力,甚至與城市權力合謀,打壓農民,尤其農村婦女、知識青年的合理要求,農民的正義呼聲他們聽不到,甚至聽到了也裝做不知或誤聽誤判。因為鄉村及農民的文化及文物話語表達的機會欠缺,總是處于失語狀態。農民不能說話,即使能說,也往往被誤聽或誤解。在敘述與被敘述中,農民處于不對稱的地位,沒有話語權,任憑他人評說。
但作家畢竟出身于農民,與農民有天然的血緣親情,并且親歷了農村的變化,體驗了農民的酸甜苦辣,在他們葡蔔于政治權力的同時,他們還有意無意地對政治權力表示些許的齟齬,對農民表示微弱的理解與同情。“個別的敘事,或個別的形式結構,將被解作對真實矛盾的想象解決。”③雖然有某種誤解,畢竟也只有他們能為農民說話。《山鄉巨變》表現了種種粗暴、簡單化的做法。鄧秀梅用“外交手段”(不能不說含有奸詐和欺騙的因素)使人們入了合作社,她不是以使人放棄舊思想、舊生產方式為目的,而是以動員入社為目的,因此不管懷著什么動機和心理,只要一入社就萬事大吉。她(包括朱明)已明顯地暴露出了上級領導的那種左傾、機械命令的官僚作風。陳大春、陳孟春、盛淑君等人富有朝氣,充滿活力,嫉惡如仇,但是在他們的正義下面卻掩蓋著一種專制、獨裁、粗魯、甚至野蠻和殘酷。他們不把對手當人看待,聽不進別的意見,容不得別人的思想,一切唯自己正確,并把對手置于死地而后快。這些人發展到后來,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必然是“土皇帝”。陳先晉的入社,是被鄧秀梅的“外交手段”脅迫入社的。在外受著政治輿論的壓力,在內又家庭不和,他也沒有了發家的可能,他只好狠狠心加入了合作社。這說明了革命的殘酷與野蠻,對農民最神圣的情感(家庭的和諧、親人的愛與誠信等)進行褻瀆與摧殘。作家如實地表現了這種處境,雖然態度有時曖昧,甚至有點贊同,但在評價與敘述過程中卻留下了農民“革命”的辛酸。這類文本的真正功能則表現出了“層面之間的干涉,一個層面對另一個層面的破壞”④。
《“鍛煉鍛煉”》對“小腿疼”、“吃不飽”、王聚海們與楊小四們的沖突的表現作家便有較多的保留。這種沖突與力量的不對等,使人很容易聯想起后來的群眾批斗會。這是變相的刑場,它使每一個參加批斗會的群眾都失去人性,成了盲從暴力的幫兇。本來是干部們誘民入罪,然后利用群眾的盲目性來整治落后的農民,是典型的“釣魚”案件。即便是“小腿疼”真的偷了棉花,又是多大的罪?趙樹理自己也說:“這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們一頓,犯不著,他們沒有犯了什么法。”⑤
作為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趙樹理們實實在在地寫出了農村出現的真實情況。農民就是這樣“被入社”,干部就是這樣橫行霸道地欺侮農民,農民就是這樣消極怠工和自私自利,農業社“大躍進”并沒有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只能用強制性的手段對付農民……“藝術的真實,就這樣給后人留下了歷史的真實性”⑥。他們只是想反映農村真實的歷史現狀,而且從當時可能表達的方式來看,他們也只能站在鄧秀梅、楊小四們這些所謂新生力量的一邊,但“審美或敘事形式的生產”是“自身獨立的意識形態行為,其功能就是為不可解決的社會矛盾發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決辦法’”⑦。正是這種敘述的相對獨立性,正是政治革命與思想革命之間的“張力或不連貫性”,為文學闡釋留下了較大的空間,這種張力的擴大使作家們維護農民的立場得到曲折的表達。
注 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74-276頁。
②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頁。
③④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頁、第45頁,第68頁。
⑤趙樹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樹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頁。
⑥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