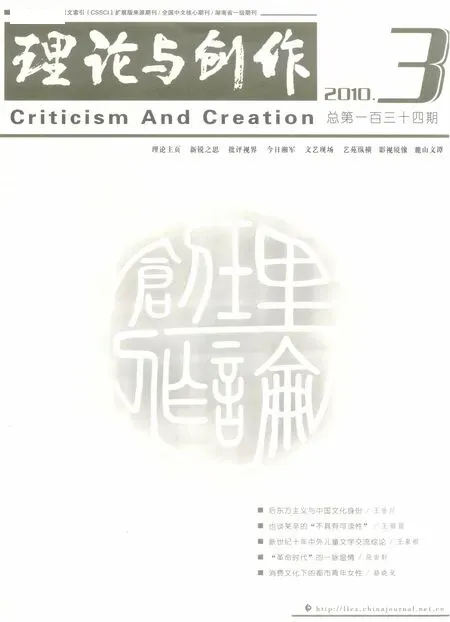也談萊辛的“不具有可讀性”?——兼論其審美對象的建構策略
■ 王麗麗
在多麗絲·萊辛獲得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好評如潮,名至實歸的贊譽聲中,也出現了不甚和諧的聲音。當今美國著名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得知萊辛獲獎之后對美聯社記者說:“盡管萊辛在早期的寫作生涯中具有一些令人仰慕的品質,但我認為在過去15年中萊辛的作品完全不具有可讀性”,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頒給萊辛獎純粹出于“政治正確”的目的。①所謂“可讀性”,按照《世界圖書大字典》的含義,是“easy or pleasant to read;interesting”。翻譯過來就是:“容易讀或能帶來快樂的閱讀;有趣。”從此意義上講,那么布魯姆的話也許不無道理,因為從表面上看,萊辛的小說,特別是中后期的小說既沒有激動人心的情節,跌宕起伏的矛盾,更沒有故意吸引人眼球的噱頭,就連她的許多崇拜者都說她的語句拖沓,情節枯燥,但如果因此就斷言萊辛獲獎只是偶然,甚至貶斥為“政治”因素,那不僅天真,甚至有些荒唐。“當鑒賞為了愉快,仍需要刺激與感動的混合時,甚至于以此作為贊美的尺度時,這種鑒賞仍然是很粗俗的。”②如果諾貝爾文學獎針對的只是具有這樣“可讀性”作品的作家,那么它的權威性和國際性就會成為天大的笑話。事實上,萊辛的作品“拒絕非常狹隘地審美分析,因為他們并不是為我們的藝術快樂而寫作的”③。她的作品所觸及的是我們的“深層自我”,按照蓋格爾的說法它是帶給我們“幸福”而非“快樂”的“藝術體驗的最高峰”。④布魯姆在這樣評價萊辛的時候,他一定忘了萊辛歷來就是一個不按常規出牌的作家,忘了自己曾經寫過的名噪一時,并仍然對評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影響的焦慮》。在這本著作中,布魯姆具有創見性地指出:新詩的形成乃是后來的詩人對前輩傳統詩歌的“誤讀”,原因是前輩詩人影響所引起的“焦慮”,故而為了超越所作出的“修正”。⑤縱觀萊辛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創作,從她的寫作風格的不斷轉換到寫作題材的多樣化,從她公開聲明自己是非女權主義者,到不斷在各種機會對評論界歪曲自己意圖的說明,我們不難看出:萊辛這些“不按常規出牌”的舉動和拒絕“貼標簽”的努力無不顯示出她試圖擺脫“影響”的“焦慮”。萊辛的審美思想正是在試圖不斷對前輩進行“修正”的努力中實踐著、完善著。實際上,正是她無所不在的“修正”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時代的獨創性,也正是她別具一格的審美對象的建構策略使她的作品擺脫了平庸作品表面所謂的“可讀性”,而躋身于極具審美價值的偉大作品的行列。而布魯姆的“影響”理論也不失為我們揭開萊辛作品魅力的一把合適的鑰匙。
一、“生活世界”中作者和讀者自身的對話
關于“什么是美”等的思想爭論無論在哲學上,還是就“美學”本身,從古至今歷來就沒有停止過。從傳統美學以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為基礎的本質/現象的“本體論”到笛卡兒主體/客體的“認識論”轉向,從康德和黑格爾試圖重建形而上學的努力,再到現象學和存在哲學試圖擺脫二元論思想,用“純粹意識”、“存在”等超越本質/現象、主體/客體或消弭其人為的界限,試圖回到本源狀態的“渾然一體狀態”,美學在思維方式上發生了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轉變。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生活世界”⑥概念的提出,“交互主體性”⑦的運用對我們重新認識處于世界之中的作者、讀者和作品以及世界的關系,擺脫原本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單一文學批評思維具有重要的作用。雖然有許多批評家都對作者和讀者的作用有過不同程度的強調,但是法國美學家杜夫海納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審美對象是一個準主體”⑧,使作者的主體意義同讀者的主體意義第一次在審美對象實現的過程中“遭遇”,并具有了平等對話的可能。而這種對話的基礎就是我們共同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因為生活世界是“一個我們本身也屬于其中的、事實上存在著的周圍世界”⑨。我們存在其中的世界就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是一個由各種主體交互關系構成的意義世界,生活世界“構成了審美對象的意義本源”⑩。實際上,正是在對生活世界的人與世界、人與人、人與社會等各種復雜關系的感悟中,藝術家才有了創作的沖動。“藝術的任務就是要揭示人與他周圍世界生活時刻的關系。”?而讀者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和作者共同生活世界各種復雜關系的經驗基礎,“詩人的沖動和他的讀者可能產生的沖動之間的緊密的自然一致”?才是可能實現的。
然而,作者和讀者的關系卻遠非如此涇渭分明。首先,作為社會文本的閱讀者,創作者本身就具有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作者挑選創作素材和實際的創作過程,實際上就是自己對社會文本閱讀的體驗和理解。這些體驗和理解由于個人生活世界和認知水平的局限和不同,必然會影響作者選材的偏好和敘述的角度。作為讀者的填充“空白”或對社會文本“空白”的“具體化”正是作為作者選材獨創性的基礎,但這種選擇無意中又留有許多的“空白”。這是作者和其他讀者產生共鳴和分歧基礎的“交叉空白”。作者選擇和留有的交叉空白不同,作品的感染力就不同,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和共鳴也不同。其次,在創作中,在把自己的體驗化作藝術品的過程中,作者還會根據自己的創作目的,故意設置一些“空白”,阻止讀者過早識破自己的意圖,這是作者阻礙或期待讀者理解的“設置空白”。這種作者心目中的讀者被稱為“理想讀者”或“隱含讀者”。而理想讀者的存在正是以作者本身也是社會文本的讀者為存在基礎的。正是這種作者和讀者的一體性共同構成了藝術品的審美基礎。但是理想讀者只是預設能夠理解作者意圖的讀者而已,在作者心中,這種隱含讀者也是分為不同層次的,因而其“設置空白”也是分為層次的。這些“交叉空白”和“設置空白”共同構成了伊瑟爾審美對象“具體化”的基礎,而兩者的多寡和填充的層次、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既反應著作者作為作者和讀者雙重身份的智慧,也是劃分偉大作家和平庸作家的重要標準之一,同時還是作品是否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就萊辛《青草在歌唱》的創作背景來說,當時的英國文壇對傳統殖民主義題材的作品已經司空見慣。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吉卜林的《吉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這些當時的扛鼎之作無疑會引起萊辛“影響的焦慮”。但是作為社會文本的閱讀者,萊辛親眼目睹殖民地人民遭受壓迫和歧視的現狀,她覺得自己有責任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出“自己微小的聲音”。萊辛敏銳地注意到了殖民地貧窮白人這一受忽視的夾層群體的生存狀況,作為讀者,選擇了這一“空白”切入,并在創作中“具體化”為對傳統的直接描寫白人和黑人沖突的殖民地題材的“修正”,引起了社會和讀者的廣泛興趣。而作為自己作品的創作者和讀者,萊辛又不得不考慮社會不同讀者的接受和期盼,同時還要擺脫“影響”的痕跡,因此建構了適應各種層次讀者閱讀的審美對象。這部小說主要從瑪麗的視角,對瑪麗個人生活環境的壓力和心理的矛盾進行了寫實描寫,而全知敘述人則不露聲色,表面采取客觀的旁觀者觀點,實則貼近白人傳統觀念的敘述,并不時轉換視角,構成不同的多層次閱讀層面。這些閱讀層面又隨著語氣或贊揚、諷刺或揶揄、反語等的不同,人物的欲言又止和語言意義、隱寓、互文的豐富性構成了更多不同的視角,也形成了各種不同解讀空間的“空白”。對于消費型讀者來說,文本形式上顛倒事件發展順序,突出以媒體刊登“謀殺”這樣轟動性的新聞開頭,對讀者造成了極強的視覺上的沖擊力和逆向思維、探究本源的吸引力。對于評論家來說,無論是敘事方式等藝術手法、抑或是主題意義都有極為豐富的“空白”有待“具體化”。持傳統白人至上觀點的讀者認為,瑪麗的死罪有應得,這部小說是一個難得的反面教材;對于同情黑人遭遇的人來說,這部小說提供了白人壓迫黑人的證據。對于哲學家來說,這部小說是研究人性的絕好材料,等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一切解讀的豐富性,雖然有賴于讀者的審美能力,但作者在建構審美對象時從選材到構思,從作者/讀者體驗的“交叉空白”到作者“設置空白”過程中,尋求基于作者和讀者自身對話的視角的多層次性和開放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虛擬世界中現實與藝術的對話
如果說“可讀性”是萊辛進入英國文壇初始階段必要的敲門磚策略的話,那么這種可讀性中顯然已蘊涵了非“可讀性”本身能夠解讀和填充的“空白”的豐富性,而這是基于萊辛對社會現實文本閱讀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如何“再現”現實,用什么方式表現現實一直是藝術家們探討和實驗的焦點。斯泰西在解讀俄國形式主義美學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時曾說過:“習慣毀滅掉作品,衣服,家具,妻子和對戰爭的恐懼。‘如果許多人全部復雜的生活無意識地繼續下去,那么,這樣的生活就好像從來沒有經過一樣。’藝術之所以存在是人們可以重新喚起生活的感覺;它讓人能感覺到事物,能使石頭成為石頭。……藝術的技巧是使物品‘陌生化’,使形式變得艱深,以增加被感知的困難,延長被感知的時間,因為感知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物品藝術技巧的方式:物品是無足輕重的。”?對于藝術家的創作來說,“陌生化”手法實際上是作家擺脫“影響”的焦慮,“修正”和建構審美對象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金色筆記》中,她在體現藝術和現實的關系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實驗。她不僅運用“碎片”的形式“陌生化”和“突出”當時“混亂”的現實,而且故意設置了“自由女性”在結構上的循環,模糊了藝術和現實的界限,使讀者在現實和藝術的互相對比中更加深入地思考現實,成為“陌生化”理論在形式上、結構上、細節上完美體現的例證。誠如她自己所說:《金色筆記》“是打破一種形式,打破某些思維方式,并超越它們的一種嘗試。”?然而,也正是由于這種嘗試,增加了閱讀的“不可讀性”和多義性,從而使這部小說在取得驚世駭俗的藝術效果的同時,也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萊辛不得不出來澄清事實,闡明自己的創作意圖。實際上,在此后的創作中,雖然萊辛沒有安娜那樣“作家的障礙”,然而卻陷入了因《金色筆記》的巨大成功而帶來的超越自己的焦慮,并對以后審美對象的建構策略產生了巨大影響。
蓋格爾在論述審美經驗時,從欣賞者的角度提出了內在專注和外在專注、表層藝術效果和深層藝術效果等幾對相互對立的概念。他以風景畫為例說明了內在的專注和外在專注的區別。“假設當一個人正在瀏覽一幅黃昏的寧靜風景畫畫面的時候,受到了某種感傷意味的刺激,并且使他自己被這種感傷意味的魔力攝住了。……這里不存在出于這幅風景畫本身的、關于這幅風景畫的情感,……人們并沒有專注于這幅風景畫,與此相反,他們生活在由這幅畫啟發出來的情感之中。我們享受的是這種情感,而不是這幅風景畫。……人們就生活在對這種情感的內在專注之中。”相反,如果人們關注的是“構成這幅風景畫的那些結構成分”,并“向從它那里洶涌而來的東西開放自身”,那么它雖然喚起情感,但“對這種外向的態度卻沒有什么干擾:他們就生活在外在的專注之中。……只有外在的專注才特別是審美的態度,……只有在外在的專注中,藝術作品才能夠真正發揮它的效果。”?同內在專注和外在專注緊密相連,并相對應的是表層藝術效果和深層的藝術效果。內在專注帶來的是快樂,是表層的藝術效果所追求的目的,而外在的專注所帶來的是理解而引起的“幸福”,是觸及自我深層領域的“藝術體驗的高峰點”。“幸福是作為一個整體自我所具有的一種總體狀態,是一種充滿著快樂的狀態;它是從某種崇高狀態中產生出來的自我的完善。”?一部書能夠暢銷也許是因為它“具有可讀性”,能夠帶給讀者快樂,但是它只有帶給人“幸福”才能被稱為偉大的作品。怎樣使讀者擺脫“內在關注”的情感漩渦,而更加注重“外在關注”的理解內涵,萊辛在《金色筆記》之后,在構筑審美對象時,開始對藝術和現實的關系從三個角度進行了新的嘗試。
第一,透視:陌生化人物內心的意識和反應,透視現實。萊辛“內在空間”小說《簡述地獄之行》的敘事主要有喪失記憶、精神錯亂的病人的囈語和幻境,穿插有現實中醫生的診斷和對話,后輔以相關人物的通信交代事件的現實緯度。顯然,這樣一部“情節”單純,但敘事結構復雜的小說,和《金色筆記》一樣,其“外在關注”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內在關注”的可能性。但是同《金色筆記》不一樣的是,其“現實性”更加隱蔽。它深入人物扭曲的內心世界,透過失憶病人內心對外在現實世界的“非正常”反應的意識流,“使世界如此陌生以致于讀者會用新眼光和開放的心胸來審視世界”。?
第二,并置:藝術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參照物。在萊辛的“外在空間”五部曲《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檔案》中,她把現實移植到完全陌生化的星球,“一個全新的世界”?,試圖直接運用虛構藝術為現實矗立參照物。在評論《什卡斯塔》》時,蓋爾·格林說:萊辛“在圣經歷史中發現了一種使熟悉的關注點——我們想象的缺陷、對我們之間和宇宙之間是一個整體的不了解以及我們的‘陷入遺忘’——神話化,也是陌生化的方式”?。然而,在某些讀者,甚至評論家的眼中,這種極端陌生化的方式也造成了作品的“不可讀性”。一直以來就是萊辛忠實支持者的約翰·倫納德(John Leonard)在1982年對萊辛一部外在空間小說的評論中抱怨說:“萊辛是本世紀選擇用英語寫小說的最有趣的半打才子之一。她為什么一定老要寫那些使她的忠實讀者不知所措和沮喪的作品呢?”他認為,“萊辛是故意的。”?沒錯,如果說萊辛在《金色筆記》中對現實和藝術相互滲透,相互糾纏的關系,以及藝術家創作的困惑用外在形式作了很好的詮釋的話,那么萊辛在五部曲中則故意嘗試了距離的用法。布萊希特曾在闡述自己的戲劇理論時,強調“陌生化”和“間離效果”。他把自己劇本發生的地點都置于遙遠的過去或異域他鄉。他認為:“使我們的問題‘錯置’才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這些問題,更全面地探討總的觀點,例如戰爭和資本主義的聯系。”?同樣,萊辛把自己的故事背景陌生化到了極致,打破了讀者“內在專注”的幻覺,使讀者從感情的俘虜轉變成了事件的觀察者和評判者,運用加大藝術世界和現實世界距離的方式,拉近了作者和讀者在主體地位上的距離,在藝術和現實的對話中,使審美對象置于作者和讀者的雙重審視之下。
第三,遞級式寓言:把現實表面簡單化,實則寓言化。從表面看,無論是《簡·薩默斯的日記》,《好恐怖分子》,還是《第五個孩子》,探討的都是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老年問題,友誼和愛情,社會暴力,異己和單身老人的情感等,情節簡單,敘述單一。然而,和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以及萊辛早期現實主義小說不同的是,這些小說都具有明顯的寓言深度。顯然,這是萊辛為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而設置的“快樂”層次和“幸福”深度。不過,即使是“快樂”層次,萊辛也不是為了讓讀者得到膚淺的感官快樂,而是為了讓讀者最大程度地感受時代的“思想脈搏”,引起感情的共鳴,并以其過于簡單的外表吸引讀者深入表層下面,讀出字里行間的意思來。蓋爾·格林說,正是這一點使萊辛的作品具有了非凡的吸引力。?在萊辛其后的作品中,一方面,寓言的比重加大,如《本,在人世間》,而另一方面,作品呈現萬花筒般的寫實和夢幻、意識和潛意識交叉映現的敘事手法,如《又來了,愛情》、《瑪拉和丹恩歷險記》等,大大增加了形式上的“艱深”程度。似乎萊辛隨著自己年齡和閱歷的增加,也想當然地提高了自己理想讀者的審美的主體地位。不過,對萊辛的讀者而言,這并不奇怪,因為早在1971年《金色筆記》的再版前言中萊辛就說過:“只有當人們不理解作品的計劃、形式和意圖時,它才是鮮活的,有說服力的,富有成果的,才能夠推動思考和討論,因為了解作品的計劃、形式和意圖之時也是它再無可取之處之時。”?
三、精神世界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對話
萊辛在《金色筆記》中,借安娜的口說:“小說應該使之成為小說的品質就是哲學的品質。”?雖然安娜由于“作家的障礙”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然而萊辛在實踐中卻始終在履行這一原則。從她的第一部小說《青草在歌唱》探討白人和黑人以及白人之間的種族、階級問題,到《暴力的孩子們》中“個人良心同集體的關系”中人與社會的問題,再到《金色筆記》集社會中各種關系于一體的大討論,無不是從社會紛繁的“現象”中,讓人“直觀”其本質,最后在“懸置”“客觀實在”中,洞悉或達到“形而上”的思考。《青草在歌唱》中,從表面看是通過摩西這個黑人奴仆刺殺白人主人瑪麗來探討殖民地關于白人和黑人之間種族關系的問題,但其更深一層的含義,實際上是透過貧困白人這一特殊階層同上層白人和下層黑人之間的矛盾,揭示出黑人更悲慘的遭遇,并借此表明殖民統治對人性的扼殺。萊辛通過現實中凹凸不平的等級關系,從摩西、瑪麗和查理這些具體的人,透過其借用T·S·艾略特詩行的書名,展示出一幅觸目驚心的人性的“荒原”景象,上升到了對“形而上”這個精神層面的的人性問題的探討,呼吁惠特曼所歌唱的代表民主和自由的“小草”。《暴力的孩子們》沿著瑪撒的人生旅途,在縱向上通過瑪撒的婚姻和戀愛經歷,探討了“靈與肉”的自我掙扎,在橫向上,通過瑪撒的社會和政治活動,直達“個別性”和“群體性”的根本問題。萊辛對哲學問題的探討在《金色筆記》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整體構思來看,四本顏色各異的筆記本和框架小說“自由女性”所探討的問題既獨立成章,又相互印證,涉及具體的政治、戰爭、種族關系、階級關系、男人和女人、不同輩分之間等等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關系,抽象的藝術和真實、語言和表達、歷史與現實、記憶與創作等之間的思想關系。在各種復雜的關系討論中,四本筆記本歸于一本。在金色筆記的光輝中,各種社會和思想問題匯集成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我們看到,安娜和索爾在感情的交流和互寫小說的實踐中,身心融為一體,幻化成每一個個體,成為大千世界中“推圓石上山的人”。?
在萊辛中后期的小說構建中,萊辛一如既往繼續探索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然而面對高科技的發展和“分裂的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她在對“形而上”問題思考的同時,并沒有脫離對生存基本問題的憂慮。實際上,在《青草在歌唱》和《一個合適的婚姻》中,萊辛已經開始關注這一問題。而在她外在空間五部曲系列小說中,生命的基本需要已成為和諧宇宙中起重要作用的問題。?在以后的小說構建中,她把自己對“形而上”的探索和對“形而下”問題的關注更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通過并置和對話,在更廣闊的層面上引發讀者的思考。《第五個孩子》和《本,在人世間》是萊辛分別創作于1988年和2000年的姐妹篇。它們表面上是一個家庭隨著第五個怪異孩子本的誕生逐漸解體的故事以及本離開家后在世間流浪的遭遇。但很顯然,這兩部小說通過其豐富的寓言性,揭示了后現代人類社會的生存危機。《第五個孩子》通過各色人等,包括本的父母對本的態度和反應以及對本悲劇的最終造成,折射出了現代社會人性的危機。《本,在人世間》通過描寫本在對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追求中屢屢受騙的經歷,進一步凸現了人性退化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追殺本,直接導致本自殺的人的居然是現代社會最令人崇敬的所謂的“科學家”。萊辛在一次采訪中說:“我們一直不停地創造,不知道會出現什么問題。就好像我們手忙腳亂,幾乎沒有時間趕上自己的步伐。”?在這里,本應是推動歷史進步的科學成了扼殺人性的幫兇,而人性的退化和墮落直接威脅到了人的基本生存。至此,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問題在審美過程中被統一起來。
在1999年,《瑪拉和丹恩歷險記》剛剛出版時在線回答網友就《瑪拉和丹恩歷險紀》等小說的幻想性質的提問中,萊辛反駁說:“我可沒有把它們當作是非現實主義的。”?是的,萊辛從來沒有脫離過現實主義。無論是以寫實的手法,還是幻想的形式,無論是現實的憂慮抑或是哲學的思考,萊辛構筑的都是對人類命運的反思。根據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意識主體在“本質直觀”意向世界的時候,要經過反思而“回到事物本身”。而作為創作者,萊辛希望通過“再現”這個意識世界,讓讀者能夠借助于她的虛擬世界,更清晰地“直觀”到“事物本身”的精神本質,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中,洞悉未來。正是這種在構筑自己的審美對象的過程中,作者、讀者和社會文本之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動態關系、立足于現實,思考于虛擬世界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精神世界的“幸福”深度使萊辛的作品具有了超越一般可讀性,超越時代、超越時間的魅力。
注 釋
①布魯姆在萊辛獲得諾貝爾獎后接受美聯社記者采訪時如是說。請參見http://www.iht.com/articles/ap/2007/10/12/america/NA-GEN-US-Nobel-Literature.php
②轉引自章啟群:《新編西方美學史》,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76頁。
③Pratt,Annis and L.S.Dembo.ed.Doris Lessing:Critical Studies.Madison:The University ofW isconsin Press,1974.p.xi;p29.
④[德]蓋格爾著,艾彥譯:《藝術的意味》,華夏出版社1998 版,第 63、101-102、65頁。
⑤Bloom,Harold.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0.
⑥⑩張永清:《現象學審美對象論》,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版。關于“生活世界”的討論可以參閱第163-178頁;第164頁。
⑦請參閱于爾根·哈貝馬斯著,洪佩郁、藺菁譯:《交往行動理論》(2),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頁。
⑧[法]杜夫海納著,韓樹站譯:《審美經驗現象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頁。
⑨[德]胡塞爾著,李幼蒸譯:《純粹現象學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
? Law rence,D`H.“Morality and the Novel”.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vid Lodge.Essex:Longman,1972.p.127.
? Richards,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tist”.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vid Lodge.Essex:Longman,1972.p.108.
?Stacy,R.H.Defamiliarization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7.p.34.
??Pickering,Jean.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Columbia: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90.p.130;p.142.
?Lessing,Doris.Shikasta,NewYork:Vintage,1981.p.xi.
??Greene,Gayle.The Poeticsof Change.Ann.Arbor:The University ofM ichigan Press,1994.p.159;p10.
?倫納德在2007年1月20日接受記者 Lisa Allardice采訪時如此說(http://books.guardian.co.uk/review/story/0,,1993745,00.htm l#article_continue).
?Cited by Watson,G.J.Drama:An Introduction.London:TheMacm illan Press LTD,1983.p.162.
? Lessing,Doris.“Preface to TheGolden Notebook”.A Small Personal Voice:Doris Lessing:Essays,Reviews,Interviews.ed.PaulSchlueter,New York:VintageBooks,1975.p43.
?Lessing,Doris.The Golden Notebook.Herts:Panther,1973.p.79.
?請參見拙著:《多麗絲·萊辛的藝術和哲學思想研究》(“A Study of Doris Lessing’s Art and Philosophy”),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請參見Boston Book Review上登的一篇Harvey Blume1998年2月采訪萊辛的文章。http://www.dorislessing.org/boston.htm l
?請參見2007年11月29日鄧中良、華菁在《中華讀書報》上翻譯萊辛接受采訪的文章。http://www.zgyspp.com/Article/y3/y22/200711/94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