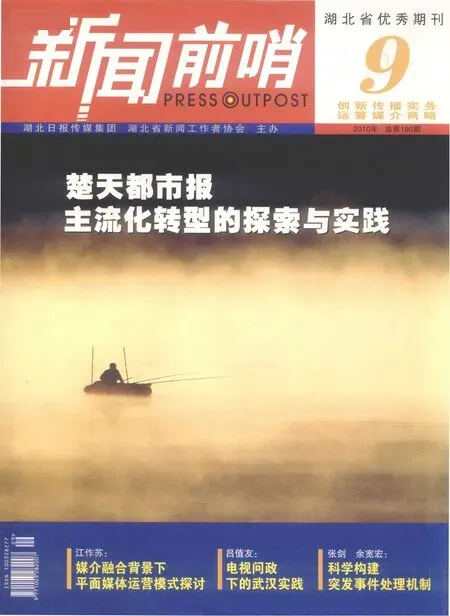虛擬網絡社團中社會資本的構建
◎張 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博士生 430072)
“社會資本”是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之后,一個新的被廣泛關注并認可的資本形式。1977年,它第一次由經濟學家格林·洛瑞(Glenn Loury)提出,不過當時它僅是作為與 “個人資本”相對應的一個經濟名詞出現。隨著對它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它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20世紀80年代,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爾迪厄 (P·Bourdieu)首次把社會資本概念引入社會學領域,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 “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些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的網絡,這一網絡是同某團體的會員制相聯系的,它從集體性擁有資本的角度為每個會員提供支持,提供為他們贏得聲望的憑證。”其核心主張即:關系網絡創造了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有價值的資源,并向成員提供集體所有的資本。這一理論的提出,引起了極大關注,并被廣泛地用來解釋許多經濟、社會現象乃至一個區域或國家的經濟繁榮。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指出,社會資本對一個社會經濟繁榮和可持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社團組織較多的國家一般民主制度績效高,反之則低。
20世紀80年代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伴此而生,社會出現了如羅伯特·普特南所言的 “獨自打保齡球”、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大分裂”現象,其中最為典型的問題是社會資本的流失問題,主要表現在政府的權威不斷流失、公民參與社團的積極性大為降低、公民花費在志愿事情上的時間不斷減少、關心公共事務的責任心不斷下降、公民彼此之間的信任度嚴重下降、機構與團體之間的協作與合作精神缺乏等等,人們對現實生活中社團公共事務喪失興趣。但是,尋找團體、尋找組織是人的社會本能。進入數字時代后,越來越多的大眾將這一腔熱情投入了細化、無邊界、虛擬的網絡團體,并逐漸對之傾注高于現實生活中的信任度,各種公民自發的網絡團體發展一路升溫。在以網上社區、論壇、博客等非正式團體生活為主的網絡中,人們通過傾訴遭遇、交換經驗、共同針對具體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達到彼此信任,形成互惠。社團活動的參與從公共領域轉移到網絡空間,網絡團體中社會資本的力量開始凸顯。
網絡營造出人們熟悉的社團空間,給予人們經濟、應用以及娛樂方面的滿足,但由于網絡本身的特點,它所構建的社會資本區別于現實社會中的社團。普南特曾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三要素的結合——社會網絡、互惠性規范及由此產生的可信任性。這三點,在虛擬網絡社團中似乎都有了新的形態,為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意義。
一、虛擬社團社會網絡的構建
社會資本是嵌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網絡中的行動者因此在行動時能方便得到并利用這種資源。網絡普及前,人們的社會網絡一般來自于三個方面:血緣、地緣與業緣,包括親戚、朋友、同學、鄰居、同事、業務往來伙伴等等。在現代社會,人際交往以及依托于此的信息交換已構成人的發展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樣也是人的發展最重要指標之一。因此,現代社會,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團體,精心經營各自社會網絡成為一大生活重心,它決定著個人或團體的發展潛力及速度,有時甚至決定其生死。然而,這種關系網絡的構建并非沒有成本的,它需要行動主體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感情甚至金錢,并且,層次越高的社會網絡,網絡規模越大(擁有較多關系、信息和橋梁)、網頂越高(網絡內擁有權利大、地位高、財富多、聲名顯赫的關系人多)、網差越大(網絡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處于不同的職位,資源及影響有互補性)、網絡構成越合理(與資源豐富的社會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其投入要求也越多。
進入21世紀,網絡技術飛速發展,人類邁入信息社會,地球成了“一個村子”,人們視野變得空前開闊,活動領域空前寬廣,遭遇問題也大大超出原有社會網絡資源范圍——人們對社會網絡的規模要求迅速膨脹。為了充分享受“信息”帶來的“利益”,它需要人們加速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然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讓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更加冷漠,長期作為一個社會“部件”的生活方式,逐步減弱了現代人構建生活中社會網絡的能力;同時,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也讓現代人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擴大、完善自己的社會網絡,維持已有社會網絡已顯得筋疲力盡。即使少數精力充足者,能重新尋找合適的資源,但構建相應社會網絡需要大量時間,而信息獲取速度帶來的利益差異是巨大的,當網絡構建完畢,它所帶來的價值已大打折扣。
由于地域、時間、精力、財力等方面的限制,人們越來越發現現實生活中社會網絡的構建相對于人的需要,總是顯得速度過慢、范圍過窄、信息過少。此外,由于現實社會網絡資源利用的有限、有償性,對于瑣碎、次重要或目的不明確的事情,人們不愿輕易動用社會網絡的資源。現實社會網絡的不便凸顯出來。這種不便迅速推動人們在21世紀逐步普及的網絡中找到了替代品——虛擬網絡社團的社會資源。
同樣是社群的集合,但由于網絡的虛擬性,人們只需要坐在電腦前,鏈接網絡,打開搜索頁,輸入需要群體關鍵字符,即可進入相應社區,并獲得所需資源。匿名式的參與,讓人們關系網絡的構建少了面對面情感的試探、寒暄、必要的應酬交際、個人背景的打探以及路途的奔波,只要進入共同的“社區”,大家就已具有一致性與認同感。少了現實社會網絡關系的羈絆,自發的社區中人們說話更自由,沒有利益的考慮,大家都自發地愿意提供一定資源與眾分享。社群網絡的構建變得簡潔、迅速,構建成本的投入大大精減。
此外,不同于現實社會網絡資源使用的排他性,網絡社團組建的隨機性與無界性,讓個體的發展不再局限于其所屬的狹隘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背景、資源之中,網絡以自身所固有的虛擬性、交互性、廣泛性和超時空性,使得網民可以通過網絡發生豐富多樣的社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種類的網絡交往群體。個體能從整個人類、整個世界中吸收自我發展的養料,從而實現人的本質、需要、個性的發展,以及人的發展階段的提升。
總之,相對于現實社會資本的構建,網絡社團中社會資本構建的優勢是明顯的:它范圍廣、速度快、投入成本較小,面對瑣碎的問題更是方便快捷。當然,其劣勢也是突出的:由于網絡社團的虛擬性及網絡成員的偶然性,導致網絡社團社會資本的構建以低層次社會網絡為主,若沒有現實社會網絡構建的加入,較難建立高層次社會網絡。
二、網絡虛擬社團互惠性的形成
普特南曾把“互惠”分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前者指人們同時交換價值相等的東西,后者指在特定的時間無報酬或不均衡的付出,即“現在己予人,將來人予己”,是一種短期的利他主義和長期的自我利益的結合。[2]不過,普特南的這種分類主要是針對現實社會社團而言,即相對身份明示、結構穩定的現實社團。網絡的開放性、流動性與匿名性,決定了網絡虛擬社團的互惠性在沒有現實交往介入的情況下,只能以“普遍的互惠”為主。一方面,網絡社團之所以能生存,在于廣大網民自覺自愿不計報酬付出;另一方面,網絡自身的特點讓網絡社團的“利他”不可能帶有任何針對性,只能是“普遍的互惠”。但即使都是“普遍的互惠”,虛擬網絡社團也有其自身的特點。
首先,現實社團的“普遍互惠”是基于網絡結構中“互惠預期”的推動下行動者的行為,所謂“現在己予人,將來人予己”,含有回報的期望。網絡虛擬社團中,除少數需要資源交換的社區外,多數網民的共享資源行為是不求回報的,至少不是在“互惠預期”的本意下發布信息的,其動力似乎更多來自于一種“自我滿足”——提供的資料如果為人所肯定,會帶來為人師的成就感;如果為他人所否定,會激發行動者的反抗,帶來一種參與競爭的滿足感;抑或僅僅滿足行動者進入社交的需求。不管緣于何種動機,行動者主觀的“非功利性”帶來的客觀結果卻是全體社區網民的“互惠”,并且這種“互惠”的普及更為廣闊。
其次,“互惠”作為人們精心經營各自社會網絡的核心動力,其效益也有層次之分:有關于社會地位獲得、職業流動、財力資助等較高層次的社會資源;也有僅限于一般性的資源共享。互惠效益越高,需要行動者的投入也相應要求越高,網絡成員對資源的控制也越加嚴格,不會輕易轉讓。因此,能在網絡虛擬社區中輕易獲得的共享資源,大多屬于低層次社會資源,主要表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它一般不能帶來直接的實惠,僅能為行動者提供追求實際實惠的信息支持,這種信息支持的維度和廣度遠遠大于現實社團。
三、網絡虛擬社團信任的產生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要素,也是互惠交易的關鍵組成部分。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所謂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個體隸屬于那個社團的角色”。[3]網絡結構中不同成員之間的信任有強弱之分,一般對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親屬以及密切交往的朋友圈信任度最強;對與自己有合作關系的公司領導、同事和鄰居等的信任度居中;而對包括生產商、銷售商以及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任度最弱。網絡虛擬社團中成員的信任屬于信任度最弱的一種,但它特殊的形成方式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傳統社會中,現實社團關系網帶有相當的封閉性和排他性,信任僅限于關系網內部,“陌生人”之間難以給予信任,因而也難以發生頻繁交易或交往。而已步入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需要交往的多元化,即交易主體的多元化。無數交易者以陌生人的身份進入市場,但依賴傳統關系網的信任無法覆蓋“陌生人”,市場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于是,為了彌補由傳統關系網對陌生人排斥帶來的經濟發展障礙,“契約”應運而生。通過契約的外在強制力——法,“信任”產生,陌生人第一次強行進入傳統關系網,進而逐步成為關系網的一員,新的關系網得以形成。契約雖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傳統關系網的不足,但它主要限于經濟交往領域,并且多用于大型、重要的經濟項目,對于小型、微型經濟項目或非經濟領域,契約在社會交往中顯得繁瑣、累贅,并消耗大量社會資源,造成資源浪費。
虛擬網絡社團中交往雖同樣以陌生人為主,但其信任產生的特殊方式避免了這種資源消耗。網絡匿名性帶來的安全感讓人放松了現實交往中的警惕,虛擬網絡社團中傳遞信息的無指向性以及社團中交往主體無利益沖突性,讓網絡成員排除了現實社團中大量由利益權衡帶來的不信任,懷疑多限于信息的客觀真實性,不再以對信源主體的懷疑為主(而這在現實社團中是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基本信任已然產生。此外,虛擬網絡社團不同于現實社團的是相同信息具有高度選擇性,即同一疑問會有多個成員回應并提供信息,求助者可以在多個信息中比較分析,最終確定認可的信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減輕了人們對信息客觀真實性的懷疑。與此同時,現實交往中暴露過多可能會帶給自身一定的危險,但虛擬交往中不存在現實的危險,保留過多反而會妨礙交流,因此網絡社團中“自我暴露”會更多,共享信息相應更加豐厚。不過,虛擬網絡社團中的信任多限于網絡之中,如果脫離網絡進入現實交往中則需要重新適應現實社團運轉邏輯規則,信任需要重新構建。但無論如何,在信息資源共享層面,虛擬網絡社團信任產生的特殊方式,節約了大量成本,創造了豐富的社會資本財富。
總之,社團進入虛擬網絡,其社會資本的構建無論在網絡的形成還是互惠性、信任的產生中都有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讓虛擬網絡社團在普遍性的信息資源共享上擁有現實社團無可比擬的優勢,也必將為社會的發展注入新的力量。
注釋:
[1]邊燕杰:《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來源及作用:網絡觀點與調查發現》,《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2]胡榮:《社會資本與中國農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參與》,《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3]弗蘭西斯·福山:《信任》,湖南出版社,2001
[1](美)羅伯特·普特南著,王列、海榕譯:《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帕薩·達斯古普特、伊斯梅爾·撒拉格爾丁:《社會資本——一個多角度的觀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張其仔:《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4]顧新等:《社會資本及其在知識鏈中的作用》,《科研管理》2003年第2期
[5](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曹義烜譯:《社會資本、公民社會與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2期
[6]秦琴:《社會資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及其出路》,《長江論壇 》2006年第5期
[7](美)林南著,張磊譯,《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寇東亮:《社會資本的倫理意義》,西北大學學報,2004
[9]郭毅、朱揚帆、朱熹:《人際關系互動與社會結構網絡化——社會資本理論的建構基礎》,《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10]李維安:《網絡組織:組織發展新趨勢》,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11]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6
[12]Bourdieu&L.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